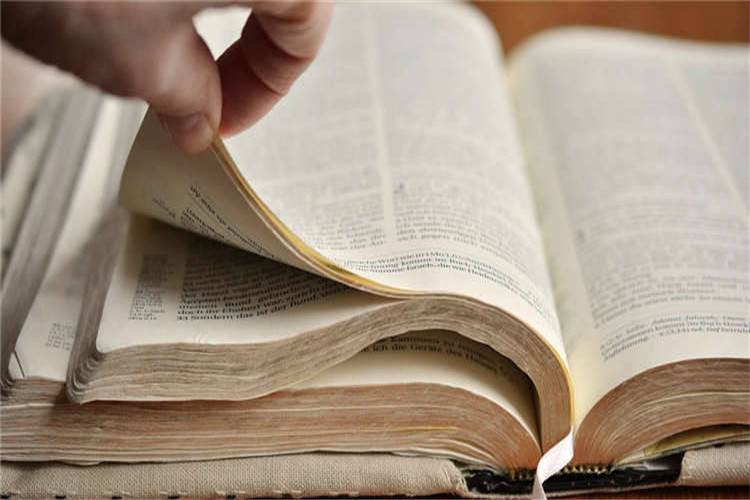“鲁迅与国学”看似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一方面,鲁迅对于“吃人的礼教”的批判深入人心,“几乎成了破坏旧文明的代表人物;另一方面,鲁迅毕竟还是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旧学功夫很好,这也是在文学史研究中经常被提及的。
那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孙郁为什么还要写《鲁迅与国学》这样一本书?孙郁教授很谦虚地说“是出于好奇心,也是为了补古代文化的课”,所以试着从另一个角度谈论鲁迅的风骨。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研究鲁迅,不能绕过鲁迅与传统文化的“纠葛”。
孙郁教授的著作《鲁迅与国学》从金石与考古学、儒家与孔子、庄子、墨学、佛家、旧戏、野史等十五个方面,对鲁迅的旧学修养、鲁迅对国故学的态度进行了讨论。在孙郁教授全面和详实的论述中,更让人感到鲁迅和国故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对国故他有自己的取舍,对同时代人对国故的态度也十分警觉。
在孙郁看来,鲁迅的“暗功夫”很深,“他对刻本源流、著录残稿、增补缺漏、史实考辨,都有心得,一些地方是可以与晚清一些大学者比肩的”。而“鲁迅的不凡,在于从旧学里走出,又没有迂腐之气”,正如墨子所说的“以往知来,以见知隐”。
探究鲁迅与国学的关系不仅对于鲁迅研究很重要,也能让读者了解100多年前新旧文化的冲击到底是怎样的。
近日,澎湃新闻就《鲁迅与国学》这部著作中的相关问题专访了孙郁教授,以下为访谈全文。
孙郁教授
澎湃新闻:您在《鲁迅与国学》一书的后记中讲到“仅仅就新文学的背景讨论新文学家,大约是有问题的”。想请您解释一下,这里的问题具体是什么表现呢?这个问题是不是在现代文学的研究中经常出现?
孙郁:新文学是从旧文学那里一点点发展过来的。最初的白话文作家,都有很好的旧学根底,他们的文章背后有着古文的影子。而文学创作中的审美意象,多少也受到了古人的影响。这里涉及一个文脉的问题,不懂得新文学背后的东西,可能对于文体的来龙去脉,就搞不清楚。比如鲁迅的文章,沿袭了周秦汉的文脉,他的辞章特点,和六朝的关系很近。胡适的述学文体,有乾嘉学派的影子,他的审美观,也是从晚清以来的诗文传统过来的。像周作人的文章,也有六朝因素,偶含明代小品之气。这也影响了废名、俞平伯等人。只有明白此点,我们才能知道,新文学是进化的产物,一方面受到域外文学冲击而成,但另一方面,是古老的文化演变的结果。对于这类作家,要考虑到传统辞章之学的背景。
澎湃新闻:您在“从新知到国故”这一章中概述了鲁迅自己对于国故的取舍:兴趣主要在经学之外,喜欢《山海经》《花镜》等奇书,钟爱美术,兴趣后来还受到民俗学影响。从这里以及您在后文的论述可以看出,鲁迅对国学的取舍有时候还是文学家或者艺术家的视角,有着审美上的追求,但对于思想性的内容更多的似乎是批判。应该怎样看待鲁迅这样的取舍,他骨子里是不是还有很多传统文人的印迹?
孙郁:鲁迅眼里的经学,是被士大夫僵化思路熏染过的遗存,很难有鲜活之气了。读经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如何读。金克木先生说:“如果一点不知道‘经’是什么,没有见过面,又怎么能够理解透鲁迅那么反对读经呢?所谓‛读经’是指‘死灌’‘禁锢’‘神化’;照那样,不论读什么书都会变成‘读经’的。”这很对。倒是《山海经》《花镜》这样的书,不易让人变得那么正襟危坐。它们的价值在于引起青年人的好奇心,对于山川、草木、河流产生兴趣。而这些远离说教的文字,会有一种想象力的培育。其实,无论是审美的培养还是认知观念的培养,都不能离开想象的因素。鲁迅并不排斥对于古书思想内容的接受,主要是在批判性思维里建立了一种新式思想。比如他在志怪小说里,就发现了唯道德主义的可笑,在神话里就感受到儒家的僵硬教条的迂腐。经学之外的文化原野,可吸收的东西很多,有的与人的初始的生命觉得十分接近,可以唤起人们对于存在的深切体认。尼采曾经说“大问题都在街巷里”,其实就是对于空洞化的学理的揶揄。所以说,鲁迅的远离经学,其实不仅没有弱化思想性,而是获得了天地之气,精神显得更为辽远了。
《鲁迅与国学》
澎湃新闻:有一点令人困惑,鲁迅对于国故之学的热爱同他批评的施蛰存、周作人身上某种得意的雅士追求的不同之处在哪里?他对传统文化也有审美的爱好,却对别人学篆字、填词嗤之以鼻,他认同和反对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孙郁:鲁迅批评过的一些人,多为学者和作家。他最警惕的是这些新式文人被士大夫趣味所俘虏,失去锐气。古书不是不可以读,但在人道精神和批判意识没有在知识界建立起来之前,他不赞成提倡旧的东西,那些标榜旧趣味和旧辞章的人,会诱导青年远离新的文化。周作人、施蛰存都是翻译家,也有学识,在古代文化方面心得很多。鲁迅觉得这样的知识人应当保持新思想的锐气,士大夫气多了,会遮蔽什么。问题不在于是否要读古书,填词写字,而在于清除旧文化的积垢,保持建设新文化的热心。鲁迅是从知识人的使命感出发来批评同代的一些学者的,这种斗士的角度和心态,才是他与众人分道扬镳的原因。
澎湃新闻:您在《鲁迅与国学》这本书中有个比较重要的总结:“说了传统许多坏话的鲁迅,其实很少有专门文章作学理的阐述。一个特别的现象是,他对于旧的遗产的批评,多是通过对于知识人的批评来进行的,要清理的是知识人身上旧的精神形影。”您还讲到:“三十年代以后,鲁迅的那些犀利的文章,很少针对国故自身,而是指向研究国故的话语方式,即我们该如何描述国故。”这一事实对于我们理解鲁迅与国故的关系是不是特别重要?鲁迅并不是单纯批评国故的某些方面,而更看重他的同辈人对待国故的态度?还是说这是不同时期的鲁迅的想法?
孙郁:鲁迅很看重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比如国民性问题,在他的小说里都有体现,那些小人物的身上有旧文化留下的痼疾。但旧的思想,有时候主要在读书人的世界里留存更多。他以为这些读书人对于历史与文化的理解,存在很多盲区。古代经典自然有其特有的价值,但如何阐释它们,是要有独特眼光的。比如,许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人,对于国故的认识,并不准确。像学衡派一些人,就把古典文献从时代语境里剥离出来,作纯然的静观,这就不能道出古代文化的隐秘。自然,从古典学的角度看,这样理解旧文化也并非不可。重要的在于,中国旧典籍需要辨析,而其中存在的瑕疵不能不关顾。倘从世界文明的角度回望东方文化,当感到优劣究竟在什么地方。中国的学界,对于文化的负面遗存清理不够,有时候甚至会误导青年。像章士钊这样的人,有域外学术的背景,又是辛亥革命的健将,但掌握权力后主张读经,号召青年埋头在古书里,鲁迅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读经不过是统治术的一种,主张读经者,自己未必都信其中的思想。从中国多次遭受异族统治的历史看,那些窃取美名和弄权的人,嘴上讲得甚好,却都把国丢了。读经并不能救国。那些所谓权威的知识人背后的东西,鲁迅是看得清清楚楚的。这是他不同时期不变的看法,也是新文化建设者一以贯之的思想。
澎湃新闻:您在书中写到:“直到三十年代,鲁迅与考古界、史学界若即若离的关系,折射出新文化建设者在古今之争中精神的复杂性。”鲁迅为什么会对金石和考古感兴趣?您在这里说的“精神的复杂性”具体应该怎样理解?
孙郁: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考古学在中国兴起,鲁迅一直是关注这个动向的。他自己也购买了一些考古学的著作和域外的考古报告。此前他自己是喜欢金石学的,对于出土的文献颇感兴趣。对于鲁迅而言,考古学属于科学的研究工作,十分重要。但他更关注的是考古思想,考古思想史的意义不亚于文学史。因为前者可以颠覆人们对于以往历史的认识。史学界在五四后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梁启超新史学的理念之后,疑古派理念影响较大,这些都是外来思想启发的结果。不过,鲁迅对于新思潮影响下的史学的成就,评价不高,特别是对于顾颉刚的著述不以为然,他以为一些结论是可笑的。这可能受到章太炎的思想的影响,也基于金石学的经验,觉得疑古派的材料有限,一些推理存在缺陷。那时候金石学与史学的研究者,在思想史层面提供的东西有限,鲁迅倒是从文献学、艺术史层面,发现了历史的诸多隐秘。比如,从汉代造像里,看到儒家文献没有的审美灵光,在六朝碑文中读出世俗社会的幽怨和文字趣味,这些都说明,历史中被遮蔽的东西实在是多的。
澎湃新闻:您在《鲁迅与国学》这本书中对比了鲁迅和孔子,找出了他们的相似之处。在其中,您认为他们最为相似的地方是什么?
孙郁:鲁迅与孔子的话题,王得后先生有专门著述,已经讲得较为清楚。毛泽东也说过,孔子与鲁迅都属于圣人。这是看到他们的重要价值的。我觉得鲁迅与孔子最大的相似是积极入世的精神,有知其不可而为的精神。也就是说,在价值失范的时代,选择了与流行文化不同的路径。只是孔子是克己复礼,而鲁迅则是在没有路的地方走路,创造新的现代性的文化。
澎湃新闻:如果说存在一个文化史上的孔子,那么有没有一个文化史上的鲁迅,偏离了真实和真正的鲁迅?
孙郁:是的,的确存在一个现代文化史上的鲁迅。我在《鲁迅遗风录》一书里专门讨论了此点,现在想来,还不够深入。我们从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新中国各个不同时期,都能够看到鲁迅被不断叙述的情况。有时与时代风云近些,有时仅仅在民间知识人的群落里。不同时期的鲁迅形象是略有不同的。抗战时期,知识界高举的是鲁迅的独立的战斗精神,为捍卫国家独立而战。解放战争时期,关于鲁迅有一个大众视角的问题。到了新中国初,则是偏重于他的革命性的一面的描述。八十年代的鲁迅研究开始转型,启蒙意义的鲁迅和现代主义视野下的鲁迅成为讨论的热点。新世纪以来,研究鲁迅的论文与著作增多,研究更为细致化。有的在文明观的视野下思考他的文本,有的则比较他与海德格尔、卡夫卡的精神关联。日本学者有段时间注重他的革命性的讨论,而韩国学界则在东亚的文化中思考各自主体的可能性。我曾在美国分别参加过哥伦比亚大学与哈佛大学召开的鲁迅研讨会,发现世界文化史中的鲁迅的研究论文也多了起来。我相信,在百年作家与思想家中,鲁迅是被叙述最多的人,他必将成为文化史中难以绕过的存在。
澎湃新闻:从您的论述中可以感觉到,鲁迅对于知识分子如何看待国故是特别敏感的,有时候像一个斗士,四处攻击各个派别的知识分子。您在“对新学人的警惕与质疑”这一章中说“鲁迅的偏激之言,现在想来也并非句句都是真理”。能否请您举例谈谈他的哪些言论在今天看来是比较偏激的呢?
孙郁:鲁迅的杂文的特点是十分犀利,有时候考虑到论述策略,就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种笔法带来了认识的深刻性,但过多使用,会放大被批评对象的缺点,以致将对象漫画化。作为艺术表达,这没有问题,但如果将鲁迅的评价当成看待对象世界的唯一标准,大概有点问题。比如,他晚年多次批评过胡适,有一些是对的,有一些则遗漏了整体性的原则,就不太准确。《出卖灵魂的秘诀》对于胡适的批评,应当说是没有问题的,但他也故意舍去胡适言论的其他语境,给人造成一种错觉,是胡适在向日本帝国主义出卖灵魂。这是不对的。对照胡适的原文,就会发现,他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只是从世界主义的层面说了几句超越民族的话,便被纠结上,这自然不能涵盖胡适的全面的观点。再比如对于梅兰芳的讥讽,也有失度的地方。男旦表演,是一种艺术,完全以为无价值,也并不正确。他对于京剧的意见不是没有道理,但过于苛刻的描述,也有失公允。不过,作为思想家与论辩家,鲁迅这样艺术化处理自己的表达,并非不可,只是我们要把审美表达与价值判断略作区分才好。
澎湃新闻:鲁迅不在学院内,影响力又特别大。那么鲁迅对于儒家的批评在今天看来有没有哪些地方是可以商榷的?
孙郁:许多研究者发现,鲁迅对于传统文化的评价,可以从他研究的著述里看到,基本都是严谨的,有科学的求是精神,比如《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都是。在这些文字里,是没有偏激的声音的,这代表了他的学术风格。今天看来大多数是站得住脚的,但是在小说和杂文中,他主要针对的是现实存在的问题,涉及传统的话题,都有所指,有时候有艺术上的夸张和变形,表现主义的意蕴也是有的。《狂人日记》暗示礼教是吃人的,是艺术的表达,这是狂人感知世界的一种心得,带着作者思想的隐喻,我们当从审美上来理解,不可当成鲁迅的学术判断。文中所指的是礼教,而非儒学。鲁迅对于儒家的思想,批评的居多,肯定的少。这与他要清除旧习、拓展新途的思路有关。他在批判传统文化的时候,对于儒家思想的抨击,的确带有摧枯拉朽之力。有时候只谈负面,而简谈优点,这是叙述策略,当然就漏掉了什么。比如,他说孔子为权势设想的东西多,那是对的,但“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一句话,有点绝对主义。再比如,他以为一些儒者一心要做官,也并非不对,但儒家其实有思想的弹性。马一浮就说,儒家重要的是爱人之心,“君子未尝不欲行其道,然有可有不可。或出或处,或默或语,无二致也”。马一浮就发现,陈独秀虽然偏激,但还是保留了儒家的精神,“以前种种新奇言论全是知见,本心固未尝熄灭也”。用这一句话来形容鲁迅的言与行的复杂性,也是适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