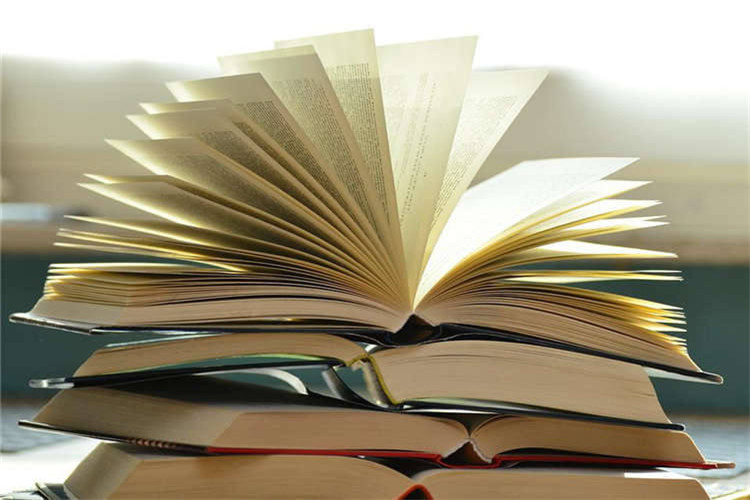编者按:202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安妮·埃尔诺作品集第三辑出版,分别为《事件》《迷失》《空衣橱》《外部日记》《真正的归宿》《被冻住的女人》六部重要作品,均为国内首次引进出版。至此,安妮·埃尔诺的作品基本全部得到了中译出版。本文为作家萧耳对安妮·埃尔诺其人其作的综合细读评论。
1
“是的,人们会遗忘我们。”这是生活,毫无办法。
安妮·埃尔诺在《悠悠岁月》中的第一句话就是:所有的印象都会消失。
正因为所有的印象都会消失,她需要以日记,相片和超八摄影机来纪录关于活着的一切。她的时代,她的国度,她的家庭,她的个人生活。
2022年,瑞典学院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
安妮·埃尔诺可以说是我从过去一年阅读中发现的宝藏作家,关于她作品的阅读也从2024跨年到了2025年。可以说读文学作品至今,好像还没见过有谁比安妮·埃尔诺自我审视得更彻底的作家。在女作家中没有,在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中没有,在仍然活着的当代作家中不曾见过这么勇的人。
勇字当头,安妮·埃尔诺将自己作为一个人类学样本,方方面面地剖析开来,献祭给了文学。这是一件极严肃的事情。真的,严肃到了令我敬畏的程度。严肃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在她之前,同样得过诺奖的女作家耶利内克,总觉得还差了点东西。
她的献祭式写作,要突破的极限实在太多。对自己出身的阶层下手,对自己父母下手。对青春期女学生的自己下手。对通过婚姻实现了阶层跃迁的上位者安妮下手。对中产阶级家庭内部下手。对中产阶级内部的男性下手。对男女关系中的自己和他者下手。对女性层面的堕胎者安妮下手。对迷失在情欲和作家权力之间的中年女性安妮下手。对深度沉迷性爱的中年女人的自己下手。对拥有权力的成功大女和相对弱者地位的年轻男人的关系下手。对沉沦式的激情、羞耻、占有欲、嫉妒等当代人共同的精神困境、人性之恶、无力感下手……
刀刀精准,刀刀见血,手术刀式的深入人的肌体直至骨髓。更难得的,她用以放大、端详的样本是她自己,然后辐射到她自己的最小圈层。她不是那种把自己深深藏起,只去窥视别人的人。读完一本又一本她的书后,击节拍案,她,大写的她,无疑是不可多得的当之无愧的这个时代的大作家。
《迷失》(袁筱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
在日记体的《迷失》中她这样写道——
“在他面前,我既扮演一个荡妇的角色,同时也扮演一个母亲的角色。”
“在我的脚下仿佛纩开了一个巨大的未知的深渊:在他的存在之中,我出演的是怎样一个角色啊!……或许我写给他的信被留了下来,作为值得留存的资料,至少可以作为西方糜烂生活的物证……”
“我的疲倦就是他曾经在的印证。”
“我也知道我为什么会如此依恋S,他是那种其实并不能真正控制我的男人,既遥远,又温柔的父亲(就像我的父亲一般)和可爱的金发王子。在扎戈尔斯克,我本应该三思而后行。但这是个无与伦比的俄罗斯男人,与一个女农民十分相配,其实在我的心底,我就是个农民。”
“他下午四点二十分来的,八点不到离开。时间过得很慢,他说话不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在精神上已经离开了,仅此而已。我趴在他肩膀上,在他怀里哭泣。”
“十九点。为什么我就是不能相信他会这样不辞而别……他到塞尔吉来过三十四次,去过小公寓五次。”
“理发店。音乐。我不想过多地看自己,素颜,打湿的头发:年龄。报纸上的女人令人兴奋,穿着清凉。整个这段时间,走路的时候,开车的时候,都觉得自己还在经历,还在续写这个美丽的故事。我望着城市新建的街区、公路,仿佛此前我一直都在这样的地方,我过去的生活已经不存在了。”
“很像我1964年堕胎后的日子。现在,我想睡觉。”
……
还有日记中的一天又一天,一年多甚至更长的时光里,她在焦灼中等待与一个男人的幽会,如此焦虑、无力、悲伤、激情、不堪、破碎,身体也随之做出各种应激反应,她成为女性欲望的奴隶,身体受荷尔蒙膀胱炎折磨,甚至害怕自己因为性生活感染上艾滋。“今天夜里,我泪水滂沱,想要死,恐惧地发现我的臀部不再紧致,我知道我不可逆转地老去,从而会不可逆转地坠入孤独。”“十一点,一言难尽。嫉妒,被排除在外,几秒钟的时间里似乎已经到了故事的终结”“男人、写作、恶性循环”。因为过度的失控的激情而产生的类似死亡的体验,以及无数个梦境中失序的幽暗中的自我……这些都是疼痛的安妮,安妮的疼痛。
年轻时的安妮·埃尔诺
读完安妮,才知本没有什么体面的文学。《红楼梦》里只有两只石头狮子干净,一个活生生的安妮也是不体面的。她不是什么公共印象中的光鲜名流,而是一个最真实的女性,她有自己的“私人问题”。看起来体面的东西,如王尔德笔下少奶奶的扇子,往往会流于肤浅,或避重就轻,粉饰太平。一揭伤疤,伤疤或许还正在流脓,或许已经结痂,总之都非体面之物,众目睽睽之下难免有“做人多少尴尬”之叹。可如果一个作家只想要体面,也不太可能成为优秀的作家。
几乎她的每一个小说,都能看到身份政治的影响。如果要做一个安妮·埃尔诺的沉浸式读者,我的建议是先读她的个人自传式三部曲:《一个女人的故事》、《一个男人的位置》《一个女孩的记忆》,然后是《空衣橱》《简单的激情》《我走不出我的黑夜》、《占据》、《羞耻》、《年轻男人》《相片之用》等等,每一本书都是她人生的一个侧面,一个阶段的呈现。最后才是无人称写作的《悠悠岁月》,《悠悠岁月》,是一个所有她的小说的剪辑版本,浓缩版本。每一个其他的小说,都能在其中找到它的存在。它们与《悠悠岁月》是如影随形的关系。
身份即政治。她笔下是阶层之间的巨大差异。
安妮·埃尔诺出身底层阶层,通过上大学、婚姻实现阶层跨越,从工人阶级到资产阶级,她一直在阵痛中。她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游走在两个阶层之间,她在不同的文化取向和趣味之间上上下下。她自卑又自尊。在她成长的过程中,痛苦矛盾一直在左右着她。
《一个女孩的记忆》(陈淑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
她自我定位于一个“阶级叛逃者”。在她的《一个女孩的记忆》中,我们看到她在18岁时的亲身遭遇。她回忆了1958年夏天在诺曼底担任夏令营辅导员的经历,并讲述了她与一个男人度过的初夜。六十年后,她将那个夏天不可磨灭的记忆带入现实,她发现,她写作生涯的重要和痛苦的起源是建立在耻辱、暴力和背叛的少女时代的记忆的基础之上。
她在书中描写这段少女时期的创伤经历。伤痛是身体上的,又绝非仅仅是身体上的——畏惧、软弱(甚至因软弱而长期逃避)、被身边人离弃背叛的孤独、无法澄清事实的绝望,诸如此类的。
在《迷失》中,1989年7月20日的日记她写道——
《一个男人的位置》已经离我很远。唯一令我激动的时刻,是想起来到这里的人,坐在板凳上,听我父亲的故事,父亲曾经历的一切的总结与意义,不明就里——我想他们应该也能够感受到痛苦【因为父亲一直很消沉,我也一样,祖母那边整个家族,勒布尔家族都是这样。】是的,我完成了什么东西的报复,我报复了我的出身……
说说他的父亲。”是利勒博讷小镇一家咖啡馆杂货店的店主,在成为小工商业主之前,他出身农民、当过工人,完成了一段“阶层的递进”,他向往进入上一个阶层,对自己的北部乡下口音感到自卑,他苛求自己和家人都说标准法语,在家庭餐桌上练习巴黎人的礼仪,要求女儿“有教养”并考学,他对女儿的婚姻感到满意,因为女婿的城里人出身对这个家庭来说是“升迁”。父亲同时又是对母亲的家暴者,有一次差点掐死了母亲。
她随着成为一名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的一员,与父亲越来越疏远。
从社会生活,缩小到家庭生活。她母亲所代表的社会阶层正是她拼命想要叛逃的阶层。她的母亲和她的丈夫,代表了其社会旅程的两个端点:起点和终点。
安妮的父亲去世后,母亲便离开伊沃托,来到安纳西和他们一起生活。《一个男人的位置》、《一个女人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原生家庭中的少女。她的起点,一个杂货铺里写作业,总在被人观看的小女孩。
《一个女人的故事》中,当母亲死于阿尔茨海默症后,她开始了令人生畏的时光倒流之旅,她试图捕捉真正的女人,那个独立于女儿而存在的女人,那个出生在诺曼底小镇、死在巴黎郊区医院的老年病房里的女人。她探讨了母亲和女儿之间既脆弱又不可动摇的纽带。和《迷失》一样的风格,她的笔调疏离冷峻,仿佛是在说别人。
《一个女人的故事》(全新修订版)(郭玉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
《一个男人的位置》(全新修订版)(郭玉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
2
也许当一部分读者认为安妮·埃尔诺是又一个只沉溺于自我书写,自我小世界的女性作家,又拿什么格局小之类的话术来贬低或轻慢她时,安妮还有《悠悠岁月》。在《悠悠岁月》里,所有从二战前她出生后的世界变化,她都在场。她以自己的打开一张张相片的方式,接住了宏大叙事里的历史时间,也接住了私人生活里的静水深流。
作为一个法国人,她似乎很关注社会事件和历史事件。比如斯大林去世时间、911那一天。二十世纪中叶和下半叶法国和全世界重要的社会历史事件,如二战、匈牙利事件、阿尔及利亚战争、1968年的五月风暴、苏联解体、“9·11”、法国总统选举、越南战争。她也关注死刑废除、移民合法化、同性恋被允许、假期延长、失业人数等等社会性事件。
《悠悠岁月》(吴岳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
她是文艺先锋。从萨特到加缪到尤瑟纳尔,从罗兰·巴特到米歇尔·福柯再到阿尔都塞,从布托尔到萨特再到勒·克莱齐奥,她在《悠悠岁月》中都一一掠过他们。
她生活时代的文艺现场。从文化明星到娱乐明星电影明星。披头士指环王性手枪平克-弗洛伊德等等。
她的笔触又是特别的。比如她在书中提到了“萨特之死”,她写了一句:“葬礼时波伏瓦的头巾滑落下来了”。
这是一部时间河流里的漂流之书。时间跨越了无人称的主人公1941年之后60多年的生命历程。
小说也可以说是独特的长篇照说。主体结构就是架设在一幅幅家庭或个人照片之上。她结合照片当时的空间和时间,对自己及周边的生活加以言说。
比如1949年在索特维尔海滨的照片拍的是她和父亲的一次度假;
1963年在大学城的照片呈现出她的少女生活;
1980年在西班牙的照片描述了她成为两个孩子母亲之后的旅途,四十岁的女人的疲惫状态:“不在乎是否取悦于人”了;
1992年,自由自在的恢复单身女性后的“完美印象”。
50岁出头的女性新生活。女性打量自己的不再年轻的身体。
1999年在特鲁维尔的照片旁及她作为中年母亲的角色。
以此为支点推及开去,埃尔诺在小说中几乎勾连出了对她人生影响至深的所有往事,从少年求学到结婚生子,从初为人母到年华老去,俨然是一部作者自传。虽然埃尔诺作传的方式也是回忆,但是她的回忆是片段或断点式的,是“现代”的回忆而非古典的回忆。故事和情节是隐在碎片印象背后的。需要细细地去揪出来。
3
要直接了解安妮·埃尔诺,还有一部纪录影像《超8岁月》。影片长仅一小时,2022年12月14日正式发行。由埃尔诺和她的儿子达维德·埃尔诺-布里奥联合制作,利用前夫1972年到1981年间拍摄的八毫米胶片,讲述那十年的家庭生活,兼及社会变迁和冷战记忆。
《悠悠岁月》是用照片串起她经历的过往人生,时间线是打乱的,回忆是凌乱的。而《迷失》是日记体,每一天都是清晰可见的。她的所谓叛逃式生活,我们在日记、相片与小说之外,又从一部用超八摄像机的纪录电影中,看到了一种互文。《超8岁月》在突破了文字的静默后,又有新的质感。
《超8岁月》海报
在《悠悠岁月》中,她提到买了“一台超八毫米贝尔摄像机”,这是当时她这样的优越的中产阶级家庭才能拥有的时髦货。但她极少提到拍摄的内容,这些都在她儿子参与的《超8岁月》中给出了答案:孩子、父母、家庭生活……纪录始于1972年冬末,当时的埃尔诺夫妇刚过而立之年,丈夫菲利普是市政府的副秘书长,安妮在高中当语文老师。但后来她和丈夫离婚了。二人离婚之后,前夫带走了摄像机,却留下了拍摄过的所有胶片及其承载的记忆。可以说《超8岁月》的执镜者居多是她的前夫菲利普·埃尔诺。当年的她还是一位年轻的女性,在破茧而出的过程之中。她说过由于传统的性别分工,操作摄影机的工作总是由丈夫来做。电影中的画面:安妮·埃尔诺在阿讷西的家中批改作业。在拉克吕萨。在阿尔巴尼亚的旅行。安妮·埃尔诺和长子埃里克在英国伦敦。她成为被观看者,前夫才是那个观察者。但最终,是她和儿子一起完成了这个电影,她本人提供了贯穿始终的旁白。
《超8岁月》中的安妮·埃尔诺
由大世界,往小世界里聚焦,家庭作为社会的单元,她自己家的超八家庭摄像机,她的相片和日记,都是时间与记忆的道具,超八摄像机纪录的是“优雅的”法国资产阶级家庭生活。在摄像机里,她,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滑雪、满世界旅行,在文学之外,摄像机呈现了一个时间段里的真实影像——小家庭内部的细微,以及她作为职业女性的生活。有意思的是,在丈夫的镜头中,我们从未看到安妮·埃尔诺在书桌前写作。
4
她的《悠悠岁月》,可以和另一个法国作家、诺将得主勒·克莱齐奥的《战争》对照着看。同样是女性的翻译家袁筱一也是《战争》的译者之一,另一本法国人写的,不像小说的小说。
在她之前,有一个极有名的上一代法国女作家杜拉斯,但安妮埃尔诺的气息跟杜拉斯完全不同,她的文字剔除了顾影自怜。她根本不自恋,也不心疼自己。她跳出了自我,站在芸芸众生的角度,将自己抽象化,自己将自己打入到一个“他者”的位置,所以她才能做到对自己毫不留情。
在用文学探索世界,探索心灵的路上,安妮·埃尔诺不设禁区。连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性与情欲,自己的父亲某一天差点杀了自己的母亲,自己进入高阶级后对父亲的疏离,在两性关系中当女性处于弱者位置时的种种不堪,通通不是禁区。
安妮·埃尔诺
可能有一种人,生来就是观察家。她来到世界的任务是以自己为样本,以文学的形式来感知她生活的80多年(至今她活了80多岁)的全部体验,极负责任地呈现给世界。她是一个人性的,时代的通灵者。
之前我读完了《悠悠岁月》等一系列书,最近一本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翻译家袁筱一翻译的《迷失》,庆幸这个译本的质量非常好,文字简炼干净,我由此推测安妮本来的法语写作就是这样的气质。简洁冷静,当某一个字即将沉迷于一种情绪之时,她随即一个激灵,冷静客观抽象回到了她的身上,她的文字并没有坠入“私人小说”式的深渊。你在读她的日记,你以为自己是在读一个社会调查文本,一个人类学文本,这就是安妮式的清醒。
1989年安妮·埃尔诺写于8月29日的一段日记——
他十月份走。他希望能够在两三年后与我再度重逢。甚至“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后,我第一个打电话的对象,是你”。
这段话令人想起杜拉斯的情人,一样的法国女子,异国恋人。不同的是《情人》中的异国恋人都未婚,男大女小。《简单的激情》《迷失》中的俄罗斯恋人是有妇之夫,外交官,另一方是知名法国女作家,女人比男人大十多岁。但只要深究下去,安妮决不会将一段异国激情推到时间上成为永恒记忆的高度。杜拉斯的《情人》似乎有滤镜,最终要回到爱情,而《简单的激情》《迷失》毫无滤镜,探讨的并不是爱情,而是人类情感、情欲的多样性和深不可测。甚至在一些男欢女爱的细节描写之后,她同样在审视:他总是拿走她刚打开的拆了一包的整条万宝路香烟。她是介意的,这暴露了法国女人与俄罗斯外交官在经济地位上的不平等,她是施的一方。她一面沉迷于情欲,一面却有如此高冷到令人不适的批判(说实话我读到这里是难受的,奇怪她为什么还会介意一条香烟)。
《简单的激情》(袁筱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
在《情人》中,因为中国少爷是施于金钱的一方,法国穷女孩甚至被自己的兄弟侮辱为“妓女”,金钱就是这么势利眼。而在《迷失》中,盛年女作家安妮提到了“嫖客”一字,这是日记中极其隐秘的思想运动,可能连她自己也不确定,只是一闪现而已,相当于一个杂念。但她真的不放过,那如鱼刺的一闪现也要如实呈现出来。
在我们自己的某个年龄段,可能需要杜拉斯式的呓语,像《印度之歌》《副领事》那样的呓语。如果杜拉斯的爱都属于自己,安妮·埃尔诺的爱属于全人类。
安妮·埃尔诺出生于1940年,艾丽丝门罗出生于1931年。杜拉斯出生于1914年,她们都经历了二战。从女性勇者来说,她比她大9岁的艾丽丝·门罗前进了两步。第一步,是她和盘托出从一个父母是农民的杂货铺女孩走向大都市,走向文坛的一生,她有大无畏的不怕网暴的勇敢。她呈现的好几部作品中的自己离完美相去甚远,如果神经不够强大,足以被网络口水和大众的视奸整疯掉,但是她一方面可能成为大众眼中的“暴露狂”而被人说三道四的危险,另一方面,她,就像一座雕像那样地立于广场上。人们可以打量雕像,但不可以亵渎雕像。她有那种让人不能亵渎的力量静静地在那里,以抗衡这个口水漫天飞的网络社会。一步是观念上的女性的进步,她,不再囿于“第二性”的身份,她既尝遍女性成长路上的种种伤痛,又终于挣脱出了女性身体的客体困境。
5
最后,她在写女性。
她写女性,把自己当作观察和研究的对象。一个女孩,从法国北部乡下的贫乏出身,萦绕其一生的少女时期的不幸经历,依照父亲意愿考学、上嫁,离婚,当中学教师,当作家。与患上阿尔茨海默症的母亲漫长的告别,一直写到自己的衰老,暮年回望那半生不愿去触碰的伤痛……
我们看到,当她陪同丈夫出席活动时,她心里想的都是家中藏在抽屉里的创作手稿。
我们看到,她最早夫妻关系破裂,一个原因是她的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丈夫,因为她瞒着他“秘密写作”而感到愤怒。
《正发生》海报
我们读到她作为一个女性的身体记忆。她的堕胎记忆,就如电影《正发生》中的那个孤独冒险去“解决身体负累”的女大学生。
我们通过《简单激情》和《迷失》,跟她一起直面女性的爱欲本身——“一个来巴黎短期任职的已婚东欧商人重要吗?无关紧要”!在这段亲密关系中,女性是自己爱欲的主人。但另一面,她将女性生命经验中的软弱、敏感、孤独、屈辱、爱与嫉妒以及那些过不去的伤痛和难以释怀的情感直接呈现给了我们。
我们还在她的不同作品中,看到了西蒙-波伏瓦对她的成长的影响。
《正发生》剧照
50岁后,她再次认真打量自己的女性身体。波伏娃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在同样的年纪,也曾这样做过。
她是一个普通女性,一生在阶级、社会、性别和婚姻中挣扎。“我处在这样的一个空洞中,在这里,死亡、写作与性纠缠在一起,我看到它们之间的关系,但是无法战胜”。但是,不能忽略的一点是,她就是一名作家。她是可以依靠词语来填满生活的空洞的作家。无论遭遇激情还是爱情,写作的需要一直存在。
《迷失》中的日记止于1989年4月9日,一个星期一,她这样结束——
自11月6日(我最后一次见S.)以来,这是第一次,我醒来时体会到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幸福……
对我来说,想要写点危险的东西,就像是地窖的门开了,必须走进去,不惜一切代价。
晚年安妮·埃尔诺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