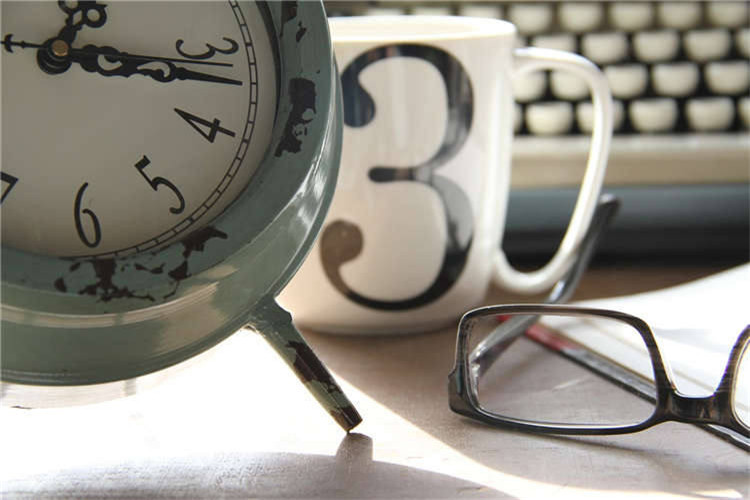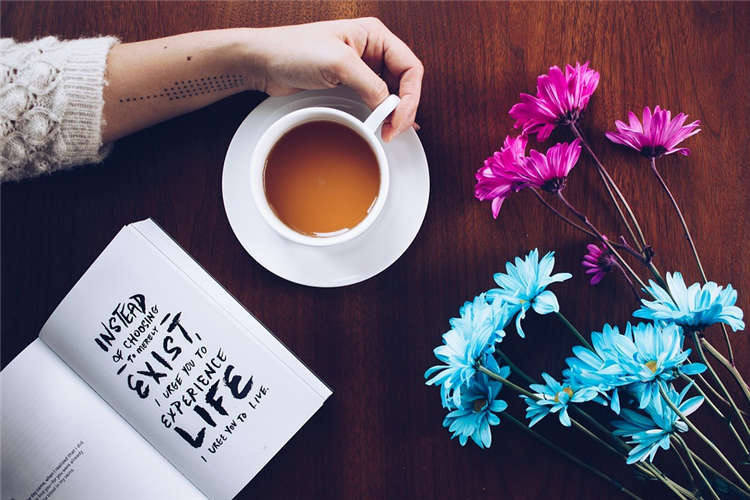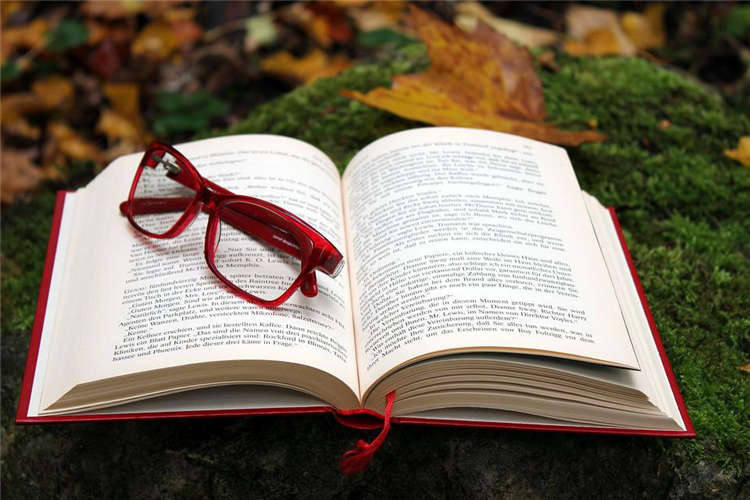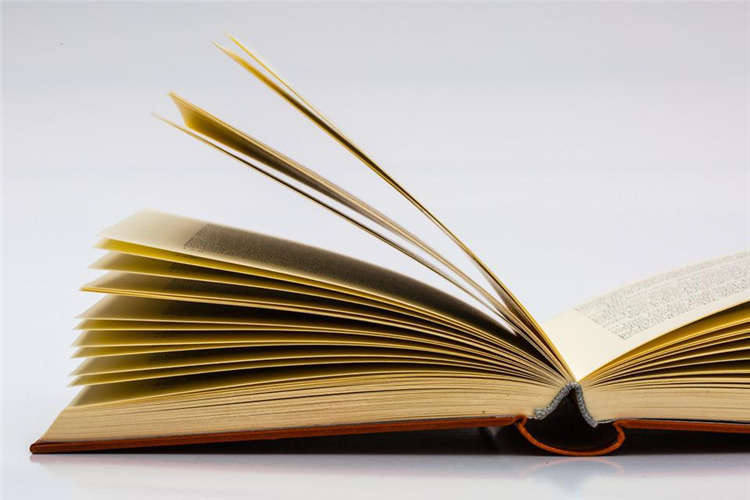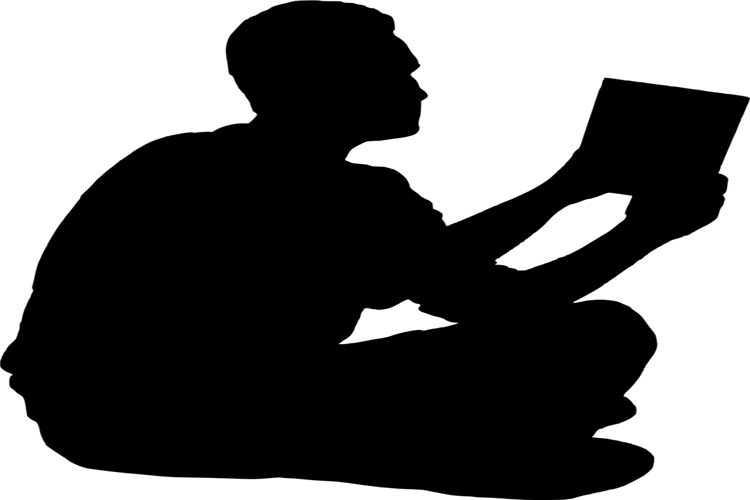《三国志·方技传》除了华佗及其弟子的活动之外,还有善于音律的杜夔,善于相人术的朱建平、善于占梦的周宣以及善于卜卦和筮占的管辂。由此也可见,在陈寿看来,所谓“方技”主要包括的就是医术、音律、相人术、占梦以及卜卦等等。《后汉书》的《方术列传》被认为是更为完善的方术列传,而且对后世方术传的编纂有更大的影响。《后汉书·方术列传》前有一段序言,范晔详述了撰述《方术列传》的原因,他说占卜之事最早是用来“定祸福,决嫌疑,幽赞于神明,遂知来物者也”,这和《史记·龟策列传》所载司马迁的序言在思想上基本是一致的,即肯定卜筮行为在帮助人们解决疑难问题时的合理层面。范晔还提到所谓河洛之书、龟龙之图等,以及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之术,也肯定这些方术具有“探抽冥赜、参验人区”“时亦有以效于事也”的实用价值。但范晔同时指出,“圣人”对鬼神方术的基本态度是尽可能利用其合理层面,而对于可能的危害要有充分的防备。
然而范晔《方术列传》多载神异以及志怪等内容,对于这一点前人已有不少批评意见,例如刘知幾《史通·书事》说:
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至于《方术》篇及诸蛮夷传,乃录王乔、左慈、禀君、槃瓠。言唯迂诞,事多诡越,可谓美玉之瑕,白圭之玷,惜哉!无是可也。又自魏晋已降,著述多门。《语林》《笑林》《世说》《俗说》,皆喜载啁谑小辨,嗤鄙异闻,虽为有识所讥,颇为无知所悦。
刘知幾认为《后汉书》的《方术列传》所载内容“迂诞”“诡越”,是《后汉书》中的白璧之瑕,如果没有这些内容也是可以的,这样的看法是值得重视的。而刘知幾还提到范晔之所以会如此写作《方术列传》,和当时“无知所悦”志怪类著作的社会风气有关,这样的判断也是后来学者们所认可的。与刘知幾的意见相似,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也说:“汉人称太守为‘府君’。然叙事之文,当从其实,此传多采鄙俗小说,未及厘正。若东海君、葛陂君之称,岂可秽正史乎?”这其实是非常严厉的批评了。
也有学者肯定《方术列传》的成就。根据日本学者坂出祥伸的说法,《后汉书》的《方术列传》“内容和记述方法成为后世编纂正史方术传的一种固定形式”,而且医者、天文学家、相术者、占术者逐渐成为术数者队伍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从历史编纂者的角度来看,人们倾向于把方术和方术者纳入国家正规的统治秩序中去。这样的观点无疑是准确的,在《后汉书·方术列传》着重记载的方术者中,有一多半是政府官员,可以认为这是一部记述能够使用方术的政府官员的传记。白寿彝等人注意到,司马迁和班固对于方术的基本态度是以批判和揭露为主,并提醒君主和世人不要上当受骗,然而“《后汉书》记方术之士,品种复杂,有真有假,似乎客观记述,不像有意揭露,容易使读者不辨真假,信以为真。范晔所论‘幽贶罕征,明数难校。不探深远,曷感灵效?如或迁讹,实乖玄奥’。他对方士之术,是信还是不信,令人捉摸不透”。这是客观中允的论断,而且意思有所保留。其实范晔和当时多数世人一样,相信方术能够验证。
可以认为,在魏晋南北朝整体社会风气的影响下,范晔对于方术能够真实有效验证应该是真心相信的;而正如白寿彝等所言,这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读者对于方术现象的认识。
相人术
《三国志·方技传》记载朱建平曾经为曹魏君臣占测年寿,而这些占测后来基本都应验了:
朱建平,沛国人也。善相术,于闾巷之间,效验非一。太祖为魏公,闻之,召为郎。文帝为五官将,坐上会客三十余人,文帝问己年寿,又令遍相众宾。建平曰:“将军当寿八十,至四十时当有小厄,愿谨护之。”谓夏侯威曰:“君四十九位为州牧,而当有厄,厄若得过,可年至七十,致位公辅。”谓应璩曰:“君六十二位为常伯,而当有厄,先此一年,当独见一白狗,而旁人不见也。”谓曹彪曰:“君据藩国,至五十七当厄于兵,宜善防之。”
朱建平因为善于“相术”而且“效验非一”受到曹操的重视,而《方技传》随后用较大的篇幅记载朱建平相人术的应验方式。例如朱建平预测魏文帝能活到八十岁,但曹丕四十岁的时候病重,对左右说:“建平所言八十,谓昼夜也,吾其决矣。”随后魏文帝去世,朱建平的相人术得到验证。而夏侯威到四十九岁的时候生了一场病,本来以为自己就要死了,但不久之后疾病痊愈,夏侯威以为自己度过了劫难,就对旁人说:“吾所苦渐平,明日鸡鸣,年便五十,建平之戒,真必过矣。”然而就在当天晚上夏侯威疾病复发而卒。朱建平的预言就这么神奇地应验了。
但是陈寿也提到朱建平的预测并不是每次都完全准确。例如朱建平预测应璩六十二岁去世,结果“璩六十一为侍中,直省内,欻见白狗,问之众人,悉无见者。于是数聚会,并急游观田里,饮宴自娱,过期一年,六十三卒”。应璩去世的时间与朱建平的预测并不完全相符,但是相差也并不太大。另外陈寿还说:“惟相司空王昶、征北将军程喜、中领军王肃有蹉跌云。肃年六十二,疾笃,众医并以为不愈。肃夫人问以遗言,肃云:‘建平相我逾七十,位至三公,今皆未也,将何虑乎!’而肃竟卒。”汝企和由此认为陈寿是秉笔直书,并没有溢美之词。然而联系陈寿前后文的意见,可以发现陈寿总体上还是认可朱建平拥有能够预测生死的能力。
《史记》多次提到相人术,两相对比可以发现司马迁和陈寿在认识相人术方面的差异。《史记》中载有擅长相人术的许负,说他曾经为薄姬以及周亚夫相面,《史记·外戚世家》云:
及诸侯畔秦,魏豹立为魏王,而魏媪内其女于魏宫。媪之许负所相,相薄姬,云当生天子。是时项羽方与汉王相距荥阳,天下未有所定。豹初与汉击楚,及闻许负言,心独喜,因背汉而畔,中立,更与楚连和。
许负的相人术影响了魏豹的政治判断,让他做出背叛刘邦而与项羽联合的决定,并最终影响了魏王豹家族和魏国的命运,甚至影响了楚汉战争的走向。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写许负预言的应验方式是薄姬为汉高祖刘邦所幸,生男为后来的汉文帝。有学者注意到许负相人术与汉文帝合法性建构之间的关系,认为:“薄姬‘当生天子’相辞如同谶言一般神化了文帝形象,文帝借相人术,巧妙地将其权力来源从功臣转向天意,相人术为文帝即位提供了方术意义上的合理性论证,也化解了其统治过程中的正统性危机。”也就是说,司马迁关于文帝相人术的书写有着较为明显的政治目的,这与陈寿关于朱建平相术的记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另外《史记》还提到许负相周亚夫:
条侯亚夫自未侯为河内守时,许负相之,曰:“君后三岁而侯。侯八岁为将相,持国秉,贵重矣,于人臣无两。其后九岁而君饿死。”亚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当代,亚夫何说侯乎?然既已贵如负言,又何说饿死?指示我。”许负指其口曰:“有从理入口,此饿死法也。”居三岁,其兄绛侯胜之有罪,孝文帝择绛侯子贤者,皆推亚夫,乃封亚夫为条侯,续绛侯后。
司马迁还记载了周亚夫“饿死”:“初,吏捕条侯,条侯欲自杀,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呕血而死。国除。”许负的相术最终应验。
可以发现,司马迁写相术的时候刻意突出命运的不确定,例如《佞幸传》载文帝时邓通故事:“邓通无他能,不能有所荐士,独自谨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当贫饿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谓贫乎?’于是赐邓通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邓氏钱’布天下。”然而尽管“其富如此”,但汉文帝去世之后邓通“竟不得名一钱,寄死人家”。邓通的命运并不因为汉文帝“能富通者”的能力而改变,这是司马迁对于命运无常的思考,也是司马迁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史记·黥布列传》说黥布在秦时为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当刑而王。’及壮,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当刑而王,几是乎?’”后来黥布果然得以封王。另外著名的例子是卫青故事,《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青尝从入至甘泉居室,有一钳徒相青曰:‘贵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骂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然而后来卫青竟得以封侯,“钳徒”的相人术最后得以验证。
需要注意的是,司马迁对于外在相貌与内在品德之间的差异是有思考的,对于相人术真实性的基本态度是“疑则存疑”。例如司马迁引述孔子的意见反对“以貌取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名施乎诸侯。孔子闻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索隐》云:“《家语》‘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胜其貌’。而上文云‘灭明状貌甚恶’,则以子羽形陋也。今此孔子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与《家语》正相反。”子羽也就是澹台灭明,孔子因为他相貌丑陋而认为他“材薄”,“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可以说是孔子对于“以貌取人”的反思。另外,在《留侯世家》中司马迁再次提到了“以貌取人”的问题:“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此外,《游侠列传》“太史公曰”:“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谚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于戏,惜哉!”其中“人貌荣名,岂有既乎”的谚语,原意指的是人的外在美好的容貌和名声不能够同时兼有,司马迁在这里表达的意思和“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相同,都是不能简单根据容貌对人进行判断。
也就是说,在司马迁看来,人的外表与内在品德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简单依靠容貌和外形对人进行判断往往会出现误判。如此而言,外貌与人的命运之间也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根据人的外貌对未来进行预测也是不可靠的,相人术的理论基础既然已经不存在,那么相人术也就不是能够持续有效验证的方术。然而分析陈寿对于朱建平相术的书写,可以发现陈寿确实相信寿命是可以预测的,司马迁和陈寿对于相术是否能够持续有效验证的认知差异应当引起特别的重视。
劾鬼术
范晔《后汉书·方术列传》提到了当时有人擅长“劾鬼”的巫术,“劾鬼”类巫术在秦汉简牍《日书》文献中就已有记载;而在有关黄帝和大禹的神话传说中,就提到他们能够召唤、役使甚至是处罚鬼神。《汉书·艺文志》中有“《执不祥劾鬼物》八卷”,杨树达《汉书窥管》引姚振宗的看法,认为《后汉书》中所载的费长房、寿光侯等“皆劾鬼物之术也”。秦汉社会对于鬼的恐惧和信仰是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司马迁并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一问题,前文讨论《史记》中的“鬼”,提到司马迁对于“鬼”的基本态度是“存而不论”。然而从《方术列传》的书写来看,范晔对于这种类型的巫术似乎深信不疑,对于民间流传的鬼怪故事并未认真甄别筛选,《后汉书》中所载的几则故事都在说明劾鬼巫术能够有效验。
《方术列传》载费长房故事中,厌劾鬼神是重要内容。范晔说费长房具有“医疗众病,鞭笞百鬼,及驱使社公”的神秘能力,而费长房之所以具有这样的能力,是因为其师“为作一符”,有这样的符就可以驱使鬼神。此符极为关键,范晔说后来费长房丢失了此符,“为众鬼所杀”。这里的“符”显然和后来的道教有关,许地山指出:“文字能够治邪,圣言可以辟鬼底观念很古,《淮南子》记仓颉作书而鬼夜哭,便是根据这观念底传说。”连劭名也认为:“符是古代方术中使用的一种重要法物,据云可以代表天神的庇护,驱劾鬼魅,消灾除病,具有无上的威力。”徐西华认为,在原始道教产生以前方术士们就已经发明了“符”,后来太平道和五斗米道沿用了这一发明。
另外,《方术列传》还载有“东海君”与“葛陂君”的故事:
后东海君来见葛陂君,因淫其夫人,于是长房劾系之三年,而东海大旱。长房至海上,见其人请雨,乃谓之曰:“东海君有罪,吾前系于葛陂,今方出之使作雨也。”于是雨立注。
这是典型的“降妖除怪”故事。汉魏六朝时期道教体系逐渐完备以后,“降妖除怪”就成为道士们最主要的任务,道教典籍中有大量类似故事,而范晔显然也受此影响。“东海君”与“葛陂君”显然都是地方区域神灵,而费长房能够拘押东海君,导致东海大旱,神明的人格化与世俗化的趋势应当引起特别注意。另外,《后汉书·方术列传》还提到“河南有麹圣卿,善为丹书符劾,厌杀鬼神而使命之”,这同样是“降妖除怪”类型的故事。
《方术列传》载刘根故事也较为神异,其中提到:
刘根者,颍川人也。隐居嵩山中。诸好事者自远而至,就根学道,太守史祈以根为妖妄,乃收执诣郡,数之曰:“汝有何术,而诬惑百姓?若果有神,可显一验事。不尔,立死矣。”根曰:“实无它异,颇能令人见鬼耳。”祈曰:“促召之,使太守目睹,尔乃为明。”根于是左顾而啸,有顷,祈之亡父祖近亲数十人,皆反缚在前,向根叩头曰:“小儿无状,分当万坐。”顾而叱祈曰:“汝为子孙,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辱亡灵!可叩头为吾陈谢。”祈惊惧悲哀,顿首流血,请自甘罪坐。根嘿而不应,忽然俱去,不知在所。
由范晔的叙述来看,刘根“能令人见鬼”的巫术确实能够有效验,范晔同情并且相信见鬼巫术的态度是比较明显的,而这也很可能是当时民众对于类似巫术的基本态度。正如蒲慕州所言:“鉴于《后汉书》的作者范晔(398-445)生于南朝,而当时鬼故事开始被大量记载,故将此类故事列入史书可以看作是对他那个时代总体氛围的一种反映。”也有论者指出,范晔书写《方术列传》充满明显的夸诞色彩,与作者有意显露其文学才华有关,也与作者所生活的时代风气有关。
召唤和役使鬼神显然与道教法术有密切关系,多有学者由此展开讨论,章太炎指出,刘根之术出自墨子,“见鬼”其实就是《墨子》中的“明鬼”。李远国也认为费长房等人的法术近乎于墨家所提倡的鬼法。卿希泰注意到:“这些方士都不再用祭祀去讨好鬼神,而是以丹书符箓、禁咒方术发现、鞭笞、驱使、招引、镇劾乃至厌杀之。这些方术,在张陵那里大多能找到。”刘仲宇也认为:“到了汉代,有某种神通便可召劾鬼神的观念极有市场,而且是早期道教形成的基础之一。”杨英认为费长房等人所擅长的劾鬼术后来成为道教的组成部分,随着道教的发展,符箓派和丹鼎派都包含有劾鬼方面的内容。蒋波也认为东汉道术控制鬼神的能力为后来道教信徒继承,“降鬼”成为道教徒常见的法术。而道教的劾鬼巫术显然也与争取教众、传播神仙思想有密切关系。
再者,《后汉书·方术列传》中还有汉章帝与寿光侯的故事:
初,章帝时有寿光侯者,能劾百鬼众魅,令自缚见形。其乡人有妇为魅所病,侯为劾之,得大蛇数丈,死于门外。又有神树,人止者辄死,鸟过者必坠,侯复劾之,树盛夏枯落,见大蛇长七八丈,悬死其间。帝闻而征之。乃试问之:“吾殿下夜半后,常有数人绛衣被发,持火相随,岂能劾之乎?”侯曰:“此小怪,易销耳。”帝伪使三人为之,侯劾三人,登时仆地无气。帝大惊曰:“非魅也,朕相试耳。”解之而苏。
李贤注认为寿光侯是人名,钱大昕则认为“寿光侯”是“侯失其姓名,故举其爵”。寿光侯故事中出现了身为帝王的汉章帝,作为厌劾之术能够验证的见证者,这显然也是道士为神异其说刻意而为的,范晔也没有怀疑这则故事的真实性。《搜神记》和《列异传》中都记载有寿光侯的故事,与费长房故事相似,这也属于道士捉妖伏鬼类型故事;而这种故事的传播,显然也与六朝道教体系完备和传播范围扩大的整体社会背景有关。
千里取物方术
汉代有“千里取物”的方术,这其实是人们对于神异速度的想象。这些故事大多是民间流行的神话传说,但范晔并没有辨析整理,而是原封不动写入《后汉书》之中;成为正史记载之后,势必也会对人们认识方术的真相造成一定干扰。
《后汉书·方术列传》有王乔故事:
王乔者,河东人也。显宗世,为叶令。乔有神术,每月朔望,常自县诣台朝。帝怪其来数,而不见车骑,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临至,辄有双凫从东南飞来。于是候凫至,举罗张之,但得一只舄焉。乃诏尚方视,则四年中所赐尚书官属履也。
王乔没有车骑而能够快速往来叶县和洛阳,从《后汉书》文意来看是化作“双凫”飞行。与之类似,《后汉书》还有费长房的“乘龙”故事:
长房辞归,翁与一竹杖,曰:“骑此任所之,则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也。”又为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长房乘杖,须臾来归,自谓去家适经旬日,而已十余年矣。即以杖投陂,顾视则龙也。
可以发现,王乔所乘之“双凫”与费长房所乘之龙,都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跨越空间,这当然是过于神异而不现实的故事。而费长房跨越空间的能力还不止于此,《后汉书·方术列传》还记载说:“又尝坐客,而使至宛市鲊,须臾还,乃饭。或一日之间,人见其在千里之外者数处焉。”费长房设宴款待客人,而能够到外地取物,这种“千里取物”的能力在东汉三国时代的文献中较为常见。同样的故事也见于《方术列传》所载左慈故事:
左慈字元放,庐江人也。少有神道。尝在司空曹操坐,操从容顾众宾曰:“今日高会,珍羞略备,所少吴松江鲈鱼耳。”放于下坐应曰:“此可得也。”因求铜盘贮水,以竹竿饵钓于盘中,须臾引一鲈鱼出。操大拊掌笑,会者皆惊。操曰:“一鱼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放乃更饵钩沈之,须臾复引出,皆长三尺余,生鲜可爱。操使目前鲙之,周浃会者。操又谓曰:“既已得鱼,恨无蜀中生姜耳。”放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即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买锦,可过敕使者,增市二端。”语顷,即得姜还,并获操使报命。后操使蜀反,验问增锦之状及时日早晚,若符契焉。
曹操“验问增锦之状”,居然能够“若符契”,范晔对左慈“千里取物”能力的书写也过于神异了。后来葛洪《神仙传》,载有介象的故事,与左慈故事基本相同:
与先主共论鲙鱼何者最上,象曰:“鲻鱼为上。”先主曰:“此鱼乃在海中,安可得乎?”象曰:“可得耳。”但令人于殿中庭方塪,者水满之,象即索钓饵起钓之,垂纶于塪中,不食顷,得鲻鱼。先主惊喜,问象曰:“可食否?”象曰:“故为陛下取作鲙,安不可食?”仍使厨人切之。先主问曰:“蜀使不来,得姜作鲙至美,此间姜不及也。何由得乎?”象曰:“易得耳。愿差一人,并以钱五千文付之,象书一符以著竹杖中,令其人闭目骑杖,杖止便买姜。买姜毕,复闭目。”此人如言骑杖,须叟,已到成都,不知何处,问人,言是蜀中也,乃买姜。于时吴使张温在蜀,从人恰与买姜人相见,于是甚惊,作书寄家。此人买姜还,厨中鲙始就矣。
这种在瞬间能够往来千里的故事也见于“肥致碑”,其中提到肥致能够“行数万里,不移日时”。邢义田也注意到,这样的法术在汉代非常流行,同样还有“唐公房碑”,其中提到唐公房在王莽时期为郡吏,府去家七百余里,“休谒往来,转景即至,阖郡惊焉”。其中所谓的“转景”就是“转影”,与“不移日时”含义相同,指的都是极短的时间。其实无论“不移日时”还是“转景即至”的说法,都无限缩短了时间,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空间的跨越,而这种跨越空间的想象其实有着悠久的传统,庄子“御风而行”也属于这种类型的想象。
另外,《史记·楚世家》有楚顷襄王时期“好以弱弓微缴加归雁之上者”的对话,其中提道:“若王之于弋诚好而不厌,则出宝弓,碆新缴,射噣鸟于东海,还盖长城以为防,朝射东莒,夕发浿丘,夜加即墨,顾据午道,则长城之东收而太山之北举矣。”这种在一天之内跨越超远距离空间的想象,其实也属于“千里取物”。有学者认为,《后汉书·方术列传》中的这种叙事模式可以总结为“提出远地取物难题—完成远地取物—验证远地取物”。
今天看来,无论相人术、劾鬼术还是千里取物的方术,在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真实有效验证的。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们尚缺乏辨析类似方术真伪的能力,诸如左慈之流能够使用类似现在魔术的“幻术”一时幻惑人心,但如果稍加留意思考,便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事实上,司马迁与班固都注意分辨秦皇汉武以及宣帝、成帝时代方术的真伪,但陈寿与范晔却在“广异闻”的名义之下对于当时社会流行的各类传说照单全收,这样确实会给后来读史者认识巫术和方术无法持续验证的真相造成不小干扰。
(本文摘自董涛著《不验辄死:秦汉时代的方术、谶纬与政治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8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