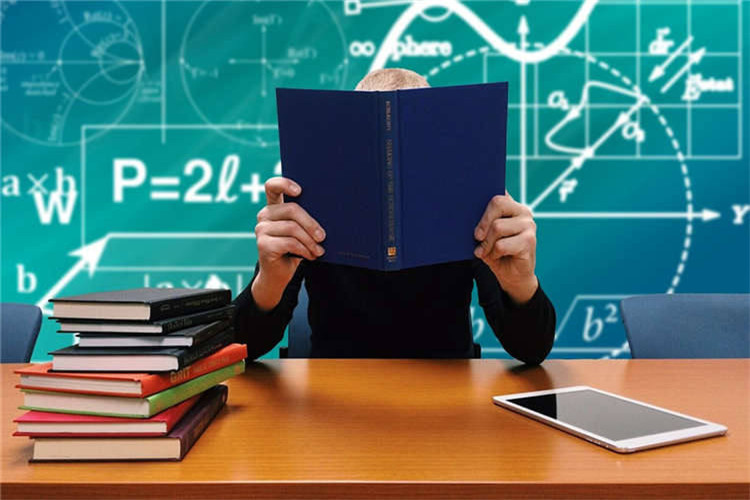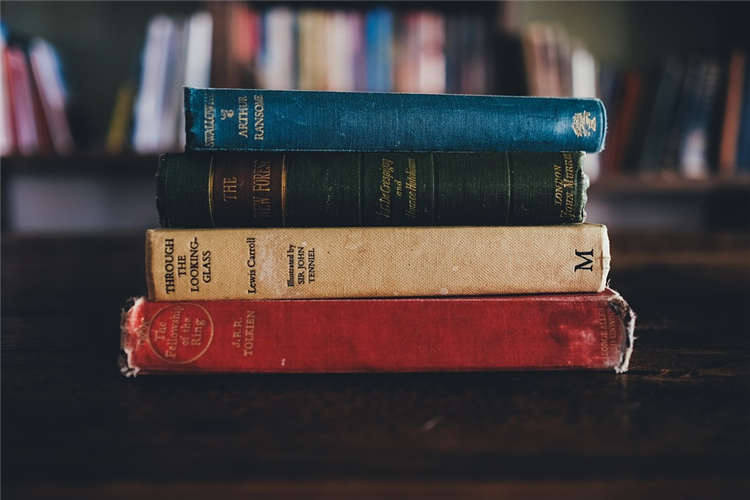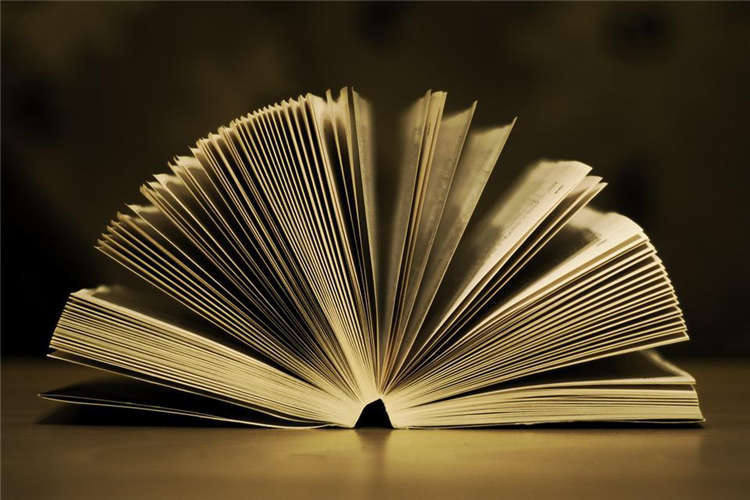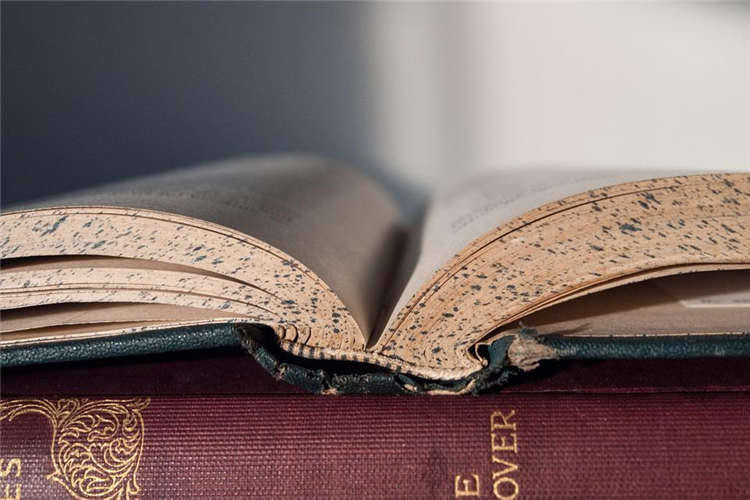金农(1687年-1763年)是清代“扬州八怪”的核心人物。他在诗、书、画、印以及鉴赏、收藏方面均称大家。
本文为八十多岁的知名画家了庐新撰论画文章,他认为,金农是真正的传统中国绘画史中历史性转轨的开拓者,其艺术作品越来越被当代人所关注,对当下艺术界的启发是多方面的,尤其是要沉下去,再沉下去,就是甘于寂寞,沉得住气。
清代金农的书法和绘画作品,总是让人觉得像一块石碑一样沉甸甸的。面对着他的作品,人的气不但一下子沉到了丹田,而且一直沉到了脚底的涌泉穴,好像扎了根一样,让人无法离开。金农是从碑学中得以感悟而蹦出来的一位书画家,他的艺术作品之所以越来越被当代人所关注,究其原因就是原始中孕育着现代,现代中又不失原始的基因。
金农自画像
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有树碑立传的传统。从现在留下的碑文来看,最早刻碑文的大都是一些民间书匠,直到唐以后才渐有书家的参与,像欧阳询的《九成宫碑》,颜真卿的《多宝塔碑》、《颜家庙碑》、《郭家庙碑》,柳公权的《玄秘塔碑》等。这虽然是书法史上的一种文化现象,但碑学在明末清之前其实没有引起书坛学习和传承的风气,这与唐以后科举时代以书取仕的文化传承有关。
金农临汉隶
碑学,我们现在所见的传世拓本大多还是以明以后的拓本为主,如明拓的《夏承碑》、《曹全碑》、《礼器碑》等。在明代的书坛上,书法的传承和学习还是以帖学为主流,这个现象一直延续到晚明及清初。金农是一个从碑学中感悟出来的文人画家,客观上,这与当时贵族的文化精神日渐衰弱、市民的文化精神却日益高涨的时代有关。画史上的“扬州八怪”比较以往的文人画家,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典型的市民文化群体,当时甚至被认为是一种不入流的怪,所以被称之为“扬州八怪”。
在“扬州八怪”这个群体中,金农更是一个另类的怪中之怪,但金农学养深厚,不为所动,甘于寂寞,沉得住气。他不但从碑学中感悟,而且他取的碑学,《爨宝子》、《爨龙颜》,都是西南滇东北地区曲靖一带出土的古代彝民书写的汉文,笨拙凝重,它比较中南地区崇尚潇洒秀丽的碑文是一个奇怪的书体,更接近文字的原始形态。这与金农朴拙无华的气质有关,他自甘寂寞与清贫,到了近现代,在一种新的文化理念日益活跃的当下,他倒成了人们关注的典型,这就是一种必然,原始中孕育着现代,现代中又不失原始的基因。
在金农以前,石涛虽然提出了“笔墨当随时代“的豪言壮语,引领了时代的潮流 ,但是真正的顺从者甚少,所以我认为,金农是真正的传统中国绘画史中历史性转轨的开拓者。
金农画佛
原始与现代,永远都是在历史发展中得以平衡的两端,像体育运动中的哑铃一样,每一方都不能偏废,而失去平衡。在当下日趋活跃的现当代艺术中,不是就有很多艺术家在各种原始艺术中吸取灵感而取得成就吗?这也是金农朴质淳厚的艺术作品越来越被现代人所关注的时代原因。在金农之后的书法史上,碑学越来越被后人所关注,出现了像赵之谦、吴昌硕等人,而更典型的是则是后来的齐白石。
沉下去,再沉下去,向金农学习,就是要甘于寂寞和清贫,沉得住气。文采盖世的苏东坡在《留侯论》中曾说:“夫天下之成大事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忍就是沉下去,再沉下去的精神核心。
我的好友周思聪先生身前说过,轻浮的东西飘在水上,最终都被水流带走了,只有沉下去的东西会永远存在。
在今天我们所耳闻目睹的画坛上,不就有很多当年的时代宠儿,已经被历史所淘汰了吗?淘汰是毫不足惜的。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他们这代人在1976年以后重进校门,又在三五年毕业后幸运地填补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不幸去世的老艺术家们的学术领导岗位,但他们在取得权力之后,不但没有自重自爱,发奋努力为社会作贡献,反而自我膨胀,把权力延伸到了权威,口出狂言说什么大师从这里起步。更有一些空头理论家他们洋洋千语,著作等身,可是有哪句话是自己的呢?这些至今不是都成了历史的笑话吗?所以在竞趋风光的当下,我们更需要像金农那样有着沉下去、再沉下去的精神。
金农简笔像 了庐绘
在人类的文化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有成就的人不是以终身不懈的努力而取得的。我常说,“励志还须多道德,雄心尤贵伴谦尊。”想要做大事的人先要从小事做起,要用做大事的精神把一件小事做好,就可以一通百通。金农那种沉下去、再沉下去的求实精神,对当下的启示是多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