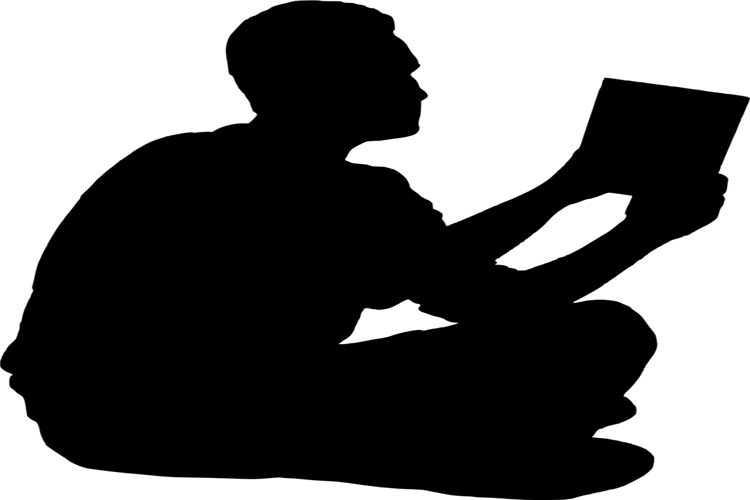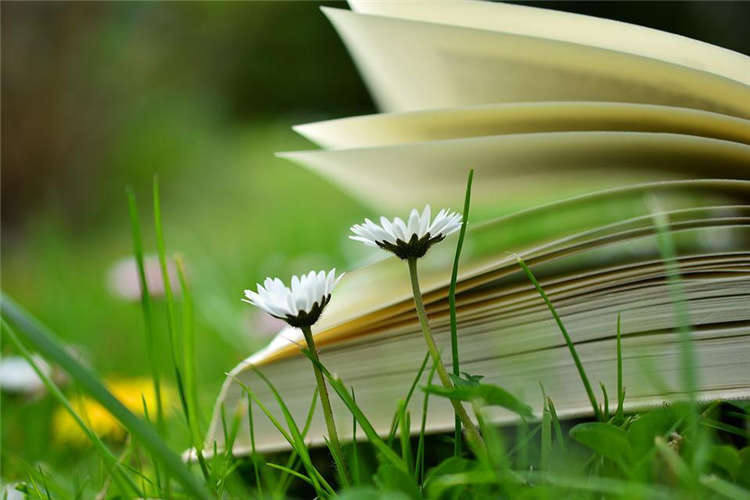10月17-19日,改编自老舍经典作品的专属版《茶馆》和曲剧《四世同堂》在上海上演。笔者认为,这两部作品所关注的,乃是空间在漫长的20世纪中如何被书写,如何被着色,如何在被入侵与被重塑之间,抵达那不可测的平衡点。
很多时候,戏剧都在扮演应时应季之文化产品,被使用,被观看,它自有其新陈代谢,即使那些戏剧名家,在其漫长创作生涯中,也只有少数代表作能够长演不衰。
老舍的《茶馆》正是那少数之一。该剧首先于1957年7月在《收获》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次年3月29日,焦菊隐和夏淳导演将《茶馆》带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舞台,并成为该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其虽于1992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40周年之际,短暂告别,但1999年10月12日,该剧院又以林兆华为导演,启用全新阵容,融入表现主义手法,重新排演该剧,并在首都剧场公演。
《茶馆》剧照
2005年,焦菊隐诞辰100周年之际,林兆华又透过录像资料,还原了当年的“焦版”《茶馆》,由梁冠华、何冰、杨立新、濮存昕、宋丹丹等一众名演员担纲,这一经典再次向新一代的观众证明了经典剧作的魅力所在。由于戏票热卖,北京人艺不得不将最高票价从260元调整为680元,这是该剧团6年来首次提价。
对《茶馆》的改编,常常成为喧嚣一时的文化事件。成功者,如2017年王翀在薪传实验剧团制作的《茶馆2.0》,以及同年四川人民剧院和四川籍导演李六乙的四川话版《茶馆》;毁誉参半者,如2019年孟京辉版《茶馆》,台词和背景被完全改变,茶馆由历史空间蜕变为未来空间,许多观众不能接受如此大幅度的改变,甚至有观众现场吵嚷起来,要求退票。
不过,以上种种改编也证明了《茶馆》在戏剧构作上的弹性。它是为标准的中型剧场制作的作品,此一类型的剧场,如此广泛地作为基础设施存在于中国各大城市,因此,《茶馆》既能够向下兼容小剧场那种观看与演出细密交织在一起的狭小环境,又能够在大型剧场的繁复布景下充分释放其戏剧潜能。
《茶馆》剧照
2025年7月12日起,北京老城门剧团携专属版《茶馆》开启全国巡演。其中,上海场的演出于10月17日及18日在闵行区的保利城市剧院举行。这便是一出在中型剧场上演的,近乎标准的《茶馆》。
但专属版《茶馆》并非10月于沪上舞台呈现的唯一一部老舍作品。18日及19日晚,位于静安区江宁路66号的美琪大戏院,搬演了由老舍长篇小说《四世同堂》改编的同名曲剧。该剧根据同样由来自北京的制作团队担纲。成立于1959年的北京市曲剧团,素以其排演的老舍作品,如《茶馆》《四世同堂》《龙须沟》《正红旗下》闻名。该剧团与老舍的渊源颇深,其所代表的地方剧种“北京曲剧”,即在1952年由老舍亲自定名。
观众们不难发现,专属版《茶馆》与曲剧《四世同堂》的共同点,尽管它们改编重排所依据的蓝本,一个是话剧,另一个则是小说。但在这两出剧中,我们都能听到,帷幕揭开时,那突然如陨星般撞向我们耳膜的尘世喧嚣,仿佛开场时刻,演员们鼓足了劲,要在三教九流汇聚的茶馆中,抑或在为祁老太爷贺寿的热闹场面中,如敲下定音锤般,制造出些许声响,以显示他们所身处的公共或私人场域,都曾是时代的中心,如磁铁般,紧紧吸附住周遭的一切。
然而,到作品的结尾处,我们所看见的确是死亡,茶馆老板王利发在茶馆被政府强占的绝望中自尽,祁老太爷的曾孙女妞子因饥饿在日本投降前夕死去。
《四世同堂》剧照
这两部作品所关注的,乃是空间在漫长的20世纪中如何被书写,如何被着色,如何在被入侵与被重塑之间,抵达那不可测的平衡点。
恰如学者王笛在《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中提到的,成都地区龙蛇混杂的茶馆,接近于哈贝马斯所谓“公共领域”的概念,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政治空间,它时刻与国家机器对其的掌控保持距离。
李六乙版《茶馆》在制作时,对王笛此书多有参照。撇去成都茶馆所附着的地方特性,我们所能看到的是茶馆此类场合作为“公共领域”的共同特性,它是一个时代的剖面,最大程度地容纳有闲阶级和破落的社会底层。
不过囿于剧团的物质条件,专属版《茶馆》不像北京人艺版一样,能透过布景直观展现茶馆华贵到破败的过程。但剧团也并非如在小剧场中一般,要将道具预算压缩到极致。
作为折中,专属版《茶馆》以空间布局的改变显示茶馆的衰颓,在第二幕中,卡座被撤去,原本的座位布局变得杂乱。茶馆的桌台铺上了现代化的桌布,西洋来的留声机取代了旗人们的鸟架:在开幕时刻,观众所能留意到的,常四爷、松二爷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将蒙着罩子的鸟笼,挂在鸟架上。
这一动作标示他们作为旗人的身份,也间接提示观众彼时裕泰大茶馆的地位与格调:它首先是京城有闲阶级聚集的地方,各种流言与传闻在这里如赝币般流通,最雅致的闲趣与卑劣的人口买卖互相混淆。
这一“公共领域”中并不存在单一的主角,即使茶馆的掌柜也并非主角。他是一个叙述者和见证者,直到戏剧第三幕最后才被卷入时代的漩涡中心。
来自不同阶层的茶客,亦无法形成某种共同体意识。民族、国家的概念都离他们太遥远。茶馆中,只有生存与生活,只有不断渗入,不断膨化的权力的阴影:鹰犬们总是一如既往地存在着,将他们的暴力触手伸向愈发广泛的民众。
《茶馆剧照》
在此背景下,混杂的声音此起彼伏。而得益于老舍原作,《茶馆》的戏剧力量主要来自台词。第一幕中,戏剧舞台往往被切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作为背景的哑剧,一部分是正在台前上演的生活片段。两者的彼此转换,构成舞台的叙述节奏。
可以说,《茶馆》是一出完全由碎片构成的戏,其贯穿始终的张力,来自角色迎来送往,上台下场而自然生发的节奏感:这正是茶馆生活本身所富有的节奏感,在这里你管中窥豹,透过生活的一个切片照见时代水面之下沉渣泛起的精神底色。
虽然《茶馆》的时间跨度达50年,但具体到每一幕,却严守三一律,因此,专属版《茶馆》舞台灯光的使用是十分经济的,一幕中往往只有照射全场,恒定不变的亮光,黑暗作为幕间间歇,起到链接作用。只有在王利发撒纸钱祭奠自己,并最终自我了断的两场戏中,我们可以看到,灯光在黑暗中劈出一条甬道,王利发行走于其中,并被黑暗吞没。骤然转变为猩红色的灯光里,一条绳索隐隐摇晃。
不约而同地,曲剧《四世同堂》也将最后一场送葬的戏份作为重头戏。当那与祁家同在小羊圈胡同的,一位子孙都牺牲于战争中,内心厌恶战争的日本老妪,向她的中国邻居,宣布日本投降的好消息时,妞子死去了。舞台灯光由此成为了反高潮式的,在举国欢腾时刻,灯光却只像豁开黑暗的一把把匕首,人们欢呼的声音依然浮动在黑暗中。随后是由宝石喷头制造的舞台雾效,艳色的染色灯光浮动于其上,两者共同模拟出水面的效果:这几乎不像一般的水面,而是迷惘的忘川。
两相照应之下,我们可以将《四世同堂》看成《茶馆》的补充,后者一笔宕开,直接从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时期,跳到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时期。《四世同堂》则弥补了《茶馆》对抗战时期北平描写的缺失。
曲剧《四世同堂》所呈现的空间,亦与《茶馆》恰成对应。小羊圈胡同是一个典型的私人场域,个中生活的人物有着强烈的身为家族的共同体意识,即使他们在公共场域的身份截然不同,一俟进入小羊圈胡同,他们便重新置身于“四世同堂”的家族秩序之下。当《茶馆》揭示出公共领域在时代冲击下的萎缩与凋零时,《四世同堂》则告诉观众,连私人领域也不能独善其身。
虽然在这两出戏中,我们明显地看到空间的内与外之分,戏剧空间几乎执拗地集中于茶馆和胡同这样的封闭场域,甚至于在台词中,北京也被描绘为一个巨大的空间,当城门关闭,生活就如结冰的湖面般静止下来。
而这两出戏的舞台上,外部世界发生的事情,都以背景声的方式加以勾勒,但这些声音终究还是要进入到人物日常生活的内部。历史不是遥远的风景,不是舞台上干瘪的画片,不是一如既往的麻木不仁,它如同空气一样难以看见,又无处不在,它与我们的当下,我们的日常休戚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