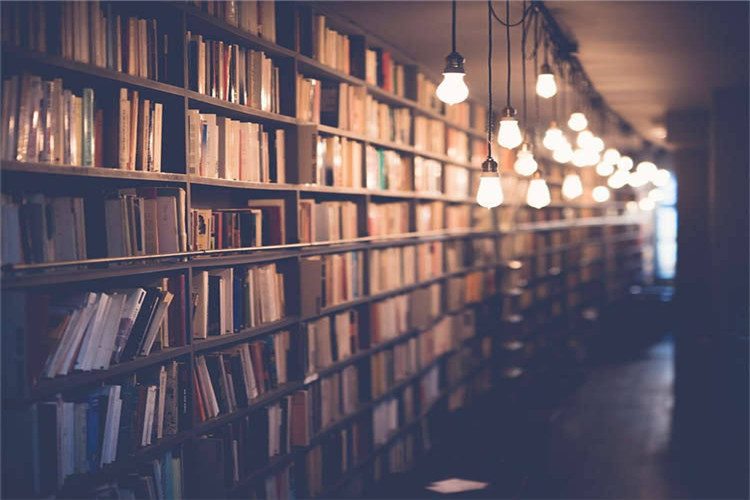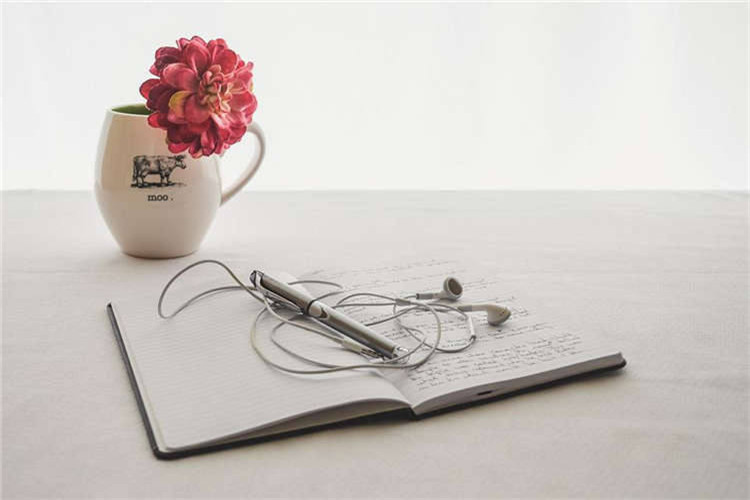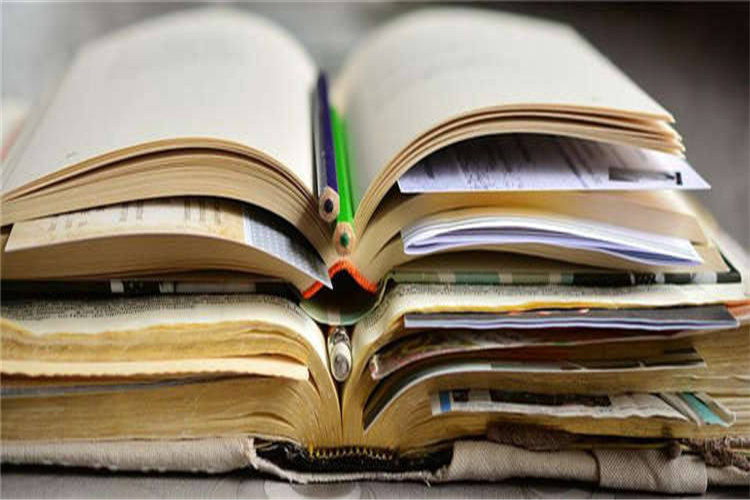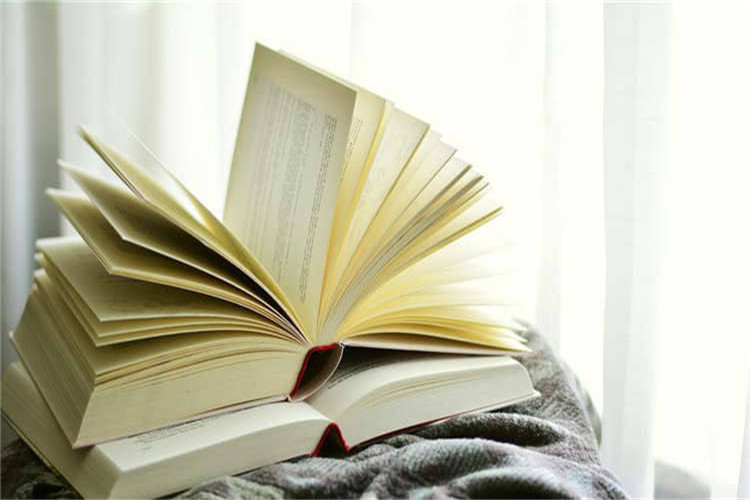蓝蓝天空绿绿草地上,绿绿草地上有栋小房子,房子里面没有人孤独,爱和自由永远伴随你。
这是W机构在围读的时候经常会带领心青年(心青年,即心智障碍青年)们一起唱的一首歌,在太阳还没落山的二楼的教室里,阳光透过窗户洒下一道光亮在围坐的人们身上,让人觉得这样美好的画面应该永远保存下来。
作者来到W机构探访大龄心智障碍群体
一、进入
在2024年的3月份,我来到了Y省的W机构,这是一家服务以自闭症为主的心智障碍者及其家庭的社工服务中心,主要为特需家庭提供喘息服务及社区融合服务。机构中有几位大龄心智障碍者和助理。
3月份,我第一次来到这个云南的小城。湛蓝的天空,远处被云覆盖的山,清晰可见,我意识到我真正来到了一个全新的地方。在这里,我的目的地在一个不起眼的村子里,沿着湖边连成一排,还没有被远道而来的游客占领,经过的村民房屋上写了风花雪月四个字。机构就在靠近湖边的一个村庄里,我站在机构房子的门口,等着里面的人开门,其建筑和周围居民的村宅别无二致。
W机构是为中重度的大龄心智障碍群体提供自主生活服务的机构,自主生活服务是一种特别为心智障碍人士设计的居住和支持环境,旨在提供一个安全、支持性的空间,促进其独立性、社会融入和生活质量。在我去到W机构时,机构中有八位心青年。
负责人带我参观了他们的教学区和生活区,教学区是机构的正式所在地,平时机构就在这里进行日间活动,生活区主要是中午吃饭和带领心青年们帮厨的地方。教学区一楼中央有一个大的活动场地,主要供心青年们活动和玩耍,左侧是宿舍区,分为男生宿舍和女生宿舍,吃完午饭后他们会在里边午休;右侧有一个扎染工坊,在每周四固定的下午时间机构助理们会带心青年们去这里做扎染。二楼活动场所更多,有大活动室、音乐室、平静室、图书室等等,整体上非常完备。
在W机构里,不仅有自闭症、唐氏、脑瘫这样的障碍,还有一些其他障碍的特需青年,他们大多是中度和重度的障碍类型截止到2024年三月,最小的14岁,最大的38岁。目前机构中大部分是中重度的自闭症谱系的心青年,他们就读的时间长短不一,最长的长达五年,最短的是只有一周的体验式试读。
每个心青年都会有专门的助理陪伴,有时候一个助理会负责两个心青年,我作为志愿者进入机构中,主要近距离陪伴了三位心青年,乐乐、冬冬和冉冉。在这里长期工作的助理大都有自己专门陪伴的心青年。在日常的某些事务中,生活助理也会教心青年们应该怎么做,比如说会让他们吃饭前先洗手、离开座位的时候把凳子放归原位、让孩子们自己上楼喝水、上厕所等等,在生活的细节层面给孩子们提供一些最基本的支持,锻炼他们的自主性。
在机构的那段时间,我陪伴最多的人是乐乐。乐乐总是笑着的。她的笑容纯粹而直接,有时候带着一点儿狡黠,像是刚刚做了什么小小的恶作剧等待被发现。她喜欢黏着人,喜欢叫人的名字,每次见到我,都会猛地凑过来,紧紧握住我的手,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嘴角扬起,不断地发问,似乎对这个世界有着无尽的疑惑。在这家为心智障碍者提供自主生活支持的机构里,这样的场景每天都会发生。
助理阳姐告诉我,其实不需要过分迁就他们,真正的尊重不是一味地顺从,而是教会他们在社会中如何建立关系、如何理解界限。“该拒绝的时候要拒绝,该说不的时候就说不。”
乐乐特别喜欢冉冉——另一个心青年,安静、内敛,和乐乐截然不同。每次见到冉冉,乐乐总是忍不住伸手去触碰她的脸或是手臂,但冉冉并不喜欢过分的亲密。有时候,她会皱起眉头,把身体微微后仰,尽量避开乐乐的触碰。这时候,老师们会轻声提醒她:“如果你不喜欢,要告诉她。”同时,也会对乐乐说:“未经允许,不可以随便碰别人。”这种提醒不会带着责备,而是一种耐心的引导。
但这并不容易。夏夏有强迫症,看到别人书包的拉链没拉上,就忍不住上前拉上;看到谁的袖子卷起来了,他会立刻去把袖子拉下,即使那个人是陌生人。而小可则喜欢拿别人的东西吃。助理们常常对他们说:“管好你自己,不要管别人。”他们不是在呵斥,而是在教他们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需要学会尊重别人的边界,同时也要理解自己的位置。
社会往往对大龄心智障碍者缺乏关注。儿童时期,他们或许还能得到特殊教育的支持,但一旦成年,许多服务就戛然而止,他们的成长也仿佛停滞。家庭、机构、社会,哪个才是他们真正的归属?他们能够独立生活吗?他们如何在这个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带着这些问题,我走进了这家机构,试图理解在一个高度依赖自理能力的社会里,这些心青年如何生存,社会又该如何为他们创造一个真正的归属之地。
二、日常
机构给我很深的感受是这里就像一间普通的小学,只不过学生比较少以及普通节假日不放假,譬如说端午、五一这样的节日。但是会有短暂的寒暑假,都在一个月左右,日常就只有固定的周末假期。周一到周五的课程基本上遵循着朝九晚五的时间,而且每个活动的时间段会有一个大致的范围,比如说早上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进行晨间运动,但提前或是延后几分钟也可以由助理们自己把握。围读的大教室中有一块可以移动的小黑板,黑板的一周计划上面写了日期和天气,黑板的右上角则写着五条简洁明了的规则:1.少数服从多数;2. 控制情绪;3. 保持安静;4. 灵活调整;5. 物归原处。这些规则常常体现在他们日常活动中的方方面面。
小黑板上,写着W机构的一周计划安排
在机构中,助理主要做的是三点,第一个是慢慢让他们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第二个是让心青年们懂得跟随课程的节奏,第三是听指令(比如说在助理说“某某,保持安静”时能够自觉安静下来)。通过这些日常规则的制定和遵守,机构的工作人员在有意识地培养这些心青年的自主性,到点了要做什么事,日常生活中细微的习惯如何形成,如何面对陌生的他者,公共场合中应该表现出怎样的行为等等这些都是机构想要让这些心青年在日复一日地生活中能够逐渐熟悉的。
工作日的早上九点,是新一天的起点。心青年们的家长往往会在这个时间前后送自己的孩子到机构门口,而助理们则会提早一些在机构门口站着迎接每一个心青年,并扬起笑脸同他们热情地打招呼。很多时候心青年们都不是很准时到,有几个会经常迟到,但这毫不影响,即使没来也没关系,家长会提前打电话和机构负责人说明情况。
到了机构之后,助理们会先让心青年们自己上楼把包放到二楼右边教室的柜子里,再下楼到机构门口摆放的桌椅前坐下等着量血压、血氧饱和度以及心率等。心青年们一个个上去测量,助理们要重复喊他们的名字和要做什么,他们才会来到桌子前的座位上等助理测量,机构负责人说这是为了让他们养成习惯,之后如果去医院测量也不会太过紧张。在每一天结束时,助理会把测量结果发送给家长。
测完之后,助理们会拉着心青年们一起围成一个圈,手拉手一起进行晨间运动,几乎只有老师在唱歌,一两个孩子跟着唱和做操。晨间运动完之后就到了户外活动的时间,助理们会带各自负责的心青年们沿着湖边走一段路,这里的天气感觉永远是晴朗的,散步的时候四周都是绿树和鲜花。
回到教学区后就到了上午点的时间,休息一会后助理们带着心青年一起去食育室,先让他们各自穿戴好挂在墙上的围裙,然后坐在餐桌旁边的座位上,当天负责的助理会跟一个一个跟心青年们说“我叫……你叫……”,让心青年们自己说出自己的名字,即使需要一遍遍地说,仍不厌其烦。接着助理会把上午点的水果拿到心青年们跟前,询问他们是什么水果,并引导一位心青年把水果分给其他人,吃完之后会让心青年们把碗洗好放回橱柜里,再把凳子放回原位,在细节中培养他们的日常习惯。
上午点结束后,助理们将心青年们分成了两组,一组去生活区的厨房帮厨,另一组则在大活动室做陶泥。我在陶泥组和两位助理带着三位心青年一起做陶泥。这个过程实际上并不顺利,但有助理们会一边握住他们的手一边解释步骤,他们会慢慢地做,在这个过程中经常可以听到助理们口中传来的赞许的话语。
心青年们从下午一点开始午休,下午两点助理们会叫他们起床,他们自己穿衣服、穿鞋等。等大部分心青年都到了大活动室后,助理会让心青年们自己搬凳子在黑板前围成一圈坐在一起唱歌,之后助理带读千字文或者讲一本少儿漫画。在围读的过程中大多数心青年们都没有回应,有的会起身四处跑动。偶尔会有一两个回应的,会被助理额外点名表扬:“刚刚我看到小可还有冬冬都跟着一起唱/读了,特别棒!”
下午三点多是社区服务时间,助理们准备好了工具,夹垃圾的铁钳子以及黑色的垃圾袋,让心青年们自己拿着,助理们带着心青年们一起围着村子绕一圈去捡垃圾。在弯弯绕绕的小巷子里偶尔也会碰到村民,有时候还会互相打招呼。回机构的路上,冉冉主动把装满垃圾的垃圾袋扔进了垃圾桶。
回机构后,大家围成一圈做这一天的回忆和告别:“感谢美好的一天”。临近五点钟,心青年们背上自己的书包,准备下课回家,门口已经有等着接孩子的家长了。
三、户外
机构的课程设置中有不少的户外活动,不论是工作日早上几乎是每日例行的湖边散步活动、定期的户外买菜和社区服务,还是每周三全天的大户外活动,都让这里的心青年有很多可以接触外界的机会。去到户外是一种看见的尝试。这里的负责人说过一句话“如果把这些孩子放在社会上要怎么办?”为他们创造一个隔绝环境的初衷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会日常该如何生活,普通人如何过一天他们就如何过一天,但在他们真正走到户外,就能够和外界接触。
爬山这天的上午,有大巴车过来,心青年们一个接一个上车,我陪着冬冬,在她旁边坐着,把耳机分享给她,一起听歌,她边听还会边跟着唱歌。到了中午,大家爬到一个寺庙的空地旁边,是该吃饭的时间了,空地上有几个石板凳,各自找位置坐下,放下书包,父母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午餐放在书包里,助理帮心青年打开饭盒,让他们自己拿着勺子吃饭。其间,有一位心青年突然直接在地上拉大便,助理们拿着卫生纸去帮他处理。
心青年去户外爬山
在山上吃完午饭后,大家又一起走着下了山,走到村中一座特色的村落建筑里,开始了围读。助理阳姐带着大家一起唱“虫儿飞”这首歌,乐乐一边唱一边流泪,不肯走,我就陪着她在那边坐了一会,我说,“我们去坐大巴车,回家”,她说“我不回家,我要张阿姨。”后面阳姐过来和她讲话,劝她跟着一起走到马路边等大巴车,她才愿意起身走,我于是理解到他们确实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其他人难以接近和进入。
四、助理
在W机构中,生活助理的角色是建立在一种平等的、非权威的基础之上。不同于传统的师生关系,机构强调生活助理与心智障碍者之间的互动是平等且没有等级差异的。机构负责人明确反对使用“老师”这一称谓,而是鼓励直接使用姓名来称呼彼此。负责人说机构更需要的是“可以根据孩子们的情况随时转换策略的人”,而非“端着”或保持权威姿态的特殊教育老师。
小易是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最早是做的创新教育,而后转向特殊教育,在他第一年做特教时,一个14、5岁的自闭症阿斯伯格患者把他按在墙角扇,他说他还手了,“干这个行业图什么?我爹也没怎么打过我,非常的崩溃。”他把这种感受叫做愤怒,屈辱到就很多时候就来自于这里,他们无缘无故地打你,无缘无故地咬你,只是因为情绪来了,所以突然就很想打人,而你是离他最近的人。
在谈到这些在我看来可能有些困难和不知该如何面对的场景时,小易看起来已经很淡然了,他表示这么多年过来了,已经把自己练就成一个多面手,不太会有很崩溃的时候了。除了崩溃,当然也会有一些带给他希望的时刻,他说这也是他踏入这个行业的契机。他向我描述了一个场景,开头仍然是一个孩子在公共场合突如其来的爆发情绪,一边哭一边笑一边薅他妈头发。小易就把他的手轻轻掰开,然后抱着他,慢慢地扶着他的背,他在小易的怀抱里放松下来了,之后小易就带着他走到一片田野,他们开始一起唱歌。
“太阳很大,微风吹过来,那个画面让我觉得我被治愈了。众生皆苦,而在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的苦难不值一提。他们需要一批能看见他们苦难的人,去支持到他们生活。”
这是小易在W机构的日常生活实践中,生活助理与心智障碍群体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一种双向治愈的关系。“关怀伦理”(Ethics of Care)强调,关怀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网络。(Noddings, Nel. Caring: A Feminine Approach to Ethics and Moral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这种关系不仅是助理为心智障碍者提供日常支持,帮助他们实现自主生活的单向付出,还反映了在互动过程中,助理本身也经历了一种内在的治愈。
五、归属何方
W机构曾尝试通过社区支持、手工艺培训等方式,帮助村里的普通家庭减少经济和照护压力。“我们之前做了一个项目,给四里八村40多个心智障碍者提供工作机会,每个月给他们发工资。”但这样的实践却没能持续下去,负责人也谈到了原因,“第一,自己不愿干,被投喂习惯了。第二,父母也觉得一接一送就得耽误一天,宁愿孩子躺在家里,大门一锁,大人出去干农活,啥也不用管。所以村子里的心智障碍者活到30岁都了不起了。”残障个体的生存质量不仅取决于他们自身的健康状况,更受到社会环境与支持系统的深刻影响。如果在政策与实践层面无法建立有效的支持系统,那么家庭就会被迫成为唯一的照护者。
随着心青年逐渐进大齡甚至老年,社会对于这些群体的支持体系变得愈发不足。机构规模的缩减、服务人员的流失以及资金问题都导致大龄心智障碍者正面临无处可去的困境。
(本文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硕士研究生,文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