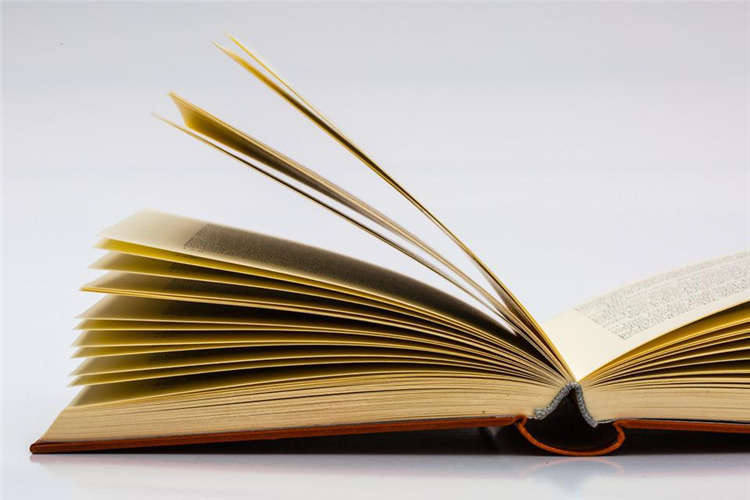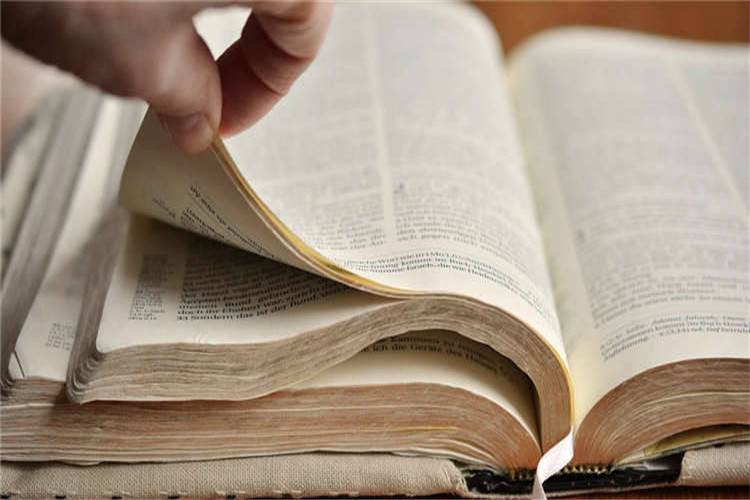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曾经以为会永恒存在的体制,却在短短的时间内崩溃。柏林墙倒塌造成的创伤成为了德国作家燕妮·埃彭贝克(Jenny Erpenbeck)的写作原动力。2024年,她的作品Kairos成为了第一本获得国际布克奖的德语译作。
这部作品中,一位五十多岁的男子和一位19岁的年轻女学生在1986年东柏林公交车上相遇,成为恋人,他们的关系开始产生裂痕,而随着东德开始崩溃,所有旧的确定性和旧的忠诚也逐渐瓦解,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它带来了巨大的收获,也伴随着巨大的损失。
Jenny Erpenbeck
New Directions 2023
1967年出生于东柏林的燕妮·埃彭贝克被《纽约时报》誉为“一位从德国痛苦历史中寻找灵感的小说家”。《与父亲的奥德赛》的作者丹尼尔·门德尔松称,“历史事件与个人意志的交汇点是她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
燕妮·埃彭贝克熟悉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是她大部分小说的重要背景。在她已译介到中文世界的作品中,《白日尽头》以一位中欧犹太女性的五段人生,描绘了跌宕起伏的二十世纪;《客乡》以位于柏林郊外的一处湖畔别墅,串联起二十世纪的历史和人物命运;《时世逝》关注当下的欧洲难民危机——一位孤独的东德教授在统一后的德国漂泊,他发现自己与那些同样在德国漂泊的非洲移民不乏相似之处。《纽约客》书评人詹姆斯·伍德在2017年提出,《时世逝》还没有得到充分重视,他甚至预测燕妮·埃彭贝克会在“几年内”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01 只要人们还在受苦受难,历史就不会终结
界面文化:在过往的采访中你谈到,如果没有政治制度的改变,自己也许永远不会成为一名作家。政治制度的改变为什么对你来说尤为重要?它给你带来了怎样的思想变化?
燕妮·埃彭贝克:整个体制,你认为或多或少是“永恒”的,却能在几周内就崩溃,这种经历会让你终身难忘。人造系统的脆弱性。还有一种体验是,有些人打开了一扇门,他们却很快被推开,通过这扇门进入的是和想象中全然不同的东西。
写作是一种穿越时空的方式,以自己的记忆为素材,仔细观察那些你不了解的事物,而它们却正是你的现在。这种方式让自己变得陌生,同时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自己。
[德] 燕妮·埃彭贝克 著 胡烨 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23-10
界面文化:1989年,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政治历史发展已经到达终点,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路,即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你是怎么看待其观点的?
燕妮·埃彭贝克:我相信永恒的变化,因为变化、过渡和蜕变是生命的原则。很显然,只要人们还在受苦受难,历史就不会终结。他们总是试图改变世界,以获得自己的那份。他们人数众多。
界面文化:很多英文材料曾提到了年轻人对东德统治的不满,对于柏林墙倒塌人们的感情多么热烈。你在小说《时世逝》中设置了一个住在柏林墙附近的人——理查德,他无视或逃避这些热烈的人们。你怎么理解意识形态革命者和群众的激情?
燕妮·埃彭贝克:革命者变老是个问题。他们改变立场、成为掌权者后,既不信任自己的人民,也不信任下一代,也是一个问题。在东德政府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问题。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属于我祖父母那一代的领导人也曾经年轻过、狂野过。但事情就变成了这样。
就我而言,我不想被群众的歇斯底里冲昏头脑。我甚至不会在别人为某首歌曲鼓掌时鼓掌。我对热情怀有深刻的怀疑,它会让人失去清醒的头脑。这些情绪很容易被人利用,把个体变成幕后操纵者的工具。
当柏林墙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在技术上被拆除时,我没有理由热情高涨。我是在柏林墙建成后出生的,以前从未见过柏林的全貌,因此没有回到“过去美好时光”的感觉。那感觉就好像巴黎乘着飞毯降落在我家旁边。我感到惊讶和恼怒,仅此而已。顺便说一句,和平革命以决定让我们成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一部分而告终。与一个已经存在了40年的国家的统一,并不是革命。
[德] 燕妮·埃彭贝克 著 李佳川 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24-2
界面文化:理查德是一个非常“置身事内”的人物,他逃避热情的群众,目光对准的是日常生活的诸多变化,比如多次强调百货商店的名字变成了超市。你为什么会这样写?
燕妮·埃彭贝克:有时候人无法停止反复思考同样的问题,这就是一种“死胡同”。统一后,连词汇都发生了变化,这是许多东德人不得不面对的现象之一。语言使人们看到,变化并非源于两个平等伙伴的统一,而是其中一个被添加到另一个既存的体系中。
界面文化:你似乎非常清楚东德政府的问题,同时也想让读者知道,这里也可以提供美好童年,也有许多美好的、值得借鉴的事物。这种对东德的怀旧情绪,在德国知识分子中是否常见?人们怀念的是什么?梳理东德的复杂遗产时,究竟是什么在当下尤为重要?
燕妮·埃彭贝克:我不会称之为怀旧,它更多是指难以适应整个社会如此深刻的变化。因此,这不仅仅是对美好事物的怀念,即使这些美好事物有很多——比如人人都能负担得起的住房和良好的医疗保健。我们也怀念不好的东西——只是因为我们对它们也太过熟悉。我们知道规则,我们知道如何应对困难,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我们的人民开启了变革的进程。
但是,从1989年秋天的自强不息,到一个必须尽快学会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存的人的谦虚,只用了不到8周的时间。从那一刻起,你就被踢出局了,成了局外人,成了一无所知的人,失去了控制。要调整自己,适应建立在个人主义和一致同意基础上的新体制,是很困难的。也许你甚至失去了工作,也许你看到父母突然变得软弱和绝望。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足够的能力和力量去赢得这场斗争,去成功,去重新开始。权威的瓦解并不只是给自由让路,并不只是产生轻松或喜悦,它也会产生恐惧和对所有权威的极度不信任——后者可能对作家有好处,但并非对所有人都是如此。
02 在无数个体的传记中,历史和政治变得清晰可见
界面文化:韩国社会学家张庆燮认为,同为追赶西方现代性、为所处劣势感到不安焦虑的后发国家,“压缩现代性”是亚洲国家共同的地区特征。不知我们是否也可以用“压缩现代性”来形容东德人的历史感受?你的几本著作都涉及到对时间的使用,身为东德人的时间感觉是怎样的?
燕妮·埃彭贝克:柏林墙倒塌时,我有一种加速的感觉——我们从一个缓慢的社会跃入了一个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为了谋生,我们必须迅速赶上这个世界。尽管如此,我们仿佛又回到了一个政治上民主、经济上仍受金钱和利润最大化理念支配的结构中。但似乎,利己主义是迄今为止人类发明的最强大动力。
从五十年代起,民主德国就开始大力发展自己的工业,而在此之前,这些工业主要集中在西方国家。现在,在统一之后,大部分民营企业以象征性的马克价格卖给了一些西方公司,这些公司在两三年内关闭了80%的东德工业。与此同时,东德还面临着数字化的挑战。现代化对人们的要求很高。我知道有很多人为了找工作搬到了西德,从未告诉过任何人自己是东德人。虽然德国的两半共同经历了工业化的前一百年,虽然东部也独立发展了不少工业,但在统一之后,东部人只会被视为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
界面文化:一篇《客乡》的书评写道,你把20世纪的创伤浓缩到一个地址上。你也说过,你的作品总是从一个个人的问题开始,可是仔细一看,它就成了历史问题。
燕妮·埃彭贝克:当我开始写作时,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历史作家,甚至不是一个政治作家。但很快我就明白,个人生活离不开历史。有时,这不过是政治家在某文件上的签名,一点点墨水却能对成千上万甚至数百万人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它可以区分哪些人可以活下去,哪些人将失去生命;它可以决定人们是否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迁往他处;它可以分裂家庭。我认为,传记总是混合了政治的任意与偶然,当然也有个人的自由意志。但即使是自由意志,不也受到政治教育和所处社会的影响吗?自由意志并不是凭空存在的。在无数个体的传记中,历史和政治变得清晰可见,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素材。
界面文化:你借理查德之口说出,“如果你想探究时间究竟是什么,最好的办法是去寻找那些落在时间之外的人,也可以寻找一个被锁在时间里的人。”什么是落在时间之外的人,什么是被锁在时间里的人?
燕妮·埃彭贝克:理查德遇到了这些正在德国等待被接纳为难民,从而被允许工作、谋生的非洲年轻人。他们长年累月地在临时住所或寻求庇护者之家等待,他们实际上是被时间锁住了。我自己也遇到过这样的人。忍受着时间的流逝,却不被允许活跃起来,这与人的正常生活恰恰相反。这是对人类精力、希望和潜能的可怕浪费,也是人生最大的苦难之一,如同被活埋。
[德]燕妮·埃彭贝克 著 李斯本 译
北京日报出版社 2023-1
界面文化:《客乡》《白日尽头》让人感受到某种历史感和距离感。你曾经谈到,所有的故事都需要很远的距离才能看到,从那么远的地方看才公平。你是怎么去掌握一部作品的距离感的?
燕妮·埃彭贝克:所谓的难民危机将在50年后成为历史事件。到那时,人们会去档案馆研究我们时代的报纸。为了写其他作品我走进了许多档案馆,我想,人们也可以想象从50年后回顾现在。我有幸与活着的人交谈,而不是阅读他们的故事。在对20世纪失去家园的情况进行了大量思考之后,我只需迈出一小步,就可以转向21世纪失去家园的人们。这些悲剧的相似之处超出了某些种族主义者的想象。我们都是人。
界面文化:有些主题与现实议题的距离或许非常近,怎么避免让小说变成某种政治宣言或者请愿书?
燕妮·埃彭贝克:方法就是提出最简单也是最复杂的问题:怎样才能过上有意义的生活?我们怎样才能意识到自己的死亡却继续活下去?追问:看不见的东西有多重要?我们有时对他人咄咄逼人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只是我们深藏于自身的恐惧?
03 我们每个人都是幸存下来的难民的后代
界面文化:在书中你写道,“非洲人可能不知道希特勒是谁,但即便如此:只有他们现在从德国幸存下来,希特勒才真正输掉了战争。”德国一直以来都被视为一个在历史清算方面做得特别好的国家,即便如此,极右翼依然死灰复燃。
燕妮·埃彭贝克:恐怕每一代人都要从自己的经历中重新认识带来民族主义和战争的法西斯政权会造成多少苦难。
界面文化:在谈及难民等当下的议题时,你在书中使用了古典学资源、格林童话、民间传说等等,看起来有点遥远,却又能和现实产生关联。你是怎么从这些传统中获得养分的?
燕妮·埃彭贝克:如果这些神话和童话不包含深刻的人类经验,就不会流传这么久。对我来说,没有与周围世界的联系的“经典教育”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可以从奥德修斯的故事中找到深刻的真理,比如他只是一个战争难民。教育不应该被用来区分富人和穷人、幸运儿和不那么幸运的人,而应该被用来获取生活经验的基本来源,并理解我们都有着同样的希望和恐惧。无论在哪个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是幸存下来的难民的后代。
界面文化:对于切身去关心他人可能存在的危险,你也没有避讳。比如说你也写了理查德家里可能遭到了难民的抢劫。你是怎么看待这种潜在危险的?
燕妮·埃彭贝克:世界上还有比盗窃更糟糕的事情。但别忘了,我在书中写的这个案件最后并没有破案。它只是被用来向读者以及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私人”(private)这个词源自拉丁词“privare”,意思是“剥夺”。(注:这个词的概念是指某样东西从公众或集体中被分离出来,从本质上“剥夺”了其他人的使用权)
界面文化:关于社会问题,理查德给出的解答似乎是采取私人行动。虽然书中提到法律的修改是必要的,但是事实上很难推动。很多人想要保住自己的既有利益或者对政治完全不感兴趣,究竟我们怎么才能够促进现状的改变?
燕妮·埃彭贝克:认真想要改变现状的并不是我们的政府,我们正在从他人的贫困中获益,因此栅栏和围墙越建越高。但边界另一边的人总有一天会开始移动。我担心会涉及暴力。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写了有趣的记者形象。“她似乎非常关心那些绝食的人,她也真的能让人们相信她的关心,这种关切的语调,也是记者的考核项目吗?”确实,很多时候我们关心一个社会议题,可能是因为工作需要,在你看来,怎样的关心才是真正的关心?
燕妮·埃彭贝克:真正的关心,需要做很多并不有利于自己的工作。
(感谢滑滑和雷韵对本文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