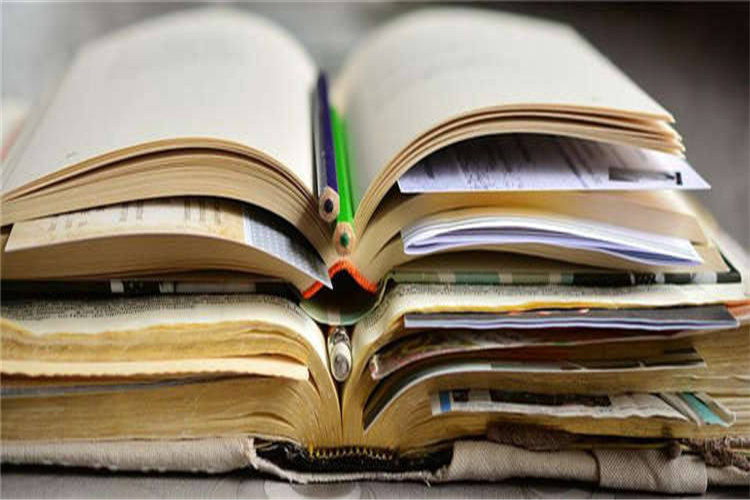2025年5月,毕赣执导的第三部长片《狂野时代》(Resurrection)在第78届戛纳电影节首映并获评审团特别奖。今年 11 月正式上映后,这部沿袭毕赣式长镜头、时间错置与梦境质感的电影,再一次让观众站在了评价光谱的两端:有人赞美它诗意丰沛、沉醉于影像记忆;也有人认为它晦涩、空洞、炫技而失魂。
在采访中,毕赣也曾谈到,《狂野时代》的创作是“关于这片土地的我的带着某种虚构的编年史”[1]。他也曾回应观众给出的“难懂”评价称:“这部电影,它里面有很多朴实的感情”[2],而《狂野时代》是“通过电影的语言去触及到人们心灵的故事”[3]。那么,在毕赣对于电影媒介的美感与精神意图的强调之内,在影评人的“元电影”盛赞之外,《狂野时代》为何在广泛的电影观众之中反响平平?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毕赣的前作,理解其作者身份、市场期待与影像风格之间的张力;而后,我们将走进《狂野时代》的六个章回,看它如何试图通过“五感六识”构建一套感官诗学,又为何最终停留于影像模拟、而非真实经验本身。
一.从“荡麦”出发
1989 年出生于贵州凯里,2008年考入山西传媒学院主修电视专业,2015 年凭《路边野餐》(Kaili Blues)一举成名的毕赣,至今仍被视为中国最具作者气质的年轻导演。
《路边野餐》这部仅凭约20万预算、几乎全部由素人出演、是导演长片首作[4]的电影,大胆地使用了42分钟的长镜头,斩获了包括2015年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国际影评人费比西奖、亚洲电影观察团推荐奖、2015年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当代电影人单元最佳新导演银豹奖以及2016年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度青年导演奖等在内的多项国内外大奖。据毕赣自己说,片中的虚构小镇“荡麦”,在苗语的意思是指“不存在的地方”。2016 年,毕赣以及几位当时与他合作的影人,一起创立了荡麦影业。
首作打下梦境与乡土交织的基础之后,《地球最后的夜晚》(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 2018)是毕赣获得充足制作投资后的一次再尝试。2018年12月,影片出品方打出“一吻跨年”的营销口号,最终获得了高达1.59亿人民币的预售票房。然而,由于影片与大多数普通观众的观感不符,许多并非文艺片受众的观众评价此片“沉闷无聊、不知所云”。随着影评反馈走低,排片和票房也开始缩水,毕赣第一次正面撞上了大众市场的期待。
暂不论奖项和票房成绩,这两部前作,已然奠定了毕赣电影的独特个人风格:游移的长镜头、松弛的叙事节奏、西南山区的地方文化感、充满记忆与诗意的影像细节、对现实与幻象的探问……
显然,《狂野时代》吸纳了更大的投资,也拥有了更大的叙事野心。毕赣走出西南,也突破了一次返乡长度的叙事时间,将作品升级为了我们眼前的这场160分钟的豪华造梦。本片上映后引发的争议,并非孤立失败,而是毕赣风格与市场预期冲突的又一次爆发。
二.“元电影”的探索与失落
1.五感六识
在今年5月的《Variety》采访中,毕赣透露这部通过“电影怪兽”展现百年影史的作品构思是:“我想将灵界拆解为六种元素”[5]。这六种元素,即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以及心智,亦可被理解为佛教的“六根六识”概念:“眼”对“色”(视觉)、“耳”对“声”(听觉)、“鼻”对“香”(嗅觉)、“舌”对“味”(味觉)、“身”对“触”(触觉)以及“意”对“法”(心智)。据此,《狂野时代》搭建起全片章回结构,分别对应六元素,讲述了六个故事。
虽然电影最直接、最核心的感官通道只有视觉和听觉两种,但电影艺术自诞生以来,就一直试图通过视听刺激,调动观众的“跨感官知觉”。
在《狂野时代》的五感六识流转中,我们可以看出,毕赣对电影何以“跨感官知觉”的理解,大致有以下两重:一方面,他遵循“电影调动感官”的因果关系,把电影当作声光技术的物质范畴来精心雕刻——布光、置景、景深、镜头的浮动、声效的远近与大小、剧情中的人物设定、叙事中的知觉涉入,都被放大为感知事件;另一方面,他也试图反转“电影调动感官”的因果关系,将感官作为生成影像逻辑的方式,来有机地组织整个电影的世界。
然而,问题在于,以上两方面的尝试中,只有第一个方面的尝试大致获得了成功。而第二个方面的失败,也摧枯拉朽地引发了《狂野时代》被盛赞为“元电影”,但却连最基本的“自反性”都无法达成的失败。
电影开篇,由舒淇饰演的手持着照相机的“大她者”,发现了由易洋千玺饰演的“迷魂者”。她将其从烟馆的地下囚室与药物成瘾中解救,并将胶片装回他体内锈蚀破损的胶卷仓,开始与其共同重返影像的百年。时间设定于电影技术诞生初期的1880s-1890s年代,在这个代表“视觉”的故事中,无声的影像与台词字幕,将电影还原为纯粹的“移动的图像”(“moving pictures”,这是电影早期最普遍、最具历史性的通俗名称之一)。此举不仅致敬了早期默片,更通过甫一开篇就进行的感官剥夺与还原,为影片其后对于跨感官知觉的唤起积蓄了能量。
第二个到第五个故事,分别对应着“听觉/耳”、“味觉/舌”、“嗅觉/鼻”、“触觉/身”的主题。其中,由赵又廷饰演的情报机关军官、由陈永忠饰演的“苦妖”、由郭沐橙饰演的小女孩以及由李庚希饰演的“吸血鬼”少女这几位章节主角,通过各自对于音乐的执迷、对苦厄的超越、对嗅觉的灵通以及对身体亲密的渴望,也一一展演着对前述感官主题的极致追寻。
人物特性与行为动机的设定之外,《狂野时代》也尝试通过极致的技术工程,来转化、传递视听之外的感受。比如,军官刺杀“迷魂者”、刺破其后背皮肤后,漫溢出的不是任何形式的血液或肉体,而是他所渴望的音乐——此处,“迷魂者”身体洞开的刺目眩光,以光的亮度转喻了那音乐的纯粹、激烈。
而在佛寺故事中,被斩首的佛像是苦、大雪夜是苦、“苦妖”化形的那个被儿子用发芽的土豆杀死的父亲也是苦。在父亲生前的长鼾中,弑父的子在雪地上搬弄破木板摆出“甘”、“苦”二字,“苦妖”也用手指划开繁茂的浮萍:本质非人的妖,以艰难年代中不幸离世的人的面目,重写着人的“甘”“苦”。
随后,在“特异功能”小女孩嗅闻被焚毁的信、“吸血鬼”少女饱尝爱人的血时,我们或许都共感到了那穿越时空的余烬的味道、恋人的体温。
幕间,“大她者”的旁白勾连时代。随着白烛行将燃尽,“迷魂者”穿越百年,故事进入最后一个“心智/意”的章节,电影的时间也再次塌缩回返,续接到第一个故事。“大她者”将奄奄一息的“迷魂者”身体梳洗、擦净,并再度为其穿上“怪物”的皮囊,将其推入了远看似宫庙为逝者点燃的长明灯、近看则是集成电路板环绕的巨大装置之中。
然而,为何这种感官诗学最终沦为影像模拟、而非真实经验?
2.谁的感官
全片落幕,银幕上,蜡制的影院与观众席渐次燃烧殆尽,归于空无。
这似乎也正是对《狂野时代》整部电影意义表达的简明概括:这是一部充满了技术执行细节,但内在极其空洞的电影。
乍看之下,它的确像是一次对“感知的本体”的回归,但细究不难发现,五感在这里并不是“生产意义的方式”,而只是被贴标签的主题对象:在这个极尽诗化的“狂野时代”里,每一个人物、每一个物品、每一个场景,都被视为纯粹由影像创作者创造、被他控制、受他调遣的非生命的元素。在这种“非生命”的底层逻辑之上,反转“电影调动感官”的因果关系、将“感官”作为生成影像的有机方式,也就变得不再可能。
这部看似如梦似幻,反对电影工业刻板的功能主义的电影,其实正是最刻板地执行着功能主义:似乎当电影需要“人性的复杂”的时候,它就创造一个热爱音乐的男性间谍;当它需要天真的时候,它就创造一个儿童;当它需要艳情的时候,它就创造灯红酒绿中的女性……在人的旁边,所有的物,也都被作为纯粹的景观,而不是被珍重地表现——物因此不再能够成为人居、人思的涌流,遑论超越人之所限、推动视听的边界?正因这种肤浅的恋物,每个场景才都那么刻意,饱含了“此幕必出片”的流俗艺术决心。
在单个章节的人物的刻板、物的刻意之外,唯二穿越并连接着不同时空的“大她者”和“迷魂者”角色,也没有建立统一的感官逻辑。比如,ta们是如何感受并理解肉体的痛苦与死亡的?ta们又是如何体验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来自叙述者视角的知觉匮乏,也就意味着,无论通过哪个人物、哪个故事、哪个时空的切口,观众都无法更具身地共感人物的身体、时间经验或情感世界。
或许可以说,电影可能涉及或唤起的共感体验,皆被扁平化了。更进一步说,影片中的感官体验也仅仅是被影像化了,从未真正被创作者问题化,即反思“虚构”影像如何挑动知觉,创造并构成新的“现实”。
在《狂野时代》中,那些本就并不丰富的感官体验,依然仅仅是电影“奇观化”的对象,而不是被质疑的生产机制。例如,在诸多视觉段落中,长镜头与景深的炫技并没有反思“看”如何发生,只是展示“如何被看”;而在细密的声音工程处理中,配乐与噪声的使用,依然仅仅是在强调情绪,但没有把声音当作叙事结构的绝对主体。与之类似地,味觉、嗅觉与触觉的段落中,所呈现的是依然仅仅是“可视化的”味道、气味与触感,并未意识到“知觉必然要被视觉建构”这一矛盾,也未让这种矛盾推动电影去反思电影本体“无法表述的限制”。
换句话说,它错过了最根本的“元电影”问题:“电影作为技术媒介,如何生产世界?”
“元电影”,并不是“致敬电影史”或“玩电影梗”的同义词,它也不是“拍一个关于电影的故事”。真正的“元电影”是对“电影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哲学思辨,其核心关键词是自反性(self-reflexivity)。“元电影”意味着:电影意识到自己是电影,并把这种意识纳入叙事结构与观看机制,让观众意识到影像控制、电影语言、观看行为本身都是被构造的,从而让观众对影像如何生成、如何虚构现实、如何观看与被观看、如何创造消费并被消费,以及作者/电影如何瓦解并创造全新的权力关系等产生认知与质疑。例如,费里尼的《八部半》(8½, 1963)让导演的创作困境成为电影本身,模糊了艺术与现实的界限;哈内克的《趣味游戏》(Funny Games, 1997)则通过角色直接与观众对话,迫使观众反思自身的观看行为和道德位置。
可《狂野时代》不问,也不回答,只是在把“元电影”做成“影像拼贴”。其中,人物没有真正的身体经验、场景没有真实的历史感或社会性,这种由“影像记忆”而非“人类经验”构建的影像世界永远不是真实。因此,其五感六识也就不是人物的感官,而是摄影机的感官;这摄影机的感官,亦绝非属于真实世界,而是属于影史与影像传统——这部电影呈现的不是“感官世界”,而是“影像可能创造的感官世界”,其“元电影”也就依然仅是“永恒的影像梦”。
这种内部循环的感官系统,将影片锁死在“影像引用”本身的世界里,于是:它无法成为“元”,因为它连“走出影像”的尝试都没有。真正的“元电影”,肇始于影像与现实发生摩擦,而不是只是跟影史发生摩擦的时刻。
三.“大她者”、“梦”与“给电影的情书”
《狂野时代》的空洞,不止于叙事的空洞、表达或意义的空洞,也不止于托物言志的政治的空洞。它的失败,也不止于故事的失败或意义的失败。它的空洞,本质上是一种缺乏谦逊的空洞。
1.从“大他者”到“大她者”
一开篇,电影就宣称舒淇是一位“大她者”。这替换了拉康原词“大他者”的性别代词,那么,这个“大她者”是否体现了原概念的意涵广度?又是否为其增添了任何新的、任何出于不同的性别意识的意涵?
拉康的“大他者”(l'Autre)理论,是理解主体欲望和文化秩序的关键。简单来说,“大他者”代表着一个社会共识、一套看不见的结构性规则,是语言、法律、道德、意识形态等象征体系的中心组织结构,正是它作为主体身份、意义和法则的保证者,规定了我们如何思考、如何行动。在电影研究的语境中,“大他者”的运作既体现于镜头语言、观众位置、叙事规则、视觉快感的生成之中,也型塑着电影的生产与观看机制背后的复杂权力结构。
在拉康之后,以露西·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为代表的一些法国女性主义学者,从女性主义的角度重写了“大他者”概念,认为“大他者”不是一个中性的象征秩序,也不能诠释中性的主体经验,而是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结构化的语言与权威体系。
在《狂野时代》中,由舒淇饰演的“大她者”捕获了“迷魂者”,并半强迫、半祝福地与之开启了随后百年的影史漂流,这似乎体现了“大他者”作为主体结构前提与意义来源的概念意涵。然而,当“大她者”只是被当作了章节间的承上启下的小标题,这一形象的强力也就不再可信。
通过性别代词的替换,“大她者”的确向我们提供了一种承续此种女性主义批判的可能。然而,通览全片,我们很难指认存在任何一处试图批判父权制结构化的语言与权力体系的情节。相反,由于“迷魂者”形象始终鲜明地呈现出一个“男性”的性别,电影中的主体经验也就几乎完全通过这一男性角色的情感与记忆来组织,而作为“大她者”的女性,只是这些感官的触发器。通过这种没有深度的直接宣称、没有考量过的后续角色塑造,《狂野时代》中的“大她者”形象,或许只是概念噱头罢了。
2.电影的“造梦”与毕赣的“迷魂”
《狂野时代》试图将梦寐与历史对应、融合为一个新的“梦—现实”的阈限空间。在前文,我们已经解析过电影的一些灵光,此外还有未曾提及的:第一个故事中使用了模拟早期电影剪切、遮罩和拼接胶片的技术,来构建烟馆的空间;在触觉故事中,由深夜过渡到黎明时分的固定镜头,实际上压缩了背景中露天放映的《水浇园丁》与叙事中角色所经历的黑夜这双重的时间。我认为这两处都是对于毕赣所着迷的技术的恰当运用,也是对于梦的质地的动人表达,从中得见毕赣对技术执行的投入,对“裂隙”“通灵”“迷梦”等诗意元素的偏爱,以及他对形而上、对生命和时间的界限的探问。
但在对探问的热情中,他选择了“梦”这个载体,却误解了“梦”与“迷魂”的真实意义:他误以为“梦”(以及“元电影”)是非时间、非空间的;因此,他更误以为,只要复原一个时代特色浓厚的场景,并在其中错置时空,就可以抵达“梦”、抵达对于现实的超越。
但事实并非如此。“造梦”的电影,不是“非时空”、“无意识”、“纯虚构”,而是精准的时空被刺破以后产生的裂隙,是无意识自行涌流,并创造了不可完全被语言概括的、不断生成的新现实。而《狂野时代》里的时空只是拼贴式的随意堆叠、只是没能经过更细致的意义与道德打磨的粗糙虚构故事。而真正的“元电影”恰恰是因为作品自身具有非常细腻、精准、真实的时空坐标,才可以戳破那个坐标的原点,穿梭和连接更广袤的事物与时空,才可以成为“元”。
于是,纵览全片,那些偶尔的灵光,不断被随着故事逐个递进而增强的造梦者的自我神话、语焉不详的政治冷感冲散。于是,电影越来越沦落为一个“造梦者”不断展示自己的技术狂热、不断炫耀自己掌控“电影—梦境”的一切的权力的舞台。“电影—梦境”、“梦—现实”都被驯化、被解释,最终失去了它们自身的自主性和超越语言的深邃感。
如果创作者试图返归电影的元点,真挚地为Ta人“造梦”,那么,其作品的最低预期,就是创作者应当如实表达自己也受到了这种来自梦的、来自电影作为造梦的过程的“迷魂”——一个造梦的神,也不得不承认:正因梦是自行其是的,因此,自己并不完全掌控梦,而是正在反向被梦迷住。而《狂野时代》最致命的空洞和失败之一,正源自于失去了这种必要的谦虚。
3.给电影的情书还是给“荡麦”的情书
毕赣的困境在于,他既想获得商业成功,又想将电影当作纯粹的、自足的“文化遗产”来供奉。而如果说,通过将电影史当作一种可被展示的“遗产”,即影史可以被复刻、被致敬、被制作成视觉拼贴,而非进行针对电影本身的哲学反思,《狂野时代》没能成为一封写给电影的情书,那么,这部电影究竟对谁寄出了情书?
在佛寺故事中,落在雪地上的火柴盒上印着“荡麦”,吸血鬼故事中,“迷魂者”电话点歌,打给的点歌台也是“荡麦”。由《路边野餐》中的虚构小镇“荡麦”出发,毕赣似乎又转回了他虚构的原点,即他私人的象征体系。
一方面,将创作者本人不断发展和探索的意象嵌入到电影之中,本是打上作者电影水印、开启更广阔虚构空间的手段。但另一方面,当整部电影的虚构都失去了对真实的残酷探问,所有的意义都在空洞叙事中消磨殆尽,而故事在火烛的焚烧后皆沦为时间的灰烬……这种对私人符号的不断回溯,是否表明创作者的重心已经从“电影作为技术媒介,如何生产世界?”(元电影的真正命题)退缩到“如何用电影技术重现我的私人世界?”(私人符号的自我循环)。而电影寄出的这份“给荡麦的情书”,又是否沦为了一种自我指涉的迷恋与加冕?当创作的激情,多数投入于对“我的世界”的复刻与展示时,这种自恋,最终必然导向其自身的枯竭与崩塌。
最后,在生产了长达150分钟的怀旧影像之后,《狂野时代》再次打出直白的文字宣言: “这场幻梦已经崩溃!”
但即便面对着短剧的崛起、人工智能技术的铺开、受众群体的变动,电影也并没有崩溃、更不会崩溃。
只有当一种艺术形式沉浸在已逝的荣光、执迷于对其瓦解的霸权自我的哀悼的时候,这种艺术才停止了自臻、才会开始崩溃。只是毕赣所迷恋的古老电影的遗像,正因他不断将感官、主体、议题主题化、符号化、视觉化乃至自我神化,而逐步崩塌:它渐次遭遇无意义的大火,沦为时间的灰烬,并缓慢而彻底地失去了艺术的灵光。
《狂野时代》确乎是场疯狂的“造梦的艺术”,但它同时也沦为了作者私人的象征体系,是“没有生命的影像之景观”。这个横跨百年的梦,不是林奇式的梦、不是塔可夫斯基式的梦,甚至也不再是《路边野餐》的梦。在这场大梦崩溃以后的瘴郁里,毕赣可以再次带领我们重返野餐的道路吗?
注释:
[1] https://www.sbs.com.au/language/chinese/zh-hans/podcast-episode/miff-2025-bi-gans-resurrection-explores-the-soul-of-his-homeland/jkfy6hb0j?
转载请注明来自研顺网,本文标题:《《狂野时代》:毕赣的影像梦,为何不再迷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