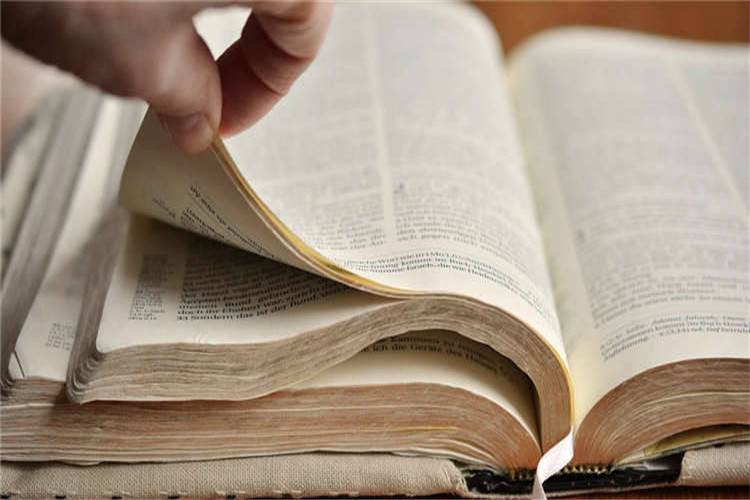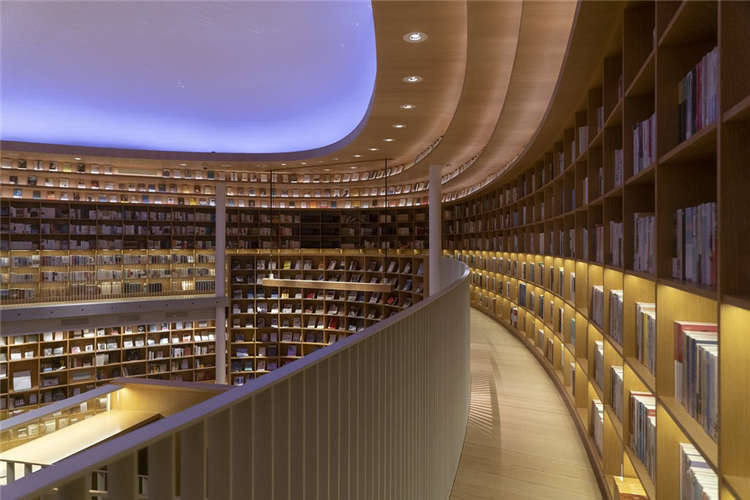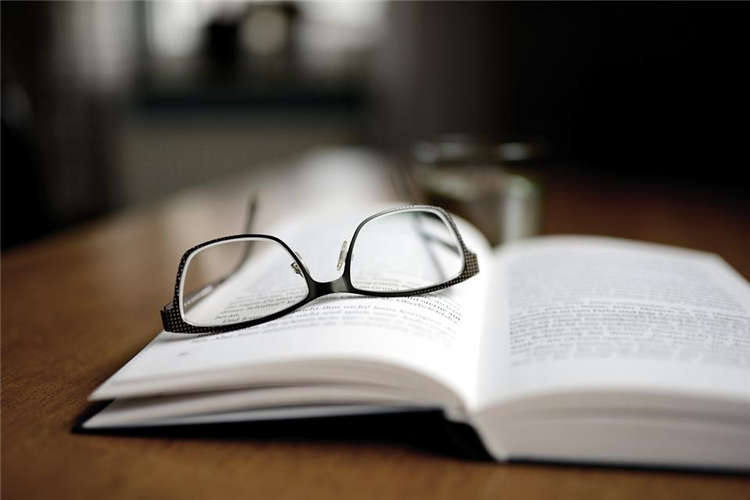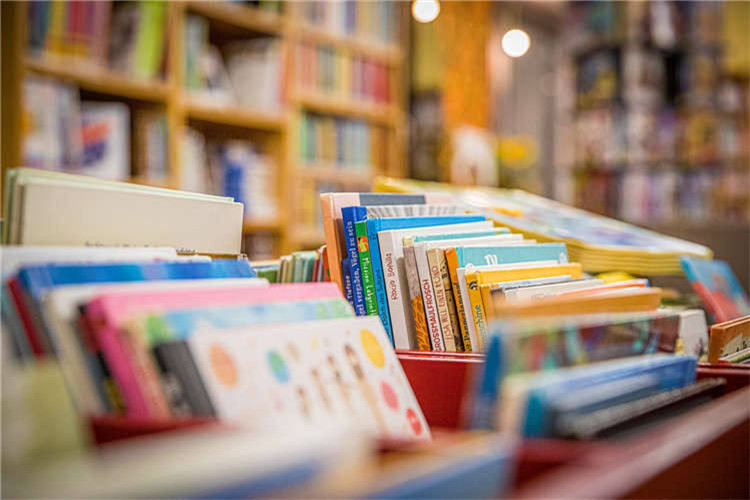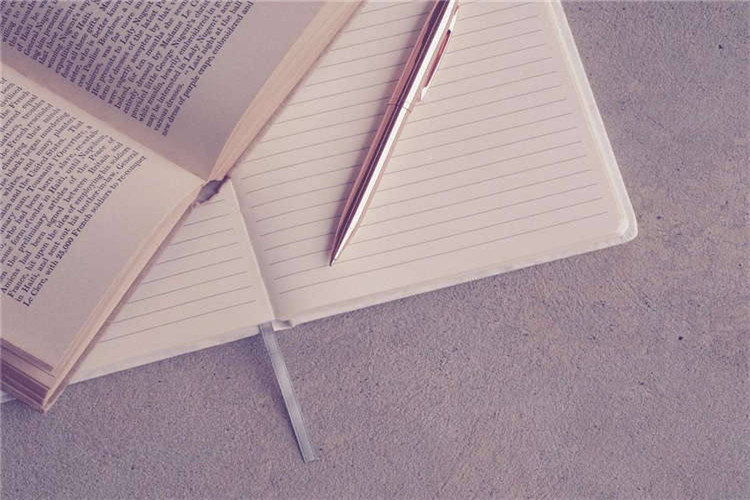2022年5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长安区贾里村安置小区项目用地发现一处唐代董氏家族墓地,其中编号为M235的墓葬出土了《张府君夫人董韶容墓志》。这块墓志呈正方形,长38厘米、厚5.5厘米,属于一个二十八岁的妇女所有。志文只有320字,除了记载家世、品行、婚姻之外,并无特殊之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墓志却在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可谓一石激起千重浪。
《张府君夫人董韶容墓志》志石拓本(约三分之一),来自《陕西西安唐董韶容墓发掘简报》
《考古与文物》2025年第9期发表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西安唐董韶容墓发掘简报》,认为张府君是盛唐宰相张九龄,董韶容是他的妻子。《收藏家》2025年第9期发表史晟《唐张九龄之妻董韶容墓志的个人解读》一文,认为董氏由玄宗赐婚而嫁给张九龄,《望月怀远》和《感遇十二首》等诗可能为怀念董韶容而作。2025年10月13日《中国唐史学会公号》发表会员赵帅淇的文章《新出“张九龄夫人董韶容墓志”献疑》,质疑董韶容的身份,该文认为董氏是妾不是妻,因为张九龄有妻谭氏,一直在老家侍奉张母,张九龄卒后十年才去世,享年77岁。紧接着10月17日“从长安到周边”公号又发表《董韶容身份问题》一文,再次重申“董氏就是妻”的观点,认为是并妻。结合唐代史实,董韶容的丈夫肯定是盛唐时期的张九龄无疑,但她到底是不是张九龄的妻子呢?
多年以来,我一直浸淫唐代妇女史研究,整理并研究过大量的唐代墓志,对唐代墓志中所载在室女、原配、继室和妾,以及比丘尼、女冠也分别做了研究,因此对这个新出的《董韶容墓志》非常感兴趣,对其身份争论问题也非常感兴趣。经仔细研读志文,结合唐代历史文化和我自己的研究,我赞成董氏是妾的说法,但她很可能是别宅妇性质的妾,她不能与张九龄同赴荆州,并且卒于宣阳坊与其别宅妇的身份密切相关。
一、董韶容是妾而非妻
作为开元盛世时期的宰相,张九龄在新旧《唐书》中都有传,但限于正史的体裁,仅记载传主生平和主要仕途履历。关于其一生经历,不仅很多内容语焉不详,而且没有丝毫个人生活信息,很难窥见其情感经历。幸有顾建国《张九龄年谱》对其一生考证精详,为研究张九龄提供了非常清晰的时间脉络,本文即依据此年谱来考察张九龄与董韶容的关系。本文认为董昭容是妾而非妻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唐代法律禁止有妻更娶
持董韶容为妻的观点主要根据是墓志称董氏为“故妻”。他们认为如果董韶容没有妻的身份,墓志不敢明目张胆地这么写,至少张家的人会表示反对。另外,有学者还认为,张九龄很可能也回到长安参加了丧礼。不过,据张九龄碑记载,始兴老家有嫡室谭氏,所以持此观点者认为董氏应该是并妻,即民间所说的“两头大”。我认为上述这些分析是站不住脚的。从法律层面上看,在嫡室妻子健在的情况下,另娶嫡室是违法犯罪的行为,不仅要判离异,还会处以流放之刑。《唐律·户婚》规定:
诸有妻更娶妻者,徒一年;女家,减一等。若欺妄而娶者,徒一年半;女家不坐。各离之,疏议注:“若欺妄而娶,谓有妻言无,以其狡诈之故,合徒一年半,女家既不知情,依法不坐,仍各离之,称‘各’者,谓女氏知有妻、无妻,皆合离异”。
《唐律疏义》编定于高宗时期,是唐代管理社会的规矩准绳。五代宋元几个时期都沿袭了唐律的法律条文。明清乃至近代社会,一夫一妻则是婚姻传统,妻死可以再娶继室,但不能扶妾灭妻,也不能娶并妻。当然,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在高门权贵阶层,在礼法疏离的社会底层与边远地区,如果原配无出,男子娶并妻、扶妾为妻的现象也是多见的。然而,进士出身的张九龄饱读诗书,且为人正直、重视礼法,他不但婉言拒绝了玄宗欲召其兄弟入京为官的好意,也不怕得罪武惠妃而反对玄宗废太子李瑛,况且还有嗣子张拯,如何又会违反法律和礼法另娶并妻?当然,唐代也有并妻的情况,但主要是受北朝影响,发生在初唐,时经战乱,夫妻长期离散,男子有另娶者,特殊情况特殊对待。而张九龄生活在开元盛世,又是朝廷高级命官,无论从个人形象来讲,还是从其本身的道德修养来讲,他应该不会娶并妻,他娶的只能是妾。
至于张九龄或者张家人可能参加了董氏丧礼之说也完全经不起推敲:张九龄外放荆州是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四月二十日,董氏卒于四月二十六日,五月十一日入葬。据《张九龄年谱》考证,张九龄五月八日才抵达荆州,如何能返回长安参加葬礼?另外,受张九龄连累,张九龄的两个弟弟九皋、九章也被外放,长安恐怕也没有能主事的张家人留在长安。所以董氏的丧事是由董家人张罗,想写什么怎么写完全是由他们做主的。
(二)董氏没有命妇封号
本文反对董韶容是妻的说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董韶容没有命妇封号。命妇制度是传统社会“夫贵妻荣”思想的具体呈现,朝廷会根据贵族男子的身份地位,赐给他们母妻一定的封号。有封号的贵妇则称诰命夫人。虽然汉晋以来上层社会的一些妇女会有封号,但封赠妇女成为制度则始于唐代。唐代命妇制度分为内命妇和外命妇两种。内命妇指的是宫廷以内的嫔妃,又称为“内官”,外命妇则指的是宫廷以外的命妇,包括一些公主、王妃等。《唐六典》规定:
外命妇之制,……一品及国公母、妻为国夫人。三品以上母、妻为郡夫人。四品母、妻为郡君。五品、若勋官三品有封,母、妻为县君。散官并同职事。勋官四品有封,母、妻为乡君。
根据志文“一嫔丞相,七载妇仪”的说法,董氏应该在开元十九年(731年)夏秋之际与张九龄成婚的。虽然此时的张九龄并没有成为宰相,但也担任了秘书监,是从三品的官员,若是并妻,董氏此时就应该成为诰命夫人。几年后张九龄做了宰相,成为正三品,董氏更应该是诰命夫人。董韶容墓志敢称“故妻”,如果真有命妇封号一定会写上。未写封号,就是因为没有封号,没有封号,则说明她没有正妻的身份。
(三)玄宗不可能赐婚张九龄娶并妻
董氏出自陇西,与关陇集团有一定的关系,而且董氏家族的女人进入皇宫成为妃嫔的不止一个。故主张董氏可能是并妻的学者认为董氏出身高贵,且当时还有女性亲属在后宫做贵妃,张九龄娶董氏很可能是玄宗赐婚。如果真是皇帝赐婚,董氏作并妻的可能性是不容置疑的。然而事实真是如此么?
唐玄宗时的确有一个董姓贵妃,她的家族墓地就在西安市长安区神禾塬的贾里村,董韶容墓志中提到的“椒掖之亲”应该就是这位董贵妃。董韶容嫁给张九龄应该是她从中穿针引线,唐玄宗可能也知道这事,也会表示赞同,即“承纶言之娉”,但并不一定会赐婚。首先,董氏家族的门第并不高,连三四流都算不上,在关陇集团中也属于边缘。董氏家族的男子在仕途上的作为并不高,入宫的女子也并没有显赫之处,连入后妃传的人都没有。尽管董贵妃名位不低,但她是玄宗做太子时的良娣,也许玄宗做临淄王时便跟了他,凭资历熬到贵妃,何况开元十九年时她已经年老色衰,唐玄宗会待之以礼,却不见得对她言听计从。所以玄宗不会反对董韶容嫁给张九龄,但不一定会出面赐婚。
唐董韶容墓地理位置示意图,来自《陕西西安唐董韶容墓发掘简报》
其次,唐玄宗本身对高宗、中宗时期礼仪纲常有失常序的现象是非常不满的,也不可能赐婚让董韶容作并妻。中唐以前,上层妇女悍妒现象比较严重,以致上层社会的男子多有娶别宅妇者。所谓别宅妇其实是小妾,只是不与主妇共居一个屋檐之下,有自己的仆从婢女,俨然一家庭主妇。因为不合礼法,朝廷官员纳别宅妇被视为违规,一旦被抓获,男主则被贬谪,女主则受鞭刑并没入掖庭为奴。武则天时期阴盛阳衰,官府对朝廷命官偷娶别宅妇行为的打击非常严厉,偷娶别宅妇的罪名也成为诬陷打压政敌的手段。唐玄宗即位之初依然沿袭这一政策,颁布《禁畜别宅妇人制》:
帝王之政,必厚风俗,男女不别,深蠹礼经,至如别宅妇人,久未悛革,近今检括配入掖庭,将示小惩,使及知禁。……自今已后,更有犯者,并准法科断,五品已上,仍贬授远恶处官,妇人配入掖庭。纵是媵妾亦不得别处安置,即为常式。
尽管这一严厉搜捡别宅妇的政策在众多大臣的反对下被取消,但玄宗坚持嫡庶分明的态度很是鲜明。另外,自打王皇后去世之后,尽管他先后宠爱武惠妃和杨贵妃,却从来没有真正打算立这两位爱妃为皇后。尽管他惑于武惠妃的美貌和李林甫的奸计,将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废为庶人,但毕竟能够听从大臣的劝阻没有立武惠妃为后,也没有立武惠妃之子为太子。在开元二十年(732年)以后,武惠妃谋划废太子瑛而立自己的儿子,玄宗一度曾经动摇,却被张九龄劝阻。《董韶容墓志》的出现及其与张九龄的关系,说明董氏家族很可能参与了此事。张九龄被外放荆州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旧传》所云“九龄为相,荐长安尉周子谅为监察御史。至是,子谅以妄陈休咎,上亲加诘问,令于朝堂决杀之。九龄坐引非其人,左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不过是借口而已。玄宗怎么可能赐婚张九龄让董韶容成为并妻呢?
二、董韶容是别宅妇
毫无疑问,董韶容的丈夫是张九龄,她在二十一岁时嫁给了五十四岁的张九龄[1]。婚后七年,张九龄被外放,没有带她一起离京,她因此病故于宣阳坊,由此也就令人产生了许多疑惑。董韶容为什么没有跟张九龄一起到荆州去?为什么卒于宣阳坊而非修政坊的张宅?赵帅淇认为可能是“张九龄不被允许带上长安的侍妾同行,或是为了表示臣服的态度,张九龄迅速上路,未暇带着董韶容同行,所以其墓志中才会有‘驿使无容’之语。或许正是这一次的离别打击,导致了董韶容的病故。而她身亡之地宣阳坊,亦非张九龄宅地所在。在张九龄离京前后,两人之间的关系显得更加微妙。”[2]这一说法非常有道理。然而按照《唐会要》所载长寿三年五月三日敇:“贬降官并令于朝堂谢,仍容三五日装束。”张九龄临走之前是有时间与董氏话别、并给予情感慰藉的。但他为什么没有这么做呢?我认为这与董韶容的身份——别宅妇有关。
(一)张九龄偷纳董韶容
张九龄长期在京城做官主要是在开元六年(718年)之后,当时他四十一岁。《张九龄碑》说谭氏一直在老家侍奉张母,那么张九龄一人外出就职,尤其是到京城就职由谁来照顾呢?在传统社会,男子外出读书、入仕经商,把妻子留在家里照顾父母子女是很普遍的现象,唐代亦是如此。但若男子长期在外,即便没有婢妾随侍,也会在其居住之地纳妾。张家在韶州也算大户,张九龄不可能只带男仆随身服侍自己,张母也不会放心儿子一个人外出身边没有个女人照顾。唐代墓志就记载缙云郡司马贾崇璋到山西为官,欲留妻子陆氏照顾母亲,但母亲坚决不同意,反令儿媳随子出行,结果陆氏半路染疾而亡。[3]如果谭氏一直在老家照顾婆母,那么张九龄身边一定会有其他女人,这个女人可能是侍妾,也可能是侍巾栉者,不论是妾还是侍巾栉者,都应该是得到张母和谭氏首肯的。
不过,随着张九龄的年龄渐长、离家时间更长,尤其是仕途发达,母亲和妻子对他私生活的影响可能会越来越弱。开元盛世,达官贵人蓄养姬侍之风盛行,张九龄难免不受影响。但他毕竟是饱读诗书之士,加之财力所限,不可能像豪门权贵那样左拥右抱,但不对年轻美貌女人感兴趣是不可能的。董氏应该是他晚年所纳侍妾,也可能是最后一位。不过,张九龄娶董氏很可能是瞒着母亲和谭氏偷娶的,他给董家的承诺是明媒正娶,这也是墓志称“故妻”的原因。从张九龄对别宅妇的态度来看,他娶董韶容很可能是瞒着家人的。唐玄宗即位以后,一些大臣陆续上表反对搜检别宅妇,张九龄就是其中之一。开元三年(715年),张九龄上奏道:
妇女事缘卑亵,纵两县检括,有所阿容,即愿宣付宪司,纠摘其罪。今便收捕入内,别加推逐,道路有云,何急于此!……昔汉丞相府尚不按吏,诚以务在尊崇,体不可失。况天子中禁,而有此名?丞尉极微,所缘至小,固不足以尘黩圣听。虽在内曹,外议切切,未为得所,即有闻知,不敢不奏。
显然张九龄是认可别宅妇现象存在的。开元三年,张九龄三十八岁,以后仕途渐渐步入佳境。在“五男二女”为理想家庭模式的时代,夫妻仅育有一子显然是很难令人满意的。[4]然而无论正史或其他传世文献,还是他的文集和各种碑石记录,都显示张九龄谦谦正人君子的形象。若不是有董氏墓志的出现,人们至今都不会知道年近六十的张九龄居然纳了一个年轻美貌的侍妾。显然,出于某种原因,张九龄公开纳妾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以致他关注别宅妇问题,并上表反对严加搜检。再考虑到他长期与谭氏分居的事实,他纳别宅妇的概率还是相当大的。
(二)董韶容为什么卒于宣阳坊?
如果本文推测不错的话,董韶容是九张龄瞒着家人偷娶的,即便如此,有玄宗和董贵妃那一层关系,董韶容的身份也是合法的。那为什么董氏没有卒于修政坊而是宣阳坊呢?推测有以下几个可能。
第一个可能是与谭氏来长安有关。张九龄之母于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冬去世,十二月十四日,九龄受诏起复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他最晚应该在百日之后重返长安。因为侍奉婆母,谭氏不得不与丈夫长年分居,虽然分居对张九龄来说不是什么问题,甚至会觉得更自在舒服,但对谭氏来说,那是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既然婆母已经离世,她就没有必要再留在老家了。所以,谭氏极有可能与张九龄一起来到长安。如此,董韶容就很难在张宅继续待下去了,张九龄必须要赶在谭氏抵达长安之前,将她安置于外,即宣阳坊。
第二种可能是董韶容自始至终没有住进张宅。在开元八年(720年)以前,张九龄生活在长安的时间时断时续,并没有购置宅第的需要。开元八年到开元十八年(730年)之间,虽然他的仕途不断发达,大部分时间生活在长安,但母妻不在身边,也没有购置宅第的需求。另据萧昕所撰《张九皋碑》“及元昆出牧荆镇,公亦随贬外台,遂历安康、淮安、彭城、睢阳四郡守”[5]的记载,张九皋后来也到长安就职。按照唐代社会同居共财习俗,张家兄弟很可能一同居住,修政坊这个宅第也许就购于此时。九皋当然不会反对兄长纳妾,但家中人口众多,难保不走漏风声到岭南。所以张九龄很可能一直与董韶容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在宣阳坊,这个宅第很可能是以她的名义购置的。
基于以上这两种可能,一些令人迷惑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解释。一,为什么《长安志》说张宅在修政坊,而“故妻”董韶容却卒于宣阳坊?二,为什么张九龄匆匆忙忙离开长安,无暇带她一同前往。三,为什么张九龄离开长安后的第六天,董韶容便因病而亡?很可能谭氏来到长安之后,董韶容的身份一直得不到承认。董氏的存在,谭氏可能并不知情,即便知情,也可能不予承认。所以,张九龄没有在外放时带上董韶容,甚至很可能都没有跟后者话别。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以后,董韶容一直与张九龄聚少离多,且身份不得承认,自然抑郁成疾。张九龄匆匆离京,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六天之后,董韶容在长安病故。
(三)董家的不平与忿争
既然董韶容是妾、是别宅妇性质的妾,且张九龄也被外放,那董氏家族为什么还敢在亡女的墓志中写上“故妻”的名号呢?本文认为这既是董家为女儿发出的不平,也是董家对张九龄的声讨。
正如前文所言,张九龄纳董韶容时可能承诺的是明媒正娶,或者承诺以并妻的待遇,所以才会有宣阳坊的购置。董家虽然知道原配的存在,但原配远在老家,妻妾双方各自安好。只是没有想到,谭氏在开元二十二年之后也来到长安,董韶容不但不能与张九龄在一起,而且其身份始终得不到承认。雪上加霜的是,张九龄外放时对董韶容没有任何交待,致她病情加剧,不治身亡。董家肯定为女儿感到不值,也会怨恨张九龄,难免不会在墓志中表达不满,写上“故妻”字样。
有学者认为,不是妻却写妻是否有违礼法?当然是有违礼法的。不过,唐代刻写墓志的风气很盛行,但除了五品以上的官员之外,唐代官府并没有对墓志书写内容作过规定,也没有检查的条例。撰写墓志通常是丧家所为,写什么、怎么写都是个人行为。除了记录逝者生平之外,通常以溢美之词为多,同时也会在墓志中表达一些特殊的情感。或是对人生境遇的感叹,或是对某事的不平。比如李绛的儿子李顼与妾章四娘欢好,致明媒正娶的卢氏年纪轻轻卒于母家,其叔卢商撰《李公夫人范阳卢氏墓志铭》云:“何幼妇之令仪淑质,蕙心玉德,慈和懿节,孝敬柔则,与是具美而不假年?吾不知其所问!”[6]颇有声讨之意。风流浪子韦肜游历卢龙镇时娶了殿中侍御史李子千的女儿李昭。后来回家省亲,说好秋天返回,“当修礼归于夫族,既而过期不至”,致使李昭积郁成疾、产子不育而亡,韦肜居然闻丧不来。李昭非常生气,于志文大骂“夫不莅妻之丧,春秋之义,肜当贬也”[7]。
既然张九龄不可能赶回来参加董韶容的丧礼,张九皋兄弟(九章很可能后来也在做京官)也受兄长连累离京外放,谭氏此时可能已经离开长安,张家留下看房子的仆从大概率不会多管闲事。另外,墓志刻写完毕之后随死者一同入葬,写的什么只有董氏父母和刻碑的人知道,董家父母自然不会对外四处宣讲,刻碑的人也会遵守行规保持缄默。深为女儿感到不平的董家,只能通过“故妻”的书写来告慰亡女,为她在阴间争一口气。
综上,董氏不可能是张九龄的妻子,而是妾,且是没有登堂入室的别宅妇。
1288年前,随着董韶容墓志被埋入地下,董韶容的一生被画上句号,盛唐宰相张九龄的一段情感经历也堙没于历史的红尘。我们今人惊喜于墓志的发现,是因为我们窥知了张九龄不为人所知的“私情”,同时也从中获悉了张九龄被外放背后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在我们感到欣喜的同时,是否感受到董韶容内心的悲凉。一个将七年青春错付的姑娘,却以这种悲凉的方式永辞人生。尽管董韶容有皇戚的虚名,但夹杂着政治、礼法、门阀和显贵的因素,注定了她无法公开得到张家的承认。董韶容生前无法登堂入室,死后不能进入张家祠堂,连姓名亦不能载入族谱,只能归葬娘家祖坟。我们不知董韶容为何选择了这位鬓发已苍的张郎君——慕其才名?迫于生计?还是无法选择?史册吝啬,未载她姓名家世,若不是有墓志出土,我们根本不知这位“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的贤相,暮年时期还有一段“秘密”恋情。然而,对张九龄这般以清流自持的显宦而言,董韶容不过是他晚年的慰藉;但对董韶容而言,张九龄却是她人生的全部,她的结局足以令人唏嘘。或许,这正是历史与人性的幽微之处:庙堂上刚正不阿的贤相,私下也亦有情感的软弱与矛盾;而盛世的光辉之下,亦掩藏着无数个体,尤其是女性的时代悲剧。
注释:
[1]张九龄的卒年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正史中的享年六十八,一种是墓志中的享年六十三。本文采用墓志的说法。
[2]赵帅淇:《新出“张九龄夫人董韶容墓志”献疑》,“中国唐史学会”公众号2025年10月13日发文。
[3]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天宝200《唐缙云郡司马贾崇璋夫人陆氏墓志铭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671页。
[4]无论《张九龄墓志》《张九龄碑》还是《旧唐书》《新唐书》都显示张九龄只有一子张拯。
[5](唐)张九龄:《张九龄集校注》卷四“初秋忆金均两弟”,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27页。
[6]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和03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911-912页。
[7]赵君平,赵文成:《秦晋豫新出土墓志蒐佚》《唐李子千亡女李昭墓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第7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