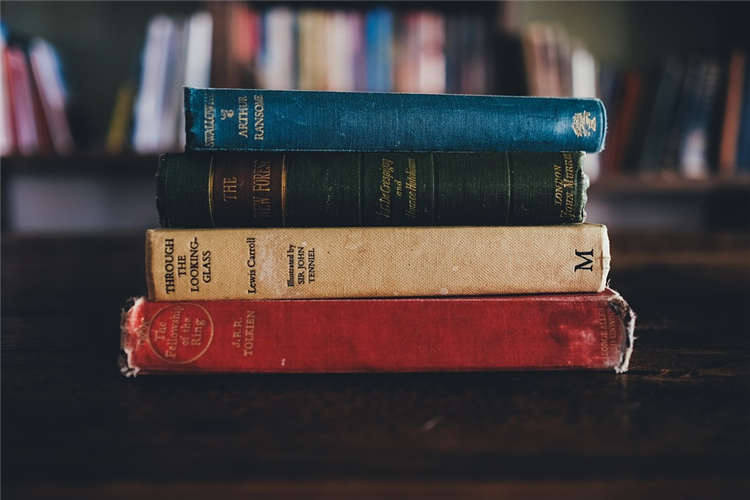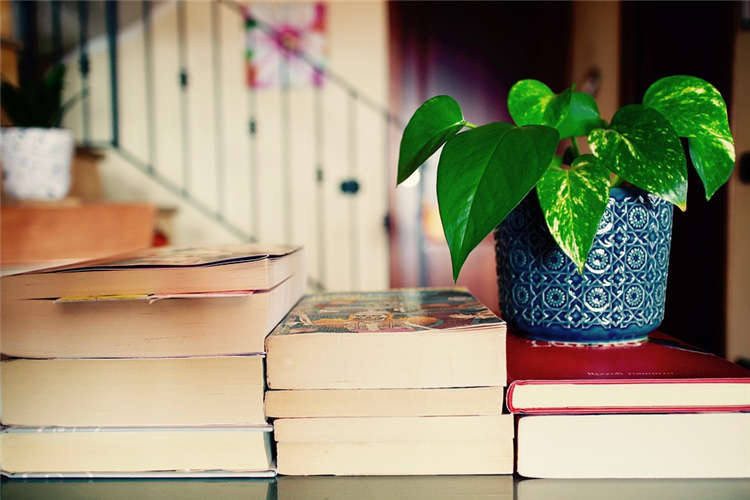在一段历史时期,我国城镇实行“福利分房”制度。“茅盾文学奖”得主陈彦的最新长篇小说《人间广厦》就聚焦于这一时期,这部小说从西京文化艺术研究院福利分房的“最后总攻时刻”开始,通过九十八套新建住房的分配,揭示利益博弈、文化人的挣扎及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值此书出版,“安得广厦,何以栖居?——陈彦长篇小说《人间广厦》新书发布会”在京举办,嘉宾们围绕小说讲述的分房故事探讨了人性、知识分子品格、传统文化等话题。
现场
陈彦,是作家与剧作家。他的《主角》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装台》获首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
谈起《人间广厦》的写作缘起,陈彦谈起了自己早年为分房而煎熬的经历,不过他坦言,这个小说写着写着也就不是一个单位分房的事了,他想以分房为切入点,书写人物的命运,探讨人何以栖居。
“《人间广厦》是对一个微观单位分房事情的延展,让它尽量辐射到城市、乡村的不同角落,甚至进入历史的‘掩埋’深层,去看有关生命安居与精神栖息的不同维度、面向,从而也为沉闷的人生现实的物欲、物役、物累、物困,打开一点减压的阀门。”陈彦谈道。
小说中,艺术研究院的知识分子们本应专注于艺术,却在分房过程中展现出各种世俗面貌。
大家被迫卷入一场没有硝烟的分房博弈:在位者心思各异;坚守传统的艺术家困顿无地;青年骨干拿着学历、职称四处奔走;退休干部说着过往贡献要求面谈;突然冒出的几十个离婚案真假难辨;找不到的人事档案与陈芝麻烂谷子等待拾捡;堵在家门口的基层职工喧嚣不断……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晶明谈道:“陈彦把分房故事放在一个艺术团体里,让从事风雅艺术的人为了分房弄得一塌糊涂,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和戏剧性。”
虽然从故事层面讲是分房,但并不是,分房是在分人。“小说中的院长满庭芳不是一个强权领导,而是一个‘延宕的哈姆雷特’,他需要照顾每个人的历史、情绪和家庭状况,这使得分房过程变成了人性展示的舞台。”分享会中,评论家杨庆祥谈道。
《人间广厦》的古典意味体现在多重意义上,故事设置上,西京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满庭芳的妻女忙碌在长安郊区的考古现场。壁画上的线条、器皿中的纹路,这些承载着文明记忆的“物”,跨越千年依旧鲜活,这部分内容与喧嚣的分房故事相映照,一幕幕事关人之身心安居,传统与现代、地上与地下、自我和他者互相映照。
《人间广厦》中也随处可见戏曲元素,阎晶明谈道:“《人间广厦》把人间的烟火气跟传统文化、民间艺术元素以及现代小说叙事方法复杂地、立体地融合为一体。”评论家韩敬群也认为,《人间广厦》从人名与词牌名的关联,到用每章首句或首句前几字作为标题的命名特色,都关联着中国古典文学中非常悠久、古老的文学传统。
杨庆祥关注,到陈彦的作品里都有一种“悲剧感”,这种“悲剧感”是中国文化中的基本质地,他以《装台》为例阐释道:“刁顺子是拆舞台的,先装起来然后再把它拆了,这就很有意思,‘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楼塌了’,是典型中国式的美学和哲学。”《主角》则体现了“戏里戏外分不清楚”的深层意蕴。《人间广厦》里也大量使用戏曲元素,“我们知道中国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是戏曲,戏曲承担了中国人绝大部分的情绪、欲望、恐惧和安慰。”他进一步指出,陈彦的创作深入挖掘了“中国式的人情与人性”,并观察到当前70后至90后作家中出现了“从中国传统的技艺和文化里寻找智慧”的创作转向。
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