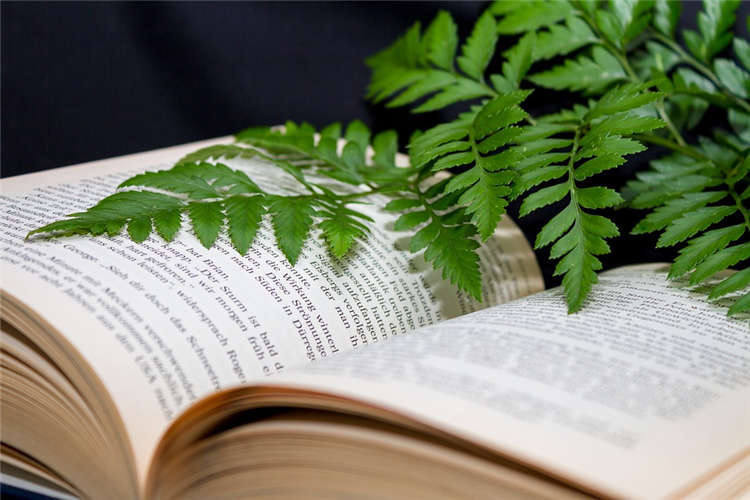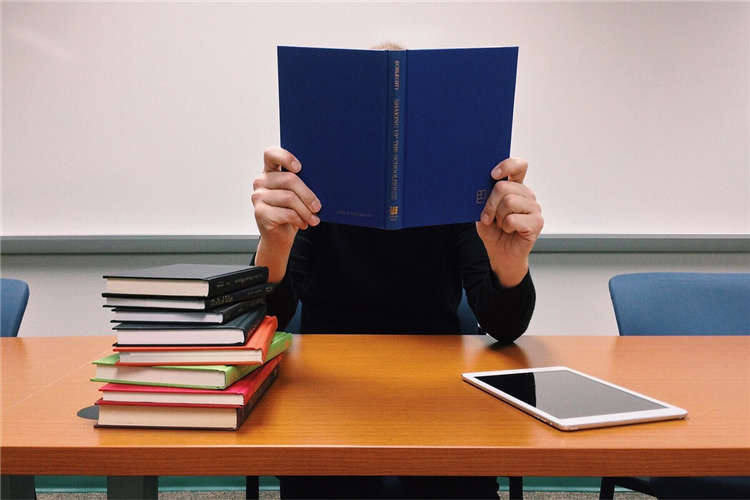《北京法源寺》在北京的又一轮演出落幕,4000张票仅用了两秒就售罄。十年间,这部剧的每一次演出都延续这样的火爆。而十年间,贾一平的谭嗣同也一如既往光芒万丈。
剧终,一句“看明月天山外,苍茫云海间。风景不殊,山河尤是,人民小康”的台词,被贾一平演绎到气吞山河、撼人心魄。偌大的千人剧场每到此处都鸦雀无声,举座为之心神共振,很多观众更是泪洒当场,为之泣绝。
贾一平在《北京法源寺》中扮演谭嗣同
十年间,作为演员的贾一平只演了《北京法源寺》这一部话剧。而他为这部剧留下了一个无法替代的谭嗣同,一个勇猛慈悲、浩然天地、赤诚果敢又洒脱超然的谭嗣同。他在舞台上的表演跨越虚实,天地纵横,有着挥洒古今、气象万千的自由。
无数观众因为这个剧和这个角色,成为贾一平的迷妹忠粉。有观众追着这部剧10年间看了50几场,天南海北追随,能记下每一句台词。而更多观众看完戏追问:贾一平,为什么不能多演一些戏?
在和《北京法源寺》一起走过10年后,贾一平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采访。穿着休闲装戴着鸭舌帽,眼前的贾一平微笑、亲和、健谈,讨论起每一个和戏有关的问题,都带着常年深思熟虑的思考。和他在社交媒体上晒出的形象一样,他似乎褪去了自己一切光环,回到一个演员,或者说“职业演员”最纯粹的样子。
贾一平是年少成名的,中戏表演系毕业,早年拍摄了《乾隆王朝》《中国式离婚》《坐庄》《兵峰》等很多影视剧,被认为是演技和颜值兼备的实力演员,更是早早被陈道明和奚美娟这样的艺术家推崇,成为忘年交。
但这些年,无论是影视剧还是话剧,贾一平都演的不多。有不熟悉他的观众在看到《北京法源寺》之后大感震惊,怎么会有这么光彩夺目的演员!
《北京法源寺》剧照
采访间,贾一平聊了很多。关于《北京法源寺》、关于表演、关于东西方戏剧差异,关于他这些年一直在思考的“中国戏剧”。他谈及了很多对当下的思考,似乎又侧面回答了为什么这些年他演戏不多。
出身于戏曲世家,在影视界多年,及至《北京法源寺》十年,这一切都在贾一平身上留下印记。他在舞台上的表演有着一种话剧舞台并不多见的“东方气韵”。而这应该正和他十年间一直在思考并想做的事情有关,“我想做‘中国戏剧’,想探索中国的戏剧该怎么弄,找到一种属于我们自己的表达方式。”
《北京法源寺》剧照
【对话】
关于《北京法源寺》:“我也是演了很多年之后,意识到这个东西是中国戏”
澎湃新闻:《北京法源寺》演了整整十年,还记得当初刚接到这个戏是什么想法吗?
贾一平:其实当时没太多复杂想法。我之前十几年一直都在拍电视剧,很久没在我们剧院演戏了,作为一个戏剧演员,心里总想着要演就演点好的。田导的戏我之前就看过,像最早的《生死场》,排得就特别好。加上李敖的小说做基础,人物又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所以抱着期望就参与了。没想到一演就演了十年。
澎湃新闻:很多人都以为你在演《北京法源寺》之前都是拍影视剧,没怎么接触过话剧。
贾一平:不是这样的。我最早进戏剧学院前,就是武汉儿艺的演员,演了三年儿童剧,后来考了中戏。儿童剧的演出场次特别多,每年上百场,一天到晚跟小孩演,所以我对舞台一点都不陌生。在中戏演了两部毕业大戏后,我就出来拍电视剧了。刚开始毕业分配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时候,还演过一个王晓鹰导演的《保尔·柯察金》。
澎湃新闻:后来怎么就专注拍影视,没再坚持做话剧了?
贾一平:1998、1999年那会儿,我拍戏赚了点钱,拿着钱就和几个同学一起做了一部话剧,那个戏是法国剧作家莫里哀的《司卡班的诡计》,我既是制作人又是导演,还演了皆隆特老爷这个角色。其实那个戏排得挺好看,不过因为当时的戏剧环境太差,没有人进剧场看戏,送票都没人看,最后把钱花光了,这戏也就没法儿再演了。事后我就想,演戏本来就是给人看的,不是自娱自乐,既然没人看,就干脆拍电视剧去了,那时候看电视剧的人多。不过现在的话剧市场和当年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贾一平生活照
澎湃新闻:从你的表演能看出来,你的戏剧训练是特别扎实的。
贾一平:从武汉儿艺到中戏,我一直都在演戏,后来虽然拍的是电视剧,但舞台和影视只是表演幅度、观影关系不同,创作本质没区别。
而且我们那时候演戏有很多榜样啊,像焦晃老师、陈道明老师、奚美娟老师,还有很多很棒的老师们,我跟他们都合作过。他们会带着我们演,这是现在很多年轻演员没有的优势。我们那时候也常看好戏,都是特别棒的演员演出,耳濡目染之下,积累自然就不一样了。
澎湃新闻:听说你和陈道明、奚美娟老师关系都非常好,演《北京法源寺》还和奚美娟老师有关?
贾一平:是,陈道明老师和奚美娟老师都是我的忘年交,我们合作过很多次,认识了有二十多年了,我把他们当作我的榜样!他们的人品、艺品都是我一直在学习的。
演《北京法源寺》确实是奚美娟老师推荐的,田导当时找她演慈禧,她就跟田导说,你们剧院有个叫贾一平的,是个好演员啊,找他演!因为当时我不常在剧院活动,而且合并之前,田导是中央实验话剧院的,我在青艺,我俩之前不太熟,没有什么交集。但我和奚老师最早是在拍电视剧《坐庄》认识的,她就觉得我有表演能力,所以就跟田导推荐了我。
奚美娟(左)、田沁鑫(中)和贾一平(右)在今年北京排练时合影
澎湃新闻:最后《北京法源寺》演了十年,现在对这个戏的理解和第一年比有变化吗?
贾一平:刚开始演的时候心里很忐忑,因为这个戏太难了。一开始,我、奚老师还有杰哥(周杰)整宿都睡不着觉。我们在戏剧学院学的都是斯坦尼体系,即通过组织舞台行动来塑造人物形象,但这套方法在《北京法源寺》这个戏里好像特别困难。我发现自己没有了手段。
后来我才意识到《北京法源寺》这戏是中国戏。我也是演了很多年之后才意识到的,这个戏跟传统的话剧从本质上就不一样。无论是从戏剧结构到审美追求,到表现形式,还有表演方式,舞台空间。所有的这些完全都跟我们以前演过的戏不一样。所以对我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一次创作。
但这个戏首演就成功了,当时北京整个文化界基本都来看了,评价也很高。但那时候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具体好在哪,就是尽力认真演。演着演着,每一轮都能有新的理解,说台词也更明白。现在一上台,感觉那些话就像是我自己想说的,都不需要刻意琢磨。
贾一平和奚美娟是忘年交
澎湃新闻:谭嗣同这个角色感觉是这部剧的一个“定海神针”,你觉得塑造这个角色最难的是什么?
贾一平:如果是按我们所说的现实主义戏剧风格,谭嗣同不会那么难演,但是放到《北京法源寺》这样一个中国戏剧形式里就特别难,最难的地方就是中国戏是以叙述为主,要求演员“立地成佛”。中国戏不是以情节来推动人物发展的,而是由人物推动情节发展的。更困难的是,我们是中国式的话剧,而不是中国戏曲,舞台上需要的那一套戏曲演员身上必备的手眼身法步,我们戏剧演员是没有的。
澎湃新闻:这个剧里你和吴彼“法华寺”那场对手戏特别精彩,是不是因为你们两位都有戏曲功底?这种呈现方式是怎么确定的?
贾一平:这一场表演就是非常中国。那主要是导演定的,刚开始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弄,那个场景很虚幻,不是写实风格。吴彼以前是唱京剧黑头的,我们俩的很多动作都是自己摸索着设计的。我要去说服他,他要推诿装糊涂,但是我们用了戏曲的一桌两椅。这种融合中国戏曲元素的呈现方式,观众很爱看,特别有中国戏剧的张力和节奏。如果有更多人愿意探索,把中国这套东西做出来,肯定会受欢迎。
贾一平(左)和吴彼(右)在《北京法源寺》中分别扮演谭嗣同和袁世凯
澎湃新闻:你父母都是从事汉剧艺术的,听说你从小在剧团长大,这是不是也对你的表演有挺大影响?
贾一平:我三岁就被拎上台演《铡美案》里秦香莲的儿子,从小在后台泡着,戏曲的那些东西耳濡目染。虽然正儿八经唱戏不行,但其中的门道我都懂。如果需要演相关角色,我可以专门去练,这种从小积累的感知力,对舞台表演很有帮助。
演出谢幕
关于“中国戏”:“我们一直在学别人的那套东西,那我们自己的东西在哪?”
澎湃新闻:你一直强调中国戏,这种认知和思考是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
贾一平:我觉得还真的就是从《北京法源寺》开始的。
我意识到一个问题,建国后戏剧学院学的是斯坦尼那一套西方理论,后来的创作,从电视剧到电影也都是西方引进的,虽然讲的是中国人的事,但审美追求大多是西方的,比如追求“灰色的人物”,这导致中国的戏没有辨识度。所以中国戏剧到底是什么样,没人能说清楚。
《北京法源寺》剧照
澎湃新闻:那你认为的中国戏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贾一平:中国戏和西方的戏从结构到审美追求是很不一样的。
西方戏要探讨人性,但中国戏的审美讲的是神性。谭嗣同身上承载了很多老百姓、中国人的想象。就比如我们遇到一个不公的事,就希望有一个包青天。你不能把他拉下神坛,如果这样演就演砸了。一个是在神格上谈,一个是在人格上谈;一个追求的是人性,一个是追求的神性,它不在一个维度上。
另外西方戏是靠对话,中国戏是靠叙述。没有太多环境铺垫,演员一上台就得“立地成佛”,通过定场诗之类的方式把自己的事说清楚,让观众相信你。如果做不到让观众相信,这个戏就败了。
西方戏求真,核心是制造让观众相信的幻觉。但中国戏左边是“虚”,右边是“戈”,就是装扮的意思,形式上就告诉你是假的、是扮演的。追求的是意境、气韵、和谐的美。这是中国传统戏的演剧观。
《北京法源寺》剧照
澎湃新闻:很多观众希望你多演作品,为什么这些年演的不多?
贾一平:《北京法源寺》我还在演啊。但现在的趣味越来越让我有点看不懂,审美我也不太能接受,演起来自己也难受,我想那些喜欢我的观众也会觉得不舒服。
澎湃新闻:那你现在有做哪些关于中国戏的事情?
贾一平:我每天都在看剧本。最近我主要集中在把《明清传奇杂剧编年史》全部五卷本拿回去看,看一看以前戏本的格式和手段。琢磨一下语言上怎么能把它们翻译出来让观众能听懂,又能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韵味。
另外中国戏的很多形式,光表演本身就是一门学问,比如形体、道白、节奏,都可以捡回来学,有很多视频、资料可以参考。我还是希望有更多的中国戏剧能够让大家看见,还是要找到一种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