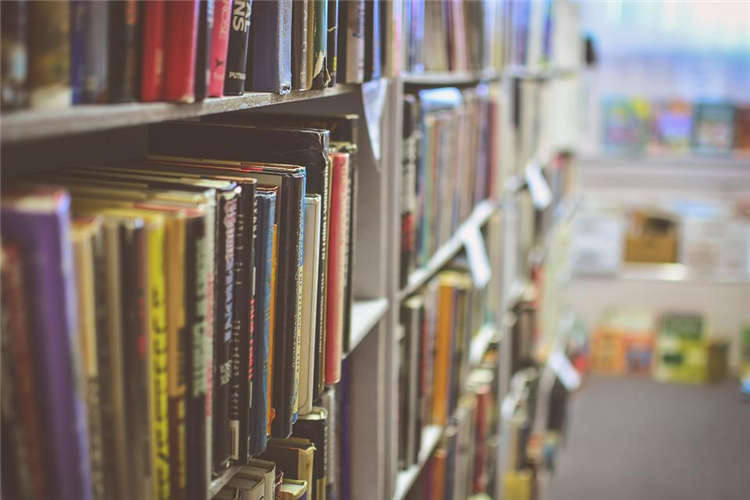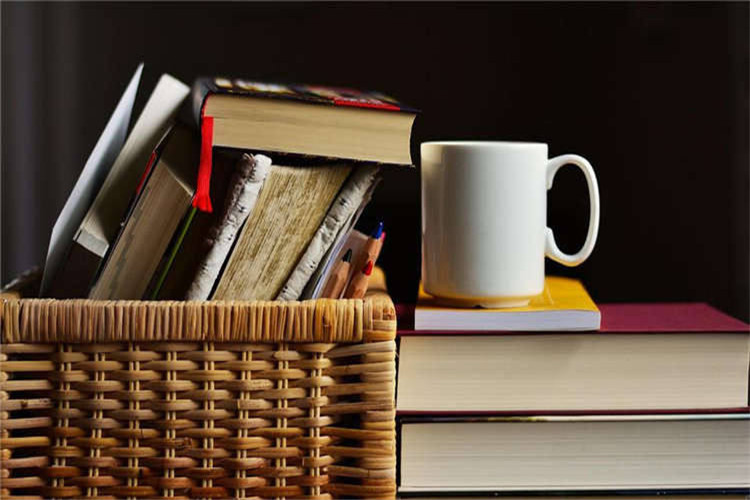7年多来在国内外60余座城市演出超800场,上海歌舞团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自诞生以来不断创下佳绩。
11月13日晚,这部“现象级”舞剧在美琪大戏院上演800场纪念演出。以王佳俊、朱洁静为首的“全A组”主演悉数登台,和观众共同庆祝这一特殊时刻。
这部作品开辟了中国舞剧的市场化之路,从上海驻演到全国巡演,掀起一轮又一轮“电波热”。800场纪念演出前,主创团队相聚一堂,拆解“电波”成功的密码。
主创团队相聚一堂
“每个人都较真,才凑出完整的电波”
“电波”的创作之路充满攻坚克难,但一开始,它就是冲着长线发展去做的。
“找选题、做创作,必须想清楚它的持续价值和未来可能性,靠‘蒙’是走不远的。”制作人/艺术监制陈飞华说,“电波”不是盲目创作,而是带着明确的长远目标推进。
“当时,很多人不看好隐蔽战线题材,觉得舞蹈语言撑不起复杂的地下工作故事。但我们不服输。”主创团队燃起斗志,最后拿出了让观众喜欢的作品。艰巨的挑战是最好的试金石,攻克了它,就握住了成功的密码。
剧照
剧照
舞坛“双子星”韩真和周莉亚最初接到的是《芦花女》委约创作,临阵要换红色题材,一时没反应过来。
两位导演决定去上海走一圈,找找感觉。“第一次来上海总觉得没摸到核心。直到聊到隐蔽战线的‘电波’,我眼睛亮了,小时候看过相关故事,发电报的画面特别清晰。”那一刻,周莉亚有了创作的冲动。
“那会儿她们才三十出头,对新事物的接受度高,也有调整的勇气。”陈飞华回忆,他们还聊到怎么让红色题材贴近年轻人,比如借鉴年轻人喜欢的“狼人杀”,帮助观众理解剧情。
两位导演也会有分歧,但“电波”的创作特别顺畅,是两人合作过的作品里“灵感和执行双在线”的一次。
“一方面,我们有了好几部戏的积累,刚好到了能驾驭这个题材的阶段;另一方面,上海歌舞团的演员和工作人员太给力了,不管是台前的演员,还是幕后的舞美、灯光,都能快速get要求,甚至能超出预期呈现。”
那段时间,两位导演正处于创作爆发期,还在作品里加了不少小巧思。故事是线性的,她们会借助蒙太奇手法,重新用舞台空间去架构故事,比如将4对双人舞浓缩在同一空间,表现李侠和兰芬相识、相近、相爱、相别的过程,感情的流动跃然纸上。
舞段“渔光曲”的部分灵感,则源自上海弄堂深处一位老奶奶洗带鱼的日常瞬间。两位导演和奶奶聊了好一会儿,她的房子有个小楼梯,李侠和兰芬住的房里也有楼梯。“她的举手投足,恰恰投射了我们对于上海女性的想象和儿时的记忆。”两位导演强调,要真正走入上海,去感受这个城市的人文温度,故事才有着陆点。
在很多人眼里,韩真、周莉亚是中国最“较真”的导演,哪个细节心里过不去,必须改到满意为止。也有观众说,“电波”里每个主创环节都没掉队,“因为每个人都在较真。不光是我们俩,编剧、作曲、舞美、演员,每个人都对自己的部分有要求,不会敷衍。”周莉亚说,所有人都较真,才凑出了完整的“电波”。
剧照
剧照
“以前人们总觉得舞剧靠肢体表达,不需要完整剧本,最多两页纸、几句话概括剧情。但我为‘电波’写了一万多字的剧本,想给所有主创一个思考的原点。”编剧罗怀臻说。
难点在于如何用文字为舞蹈铺路。电影有台词和镜头语言,话剧有对白,舞剧靠肢体,剧本不能写得太“满”,要留足肢体表达的空间,但也不能太“空”,得把人物的价值观、故事的风格感讲清楚。
很多作品有脸谱化倾向,好人、坏人一眼能分清。但“电波”突出了人性化,比如李侠不只是英雄,也是有家庭、有情感的普通人,反派也不是纯粹的坏,而是有立场和动机的角色。
舞剧对电影做了提纯和拓展:提纯电影里的核心情节,比如“发电报”“传递情报”;拓展电影没细讲的场景,比如石库门里的普通生活、上海市民的日常状态。这样一来,舞剧就和电影有了区别,更贴近生活中的红色故事,而不是概念化的英雄叙事。
罗怀臻总结,“电波”开创了两个先例:一是中国舞剧的“市场化路径”,靠市场、靠口碑走到了800场;二是红色题材的“年轻化表达”,把年轻人熟悉的情感逻辑融入故事,让观众有共鸣。如今,很多红色题材作品都在借鉴这种创作思路。
剧照
剧照
“接力棒传到我们手上,要死死攥紧”
从《渔光曲》《葡萄美酒》到结尾的吉他独奏,“电波”的音乐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穿着旗袍的婀娜女子,摇着蒲扇,踩着矮凳,在弄堂里穿寻,充满了烟火气——这一段配着《渔光曲》的扇子舞,是“电波”最出圈的舞段。
有一天,作曲杨帆接到陈飞华电话,要不试试《渔光曲》?一开始他并不想用,因为太经典,很多影视作品用过,担心观众听腻了。他试着结合舞蹈的节奏改编。演员排练时,舞蹈的速度很慢,慢到他怀疑人生。于是,他在旋律里加了很多细节,用弦乐铺垫情绪,用钢琴点缀节奏,才慢慢找到平衡。如今,每次看演员跳那段扇子舞,他都觉得《渔光曲》选对了。
“上海老歌里,除了熟悉的《夜来香》,还有很多小众但有味道的作品,《葡萄美酒》就是其中之一。”他还借鉴了国外电影的手法,用美好旋律来反衬紧张或惊悚的剧情——《葡萄美酒》用在特务搜查的片段,和柳尼娜搭在一块,形成了反差,观众更能感受到隐蔽战线的危险。
“电波”的开篇用了浓烈的乐队伴奏,突出英雄叙事的厚重感,结尾,他想换一种风格,体现平凡英雄的传承。比如,兰芬抱着孩子,身边是上海解放后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这些无名英雄更需要细腻温暖的音乐表达。
他开始做排除法:小提琴太抒情,适合表达个人情感;钢琴太冷静,少了烟火气;手风琴有年代感,但不够轻盈。最后想到吉他,它既能独奏旋律,又能弹伴奏,音色温暖又有质感,刚好契合“平凡中的伟大”的主题。
杨帆在上海待过12年,曾在上海考音乐学院求学,住过石库门,在酒吧弹过琴,对上海的海派文化特别熟悉,“没有在上海的生活,我写不出‘电波’的音乐。”
剧照
剧照
“我一开始心里没底,直到看了三段排练,被震撼,决心接手。”“电波”也是张松做的第一部舞剧多媒体设计。
开场那段充满紧张气息的“雨伞舞”,已经成了舞剧标志。导演要求,雨的变化要配合音乐、表演,严丝合缝,不能多也不能少,“我准备了七八种素材,有密码雨,小雨和大雨,慢放雨和零星雨,本想挑几个,没想到导演全要。”“电波”首演后两三年,张松接到很多创作邀约,全是舞剧,有剧组甚至说就要“电波”那种雨。
若要问最喜欢哪一段多媒体设计,张松选择了结尾的报纸段落。他从故纸堆里翻出两张当时的报纸,剩下的都是他们自己做,核对字体、设计排版,加班加点熬夜赶制,“这段设计既有历史厚重感,又能呼应剧情,是我特别满意的一段。”
剧照
剧照
执行导演吴欢被称为“留守青年”。“电波”走到800场,很多核心主创已经奔赴新的事业高峰,而吴欢一直坚守在岗位上,800场从未缺席。
“我更像舞团、导演和演员之间的桥梁。”从采风、排练到首演、巡演,他见证了每一个环节。有时,他一个月得看20遍“电波”, “我总和演员说,对某个城市的某个观众来说,这可能是他们看的第一场‘电波’,必须拿出诚意。敬畏舞台从来不是口号。”
“电波”也面临着演员更替。他把“熟戏生跳”四个字送给演员们,还总和他们起朱洁静的故事——每场演出上半场结束后,她都会第一时间发信息问他:有没有跳超了,使大劲了?表演还贴合角色吗?——“她做到了对角色的极致爱护,这也是所有人该有的态度。”有一次,朱洁静给他截了一张图,有二楼观众反映“渔光曲”的斜线不齐,之后他都会反复核对,确保不管观众在哪个位置看到的都是整齐画面。
“导演标准是唯一标准,演员不能随便改戏,必须严格执行。这么多年,舞剧口碑一直没掉,是最好证明。”韩真的一句话一直激励着他,“文艺工作者有责任讲好那一代英雄的故事,接力棒传到我们手上,要死死攥紧,一棒一棒传承下去。我能坚持,正是因为这份使命感。”
800场纪念演出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