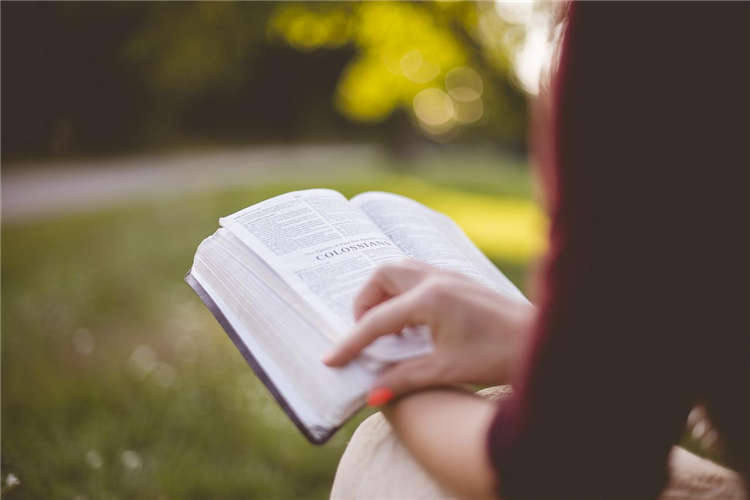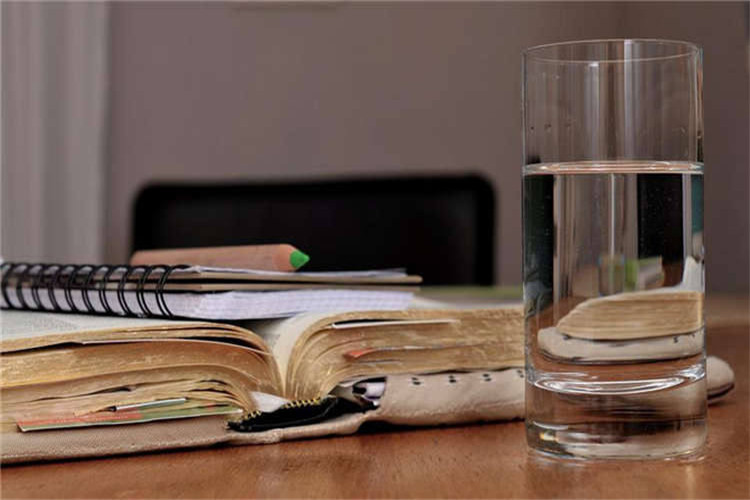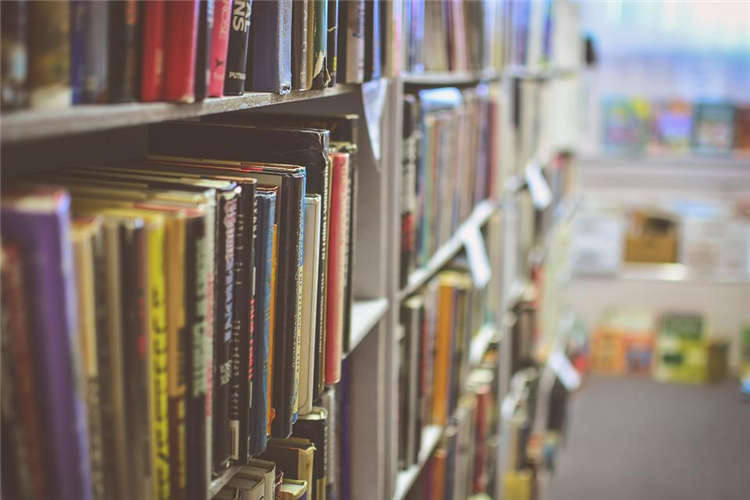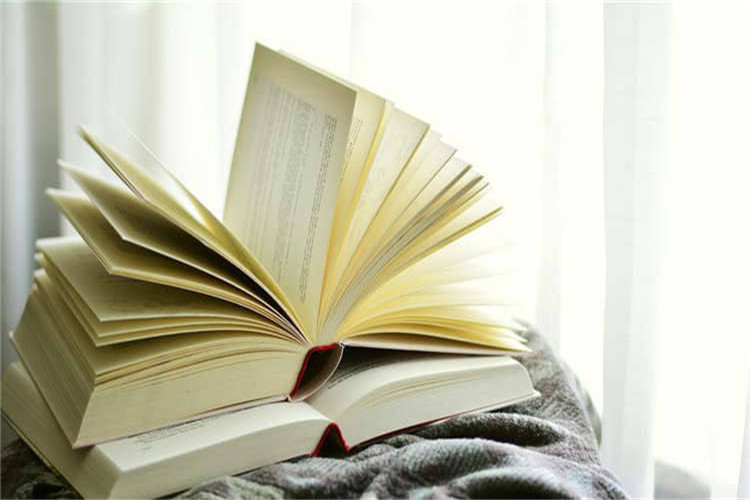歌唱家特菲尔今年参加了第二十四届上海国际艺术节
在歌剧世界里,布莱恩·特菲尔的名字是戏剧张力的象征。
这位来自威尔士的低男中音,以他深沉的嗓音、宽广的音域和独特的舞台魅力征服了世界。他曾在大都会歌剧院、皇家歌剧院、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等舞台留下传奇演出,也曾为英国查尔斯三世国王的加冕典礼献唱——那短短一分四十秒的威尔士歌谣,成为历史的注脚。
此次采访中,特菲尔谈到了从农场走向歌剧殿堂的心路历程、威尔士乡音、瓦格纳的复杂角色、对歌剧舞台上“反派”的理解。六十岁的他,仍然坚持用歌声探索人生与人性。
加冕礼
澎湃新闻:我想先问问你在查尔斯国王加冕典礼上演唱的经历。
特菲尔:能在加冕典礼上演唱是一种巨大的荣誉,那是威尔士语第一次在如此隆重的仪式上被唱响。音乐一直是查尔斯国王所钟爱的东西,他非常喜欢古典音乐,为加冕典礼委托了许多新曲。我演唱的那首由威尔士作曲家保罗·米勒(Paul Miller)创作,仅仅在一分四十秒内,就展现出威尔士音乐的和声之美与神秘气息,能做到这样实属不易。
不过,压力真的非常大。我的小心脏就像马拉松选手一样狂跳。但我依然保持冷静——我熟记了整首曲子,完全背诵下来。在典礼前的排练中,王室成员还特地来到教堂走位。第二天我们进行了完整的总排练,而再下一天就是正式典礼。那天天气晴朗万分,你能感到自己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可是一旦仪式结束,一切就归于平静。雨立刻下了起来,我们还得想办法去拦出租车!你在那一刻从荣耀中“砰”地回到现实。之后我们去了温莎城堡,举办一场更轻松的音乐会,邀请了很多大牌歌手同台演出。那真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录音趣事
澎湃新闻:能否谈谈你最新的专辑《海之歌》(Sea Songs),其中收录了不少威尔士民谣。
《海之歌》专辑封面
特菲尔:我在威尔士和几位出色的威尔士乐手一起录制完成。我非常喜欢当下TikTok上重新流行起来的海员号子,那些让人情不自禁站起来、微笑、拍手、合唱的音乐,真是太有感染力了。
我花了五天录音,过程非常有趣。有一次我唱到一个很高的音时,突然——我的一颗牙齿从嘴里飞了出来!我还伸手在空中把它接住了(笑)。结果我得立刻去看牙医,把牙装回去,然后继续录音。这种事在现场录音中常有,大家都笑翻了。乐队的人喊:“天哪,特菲尔的牙掉了!”你知道,没有牙齿是唱不了歌的!
农夫的影子
澎湃新闻: 说到民谣,这次你还带来了《屋顶上的提琴手》中的《如果我是有钱人》。为什么会一直把这首歌保留在你的曲目中?
特菲尔:我太喜欢这首歌了!这是我们家每年圣诞节都会一起看的电影。哈伊姆·托波尔饰演的特维耶真是个栩栩如生的人物。这部音乐剧上映时打破了无数纪录,是当时演出时间最长的音乐剧,直到后来被《油脂》超越。我今年六十岁,明年希望能举办一次大型的《屋顶上的提琴手》音乐会巡演,最好是全球巡演。
这部作品里有太多朗朗上口的曲子,比如《日出日落》。当然,我不是犹太后裔,但在歌剧舞台上我扮演过神明、恶魔,那为什么不能演个挤牛奶的农夫呢?我父亲就是个农民,养牛、养羊,还养过马。那就是我的童年,我是农夫的儿子。
瓦格纳和莫扎特
澎湃新闻:你演唱过许多瓦格纳的角色,比如《尼伯龙根的指环》和《漂泊的荷兰人》。这次你演唱其中的一段独白,包含了绝望和救赎。从歌者的角度,你能谈谈是如何诠释这种情感历程的吗?
特菲尔:对于像我这样的低男中音嗓音,瓦格纳写下了许多伟大的角色。比如《纽伦堡的名歌手》中的汉萨克斯,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舞台上最长、最艰难的角色之一。而《漂泊的荷兰人》是瓦格纳早期的作品,虽然篇幅较短,却极富戏剧性。开场独白《期限已到》中,荷兰人被海浪拍上陆地,开始他七年一次的救赎之旅。即使把这些独白单独拿出来演唱,也必须赋予它完整的戏剧背景和强烈的感染力。我现在已经不再在歌剧院演唱整部瓦格纳歌剧了,但仍会在音乐会中演唱其中的独白。
今年在上海的舞台上,布莱恩•特菲尔与女高音刘艺合作《漂泊的荷兰人》
澎湃新闻: 你过去也演唱过不少莫扎特作品,如今有些角色你已不再演出了。你会怀念莫扎特吗?还是说这只是自然的艺术转变?
特菲尔:我当然还能唱莫扎特(笑)。年龄并不会禁止你唱这些作品。但有些角色,比如《费加罗的婚礼》中的费加罗,总有一个该告别的时刻。我最后一次唱它时就想:“我已经不够年轻,不能再在台上又唱又跳了。”不过,明年夏天我会第一次演唱莫扎特的另一个角色《女人皆如此》中的唐·阿方索,探索角色永远不会太晚。
低音“坏男孩”
澎湃新闻: 你还演唱了另一位“反派”伊阿古。你甚至出过一张名为《坏男孩》(Bad Boys)的DJ专辑。你是如何在舞台上塑造这些复杂又邪魅的角色的?
《坏男孩》汇集了歌剧和音乐剧中的反派角色
特菲尔:哎呀,观众其实都喜欢坏人(笑)。你们喜欢梅菲斯特,喜欢《理发师陶德》里的陶德——他们虽然内心痛苦,却让人同情。我这次演唱《奥赛罗》中的《信经》。我从没在舞台上真正演过伊阿古这个角色,但当时我希望做一张《坏男孩》这样的概念专辑,后来证明大众也很喜欢。我觉得古典音乐应该更有创意——与器乐家、音乐剧演员同台演出,加入大屏幕、影像、访谈等等。我们得跳出传统框架去思考。《坏男孩》那次巡演很成功,我在近二十个城市演出,观众都很喜欢那种“魔性”的角色魅力。
澎湃新闻: 许多伟大的作曲家都为低男中音写过精彩的角色。你最喜欢哪些?
特菲尔:职业生涯早期,我最喜欢费加罗。《费加罗的婚礼》是我第一次在歌剧院中感到“自在”的角色。后来是威尔第的《福斯塔夫》,作曲家为了证明他也能写出幽默的喜剧。这是舞台上极具戏剧性的大人物,假肚子、假发、浓妆,全都有。光是在化妆间变身的那一小时我都在笑,未登台就投入到音乐的快乐中去。
接着是《指环》中的沃坦,尤其是《齐格弗里德》里的沃坦,音域和情感都非常适合我。要说最像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角色,那就是汉萨克斯——光是学会这部作品就如登顶一般艰难。瓦格纳的作品往往是每天排一两幕,直到彩排时才首次与乐团合演整部作品。首演那天总会想:“我真的能做到吗?”我在威尔士与威尔士国家歌剧院合作演出了《名歌手》,演员、合唱团、指挥、导演都很出色。可以说,那十场《名歌手》是我职业生涯中唱得最好的一段旅程。
歌唱家特菲尔在今年上海国际艺术节的舞台上
教学与继承:歌手的责任
澎湃新闻:你曾在伦敦吉尔德霍尔音乐与戏剧学院学习,不仅接受了声乐训练,也有全面的艺术教育。那段经历中,有哪些非音乐性的课程或经验让你受益终生?
特菲尔:我在那里学习了四年,又读了一年歌剧课程。那时一切并非一帆风顺——在前四年我一项比赛都没赢过,第五年才拿到“金奖”(Gold Medal),那是学院最高荣誉。评委中有我敬仰的威尔士歌唱家杰朗特·埃文斯爵士,还有我的老师亚瑟·雷克利斯。
吉尔德霍尔学院就像一棵大树,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养分——爵士、蓝调、歌剧、清唱剧、艺术歌曲。我甚至上过舞蹈课,比如踢踏舞(笑)。虽然跳得糟糕透顶,但这些课让我学会如何在舞台上自然地移动,保持体态与气场。刚离开威尔士农场、来到伦敦时,我很难适应城市生活,但我最终做到了,也很庆幸当初勇敢迈出那一步。
澎湃新闻:听说你现在也扶持年轻歌手?
特菲尔:我现在在威尔士皇家音乐与戏剧学院设立了一个基金会。本月我们将举办以我名字命名的声乐比赛,还包括大师班与讲座。参赛者必须演唱一首威尔士语歌曲和一首来自自己国家的作品。奖金不算小——对年轻歌手来说,这些钱可以帮助他们买西装、鞋子、乐谱,支付声乐和语言课程。我也很感激劳力士,我作为他们的品牌代言人,他们在支持年轻歌手方面一直全力相助。
澎湃新闻: 你最敬佩、推荐的低男中音歌唱家有哪些?
特菲尔:约瑟夫·费迪南德(Joseph Ferdinand)、塞缪尔·雷米(Samuel Ramey)、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orris)、迪特里希·菲舍尔-迪斯考(Dietrich Fischer-Dieskau)——这些人是每个男中音的必听对象。当然,听他们的录音只能借鉴,你仍需唱出属于自己的印记。
我很幸运,身边有出色的老师、教练、伴奏和语言指导,他们让我懂得如何快乐地学习曲目。你必须带着微笑和生命力去歌唱,因为观众能立刻察觉你是否准备充分。歌手需要团队,就像高尔夫球手需要体能教练、挥杆教练、推杆教练一样。我们歌手也需要优秀的声乐教师、钢琴伴奏、排练指导、语言老师。我非常幸运能与如此多杰出的人合作。现在,我也在通过声乐比赛帮助下一代。我在11月9日迎来60岁生日,而比赛就在前一天——多有意义的日子!
试镜金曲和历史乐谱
澎湃新闻: 你有试唱时属于自己的“招牌曲目”并成功打动了不少指挥和制作人。你是怎么挑选这些曲子的?
特菲尔:没有人有“万能钥匙”,但试唱时必须有计划。我通常以《费加罗的婚礼》中《不要再追求爱情》开场,然后唱《浮士德》中的“跳蚤独白”——这样就能展示两种语言、两种风格:意大利语的明快与德语的深沉。通过对比,让指挥和制作人看到你的多面性。那段时间我接到了两个工作机会:一个是汉堡的《费加罗》,另一个是在芝加哥的《福斯塔夫》(Falstaff)。其实这就够了——事业的雪球从那时开始滚动。
歌唱家特菲尔在今年上海国际艺术节的舞台上
澎湃新闻: 你还喜欢收藏历史乐谱,尤其是那些曾被名家使用过的。这个爱好你还在坚持吗?
特菲尔:当然。我有一些初版乐谱和手稿复制本。其中最珍贵的是美国著名歌唱家乔治·伦敦演唱《指环》时用过的乐谱,是他的遗孀诺拉·伦敦赠送给我的。上面有他亲笔写下的注释:比如长矛该握在哪只手,眼罩该戴哪边,哪里需要换气、哪里该前移或放慢。这些笔记就像一个“歌者的神谕”,对我意义重大。
尾声:仍在歌唱的灵魂
当谈及未来计划时,特菲尔轻轻一笑:“我想唱一回莫扎特《魔笛》中老年版的捕鸟人。为什么不呢?音乐就是不断地玩耍。”从威尔士山谷的农舍,到世界最辉煌的舞台,从加冕典礼的荣耀,到为青年歌者筹款的谦卑,特菲尔用六十年的生命,诠释了一个艺术家的真谛:歌唱,不只是职业,而是一种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