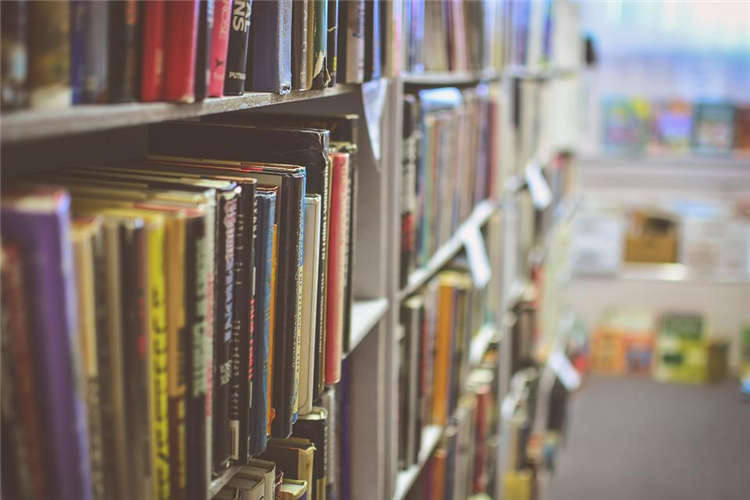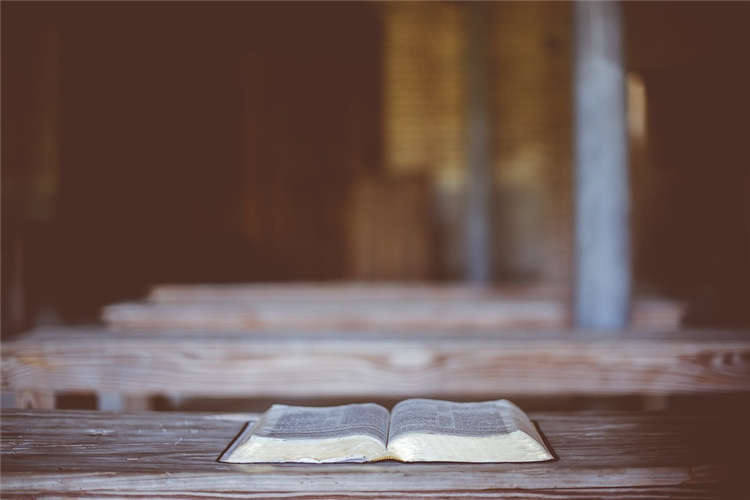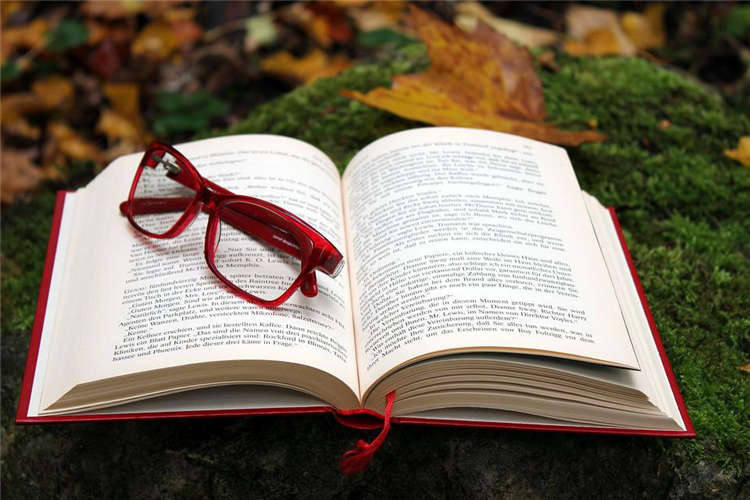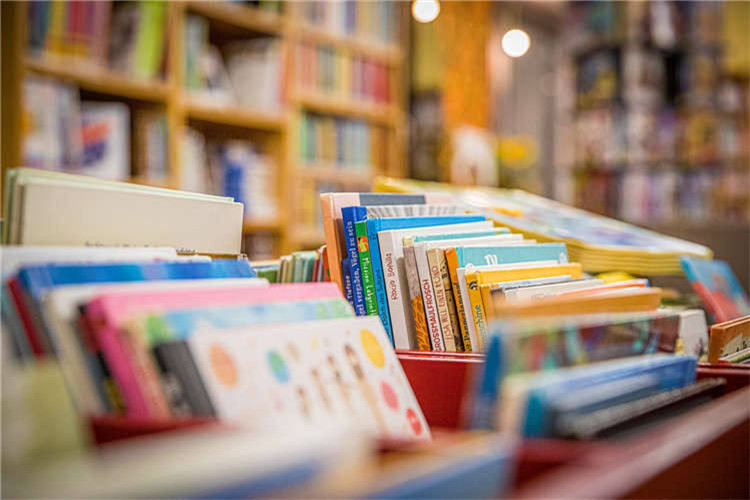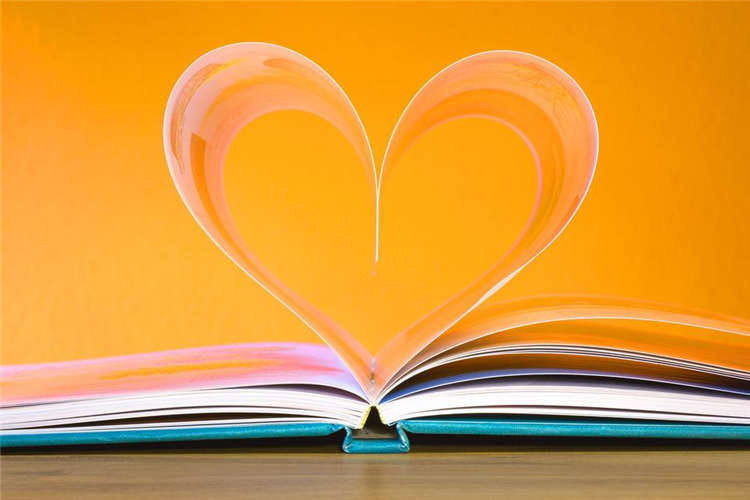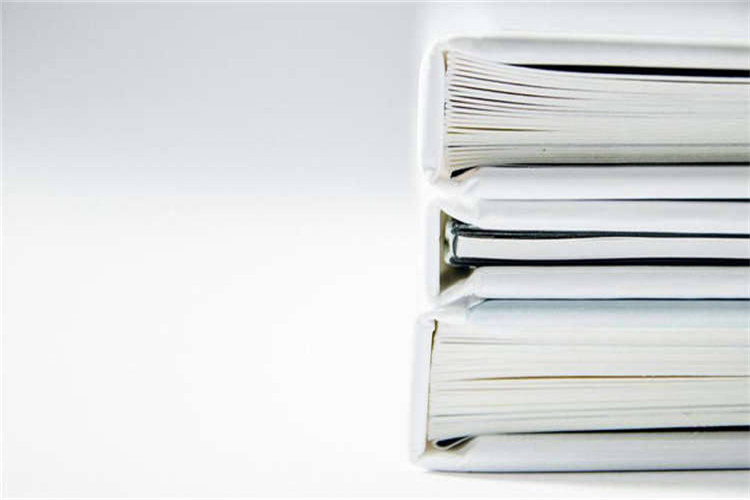“新疆是我的故乡,新疆兵团是养育我的地方。我的母亲已经八十多了,她还在新疆养老。”
作为“兵团二代”,作家张者对新疆充满了特别的感情。他在河南出生,在重庆、北京求学,但他视新疆为自己的文学创作之根。在曾经寸草不生的天山南坡的山沟,他随父母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光。如今在重庆生活,他依然会在梦中回到那个山沟,而那些大漠和干沟在梦中都变成了青山绿水。
长篇小说《天边》首发于《收获·长篇小说2025秋卷》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之际,张者在《收获·长篇小说2025秋卷》带来了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天边》。故事以一群兵团少年的成长史为经纬,通过三代新疆兵团人的命运交织,勾勒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七十年屯垦戍边的“创业史”。
小说也写到了一批上海援疆知青,他们被新疆兵团人称为“上海青年”。11月9日,张者来到上海,参加“收获首发”活动——“把大漠当青春纪念册的人们”。
“谈到新疆兵团,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上海人。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有十万上海支边青年到达了新疆兵团。至今,新疆兵团人还称他们为‘上海青年’。确实,他们在我心目中永远年轻。如今,上海还在支援新疆,不但有援疆的干部,还有援疆的资金。而当年,上海和全国一样还没有摆脱贫困,支援新疆的只有人,整整一代人。”
在活动间隙,张者接受了澎湃新闻·文学花边专访。
作家、重庆作协主席、新疆兵团作协名誉主席张者
【对话】
澎湃新闻:你会把新疆视作自己“文学的故乡”吗?这个地方对你感受世界产生了哪些具体的影响?
张者:新疆当然是我的“文学的故乡”之一。我出生在河南,新疆是我生命的第二故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养育我的地方。
1949年后,包括我父母在内的一批戍边者走向了大漠,他们是军人,就地转业成了兵团人。他们的目的就是屯垦戍边。兵团人和中国历史上的戍边人一脉相承,不一样的是他们除了悲壮决绝之外,还多了一种信仰和豪迈,乐观和坚韧,他们喊出了“我为边疆献青春,献了青春献子孙”。誓言是严肃的,有雪山和大漠作证。我们“兵团二代”这一代,这种感受恐怕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澎湃新闻:这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张者:最初是不甘心的,抗拒和叛逆是必然的。
年轻一代拒绝埋没在大漠戈壁,企图通过高考升学到达他心中的天边。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寻找自己心中的天边以及诗与远方。解决这种矛盾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兵团人的生活与内地已经无大的差别后。兵团二代的所有热血和青春,都被改写成了快乐的回忆。他们从理解父辈走向真正的扎根:真正的宝藏往往是在自己出发的地方。自己曾经寄望的天边,所有的憧憬并不遥远,原来就在眼前。
张者在新疆的早年照片
澎湃新闻:你的新疆题材常写到上海援疆知青,他们是你最早的文学启蒙吗?
张者:上海青年支援新疆的时候,我是一个少年。上海青年和兵团二代的少年在大漠边缘相遇了,这产生了“化学反应”。我曾经用鸡蛋和上海青年换书看,想起这事我常常哑然失笑。这一切都让我写在小说中了。
可以这样说。我是在上海人的教育下长大的。上海青年是我们兵二代的幼儿园老师、小学老师、中学老师。我的语文老师是上海青年,我还记住了她的名字。她在作文课时经常讲评我的作文。当我上完大学,并且发表了处女作去找她时,她和上海青年一起回到了上海,消失在大上海的人流中。我找不到她了,这让我很忧伤。
我能成为作家可以说也是上海青年培养起来的。大家都知道,一个普通人成为作家是从阅读开始的。而我阅读的第一部文学作品是上海青年借给我的。薄薄的一本,叫《少年维特之烦恼》。看来,无论你在大漠边缘,还是在大上海,少年都会有烦恼。
上海对于新疆来说,它是一种象征。他是现代的、前卫的、时髦的。它是新疆人梦想的地方,大漠中生成的海市蜃楼就是我们对上海的想象。我的有些发小现在就生活在上海,算是实现了理想。
《收获·长篇小说2025秋卷》
澎湃新闻:当你不在新疆生活,这个地方会以什么方式和你产生关联?
张者:我离开新疆很多年了,但我每年都回新疆,喝伊力特,把酒唱胡杨,对酒望大漠。那里的确是我的记忆之根、文化之根、文学创作之根。
有一种关联是十分奇妙的,那就是树。它叫胡杨树。在我的小说中是一种象征。我一直关注着那神奇的树。兵团人把胡杨树赋予了很多神奇的力量。胡杨树可以断臂求生,也可以向死而生。胡杨籽就像风车一样,随风而去,见水而停,春暖发芽,随季而长。
澎湃新闻:我想到了《山前该有一棵树》。你在这部小说里融入了自己的成长记忆,新作《天边》亦有你的亲身经历。在写作中和少年时的自己对话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张者:这种在写作中和少年时的自己对话是自言自语的。有时候是一个音调,是一首歌。
我的写作往往是从歌声开始的,有时候干脆播放一些写新疆的歌。这本身就是一种对话。比方:我在写《天边》时,会不知不觉地哼唱《在那遥远的地方》,我开始是想用这个名字的,但被用得实在太多了。后来就用了《天边》。其实也有一首歌叫《天边》,歌唱“天边”的曲更多,好在长篇小说没有叫《天边》的。我在小说中把天边赋予了新的内涵。
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山前该有一棵树》
澎湃新闻:近年新疆文学很受关注,刘亮程、李娟等作家的作品为人们阅读、谈论。你认为你有哪些独特的创作资源和视角?或者说,你的新疆写作会有哪些独属于你的痕迹?
张者:我的新疆题材是和一些作家朋友的地域背景和自然风貌不一样的,新疆太大了。刘亮程、李娟在北疆,我在南疆。他们在“地方上”我在兵团,这是自然而然的区别。刘亮程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李娟是最早的“素人写作”。李娟有生活,是素人写作的榜样。刘亮程是一个有思想的作家。他是一个智者,是一个乡村哲学家。他的文学观念和写作状态能给作家同行带来启发。
我们虽然都在新疆,中间却隔着天山。如果在内地,这相当于隔着几个省。北疆有美丽的草原,南疆有金色的胡杨。第一代兵团人无论北疆还是南疆,往往都在最艰苦的地方。比方:359旅的718团就在南疆的阿克苏,古代叫龟兹。
在寸草不生的天山南坡的山沟里,我曾经随父母度过了一段少年时光。在生活中最缺的是树。一棵树有时候比水更重要。水关乎我们的生命,树却关系到我们的心灵。水和树在我的潜意识中打下了永远不能磨灭的印记。这就是我小说的独特痕迹。
澎湃新闻:在成为小说家之前,你在新华社、《南方周末》做过记者。从非虚构转向虚构经历了什么?
张者:从非虚构转向虚构,从记者转型为作家这是奇妙的。我想不外乎三句话。首先,新闻就是新闻,文学就是文学;第二句,新闻是文学开始的地方;第三句,新闻是发生的事情,文学是想象的事情。一个是现实发生的,一个来自作家想象,这是本质上的不同。
记者无论是做新闻报道,还是做人物访谈,都会发现新闻和文学有很大区别。我当年写一件事或一个人,写着、写着就想虚构,意犹未尽。这很要命,记者必须立足事实呀。既然我喜欢虚构,那就转行当作家吧。
虽然告别了新闻职业,我依然感激那段经历。记者职业影响了我的文风,这很重要。新闻和文学虽然是两个不同概念,却是相辅相成的。记者要求文字凝练,迅速抓住事情本质,这是作家最好的训练。世界上很多著名作家都当过记者。
澎湃新闻:对于当下的现实生活,你是否也有困惑?
张者:我和中国当代作家一样,最大的困惑或者冲击是AI时代的到来。人类怎么掌控AI机器呢?
好在,人类有一种东西AI是没有的,那就是“生命”,那就是生命“意识”。虽然AI非常智能,却需要接收指令,而发出指令的是人。
未来的写作者或许是幸福的。AI可以给我们提供海量的资料,写作者再也不用在图书馆的故纸堆里查资料,做卡片了。但是,通过AI查到的只能是资料,你不能抄袭AI,抄袭AI就是抄袭我们所有人。现在无论是出版社还是杂志社,都有“查重”软件。AI查重,你无法遁形。
我想,基于生命体验的有情感有温度的创作永远是我们的独创。
澎湃新闻:有人说今天的文学现场不如过去那么纯粹,作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文学青年,你怎么看?
张者:在上个世纪80年代,大学校园里无论是什么专业的同学都是文学爱好者。大家都玩命写诗。很奇怪的是平常喜欢看小说,动笔时写出来的却是诗。这就是青春写作,靠的是荷尔蒙。少年的心需要用诗情画意来滋养心灵,伤春悲秋后需要文学疗愈。那个时代也许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
对于60和70后作家来说,所吸收的文学营养是差不多的。只不过有些作家喜欢托尔斯泰,有人喜欢卡夫卡,有些更喜欢马尔克斯等。你走进作家们的书房,在书架上有三分之一的书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读研究生没有选择中文系,而是选择了法律系。我并没有准备当什么律师和法官,我读研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想比同代作家更丰厚些。可见,我所有的准备都是为了写作。
澎湃新闻:你对当代文坛有哪些观察和感受?
张者:文学现场不如过去那么纯粹了,这是现实。过去文学是一种理想,现在文学是一种职业。现在已经有了“素人写作”。对于专业作家来说,这些写作也许会构成一种竞争关系,但专业作家内心中不应该有“鄙视链”。写作者的基数大了,对于真正文学攀登者来说,也许根基更牢固。在文学的百花园中有参天大树,也应该有绿草坪;有牡丹花,也应该有喇叭花、狗尾巴草,这样才能百花齐放。
张者早年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