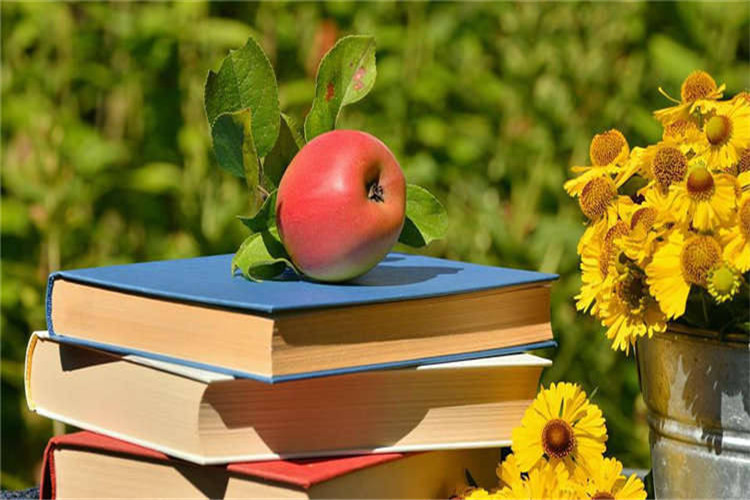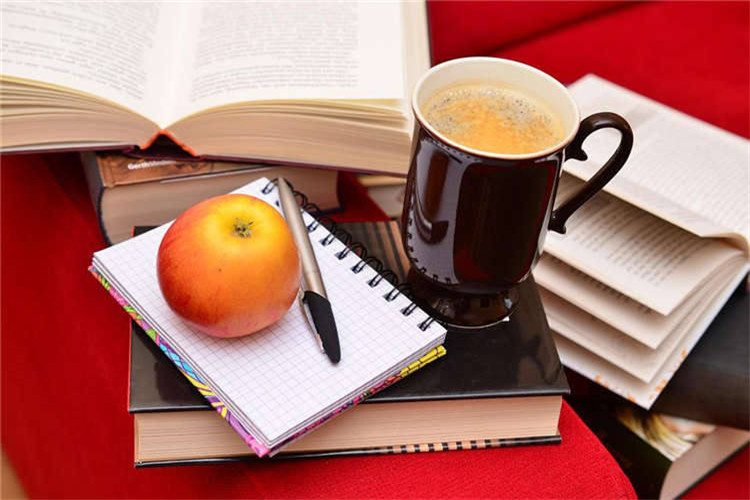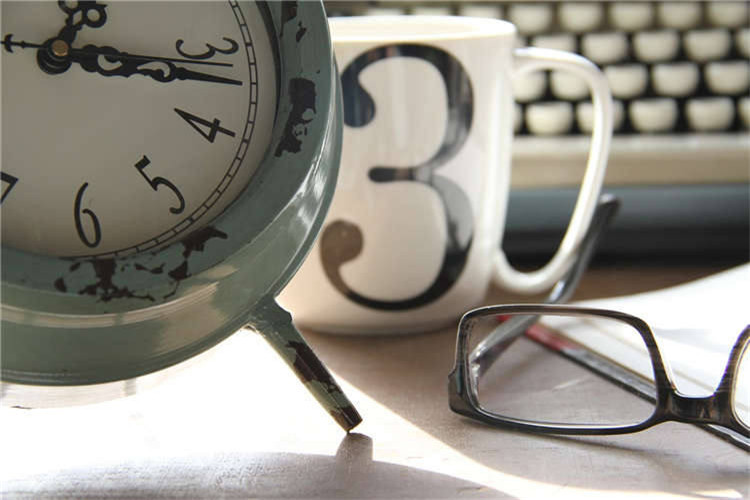他们曾在西部大地深耕理想,如今在“四叶草”续写初心。第八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一场名为“跨越山海的志愿回响”的特别体验活动,让三名曾参加过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志愿者化身一日“小叶子”,在国际舞台上服务八方来客。从支教课堂到展馆展台,从西部山川到东海之滨,他们用脚步丈量青春的广度,也用行动诠释跨越山海的双向奔赴。
从西部到进博:初心不改
第八届进博会医疗器械展区中,灯光闪烁,人潮涌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博士研究生包雨婷的目光,在一台磁共振设备前停留了很久。
“这是飞利浦首发首展的全景多核磁共振MR7700,首次将AI融入影像检查的每一环节……”包雨婷身旁的“小叶子”樊宁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正在熟练地介绍着。包雨婷作为曾经的“西部计划”志愿者,当天在医疗器械展区体验一天讲解员“小叶子”的工作。
包雨婷(左)与樊宁在医疗器械展区
她对这类设备并不陌生。但此刻,听到“术中超声”的应用场景时,她的思绪还是不禁飘到了新疆和田——那片她曾倾注一年心血的土地。在义诊途中,她曾遇到过一名肝肾功能衰竭的中年患者。那名患者曾在上海接受肝移植,辗转多家医院治疗,最终仍未能战胜病魔。
“那一刻我第一次意识到,医学并非万能的。有时候,我们能做的只是竭尽全力。”她说。
如今,站在进博会的展台前,面对全球最前沿的医疗科技,包雨婷有了新的感受。她与樊宁并肩,讲解设备原理与应用场景。“也许通过进博会这个平台,能让更多人了解前沿技术,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延伸。”
在另一侧的贵州馆,展台上色彩鲜亮的农民画吸引了许多观众驻足。画里是熟悉的山村场景——梯田层叠、屋舍斑驳、妇女刺绣、孩童嬉闹——满载真实的生活气息。
曾在贵州服务两年的赵阳,在体验贵州馆“小叶子”讲解员岗位时,瞬间就被这幅农民画夺走了注意力。站在画前的她向观展嘉宾介绍说:“我们以前帮扶的地方,也有妇女绘制这样的画作,经常能在室内陈设里看到这样的农民画。”
赵阳(左)和隋冰冰在贵州馆
赵阳曾在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区红桥街道志愿服务两年,主要的职责之一就是脱贫监测户的包保工作。那是全面脱贫后的第一年,返贫风险高,每一次入户都要仔细核对、反复确认。
她仍记得陆奶奶,75岁,和四级残疾的儿子、年幼的孙子相依为命。第一次上门时,赵阳几乎一句方言都听不懂,只能一边笑着点头,一边对照表格填信息。陆奶奶用粗糙的手拉着她坐下,递给她一杯热水,用听不懂的方言唠了半天,眼神温热而真诚。
“她的眼睛特别亮,好像不用语言也能交流。”赵阳回忆。后来每次入户,陆奶奶都在家门口等候,热情地和她打招呼。慢慢地,她开始能听懂一些简单的方言,还学会了几句贵州话,比如六盘水的地名,问老人“吃饭没有?”“孙子去上学了没?”虽然不是特别标准,但总能换来老人爽朗的笑声,连同事都笑称她成了“半个贵州人”。
那一年,陆奶奶一家是为数不多能叫出她名字的包保户,他们用方言说出的那句“妹儿,谢谢你”,让她至今难忘。
如今,站在进博会贵州馆展台前,在上外贤达“小叶子”隋冰冰的带领下,她为来宾介绍贵州的农民画、漆艺、苗药,还有酸汤、脆哨等美食,心里涌上一种熟悉的亲切感。“以前在六盘水,我们做的更多的是‘送进去’——把政策、服务和关怀送到基层群众手里。而今天在进博会,我看到的是‘走出来’,通过进博会让这么多贵州好物走向中国、走向世界,特别感动。”
从进博到西部:播撒梦想
三年“小叶子”,一年西部行。对上海师范大学的张嘉茜而言,她的两段志愿服务经历相隔千里,却像一根纽带的两端,因她简单而坚定的愿望,被紧紧地连在一起。
大三那年,她第一次走入进博会的展馆,作为第五届进博会“小叶子”在场馆内服务。那时,她在学校公众号上看到研究生支教团开设的“云端看进博”课程——学长学姐通过视频连线,把展馆中的新奇展品展示给远在西部的孩子们。屏幕那头,孩子们看到“会飞的汽车”和智能机器人时瞪大的眼睛与惊叹的神情。“我当时就在想,如果以后我也能加入研支团,就一定要把这个世界带给他们。”
一年后,她真的来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区坡洪镇中心小学,担任五年级班主任,开启为期一年的支教生活。
初到广西,现实比想象更艰难些。作为北方人,她一时难以适应山区潮湿的气候。宿舍在一楼,水泥地面常年返潮,窗框有些老化变形,衣物只能挂在窗棂上晾晒。那一年,她因水土不服频繁感冒,却依旧每天六点起床、备课到深夜,几乎没喊过一声苦。
“这些都是我早就做好心理准备的。”她说,“能站上西部的讲台,就已经是一种幸福。”
作为非师范生,她从零开始摸索教学方法。第一节语文课,她发现孩子们几乎听不懂开放性问题;课后,她主动听名师课、查教案、改教法。孩子基础薄弱,她又放慢节奏,一点点夯实。刚接手时,全班平均分不到50分,学期结束时已提升到65分以上。
真正让她骄傲的,是那堂“云端看进博”课。她将自己熟悉的进博会“带”进了西部的课堂。孩子们第一次在屏幕上看到低空飞行器、仿生机器人时,教室里爆发出一阵阵惊呼。一个叫小军的男孩盯着屏幕里闪着灯的低空飞行器,眼睛亮得发光:“老师,我以后也要开那种‘会飞的汽车’!”张嘉茜笑着回应:“那你要好好学习,保护好眼睛。”
从最初的拘谨到渐渐熟络,孩子们放学后喜欢在她宿舍窗外喊她一起打羽毛球;离别那天,微信上满屏的“老师,想你了”。那一年,她在陌生的西部留下了最难忘的青春记忆。
今年进博会,她又换上熟悉的志愿者服装,成为一名“三年级小叶子”。从最初的内宾接待员岗位,到后来的辅助管理岗位,今年她又跟随“小叶子”熊盈盈体验了一天小语种志愿者调度中心的工作。她接听外宾的求助电话,快速调度多语种志愿者,与他们一同赶赴现场解决问题。
张嘉茜(左二)和熊盈盈(左一)在小语种志愿者调度中心
“这个岗位更考验临场反应能力。”她说,“有时外宾找不到展位,有时沟通存在障碍,必须立刻判断、协调、应对。”经过短短一个小时的培训,她已能在几分钟内完成调度、反馈、处置,保障整个小语种调度系统的顺畅运行。
两段截然不同的经历,被她焐得同样火热。“无论是支教还是服务进博,我都能感受到那种‘被需要’的力量。”她说。帮助外宾顺利观展,或是看到孩子燃起梦想,“利他带来的快乐”在她心里久久不散。
而立志当飞行员的小军,仍会常常给她发消息,告诉她考试进步了几分。“每次看到他的消息,我都觉得,那些在西部、在进博会的日子,其实是一条连续的成长线。”张嘉茜始终记得,自己最初那个简单却坚定的愿望——让西部的孩子们,透过进博会这扇窗,看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当志愿的种子在生命中开花
“现在让我再选一次,我也一定会选择‘去’!”回忆起在西部的经历,包雨婷的语气笃定而温柔。
从新疆和田回到上海,她进入博士阶段,专注神经外科的科研工作。在与显微镜下的细胞、试剂瓶里的分子打交道的日子里,她偶尔感到迷茫——科研周期漫长,成果转化遥远,不确定是否能够真正“帮助到别人”。
“在西部服务的那段一线临床经历,让我重新找到了职业的根。”她说,“在那里,我能切实地帮助一个个具体的人,那种感觉特别踏实。”
她记得一名21岁的年轻小伙。那天他被送到医院时,呈现出典型的脑梗症状,医生都按照脑梗的常规方案准备治疗。但包雨婷反复对比前后两次磁共振的结果,翻阅了大量资料,觉得片子中体现的变化有些反常——不像典型的脑梗。她又仔细追问病史,得知患者入院前在海拔5000米以上极度缺氧的环境待过两周左右。
“我建议他做进一步检查。”她回忆。结果证实,病因并非脑梗,而是高原缺氧导致的血栓。治疗方案及时调整,患者顺利康复。“没有耽误治疗时机,后来他完全恢复了行动能力。那一刻我觉得,一切辛苦都值得。”
在她看来,帮助一个个具体的人,是医学最本真的意义;而现在从事科研,则是希望让更多人受益。“一个在前线救治,一个在幕后创新,方向不同,但都是在为生命努力。”
进博会与西部,这两个看似天南海北的志愿场域,缘何能吸引同一批年轻人“双向奔赴”?
上海青年志愿者协会副会长、上海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祖平告诉记者,这两者并不矛盾,是志愿精神在不同场景的体现。“无论在哪里做志愿者,核心都是在帮助他人和社会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
在不同场域中,成长的内容各有侧重。“‘西部计划’让志愿者在艰苦环境中锻炼工作能力和吃苦耐劳的品质,这是弥足珍贵的人生经历;进博会的志愿服务,则能培养国际视野与大局意识。”张祖平表示,“每种体验都带来独特的成长与快乐。”
从更宏观的层面看,这种“跨越山海的流动”也具有深远的意义。“西部计划”志愿者在支教、医疗、社会服务等领域的付出,有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我们在西部播下的种子、培养的人才和影响的孩子,都是国家未来的希望。”张祖平说。与此同时,进博会志愿者代表着中国青年走向世界的形象,展现出开放、自信、文明的新时代精神风貌。“国际友人通过与志愿者的接触,感受到中国青年的热情与专业,这本身就是一座民心相通的桥梁,也是新时代青年以实际行动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
张嘉茜在广西支教时,通过“云端看进博”课程,让西部的孩子们能透过进博会这扇窗,看到更广阔的世界。赵阳那年播下的种子,也在六盘水生根发芽——她在贵州两年的志愿服务经历,正如一抹朝阳,温暖了乡镇的清晨,也照亮了后来者的路。
“小叶子”樊宁,明年9月也将前往内蒙古鄂尔多斯参加研支团。“我觉得进博会象征着开放与包容,而在包雨婷 身上,我看到了扎根与守望。”樊宁说。
日前,新疆和田的朋友给包雨婷发来消息:胡杨林变金了。那片在沙漠边缘迎风而立的树林,像极了他们的青春——无声、坚韧,却用一抹抹金色,见证着时代的流动与志愿的延续。
志愿精神,也正如那片胡杨林,在一代代青年心中扎根、生长,年年更新,生生不息。
【青年时评】
志愿精神,跨越山海无问“西”“东”
青年报评论员 陈诗松 陈宏
今年进博会,本报策划了一场名为“跨越山海的志愿回响”的特别活动。这个充满诗意的构想,源自一个朴素的心愿:让远赴西部的大学生志愿者,与进博会“小叶子”来一场温暖的相遇。
翻阅本届进博会志愿者的简历时,我们惊喜地发现,不少“小叶子”都曾是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参与者。他们在西部的广袤天地完成服务后,回到上海继续学业,又满怀热情地走进“四叶草”。更令人动容的是,我们邀请的“西部计划”志愿者和“小叶子”在展馆内直接完成了一场双向奔赴——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说:“决定了,明年也报名来做‘小叶子’!”一名“小叶子”则回应:“已经决定明年报名‘西部计划’。”
这两种志愿服务在形式上迥然不同。“小叶子”服务于短期大型国际盛会,“西部计划”志愿者则需要扎根基层至少一年,两者对志愿者的专业素养、投入程度以及心理准备都有着不同的要求。那么,是什么让这些年轻人愿意投入时间、精力和热情?
通过深入观察志愿者的交流与工作,我们发现:在新时代青年心中,志愿服务早已突破了人们的传统认知。他们不再将志愿活动简单理解为单向度的奉献与牺牲,而是将其视为自我成长的重要阶梯——在不同岗位上的历练,恰恰是丰富人生阅历的独特拼图。
“西部计划”志愿者需要深入基层,将所学的知识全面融入当地发展。他们在相对艰苦的环境中,既锤炼了基层和群众工作能力,也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和定位。
进博会“小叶子”则身处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国际舞台,也被展商誉为世界了解中国的“彩虹桥”。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考验他们的是专业能力、应变能力和抗压能力,他们的国际视野也因此更加开阔。
今年上半年,记者曾赴新疆和田采访过的复旦大学医学生包雨婷,刚刚完成了“西部计划”志愿服务工作,回到上海继续攻读神经外科博士学位。她这次来到进博会,跟着交大医学院的“小叶子”樊宁体验了一天进博会服务后,迅速进入了志愿服务状态。曾经,她报名“西部计划”,出发点只是朴素的“想继承爷爷的遗志”,但如今,她已经在其中找到了快乐——一方面是“帮助别人”的快乐,另一方面是“感受到国际医学发展最新成果”的快乐。而和她一起服务的樊宁则说,他已经决定好了报名明年的“西部计划”,“打算去内蒙古的鄂尔多斯服务”。
志愿服务行动,在这一代青年身上,成了如喝水吃饭一般的日常。对他们来说,志愿形式或有不同,“服务社会也淬炼自我”的内在精神一脉相承。所以,无论是在边疆挥洒汗水的“西部计划”志愿者,还是在东海之滨服务国际盛会的“小叶子”,多种志愿青春跨越山海、在“四叶草”的相遇,其实是殊途同归,无问“西”“东”。
变化在年轻人群中悄然发生,这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伴随着物质的极大丰富、科技的高速发展,传统的社会职业和就业观念,正在社会的大变革中重新解构、快速重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年轻一代抓住每一个机遇,在志愿服务中找到自我价值,也在无形中拓宽了志愿精神的内涵,书写了志愿服务的新时代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