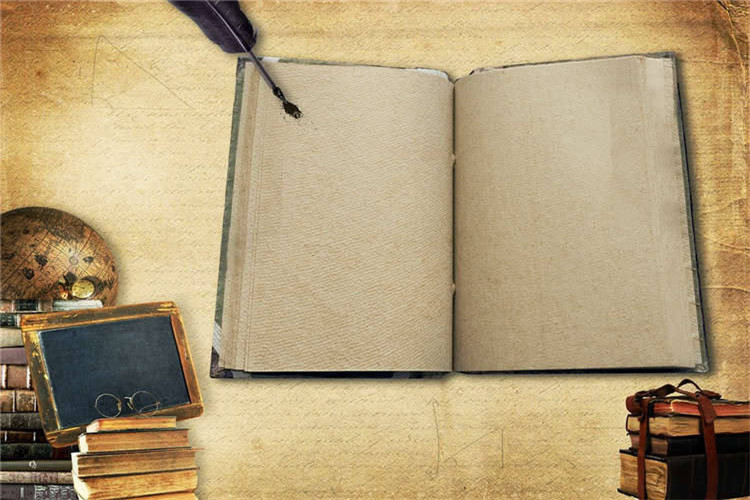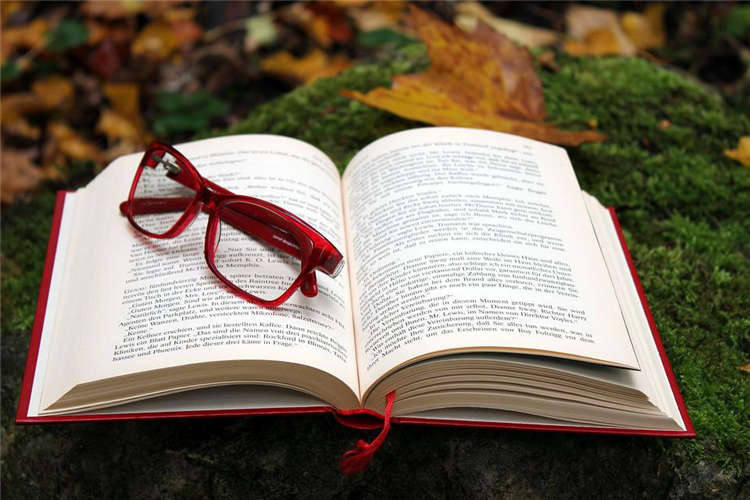《凝视远邦: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使团的视觉文化》,陈珊珊著,商务印书馆2024年10月
从多个角度看,陈珊珊博士的研究《凝视远邦: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使团的视觉文化》都具有特别而重要的意义。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这一历史事件(以下简称“使团访华”),意味着一个多重意义上的转折点。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它是200多年前一个冉冉升起的大英帝国和即将没落的大清帝国之间的碰撞,是“西升东降”的这一世界变局发生现场的微观切面,在如今“东升西降”之际,重新对其进行解剖,具有一番特别的历史意味。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这是一个鲜活的案例,一方是来访者复杂动机中充满近代人的算计,经济上要求世界市场扩张,政治上希望武力震慑,文化上坚持维护英王和其个人的尊严,而礼品风格则不乏假意的讨好献媚,而使团中具有军事、科学和艺术方面的专家,以及其冒险和科考的性质,则表明其将以冷静、隐忍和不乏敌意的态度,对这个神秘而遥远国度进行一次近距离观察。而另一方则是以一种中央帝国的傲慢,将来使团定位为远道而来的朝见者和进贡者,接见来使被理解为皇帝例行的怀远活动,策划为一场国家层面的“夸富宴”,在对来访者的行动按照天朝礼仪作了严格限制的同时,加倍回赠来访者以丰厚礼品,并居高临下地作御诗以示皇恩。这一场时代错位的碰撞,其直接的历史效应对西方远比对中国来得剧烈。在大清一方,使团来访不过是一场例行的蛮夷进贡,而在以英帝国所代表的西方列强而言,简直可以理解为对这个神秘帝国的一次祛魅活动。自此中国和中国文化在西方人眼中从一种“坐标性”的存在,一种西方人用作参考来定位自身文明的标杆,通过使团的近距离观察,呈现出其落后和愚昧的形象,这一转折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人对中国的殖民者心态,堪称“原始的东方主义”。大清仍将正在崛起的西方列强视为爪哇琉球之类的蛮夷,而处于启蒙运动中的列强正逐渐将大清列为类似印度、非洲和北美的殖民对象。其中的文化和心理的错位,为后来的军事冲突埋下了伏笔。
其实,对这个特别的历史事件中外学界均已有丰富的研究,不过多为历史学家基于文字的考察,推出的成果要么是历史档案,要么是政治和外交方面的著述。而专治艺术史的陈珊珊博士另辟蹊径,立足于马戛尔尼使团在访华期间绘制的各类视觉图像,辅以各类文字记载和后世研究成果,结合中西方科技和文化的历史背景,系统研究使团访华“视觉文化意义”,可以说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一项补白式的突破。此项研究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将相关视觉图像的科学和艺术内涵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突出出来,不仅展示了使团访华过程的复杂性,而且也让读者窥见西方在摄影技术发明之前,视觉图像的复杂功能和历史演变,以及这些与中国图景的历史演变之间的关系。陈珊珊的研究让我们摆脱了以往研究的文字论说的抽象性,以一种视觉图像的语言,井井有条地将这个历史事件呈现在读者眼前,给历史和政治事件赋予了一种更加具象和亲切的内涵。
马戛尔尼使团画师创作的使团成员拜谒乾隆皇帝场景草图
从结构上看,本书从使团访华的历史背景和筹备活动开始,按照事件发生的顺序,呈现和分析不同阶段出现的视觉图像,直至最后介绍事件的历史影响,并主张这些视觉图像在文化上可以视为“原始东方主义”。这种从头到尾逐一叙述的形式,在呈现事件的清晰发展线的同时,似乎给人一种结构单一的感觉。但正是这种看似单调的形式下,蕴含着各种文化上的矛盾和错位,而为了分析这些矛盾,作者援引了思想史上诸多著名的思想,使得本书具有了难得的立体结构。从而作者以一种学院化的结构,驾驭住政治、文化、思想等各个层次上的复杂矛盾。
首先,本书以其鲜明的主题词“凝视”呈现了一个鲜活的权力事件,因为所有外交都隐含着一个如何“看待”对方的问题。这一点对于马戛尔尼使团来说尤为重要,因为从使团成员构成来说,大量的科学家和具备制图能力的专业人士已经公开了其对神秘“远邦”的理论好奇,而这种好奇正是启蒙时代科学发展的一个直接表现,换言之,使团及其身后的科学家试图将遥远的中华帝国作为一个科学对象来考察。从古希腊开始,亚里士多德就以人类的视觉来隐喻理论活动,认为视觉相对于其他官能来说的特异性在于其最接近理论的抽象。这种视觉经过中世纪的神圣的“凝视”之后,转向了世俗世界,具体而言就是转向了自然和人类的世界。不难理解,当时的中华帝国在使团的眼中乃是一个近代科学的对象,而不再仅仅是之前耶稣会士们的神圣之眼的对象。换言之,中华帝国作为近代科学对象,可以分为不同的学科来看待,所以我们就不难从本书中识别出如地理学、民俗学、宗教学甚至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方面的图像信息。笔者惊叹于英帝国对访华这一外交行为的周密筹备,尤其是它的情报收集工作得到了英国皇家学会的直接指导,以及使团成员在其颇为紧张的行程中,竟能够对中华大地上各类风物作细致观察和记录,恨不能用显微镜窥探中国人生活的所有细节。其筹划和实施的冷静,让人惊叹。当然,使团的这种近距离观察,遇到了另一种视觉权力的抵抗。这就是中华帝国对于其外部世界那种高高在上的傲慢“成见”。中华帝国以前资本主义的俯视姿态,来应对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形式上平等的目光。这种态度上的冲突集中体现在乾隆御制缂丝挂毯与使团的记录图像之间的出入上,尤其是马戛尔尼是否在觐见皇帝时跪拜这一细节上的偏差。各自视角的出发点相互对立,体现为“泰西”与“远东”之间的对立。自此之后,从零度经线出发的凝视目光,乘着英帝国的坚船利炮一路越过“近东”、“中东”,再次抵达“远东”,征服并扭转了东方文明的视觉权力,此后这个“远邦”的知识分子也接受了自身所处的“远东”地位。
与视觉图像的科学内涵紧密相关的是马戛尔尼使团留下的众多艺术作品。这些艺术作品一方面脱胎于使团成员在旅行途中的速写和测绘,一方面又经过使团艺术家的创作,将西方人对中国的某些美好想象融入其中,从而表现出了科学记录的“如实”与艺术创作的“如画”风格之间的张力。应该说,在摄影技术尚未发明之前,“如实”的技术和“如画”的艺术是相互统一的,正如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这样的伟大艺术家兼具技术家和艺术家的身份一样,负责记录使团“看到”的一切并制作使团图像资料的成员大都身兼数职,既是军人,又是测绘员,还是艺术家。作为艺术史研究者,陈珊珊博士敏锐地将这些图像资料的艺术性突出出来,并与当时的艺术风格关联起来解释,进而以这种风格的引入来侧面解释这些图像里中国风物的美好形象出现的合理性。作为艺术固定形式的风格,自然不能完全脱离之前耶稣会士转述的中国文明形象的影响。这就导致了使团留下的具有艺术品味的视觉图像修改现实,以符合特定的美学品味的做法,而这些图像又经过版画得以在普通民众中传播,不能不说造成了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刻板印象。除此之外,使团成员的艺术创作还包含着当时流行的呈现“废墟”的创作风格,将中国大地上某些风物如雷峰塔等视为一种古希腊式的“废墟”,来表现崇高的艺术品味。这些具有典型风格的艺术作品,虽然产生于旅行记录,甚至情报收集,但经过二次创作,表达了艺术家的特殊品味和对中华帝国的另外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也构成了西方艺术史的一个特殊部分。
由于使团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作了精心准备,与乾隆视其为普通的朝贡者不同,就导致了双方留下的历史资料的不对等,所以本项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遗留图像资料,研究视角也很自然地偏向于西方,这一点从本书的关键词“远邦”即可以看出来。当然这也是历史研究的一种“如实”的态度。本书的内容丰富而精彩,其收集和整理的艺术史资料充满张力,具备多角度阐释的可能,表现出陈珊珊博士具备精深的理论知识和高超的驾驭材料的能力,笔者推测与其哲学学习经历有关。稍微遗憾的是书中收录的大量图片的清晰度还有待提高,希望本书再版之时能够整体改进,以让读者能更加真切地理解和体会本书的精彩内容。
(作者系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政治哲学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