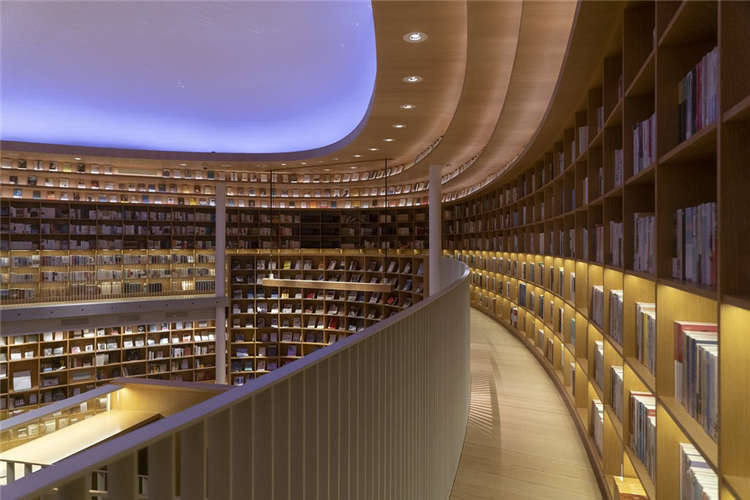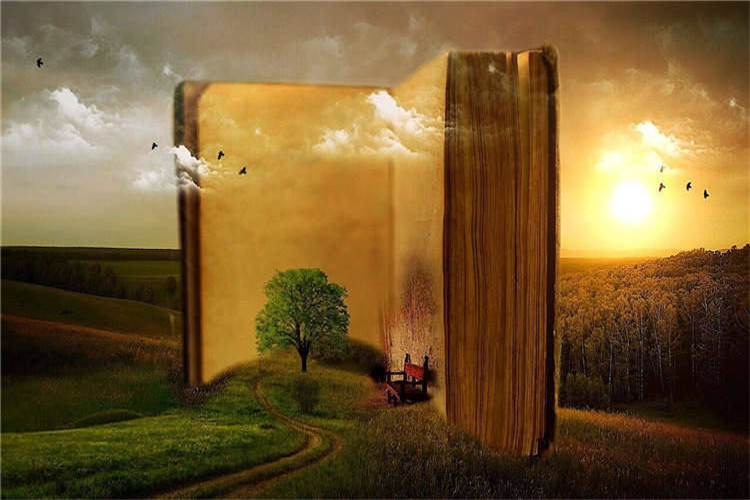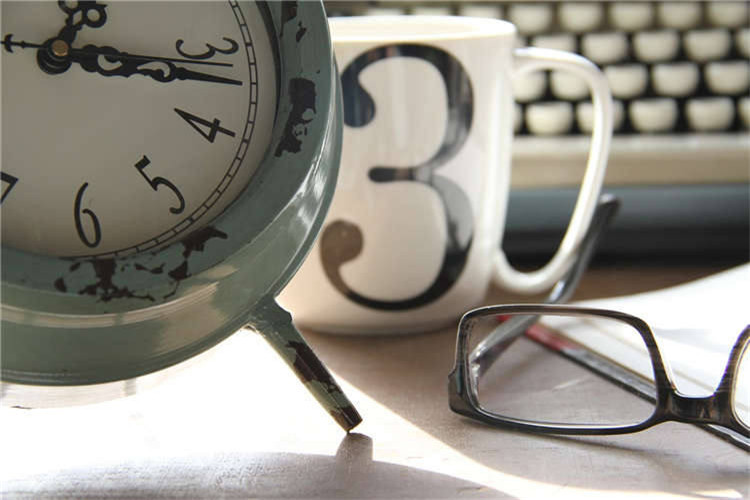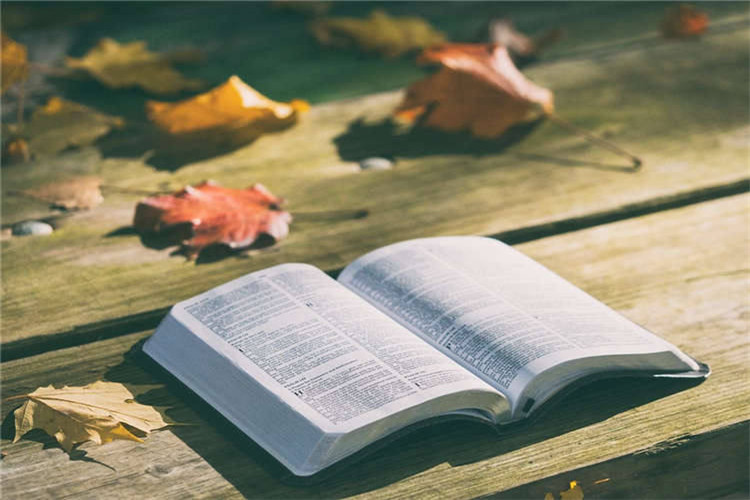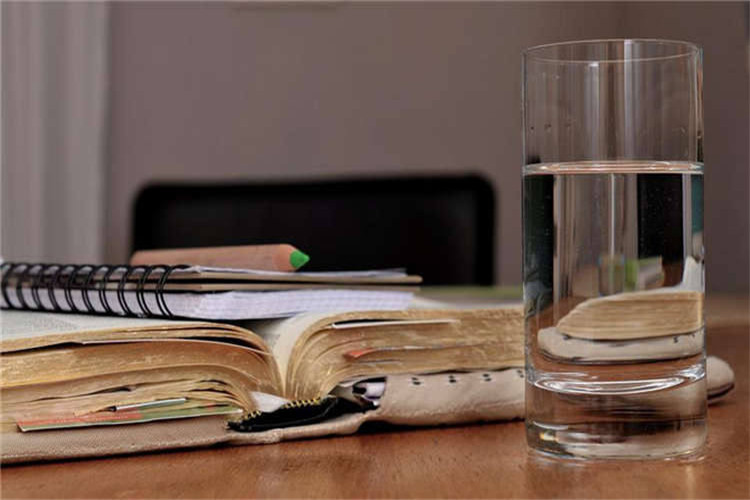结合正在举行的“其命惟新——广东美术百年大展”,上海美术馆与广东美术馆近日在沪联合推出展览特别活动中华艺术大家说“岭南文化名家大讲堂” ,由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主任尚辉主讲。以下为整理的讲座内容选摘。
最早可以从哪儿开始看到比较明确的海派和岭南画派的交集?
岭南画派当中有个叫潘兰史的人物,1907年到上海定居,加入南社。南社团结或聚集了一批在上海的广东人。潘兰史,也就是潘飞声,他和钱慧安共同发起成立了豫园书画善会,是中国近代最早的社团组织之一。潘兰史的梅花作品,让我们感受到他传统文人绘画的功底。不管怎么样,来自广东的潘兰史积极参与到上海钱慧安创办的书画善会,这是我们能够找到比较早的海派与岭南交集的一段信息。
还有重要的信息,就是岭南的“二居”,居廉和居巢。现在能够找到最早的文献证据,当然是张鸣珂在《寒松阁谈艺琐录》中提及的居廉的著作。居廉到过上海没有?如果来了,又待了多长时间?这有待于美术史家继续深入地发掘史料研究。从这样一些文献记录里面可以看到,至少在早期的海派画学的文献中可以读到居廉的信息。从居廉和海派赵之谦的作品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既土也洋,既高雅又民俗相结合,就是雅俗共赏。
刚才那些都是很小的点,回顾了现代文献中居廉、居巢和海派豫园书画善会之间的某种交集,有着最多交集的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二高一陈”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
毫无疑问,他们是岭南画派的旗帜,也是代表人物,但是特别有意思的是“二高一陈”追随孙中山的辛亥革命,1912年4月就来到了上海,实际上他们1918年离开上海,再度回到了广州。在这样短短的6年时间,他们对上海海派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二高一陈”提出的“折衷中外、融汇古今”的思想,也是海派艺术家的贡献之一。在某种意义上是不是可以说这是最早的海派与岭南交往的起点?
名家大讲堂现场
“二高一陈”在上海,不是说光人来了,他们带来了资金。这个资金是辛亥革命拿出来的资金,是想投入革命的,可以看到当时办报,办馆,推广社会进步思想,不仅仅是这种思想本身,而是通过书画的媒介,这个媒介在当时就特别重要。
今天我们回顾历史,会发现《真相画报》及审美书馆所传播的审美思想,带有先锋性,这种先锋性正是我们今天“其命惟新”的起点。广东省文联李劲堃主席谈到岭南画派纪念馆长时间以来做的多达百万字的文献研究的梳理,想论证这些艺术家实际上先是一个革命者。正是因为有了革命者这样一个社会身份,才在美术中注入思想变革的内核。
陈树人1912年在《真相画报》刊发了《新画法》一文,所涉内容与我们所知的文人绘画是不一样的。它里面有谈到透视,新画法当然是“折衷中西”,但我们不要忘了,“折衷中西”,还有“融汇古今”,这正是岭南画派在上海这6年间淬炼的思想。
陈树人 长城暮鸦 1929年 中国画 119cm×50.5cm 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藏
在审美书馆早期的出版中,除了陈树人的译作《新画法》,还有《新画选》,就是“二高一陈”在创作的新的中国画,还有十人画集,还有摄影作品集。
当然审美书馆并不可能仅仅是用广东人,它一定要用上海人。当时土山湾画馆培养的水彩画家、西洋画家徐咏青,为审美书馆绘月份牌、明信片。明信片和月份牌当然是大众美术的一种,审美书馆通过聘请徐咏青创作这样一些明信片,深深影响了民众的审美观。
徐悲鸿也曾经得到高剑父慧眼识才。1915年徐悲鸿第一次来到上海谋生,实际上是极其贫困的,是无着落的。正是高剑父、高奇峰兄弟两人以20元向徐悲鸿定制了4幅月份牌画像。这样的一种“伯乐”和“骏马”的关系,才能够有后来的徐悲鸿。我们都知道徐悲鸿是20世纪中国美术的革新者,现代美术的缔造者之一,他离不开“二高一陈”的培养。
徐悲鸿曾经在谈高剑父画作时,饱含深情回忆了他和高剑父的结识,尤其是后来他在寻访“二高一陈”的时候,说是“20年之别竟成永诀,斯中悲痛,念之凄然。”这样的经历会加深我们对徐悲鸿的一种认识。《真相画报》在当时发表了很多海派画家的作品,正是通过《真相画报》,海派画家的画风和影响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刚才谈到了黄宾虹和《神州国光社》,实际上他和岭南人的交往也是非常密切的。正是通过这个展览,让我们梳理了像徐悲鸿、黄宾虹在当时如何与“二高一陈”进行的学术交集。
第三个点,康有为是岭南人,康有为对上海的书界、画界的影响是深远的。康有为欧洲游历了一番之后,1914年到上海定居。他在上海的1914年到1923年之间,对上海的影响非常大。康有为的著作《广艺舟双楫》,他提出碑学如何不得不尊南北朝之碑的概念。康有为不仅有碑学理念,他自己也是碑学书法大家。
有关碑学和岭南,和上海是什么样的关系呢?首先是乾嘉学派的集大成者阮元,他是古文字家,提出以器物证史的学术新的发展道路,通过他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等理论著作,奠定了碑学书法传统。
继阮元之后,第二个最重要的人物是包世臣,他撰写了《艺舟双楫》,大力推崇北朝碑刻。包世臣之后,海派最为人所知的是开派领袖之一是赵之谦,其次是吴昌硕。他们都是北碑书学的践行者和倡导者。
来自于康有为所倡导的碑学传统,如何又在岭南获得新的发展?
在晚清海派书法与岭南书法上,虽然分出了华东和华南,但都是19世纪末开埠之后依托经济繁荣和对外交流形成了兼具传统根基与革新意识的地域书风。它的发展轨迹深受碑学的影响,两地书风均突破了清代前期帖学独尊的窠臼,积极回应了阮元、包世臣倡导的碑学理论,海派当然是赵之谦,岭南是陈澧、李文田,乃至康有为和梁启超。
从阮元开始到包世臣,分出两批,一批是在上海,一批是在岭南。中间有一个人,就是来到上海的康有为。康有为和“二高一陈”在哈同花园雅集会面,这个会面思想的交集是特别重要的。中国现代美术首先是学习西方,学习西方这个概念,除了“二高一陈”,我们找到最早的源头是康有为,康有为最重要的一句话:“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这是他在《万木草堂藏画目》中提出的一句口号,这是我们学界、理论界经常引用的一句话,这个思想当然有康有为游欧的经历所造成的,但是这个经历怎么才能够散发出来?我认为在哈同花园和“二高一陈”思想的碰撞,才能够强化当时中西相互结合的这种思想和观念。
还有海派最重要的艺术家刘海粟和康有为的交往,康有为对刘海粟赏识有加,是异于常人的。 1921年刘海粟正式拜康有为为师,康有为欣然为海粟的作品写下了“天马行空”这样的字,在某种意义上对刘海粟在当时的办学提倡西学又助了一把力,对刘海粟个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康有为还曾经写过一段画论赠给刘海粟,“画师吾爱拉飞尔,创写阴阳妙逼真。”这段话可以体现出康有为对西学写实主义画风的一种倡导,这在当时都是开风气之先的。因为利玛窦把西洋画传到中国,尤其是传到宫廷之后,当时的文人画家认为画得很工整,但是没有画意,缺少品位。“虽工无意”这是当时文人画家给西洋画的一段评价。康有为的“画师吾爱拉飞尔”这段话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觉得“折衷中西”没有什么难的?在那个时代崇尚国粹的艺术家占到了99%,有这样的文人来说这样一段话,意义是非同凡响的。
除了刚才说的康有为和上海碑学书法渊源,以及通过哈同花园和“二高一陈”的会面,包括刘海粟、徐悲鸿在内的赏识,都形成了岭南和海派艺术家的交集。在这种交集中,还有鲁迅对广东新兴木刻家的影响。鲁迅在1931年8月17日至22日,在上海举办了一场木刻讲习会,一共有13位青年木刻家来参加,其中广东人占了近1/2。
我们重新发现新兴木刻运动,发现鲁迅和广东美术家的关系是非常有意义的。其中有鲁迅对广东木刻家陈烟桥木刻艺术的指导。
汽笛响了 陈烟桥 版画 1934年 广东美术馆藏
怒吼着的中国 赖少其 版画 1938年 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藏
除了陈烟桥,我们还可以找到赖少其,1949年上海解放以后,赖少其是华东局专管文化的局长,他一直到1959年才调离上海。上海中国画院,他是最重要的筹办者。赖少其对上海解放初期的美术的贡献,不容置疑。但是赖少其接受鲁迅的思想是在1934年,赖少其当时是诗人,他写了字、诗与版画的手稿寄给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给他回了一封信。鲁迅给他的回信中说:“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妨做做这一木一石呢?”鲁迅对青年木刻家的影响都是通过文字凝固下来。当然还有最重要的是李桦先生。他思想的根源就是1934年、1935年受鲁迅的影响,是不是也是和海派的一种密切的交集呢?或者是鲁迅作为新文化的旗手,作为新兴木刻的导师,他长期生活在上海,是上海这座现代城市给予他很多思想的荟萃,他的思想又转化为对新兴版画的指导,又延伸到广东,这就是我们能够找到的一些线索。当然还有最重要的是黄新波。黄新波是广东台山人,1935年来到了上海,特别珍贵的是鲁迅去世以后,黄新波用他的刻刀刻下了《鲁迅遗容》这样一幅不朽的名作。还有古元、胡一川等。
鲁迅先生遗容(1936年) 黄新波 作
海上现代美术运动中的广东人,这也是我们特别想探讨的内容。首先是1919年,刘海粟、杨清磐等在上海成立天马会,天马会里面提出了国粹画、折衷画、图案画。折衷画的概念,是不是和高剑父有关呢?至少在这个画展的画册里面,我们能够看到高剑父的画作是这个陈列室的第一幅作品。传统中国画叫国粹画,新国画叫折衷画。折衷中西的概念,1919年通过“二高一陈”在上海就传播了这样一个思想。当然,在现代主义美术运动中,1921年在广州举办的第一个西洋画展览,被我们称之为尺社第一次西洋画展览。
1932年,上海成立了决澜社,在广东和上海之间,他们既有交集,也有分别举办西洋绘画展览和现代派画社成立的展览的这样一个史实。
回到广东人在上海举办现代美术展览的事情。首先,当然就是赵兽。1935年8月,赵兽与李东平、曾鸣在上海开展览活动。这次展览后来在《艺风》月刊上做了很多插页的报道,凝固这样的一个事件。
赵兽《饮早茶》 油画/57cm×79.5cm/1969年 广东美术馆藏
在我们的印象中陈抱一是上海的西洋画家,追求印象主义和后印象主义的画风。他出生于上海,原籍广东新会。他1907年就在上海开始学习艺术,1913年赴日习西画,回国后设绘画研究所、与蔡元培等创办中华艺术大学,历任多校西画教授,推动上海现代美术与油画教育发展,1945年病逝于上海。这样一个原籍广东人,实际上出生于上海,后来也生产、创作、教学于上海,但是他是广东人,在后印象主义的作品里面,体现出浓浓的岭南人的学风和味道。
陈抱一《关紫兰像》 油画/72cm×60cm/1930年 中国美术馆藏
陈抱一的学生关紫兰是广东南海人,和康有为同乡。她也出生在上海,是广东籍的上海人,我们这次展览里面关紫兰的《少女像》正在展出。她是30年代的上海名媛,她的作品的艺术水平非常高。
关紫兰《少女像》 油画/90cm×75cm/1929年 中国美术馆藏
这次展览一个特别重要的展区,是关良的作品。相信多数人都认为关良是上海的代表性画家,实际上他是广东番禺人。他1922年到上海神州女学任教,之后一直生活在上海。他最重要的是和广东人丁衍庸成立了艺术俱乐部,从上海又辐射到广东。1986年病逝。他画的戏曲人物是我们所熟悉的,他还有最重要的油画,受到马蒂斯野兽派的影响,也具有立体主义的影子,但实际上他还是中国画体系的油画。
展览现场
最重要的当然是林风眠先生。林风眠先生在1949年之前来过上海,他到法国留学的时候,实际上是从上海出发的。他真正定居上海是1951年之后,林风眠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些作品都是在上海创作的,一直到1977年他离开上海,移居香港。我们前不久在上海美术馆举办了“中国式风景”,这个展览一方面强调他是上海的画家,另一方面强调了他是中国式风景,是广东人在上海这片土壤里面成长出的现代艺术之花,通过这样一些简单地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广东美术百年大展和上海这座城市千丝万缕的联系。
林风眠 青衣仕女 20世纪60年 中国画 66cm×69cm 上海美术馆藏
这个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史学轨迹。我们今天讲座的题目是缔造中国现代美术——海上岭南。海上岭南有两重意思,一方面上海和岭南是并列关系,这两个地方共同缔造了中国式现代美术。海上岭南也表达的是海上的岭南人在上海如何进行现代美术缔造。
做个小结,中国现代美术的发生既是中国迈进现代社会自我变革的必然,也是积极引荐西方美术为我所用的结果。这个实际上是“二高”提出的“折衷中西”的概念。上海和广州作为中国开埠最早的通商口岸,在建立现代城市的过程中,均得益于口岸文化的开放性,从而形成了这两地的互动与对中国现代美术的共同缔造。广东美术百年大展不仅让我们审视学习、研究广东美术百年发展历程,更重要的是我们从这个展览里面看到广东美术百年历史和上海的一种关系。
第一,“折衷中西、融汇古今”是“二高一陈”提出来的,是岭南画派的精神,但是我们之所以把它当作20世纪的一个最重要的实践路径,是因为这8个字高度概括了中国现代美术的理论模型和实践路径。它的理论模型就是中国现代美术的发生和西方有关,但是要进行折衷,要进行融合。
上海和岭南之所以能够形成共同缔造中国现代美术,是因为“折衷中西、融汇古今”思想由岭南人在广州生发,很多的集萃、融汇都是在上海来实现的。
第二,海上与岭南都在清代“碑学中兴”的背景下,形成“以碑入书、以书入画”的书画变革方向。海上花鸟画与岭南山水画、花鸟画,也都形成了相近似的雄强、厚重、苍茫的画风,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国画的现代性探索。
第三,受辛亥革命的影响,“二高一陈”的新国画,以及海派画家钱慧安、“海上三任”任熊、任薰、任颐等人的作品,都着重表现劳苦民众的生存现实,是现代中国画在创作理念上走向现实主义的先驱探索。
第四,新兴木刻正是因为广东木刻家对鲁迅思想的积极回应,而推动这场运动的持续开展,并在艺术实践上真正引领了新兴木刻的蓬勃发展。新兴版画最重要的艺术家和作品,都少不了广东木刻家。而且广东木刻家所达到的艺术水准,也代表了新兴木刻的艺术高度。
第五,广州、上海都最早成立了中国现代美术社团,是中国现代主义绘画的先行地。以刘海粟、林风眠、倪贻德、庞熏琹、陈抱一、赵兽、关良、关紫兰为代表的现代绘画探索,给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现代艺术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也就是说改革开放时,使西方现代主义再度回到了中国,但是林风眠、刘海粟、陈抱一、胡根天、赵兽他们是这个现代主义运动的先行者。而林风眠对“折衷中西、融汇古今”的深入实践,成为中国现代美术最鲜明的,他的成就也标志着上海与广东在中国现代美术的共同缔造。
(本文据“岭南文化名家大讲堂——缔造中国现代美术的海上岭南”讲座整理,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