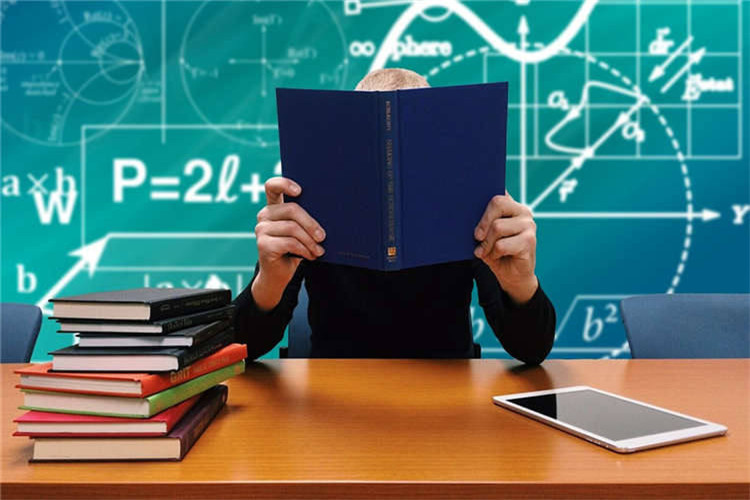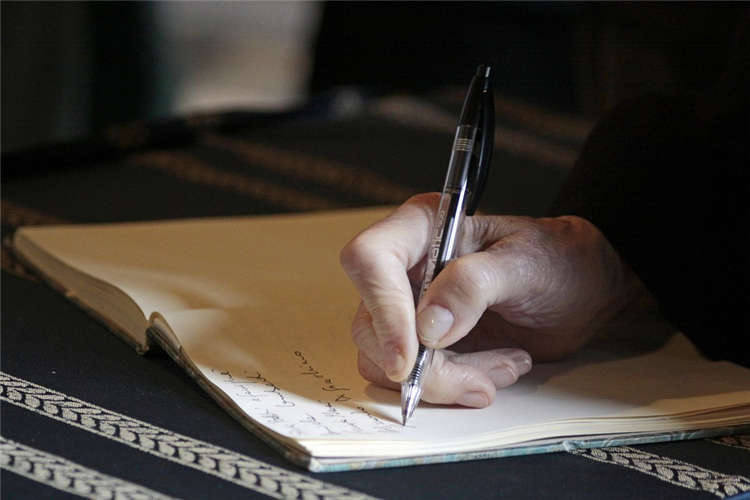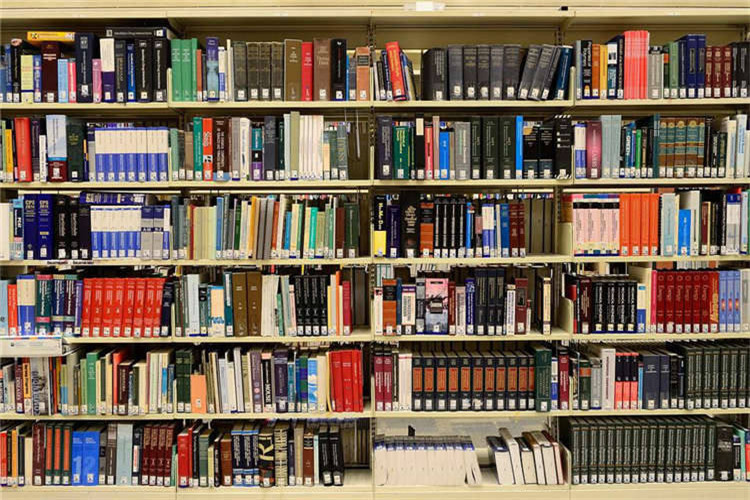按照清政府确立的立宪与变法修律宗旨,清政府的修订法律馆和宪政编查馆先后修订、制定或起草了一系列法律和法律草案。这些法律和法律草案具有明显的“大陆法系化”之特点。
晚清时期衙署理案
宪法
“宪法”一词,我国古已有之,《国语》中就有“赏善罚奸,国之宪法”的话。但是,在我国古代,“宪法”以及涉及“宪”字的词汇,只是国家典章或普通法律的代名词。近代意义的宪法概念和宪法文本,是随西方文化与法律学说的传播而输入中国的。清朝末年,制定宪法被认为是医治中国百病的良药和复兴中国的良策之一。在国际国内的压力下,清政府被迫于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在“各项法律详慎厘订”等基础上,“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被迫公布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并宣布经过9年预备立宪期限之后,再颁布根据《钦定宪法大纲》制定的正式宪法。《钦定宪法大纲》共23条,由正文《君上大权》14条和附录《臣民权利义务》9条两部分共同组成。其内容,基本抄自1889年2月11日颁布的《日本帝国宪法》;有17个法条竟完全抄袭《日本帝国宪法》,占全部法条的74%。而1889年《日本帝国宪法》又是以普鲁士宪法为蓝本的,竟有46个法条完全抄袭普鲁士宪法,占全部法条的61%。
究其原委,日本近代宪法之父、法学家伊藤博文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1882年,伊藤博文受天皇派遣赴欧洲考察宪政。伊藤博文认为,普鲁士的政治制度与日本极为相似,普鲁士的宪法最适合日本统治阶级的需要。伊藤博文的看法,得到了日本统治集团的赞同。伊藤博文回国后,立即被天皇任命为宫内省大臣,并领导宪法委员会起草宪法草案。在伊藤博文的主持下,1888年,《日本宪法》及其附属法《皇室典范》《议院法》等法律草案起草完毕,并经枢密院审议通过。1889年,《日本宪法》及其附属法正式颁布。次年,正式付诸实施。1906年,载泽到日本考察宪政,与伊藤博文“从容讨论,以求立法之原理,与其沿革损益之宜”。伊藤博文还在日本芝离宫就日本宪法向载泽等人做了演讲,并特别就日本天皇的权力大加宣扬,深深地打动了载泽等人。例如,伊藤博文在演讲时说:“日本宪法中,言君主大权之事,共有17条,贵国为君主国,以上所论种种大权,将来施行宪法时,必须归之君主,而不可旁落者。”载泽等人起草的《钦定宪法大纲》的序言即曰:“君主立宪政体,君上有统治国家之大权,凡立法、行政、司法,皆归总揽。”
刑法
清末以前的封建刑律,与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制度相适应,采取“诸法合体”的编纂形式,集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等内容于一体,用刑罚方法调整各种社会关系。修订法律馆在开馆之后,继承历代封建法制建设的传统,视刑律为国家的基本法律,决定首先修订刑律,于1904年即着手对《大清律例》进行删削、修改和补充,以此作为在新刑律颁布之前的过渡性法典。“预备立宪”的诏令颁布之后,修订《大清律例》的工作被纳入《钦定逐年筹备事宜清单》。1908年,修订工作完成。修订后的《大清律例》定名为《大清现行刑律》,于1910年公布施行。
《大清现行刑律》虽然是在《大清律例》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其体例和内容仍然没有脱离旧律的窠臼,但是,它作为清末仿照西方模式进行法制改革的产物,已经吸收了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的部分内容。其主要表现是:(1)改革名称。将律名改为“刑律”。封建刑律一般总称为“律”,如《开皇律》《永徽律》《大明律》《大清律例》等。《大清现行刑律》则以“刑律”为名。“刑”,表示刑罚,使它与民事、行政等部门法相区别;“律”,作为“法律”的略语,表示经过立法机关制定和行政机关公布,使它与命令、习惯等规范形态相区别,使中国的刑事立法步入近代化的轨道。(2)改革体例。取消《大清律例》按照封建王朝中央政府机构六部名称(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而设的六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类目体制,并依据社会危害性程度的轻重进行排列,近似根据犯罪的同类客体而重新设置篇目,为中国刑事法典体例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3)改革刑罚。废除了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等酷刑旧制,确立了罚金、徒、流、遣、死五刑制度,使中国的刑罚制度开始近代化。(4)改革罪名。删除“良贱相殴”“良贱相奸”等具有明显封建特征的罪名,增加“妨害国交罪”“妨害选举罪”“毁坏铁路罪”等具有明显近代特征的罪名。
清朝政府在修订《大清现行刑律》的同时,也开始制定新刑律。1906年,修订法律馆聘请日本法学专家冈田朝太郎担任顾问,遴选了一批国内法学专家分别担任纂辑,历经三年,四易其稿,于1907年下半年编成《大清新刑律草案》。1910年11月5日,宪政编查馆核订告竣,定名为《大清新刑律》。1911年1月25日,清朝政府正式公布《大清新刑律》。
《大清新刑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模仿大陆法系国家刑法体例而制定的刑法典。其主要特征是:(1)仿照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的体例。首先,删除全部与定罪量刑无关的内容,使它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独立的刑法典。与用刑罚手段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的封建法典相比,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司法镇压的残酷性。其次,确定新的刑法法典体系,分刑法内容为《总则》和《分则》两编。《总则》,虽然在本质上无异于封建律典的《名例》,但是其内容却更加丰富完备。《分则》以罪名为纲领,按犯罪客体分章规定各类犯罪及刑罚,弥补了传统律典中章名既不概括罪名又不便于检索的缺陷。(2)采取了大陆法系国家的刑罚体系。摈弃了身体刑,废除了以封建乡土观念为基础的流刑和折磨肉体的笞刑、杖刑,确定了一个以自由刑为中心,由主刑(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罚金)和从刑(褫夺公权和没收财产)组成的新刑罚体系。同时,大大减少了死刑的法条,并且减轻了执行死刑的残酷性,“死刑用绞,在狱内执行”,罪大恶极者才用斩。(3)吸收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制度。采用罪刑法定原则,规定:“法律无正条者,不问何种行为,不为罪。”根本否定了封建专制统治之下的罪刑擅断和诏敕断罪的制度。引进缓刑、假释、时效制度,专设《缓刑》《假释》《时效》章。对青少年犯罪,采行感化教育制度,开我国对刑事责任年龄以下的青少年犯罪施以感化教育之先河,还创设了《妨害安全信用名誉及秘密罪》等调整近代社会关系的专章。(4)删除了以家天下和宗法制度为根据的“八议”、请、减、赎、“十恶”和“存留养亲”等封建刑法制度。
民法
1907年,新设立的商部根据朝廷修订法律谕旨,奏请制定民律。不久,朝廷下令设专门机构,并聘请日本法学家志田钾太郎、松冈义正为顾问,起草民律。1911年8月,《大清民律草案》完成。“全案大体仿德日民法”,草案分为五编,总计1569条,因清朝覆亡未及公布。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专门民法典草案,仍特别值得注意。(1)其编纂体例,完全模仿日本民法和德国民法,采取“潘德克吞式”(Pandekten System),即将整个民法典的内容分为总则、债权、物权、亲属、继承五编,此为大陆法系民法典的典型编纂体例之一。(2)草案采用了大陆法系的诸多民法学说,如《拿破仑法典》(1804)、《德国民法典》(1900)所强调的“意思自由”“契约自由”“过失责任”“私有财产权不受限制”等重要原则。此即所谓“原本后出最精确之法理”。(3)“注重世界最普通之法则”,如在“关于法人及土地、债务诸规定”方面,“采用各国新制”,即抄袭德、瑞、日民法中的相应制度,亦即罗马法以来欧陆民法中的民事主体、代理、时效、法律行为制度,以及欧陆各国在契约、物权、债等方面的一系列典型制度。总之,其民事律草案的总则、债权、物权三编大多取自德国、日本、瑞士民法典;而亲属、继承二编除取自欧陆日本民法外,亦沿袭了中国封建礼教的一些内容。(4)广泛调查民商习惯。为起草民律,宪政编查馆派员到各省或指定各省委派专员负责调查各地民事商事习惯,作为民律起草之基础。此种做法,亦为受大陆法系尤其是德国法影响的标志。《德国民法典》的制定,是在萨维尼“历史法学派”理论指导下广泛采取民族习惯法而成的,而清末民律草案编制采用的是同一条思路。
商法
清末商法创制也受到大陆法系的影响。1903年3月,清廷命载振、伍廷芳、袁世凯等编订商律。次年1月,公布《商人通例》9条、《公司律》131条。1906年,又编制公布《破产律》69条。1908年,修订法律馆又聘请日本学者志田钾太郎帮同编订商律,次年完成,定名为《大清商律草案》,内分总则、商行为、公司法、海船法、票据法等五大部分,共1008条。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商事法典,但由于清亡而未及颁行。该法典的体例,基本上与1899年《日本商法典》一致。其以商法为独立法典,而没有与民法合典,更是模仿日本及当时欧陆“民商分离”体制。该草案在提交资政院核议时,人多讥其为直接抄袭日、德等国商法,不合中国国情,乃多有质疑。农工商部不得不据我国旧有商事习惯的调查加以修订。
诉讼法
1906年4月,沈家本等完成《大清民事刑事诉讼律草案》,共5章260条。因各省督抚反对,清廷未敢颁布施行。这是中国第一个专门诉讼法典草案。该法典首次引进了欧陆、日本广泛使用的陪审制度、律师制度、证据制度及涉外诉讼程序等制度。1910年12月,沈家本等人又将该案一分为二,完成了《大清刑事诉讼法草案》和《大清民事诉讼法草案》两案。《大清刑事诉讼法草案》基本上是照抄1890年《日本刑事诉讼法典》体例,分为总则、第一审、上诉、再审、特别诉讼程序、裁判执行等6编,共15章514条。《大清民事诉讼法草案》基本上是照抄1877年《德国民事诉讼法》和1890年《日本民事诉讼法》,分为审判衙门、当事人、普通诉讼程序、特别诉讼程序等四编,共22章800条。这两个草案更加广泛地借用了欧陆、日本诉讼法中的公诉自诉分离、不合管辖者不受理、依证据定罪、预审、诉讼代理、辩护、陪审、和解、强制执行等制度。这两个法典草案均未及审议颁行。在当时司法中真正暂充诉讼法的是1907年颁布的《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该章程共5章120条,其体例及作用有些像日本民刑诉讼法典之前的《法院断狱则例》。
法院组织法
1906年12月,清政府法部拟定了《大理院审判编制法》,全法分为45条。这是我国第一部正式的法院组织法,唯其所定仅以京师为范围。1910年,法部又在前者的基础上编成《法院编制法》,16章164条,这是全国各级法院之统一的组织法。该法在体例上大致模仿《日本裁判所构成法》,分为审判衙门通则、初级审判厅、地方审判厅、高等审判厅、大理院、司法年度及分配事务、法庭之开闭及秩序等16章,各部分内容也与日本略同。关于审判等级,该法亦仿德日体制,定为四级审判机关,三审终审体制。最为重要的是,该法广泛采取了包括大陆法系诸国在内的欧美日等国普遍采用的行政与司法分离、司法独立之体制和原则,采行欧美日通行的独任制与合议制并用、司法官考试任用、检察制度等制度。这都是中国司法组织近代化的典型标志。
至此,中国的“六法体系”已初现端倪。以宪法为统率,包括宪法、民法、商法、刑法、诉讼法、组织法在内的六大法典体系,即所谓“六法体系”(也有人说“六法”为宪法、民法、商法、刑法、民诉法、刑诉法等六者;更有人说六法是将前六者中民刑两个诉讼法合视为一,再加上行政法等六者)。“六法体系”,正是大陆法系即“法典法系”的典型特征。法国曾有所谓“法兰西五法”(宪法在外)之说,德国亦有“德国六法”之说。日本仿之,编成“六法全书”。中国法律近代化工程,一开始即采取此种模式。这是近代中国法制“大陆法系化”的典型体现。
(本文摘自范忠信著《殊途同归:中西法文化的暗合与差异》,山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9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