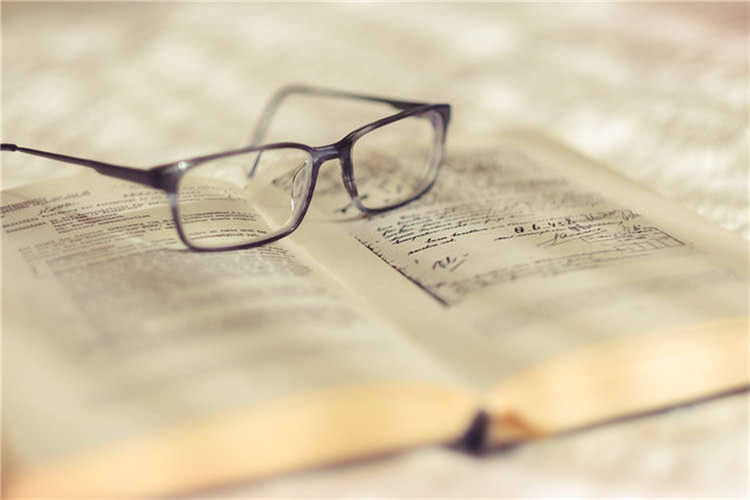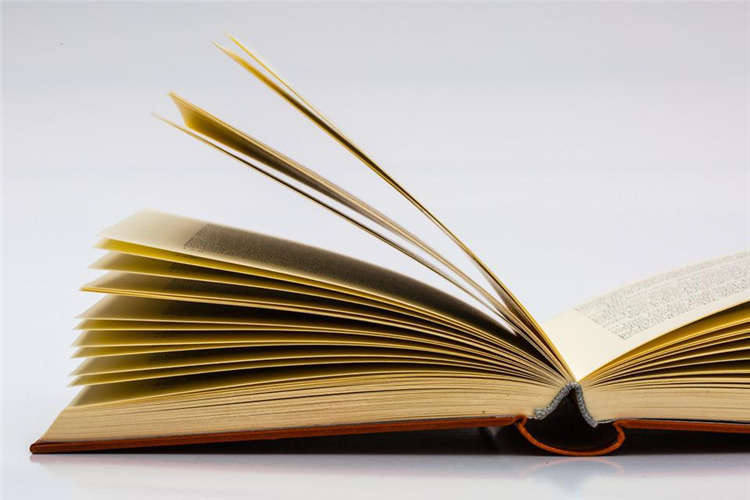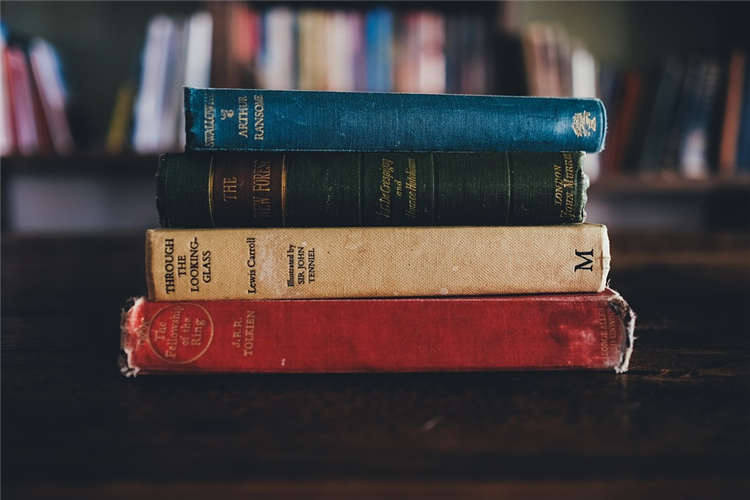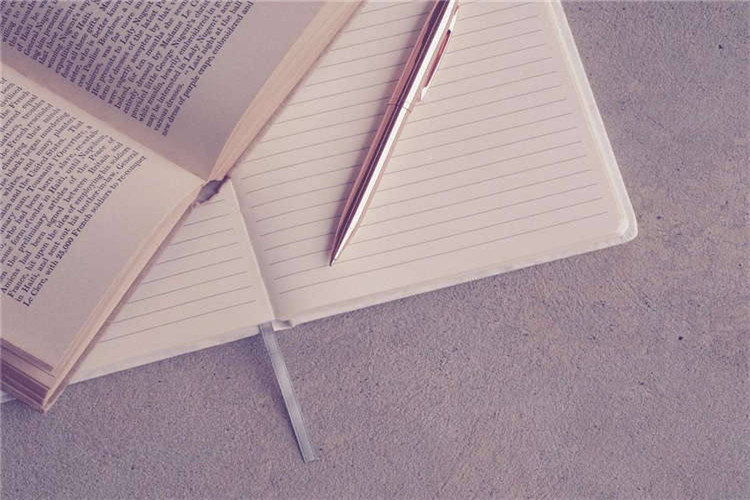作者 | 永舟
编辑 | 青霆
一段录音,将王家卫的墨镜砸在地上。
10 月底,青年编剧 " 古二 " 在网上曝光了多段录音,内容是知名导演王家卫与电视剧《繁花》的编剧秦雯等人的私人谈话,涉及多位知名演员和剧组内部的细节。其中包括王家卫对部分演员人品、身材的点评,且不乏负面词眼。此外,录音还涉及了掠夺编剧署名权与劳动成果的相关嫌疑。爆料者古二指控称,自己为《繁花》编剧付出了大量创造劳动,创作贡献却被王家卫团队拒绝承认且无偿占用。
历来神秘、曲高和寡的王家卫被偷袭,粗言不慎暴露,遮挡真实情绪流动的墨镜,猝不及防碎在了地上。从表面上看,王家卫私下言论令人惊诧,但如果真的要对整件事情进行道德评判,古二将私密聊天的擅自曝光,也是 " 小人 " 之行。
他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底线,且利用自己在某些事情上的弱势立场,擅用舆论私刑对个人进行审判,以期达到维权或报复的目的。舆论霸凌的恐慌,平等蔓延到了每一个人身上。
如古二所愿,录音公布后,的确在公共舆论中引发了一场道德审判。不过,即便擅用 " 私刑 " 似乎更值得警惕,但明星演员的八卦,以及关于创作行业内部的压榨、侵占等权力结构弊病,终究引发了更大面积的公共关注。
这不难理解。大众会自动关心带有八卦性质的信息,也会更关心与资源和权力分配相关的话题,因为这涉及每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不过,到了今天,八卦的分发机制早已改变,权威者完全意料不到自己可能 " 栽 " 在什么人手上,而实施舆论审判的普通人,也不再能掌控曝光程度与公共话语的流向。
作为香港 " 意识流 " 影像的领军人物,王家卫最初被世界看见,就像他的墨镜一样,是戴着一层新奇滤镜的。
这既是美学上的,也是叙事上的。近乎炫技的光影运用,高饱和度色调、抽帧、诗意的台词和情绪至上的画面,以及不怎么连贯和明显的叙事逻辑。《花样年华》里欲语还休的情欲,《重庆森林》里在都市丛林生长的潮湿的浪漫,《一代宗师》里写给武侠情怀的温柔挽歌。独属于现代文明的精神放逐,灵与肉的迷醉,是王家卫宇宙里属于人物和故事的滤镜。
" 墨镜王 " 开创了一个派系,这导致观众对他持以某种量身定制的宽容。他可以把故事讲得不那么明朗,可以随心所欲、放飞自我,他的电影不需要多么宏大和巍峨。他把那个年代最迷人的人物邀请到他的光影世界里,耐心地诠释那些孤独、虚空和情欲,他就胜利了。不仅对观众胜利,对那个电影的黄金年代也胜利了。
偏才的人被允许偏执。在这次风波之前,王家卫的神秘个性,在坊间传说中都是美言。哪个艺术家没点个性?王家卫的墨镜和他的滤镜一样,在公众心中一直是艺术的一部分。
他对导演主体性的绝对坚持,也在业界早已名扬。比如对演员一视同仁的高要求。拍《阿飞正传》时,王家卫让梁朝伟将一句台词说了 27 遍,梁朝伟回家后,被打击到大哭;刘嘉玲有一场擦地板的戏,擦了 20 多遍,王家卫还是不满意;拍《一代宗师》时,一场雨中打戏,他足足拍了 30 个通宵。
对创作要求的绝对精准,在大导演光环犹在的时候,这是艺术家的精益求精,是对演员的严格和对创作的敬意。
事实上,即便到了这次录音事件里,王家卫对镜头和表演的坚持也并未被打破。在谈到演员现场改台词时,他毫不犹豫地表示,如果他在现场,是绝不允许演员更改台词的。
根据王家卫的性格,如果这个话题是在采访情境里被问到,他大概率也会表达相似的意思。
王家卫从不轻易摘下他的墨镜,也不稀得掩盖个性。一个大导演在工作上有点个人的癖好,对演员挑剔一些,无可厚非。一个在创作上性格犀利的人在人际关系上也中庸温和,反而不太 " 正常 "。
2009 年,被控性侵未成年的法国著名导演、曾多次获得奥斯卡的波兰斯基在瑞士被逮捕,当时,包括王家卫在内的 100 多名全球电影人公开声援波兰斯基。在戛纳电影节组委会牵头下,王家卫参与了一封联名信,称波兰斯基是 " 当代世界最伟大的导演之一 "," 法国的、欧洲的、美国的、全世界的电影人均对这一事件表示关切 ",而波兰斯基被捕则是他们 " 不可接受 " 的。
这件事折射出文艺创作领域一个永恒的悖论,即作品价值与创作者个人道德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不是必然的,但一旦出现,就会陷入尴尬。理想状态下,有才有德最好,但当艺术成就达到一定水平,一个人的道德失范极易引发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态度:一个是绝不能容忍的震撼,即那种跌下神坛的震动和 " 塌房 ",还有一种,是对才华者的无限宽容。
而希望保护才华,牺牲道德,甚至不惜牺牲无辜者的观点,在戏剧、文学等领域一直受到不少人的支持。
在互联网信息还不如今天这般发达的当年,联名信事件不大可能在网上大面积传播,王家卫也许躲开了 " 塌房 " 一劫。可回看这起发生在十余年前的风波,便对王家卫 " 凡俗 " 的那一面不能感到惊奇了。
从电影里看,其实更是如此。电影里那些欲望、婚外情、孤独呓语,带着斑驳锈迹的欲语还休,它们只通往私人内心深处的匮乏。感受是流动的,但德性需要精神层面的稳定性。
因此," 王家卫塌房 " 虽然乍听稀奇,似乎光环碎了一地,但细细想来,其实也并不奇怪。王家卫的电影之所以精彩,因为它留下了许多与现代人生命经验息息相关的东西,对艺术来说,它们是可贵的。但它们从未向二十年后的世界,许诺一个 " 温良恭俭让 " 的王家卫。
事实上,王家卫的诞生与存在,本就有时代因素。九十年代中后期,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出现渐衰之势,曾经的商业奇迹不复持续。王家卫这样 " 非主流 " 的导演,也在当时的洪流中找到了市场的另一种可能。也可以说,他一开始就有了底气,不必迎合商业市场。
如今,他的 " 塌房 ",也有时代因素。第五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新媒体载体的多样化,对传统信息分发模式进行了解构,也直接导致了对各领域权威者的解构。在一段录音、一张聊天截图面前,一个公众人物的所有外在形象都可能被瓦解,对应地,通过自上而下分发的作品来构建对一个人的认识,也越来越行不通了。
这些年内,发生在公众人物身上的 " 塌房 ",不少都是被私人录音、聊天记录曝光出来的。这已然成为新媒体时代的特色。对公众人物私人生活的曝光和讨伐,不再是通过娱乐记者的蹲守、尾随和长枪大炮狙击,而是私密关系里的 " 背刺 " 和 " 别有用心 "。
但这意味着大家对道德戒律更加严苛吗?未必。因为在另一些层面,人们对偏离道德的包容度相当之高。当然,这种包容也许是一种生活重压之下的情绪出口,也许是迈入后现代后精神失序的必然代偿。无论如何,道德标准越来越随意、动态和模糊,在互联网上已成事实。
人们一面不断警惕着道德大棒的训导,一面却能为自己找到无数理由归顺于它们,被潮流推着亦步亦趋。
倒推二十年,单身也可以是一种人设弱点,十年前,偶像抽烟也成了 " 塌房 ",再到近些年,标准变得更加捉摸不定,不可言说。今天这个明星被全民讨厌,明天,那一个又忽然莫名其妙成为众矢之的。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真正做什么道德失范的事。只是恰好契合了某种正在流行的社会情绪和意识,就能让群众看他们不爽,就足够塌上那么一阵子。
就算没有 " 录音门 ",王家卫也未必不会 " 塌房 "。他也许应该感谢他早年的那些电影。那些迷人的、拥有道德瑕疵的女性角色,以及男性角色们颇为忧郁和被动的形象,包括 2023 年的《繁花》里各式各样的女性人物,都变相救了王家卫一命——让他至少没倒在前不久的 " 老登 " 那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