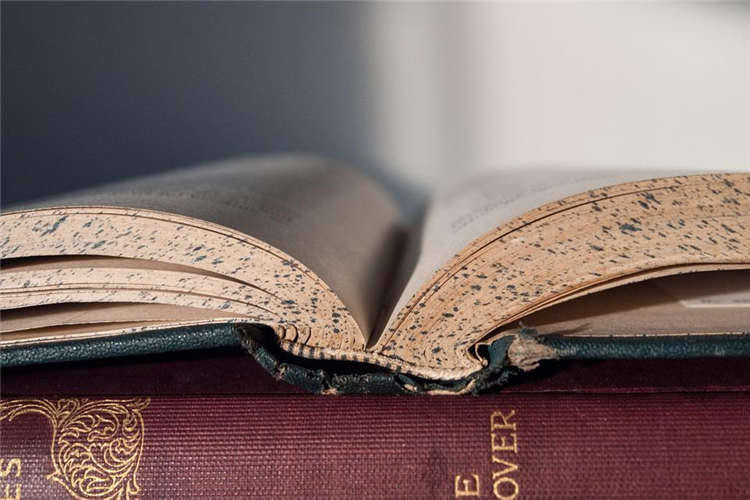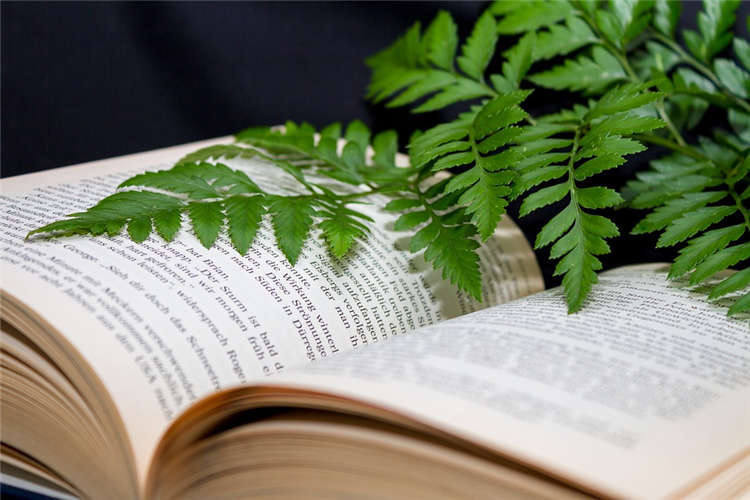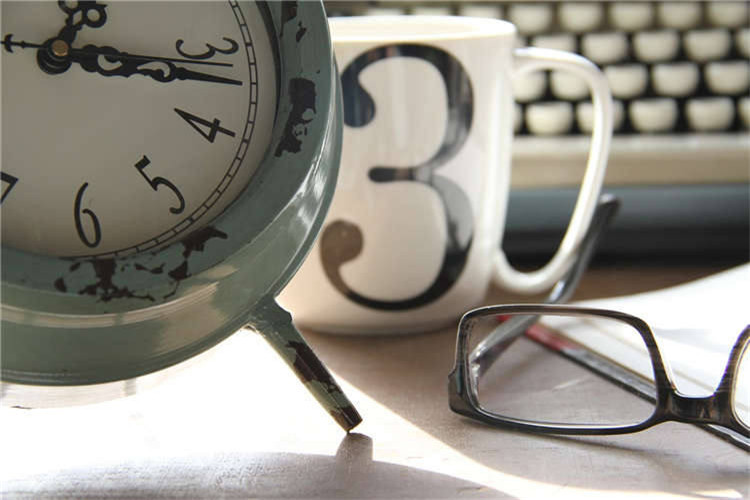20世纪上半叶,中西文化剧烈碰撞,中国艺术正经历从传统向现代的艰难转型,一群怀揣艺术革新理想的先行者,或携西方先进艺理归国拓荒,或叩击传统画坛边界寻求突破,更以学堂为基播撒现代美育火种。这其中,法国作为当时世界现代艺术中心,成为中国学子的留学首选目的地,无论是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抑或吴大羽、 庞薰琹等人,留学后又归国后纷纷投身教育事业,创建、任职于艺术院校、组建现代艺术画会……..构建起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核心阵地,以不同的路径共同完成了中国艺术由传统向现代的跨越。
澎湃新闻获悉,在即将举行的中国嘉德2025秋拍中,一大亮点正在于一批留法艺术家群像,呈现的作品既有曾影响留法艺术家的西方名家作品,更有这批艺术家留下的艺术经典,见证着百年来中国现代美术的革新与转型。
巴勃罗·毕加索 《戴帽子的女人 》
有意味的是,这一专场难得呈现了定居法国郊区的巴勃罗·毕加索的一件作品——《戴帽子的女人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等先驱留法时,毕加索的现代主义理念主要在以刘海粟、林风眠为代表的艺术家群体中产生了吸引力。徐悲鸿倡导写实主义体系,对毕加索和印象派并不推崇,而刘海粟、林风眠为代表的现代主义阵营,更推崇塞尚、梵高和毕加索,试图将西方现代艺术的理念融入中国的艺术教育与创作。
《戴帽子的女人》作于1965年6月,画中主角杰奎琳·罗克(Jacqueline Roque)是毕加索最后一任妻子,也是艺术生涯最后阶段的缪斯与模特儿, 1954年起,造型各异的杰奎琳成为其晚年作品的主题。毕加索将杰奎琳视为“无条件的爱与支持的港湾”。
戴帽子的杰奎琳
巴勃罗·毕加索 戴帽子的女人 1965年 布面油画 58×49cm
在这一《戴帽子的女人》中,毕加索将杰奎琳的正面与侧脸结合在同一平面,宽帽沿在贾奎琳脸上轻轻投下阴影,形成明暗对比,艺术家以调淡的胡克绿与粉肤色描绘面颊对比,再以深浅不一的绿色同时呈现妻子高挺突出的鼻梁、深邃的眉宇、明亮的双眼、优美的唇线与下巴轮廓。作品整体使用红、绿、蓝、黄等高彩度纯色,以及大块的平面构成,是毕加索早期受马蒂斯野兽派影响的鲜明特征,此时也已转化为自身“涂鸦式”的语言,形成从心所欲的复合式风格。整体笔触自在飞扬,朴拙中凸显简笔构成的趣味,仿佛信手拈来即捕捉下杰奎琳深邃神秘迷人的气质,也表达出对妻子深切的爱意。
李铁夫 《鱼与白菜》
李铁夫 鱼与白菜 1940年代 布面油画 62×77cm 赵昱家族旧藏
李铁夫是第一位留学西方,并广受国际认可的中国油画家,素有“中国油画第一人”的称号。此外他也是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先驱, 倾其所有,捐助革命,在中国近现代的美术史与发展史中都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孙中山曾为他题赠“东亚画坛巨擘”。
此次呈现的《鱼与白菜》完成于1940年代,出自赵昱旧藏,与此前曾在市场流通过的李铁夫静物油画有着极大差异。李铁夫的鱼类静物创作,通常是用白色瓷盘盛装鲜鱼,完成黑白关系的构建后,再于深色背景中摆上几颗蔬果,形成三角形的平衡构图,但《鱼与白菜》打破了这一惯例,画中的胖头鱼并未如惯例被放在盘中,而是与深蓝瓷瓶、白菜和青椒纵向排布在墨绿色桌面上,物象间既有交错,又有离散,尤其瓷罐的位置,高光与鱼的轮廓线的重叠关系耐人寻味。这种纵向构成令画面具有了更强的动势和节奏韵律,也突出了自然光照在物体表面所形成的明暗对比。对比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所收藏的两幅同类构图作品可知,李铁夫实际是通过这样的试验,来开发全新的构图范式。
正如李铁夫晚年回顾一生经时所说:“平生只有两大嗜好,一是革命,二是艺术。”或许对于他而言,两者并不分离,在他常年的创作早已将革命的精神寓于艺术实践之上。
徐悲鸿 《参孙与大莉拉》
徐悲鸿 参孙与大莉拉 1933年 布面油画 125×150cm 孙佩苍旧藏
徐悲鸿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体系的奠基人,他早年留学法国,系统掌握西方古典绘画与素描技法。回国后,先后执教于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北平艺专(今中央美术学院前身),并主持北平艺专校务,以“写实主义”为核心,彻底革新了近代美术教育,其理念至今影响深远。
油画《参孙与大莉拉》是徐悲鸿1933年赴欧办展之际,受友人孙佩苍之托,临摹荷兰大师伦勃朗之作。孙佩苍是民国早期重要的艺术教育家,并收藏有诸多大师作品。他于1920年代在法国与徐悲鸿结识,并意气相投,后来二人曾同游柏林,均格外崇拜伦勃朗,徐悲鸿就曾临摹伦勃朗之《第二夫人像》赠予孙佩苍。而这幅《参孙与大莉拉》也是二人深厚友谊与共同艺术旨趣的又一见证。
与伦勃朗原作相比,徐悲鸿的临作在笔触、光影等细节上极为接近,色彩关系也高度一致,保留了伦勃朗典型的粗犷风格。画面中丰富的细节层次——众人微妙的表情、夸张的肢体动作,乃至盔甲上的金属反光——都被细腻呈现,烘托出紧张的氛围。在博物馆光线不足的条件下,徐悲鸿仍能再现伦勃朗画作中复杂的画面效果,可见其卓越的造型能力以及对欧洲古典绘画色彩与构图的深刻理解。
方君璧 《隐者 》
方君璧 隐者 1935年 布面油画 97.5×78.5 cm. 源自艺术家家属
在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的宏伟画卷中,方君璧无疑是其中一抹独特而坚韧的亮色。作为首位考入国立巴黎高等美术学院的中国女性,她的艺术生涯始于西方现代主义的中心,却始终贯穿着对东方精神家园的深情回望。创作于1935年的布面油画《隐者》,不仅是方君璧艺术成熟期的代表作,更是一幅承载着时代印记与个人心志的“精神自画像”。此作以其精妙的东西方技法融合、深邃的文化意蕴与宁静的文学气质,成为了解读方君璧艺术世界与民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重要文本。
此幅《隐者》最突出的特征在于其跨文化语境下的视觉语言构建。方君璧以纯熟的西方油画技法,演绎出极具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主题。画面的近景,山石与草木的处理显示出油画媒介独有的厚重与质感。艺术家通过层层叠叠的深绿、赭石与墨青,营造出一种近乎压抑的凝重氛围。笔触果断而富有表现力,并非为了精细再现自然,而是为了塑造山石的体量感与苍劲感。这种对“体积”与“质感”的强调,是欧洲古典绘画训练的直接体现。然而,观者又能从中感受到中国山水画中“皴法”的影子—那短促、顿挫的笔法,仿佛是在用油彩书写山石的筋骨与脉络。
潘玉良 《绮罗玉眠》
潘玉良 绮罗玉眠 约1940年代 布面油画 59×90cm,法国私人收藏;1992年,亚洲重要藏家购藏自上述来源;2007年,现亚洲重要藏家购藏自上述来源。
“裸女” 是贯穿潘玉良一生的重要艺术命题,1918年她在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画期间,便对女性裸体题材产生了特别关注。留学法国之后,潘玉良主要学习的画作主题也是人体画。1927年,32岁的潘玉良便以一幅油画《裸女》在罗马意大利国家美术展览中获得金奖,这一成绩在当时的华人西画界极具含金量,是该领域内一项非常重大的成就。
1940年6月,巴黎在二战中沦陷,由于画室被德军收缴,潘玉良搬到巴黎郊区,展开对人体绘画的潜心研究,并进行大量创作,收获广泛关注,使得二度赴法的潘玉良锋芒绽放,其突出的艺术成就更被法国政府于1945年授予国家金质奖章。
《绮罗玉眠》便创作于这一时期,潘玉良在画中摒弃了西方油画中常用的强烈明暗对比,将女人体的轮廓融入到色彩与形体中,以色塑形,通过丰富、微妙的色彩和几乎隐匿的笔触去构建女人体的柔美。如手臂与躯干的连接处并无生硬分界,仅在双腿间及小腿与脚腕的交界处,运用冷暖色的明暗变化提示出体积与转折。潘玉良擅用温和的同类色对比来表现人物的立体感:在受光部使用了珍珠白、粉红和淡黄提亮,腿部阴影处则大胆地融入毯子固有的石绿色,这使得人体与所处环境和谐地统一在同一光色氛围里。《绮罗玉眠》精彩之处在于光线、色彩和质感,三者共同营造出的那种充满生命力的美,整体氛围沉静,散发着一种东方式的含蓄与内在的温婉。
潘玉良(1895-1977) 坐姿女人体 纸本 水墨 1937 年至1938 年
1938年1月,法国妇女协会为救助在中日战争中受害的妇女和儿童,举办抽奖募捐活动,奖品为中国艺术作品。潘玉良与中国留法艺术学会的会员协助征集艺术品及筹备活动。此处呈现的这件水墨人物画《坐姿女体》,便是参加活动的作品之一。
刘海粟 巴厘岛风光
刘海粟 巴厘岛风光 1940 年 布面油画 60×73cm
在1935年历经两次欧游之后,刘海粟艺术生涯的积淀期基本完成,进入了向创作全盛期升华的蓄力阶段。创作于1940年的《巴厘岛写生》正是这一重要节点的珍贵见证。
这一时期,刘海粟作油画作品数量渐少,尤其上海沦为孤岛后,他几乎搁笔,直到1939年应邀前往南洋各地为抗战筹款巡展才又动笔画油画写生。据刘海粟的书信记载,1940 年他在南洋写生期间共创作了二十余幅油画,然而受战乱、奔波影响,这批作品留存至今的仅有十余幅——其中十二幅由刘海粟美术馆收藏,能够流通于艺术市场的数量极为稀少。
《巴厘岛写生》中,刘海粟采用低视点铺陈,前景土地与植被以深赭、墨绿涂抹,短促的笔触交错叠加,呈现密集的节奏与质感。中景水面以明快的灰白舒展节奏,成为缓冲前景与远景的视觉呼吸带。远处山峦与翻卷的云气在深蓝、灰白和微带紫调的冷色中凝练成大块形状,笔触雄浑、强健。
《巴厘岛写生》既是画家对热带风物的礼赞,亦是血火年代中镌刻的文化丰碑。画家将个人心境与文化意识注入异域景观,既敏锐捕捉热带光影的瞬息变幻,又彰显出对他乡自然的跨文化感知。画笔所至,是文化交融中个人精神的淋漓投射。烽烟散尽,厚重笔触间奔涌的生命力—东方的玄远诗性、西方的色光革命、画家的赤子热血—仍在画布上搏动不息。
庞薰琹 《中国颂》
庞薰琹 中国颂 1940年代初 纸本 彩墨 35×26cm 本作即将收录于由家属参与编纂、山东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庞薰琹全集》。
1939年,庞薰琹被任命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研究员,与民族学家芮逸夫一道深入贵州、云南等地苗区进行民间艺术调查。他的足迹遍及八十多个村寨,不仅系统搜集整理了大量苗族服饰、织锦与银饰纹样资料,更以极大的文化尊重与情感投入,亲身参与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与仪式活动。
《中国颂》根据1939年至1940年间苗寨采风时的资料绘制,画家将中国传统绘画的平面造型与西画的写实技巧相结合,对画面做了高度装饰化的处理,以表现其风格特征。20世纪40年代的庞薰琹是白描高手,眼明手巧,走笔如行蛇,游丝似银钩,令本作在造型方面十分游刃有余,繁复的衣纹、饰品等都描绘得恰到好处,如上衣对襟和臂间的宽边装饰,是贵州“花苗”的特色装束,以细致的绣花制成,色彩鲜亮,纹饰多样,与腰间扎染的淡色布料形成质地差异。画家借精细的细节描绘有意识地削弱空间感,使画面感觉清新明快,从而把装饰性的魅力极大地凸显出来。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人物明净的面部及略带忧郁的神情,体现了画家寓典雅精致于平淡之中的艺术构想。
同这一时期不少致力于融合中西绘画技巧的画家相比较,庞薰琹无疑走在这支队伍的前列。香港高美庆博士在《20世纪的中国绘画》一书中如此评论这批作品:线条的运用与赋子图案型造型,使它这类作品具有一种柔和、优美的魅力和极强的装饰性……庞薰琹是透过中西艺术合璧,形成了自己的艺术表达方式。
沙耆 《古梅清音》
沙耆 《古梅清音》1942年 布面油画 82×64cm 比利时伊丽莎白女皇(1876-1965年)私人收藏,画背贴有比利时皇室专用收藏标签“R.E”
沙耆于1937年远赴欧洲深造,进入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学习,师从院长巴斯天(A.Bastien)。因在校期间成绩优异,他荣获“优秀美术金质奖”。毕业后,沙耆以独立艺术家的身份继续在比利时从事创作。其艺术生涯中的高光时刻出现在1942年:他的一幅描绘仕女奏乐题材的油画被比利时伊丽莎白皇后购藏,此件作品正是此次展出的《古梅清音》。
音乐是伊丽莎白王后人生的重要主题,而沙耆以“音乐会”为题,借仕女合奏之景,不仅既现代诠释中国传统题材,也隐喻欧洲战时对和平的呼唤。画面源于中国古代仕女图传统:四位奏乐的宫装仕女立于树荫之下,面容娴雅含蓄,衣着明艳,手持琵琶、笙、萧等中国传统乐器,并随着音乐翩翩舞动。画家运用了散点透视,将空间处理得更加平面,厚重的黄绿油彩交错间,可见强烈的笔触与清晰刀痕,充满质感与动势,是画家当时标志性的技法。通过交替使用精细、粗放的色块,沙耆塑造仕女纤细的形体,丰富的笔触丝毫没有损害色彩的富丽和形体的充实,给人一种亲切自然之感。而枝头的白色梅花、老树东方式的曲折造型、类山水结构的草地、水和山的意象在画家的笔下都显出一种生气,东方特质鲜明。
林风眠 《烟波渔舟晚》
林风眠 烟波渔舟晚 1950年代 纸本彩墨 67×67cm 1950年
林风眠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一面重要旗帜,以“调和中西艺术”为核心理念,重构了中国艺术教育的现代框架。他 1928 年受蔡元培之邀,与吴大羽、林文铮共同创办了国立艺术院(今中国美术学院),提出 “兼容并包、学术自由” 的办学宗旨,首次将西方现代艺术教育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深度融合。
林风眠的个人创作同样是中国现代艺术中的独特样本,其创作并非简单拼接西方技法与东方题材,而是追求精神层面的深度融合,这一点在其山水中具有非常直接的体现。正如此幅《烟波渔舟晚》中,许多意象的处理便能看出林风眠对水墨传统中国画的“背叛”:画中的远山基本是用墨渲染而成,并无皴擦痕迹,塑造出山峰的体量转侧和光影变化。同时,意象之间不甚分明的分界,似乎也是对宋元以来的传统中国画的程序的反动。林风眠状物寄情,寓神于形,融真情诗意于画面之中,不加雕饰而自得真趣,这正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艺术风格的高境界和绘画美学的价值取向。
李超士 葵花朵朵向太阳
李超士 《葵花朵朵向太阳 》1963年 纸本 色粉 66.5×85.7cm.
《葵花朵朵向太阳》创作于1963年,是李超士现存作品中尺幅最大的粉画,也是构图、色彩方面非常特别的一幅,保存极好,甚为难得。
《葵花朵朵向太阳》表现了两株向日葵,镜像式对称盛放。不同于艺术家其他花卉作品,本作采用了近景、满幅式的大胆构图,强化了花卉的视觉张力和压迫感。如此表现,一方面源于向日葵热烈、硕大的特性,另一方面也有时代因素的影响。
《葵花朵朵向太阳》充分利用了粉画适宜协调丰富的色调变化的特点,以恣意的笔触将花朵蓬勃的生机展现的淋漓尽致,尽显“简单朴素,大家之风”,是李超士一生粉彩艺术成就之缩影。
吴大羽《朵韵》
吴大羽 朵韵 约1980年代 布面油画 53×38 cm
吴大羽与林风眠一样,是国立艺术院(今中国美术学院)的创始人之一,他以先锋性的教学实践,培养出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等国际级大师,为中国现代艺术教育注入了现代主义基因,其贡献深刻重塑了 20 世纪中国艺术的发展轨迹。
《朵韵》以自在挥洒的笔触呈现吴先生80年代最经典的色调与画面结构,朝气蓬勃、气质独特。触目引人的便是其精湛的色彩表现,色域广阔,呈由亮到暗、从暖至冷过渡。右半明亮,以藤黄、洋红等色构出城镇街巷,显层叠空间;左半暗冷,普蓝、深绿等色作浓荫,缀粉白花朵,长线条延绿意成绿坡。深蓝浓绿平衡右半轻盈,画面收放有致,有视觉起伏与勃勃生机。
赵无极 《14.12.71》
赵无极 1971年 布面 油画 130×195 cm.法国巴黎法兰西画廊、法国私人收藏(现藏者于1986年购自上述画廊)
创作于1971年的《14.12.71》,凝结了赵无极对空间的全新建构,可谓集50-60年代之大成。据《赵无极编年集第二册》所示,其七十年代初所作120号以上的油画不超过二十幅,本作是其中尺幅最大的横幅作品,以沧桑、雄浑的青铜色泽,将传统古意与现代视觉完美融合,承载着赵无极风格演进与精神重生的双重意义,实为赵无极超越自身文化、追寻普世意义的扛鼎之作。
在《14.12.71》的横幅巨制里,上下两端的布白独具匠心,如同自画面中开辟出另一时空,使视觉层次更加深邃而悠远。而中央色域也因此更显凝练紧凑,墨线笔势因而更显得纵横驰骋,将动与静的张力推至极致。横长的篇幅引领观者宛如欣赏国画长卷一般,需要随著时间与空间的推移,方能尽收眼底。对赵无极而言,正是在1971年,他迎来了勇敢直面并大胆运用留白的时刻。彼时,他自述:“在1971年和1972年,我发现自己无法继续绘画,于是回归到水墨的技法。由于在学校里学过这一传统,我处理起来毫不困难。但我并不喜欢那种绝对的、几近魔性的偶然性⋯⋯这段水墨的经历对我帮助极大,它赋予我更大的自由与更开阔的姿态。”通过追溯水墨的传统,在虚空的张力与偶然的启示之间,赵无极重塑了自己的艺术语言,由此开拓出焕然一新的创作境界。
吴冠中 《宫墙》
吴冠中 宫墙 1972年 纸板油画 26.6×34.3cm
对于吴冠中而言,1972年是否极泰来的一年。经历60年代漫长的社会运动和下放劳动,艺术家不仅一度被禁绘画,同时亦长期被肝炎困扰。到了1972年,其所属的连队开始容许他在假日作画,尽管只能买小黑板作画板及粪筐做画架,当时被称为“粪筐画家”,但积贮多年的创作力量爆发,使他迎来了一次创作丰收。同时经历漫长的乡间生活,也令吴冠中明确了“群众点头,专家拍手”的自我要求,并逐渐形成“风筝不断线”的理念,《宫墙》正是在此背景下诞生,见证了吴冠中艺术之路重回正轨时的厚积薄发。
画中,挺拔的树木占据视觉中心,嫩绿色的新叶掩映着斑驳的红墙,形成红与绿,古与新,横与纵的对比关系。各色衣着的游人如音符般点缀其间,尤其引人瞩目的是一群穿校服、举着红旗的学生和路旁多彩的公交站牌,带着新世代特有的活力,与高处景山公园的标志性建筑—万春亭和周赏亭,形成大与小,高与低,前与后的反差。画面虽由大块的绿与红构成,但大块大面又都由镶嵌式的小块组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丰富层次,展现了艺术家在下笔前的悉心经营。
此外,同时呈现的吴冠中 《渔村之晨》《春树》与《夫人像》也是吴冠中画作的精品。
胡善馀 《中国玩具》
胡善馀 中国玩具 1974年 布面油画 73×60cm 艺术家家属
和印象主义画家一样,除了在大自然中寻找色彩之美,画室也是胡善馀作画的重要场域。在西子湖畔那个不大的斗室之中或是美院教学的课堂之上,胡善馀将花卉、水果、陶瓷、玩具等日常摆件进行组合,重新赋予它们艺术的意义。
《中国玩具》是胡善馀的静物画代表,创作于其艺术生涯风格成熟期,具有重要意义,收录于艺术家权威画册之中。本作绘于1974年,胡善馀在久经特殊时期的动荡后得以重新恢复创作,当时他的学生从西安特意带回了一批凤翔泥塑和年画,民间艺术中热烈的色彩和生命力令艺术家深为感动,并倾力绘于画中。此后《中国玩具》便被视为胡善馀的得意之作留于身边,很多朋友表达过收藏本作的意愿都被其婉拒,一直珍藏至今。
《中国玩具》色彩明艳,极具巧思,画面以红绿对比作为全花色彩关系的框架,而所有的红火绿,都有其色相和色性的微妙差别,通过深色的线条勾勒,将不同面积的色块统一起来,使画面显得十分浓郁和强烈,色彩既明快而又不浮俗,颇具东方韵味并带出装饰美感。
胡善馀的油画艺术成就,离不开他在色彩上的深厚造诣,除了较多吸收了印象派的精华外,他对中国民间艺术的色彩关系的吸收和运用同样深刻。《中国玩具》中老虎与衬布以大红配大绿为主色调,同时加入了年画与墙面的黄紫对比,形成鲜明、融合视觉基底。不过,画家并未直接挪用民俗玩具的高饱和色彩,而是以油画的笔触和色调进行调和:红色中揉入暖棕,让其更显醇厚;绿、黄、紫色里均加入灰调,使其趋于柔和。这种处理既保留了民俗色彩的鲜活张力(一如年画里红配绿的热闹吉祥),又赋予了色彩油画的厚重质感,让布老虎的纹路在油彩的晕染中,既有民间艺术的朴拙,又有西画的细腻,实现了“民俗之艳”与“油画之雅”的巧妙平衡。
钟鸣 《他是他自己——萨特》
画家钟鸣曾因1980年创作了《他是他自己——萨特》一作而在美术界引起“画家是否应存在个性”的广泛争议,引起轩然大波,并成为中国美术界“改革开放”的里程碑式的作品。《他是他自己—萨特》开启了西方思潮与观念艺术的本土化探索,与黄锐的《街道生产组的挑补绣女工》合力推动中国当代艺术从“传统写实范式”向“现代多元探索”的历史性转型,具有不可替代的开创性意义。
钟鸣(b.1949) 他是他自己—萨特 1980 年 布面 油画 110×170 cm.
1980年时钟鸣三十出头,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各种新潮流和新思想不断涌入,他也跟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对新知识、新思想都充满了好奇,尤其是哲学。1980年4月15日,萨特逝世。这激发了钟鸣的创作欲望——他想画一幅萨特的肖像。但是在构思画面的时候,钟鸣遇到了一个问题:萨特的左眼斜视,到底该怎么表现?因为当时并没有多少人知道萨特的样子,钟鸣出于对萨特的崇拜既不愿意将斜视直接表现出来,但又不想改变他的相貌误导观众。于是他采用了横构图,把萨特放在画面的右下角,并且做了版画的效果,在不失去其真实性的基础上做了修饰,并取名字《他是他自己——萨特》,这个题目也回应了萨特本人在1976年题为《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讲座 上所提出的“人的存在,是自己创造自己。”
而在画面的左上方,钟鸣画了一只杯子,牵扯到萨特存在主义哲学中的一个核心观点:杯子的本质先于存在,而人的存在先于本质。钟鸣通过这幅画所想表达,也是针对绘画存在意义的呐喊,正如他在《从画萨特说起——谈绘画中的自我表现》结尾所写:“每一个艺术家在他的创作动源与行为中说明他自己。”
回望1980年,这是中国艺术界在解冻之后的第一个爆发点,罗中立《父亲》、陈丹青《西藏组画》、程丛林《夏夜》……等一批名作的出现,开启了对前一个时代艺术的校正、反叛与超越。而作为其中之一的《他是他自己——萨特》以其独特的冷峻气质、以及高屋建瓴的哲学思辨,对不久后的85新潮,乃至90年代的理性、哲学艺术思潮起到了先声式的引领效果,并将长留于中国艺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