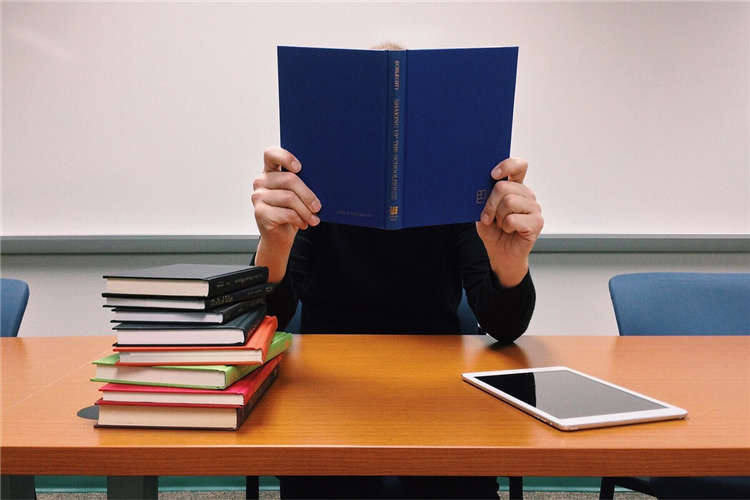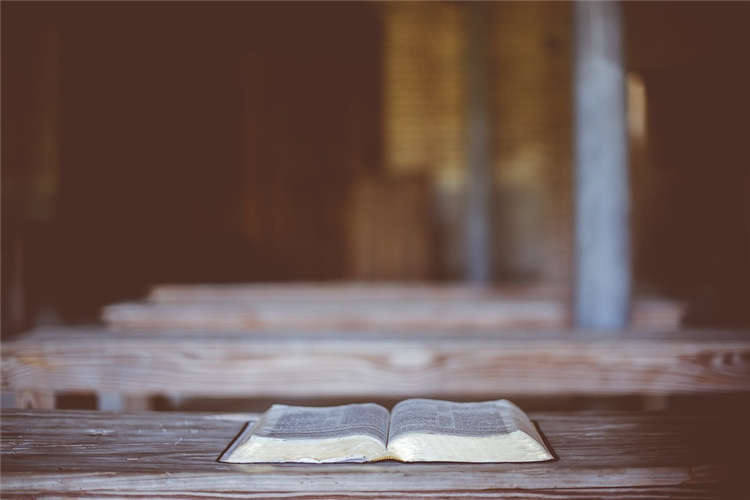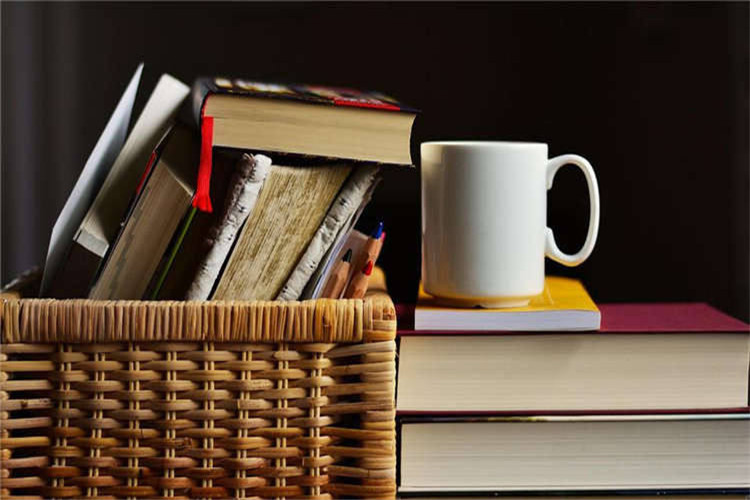采写 / 钟楚笛
编辑 / 宋建华
小豆暴食一顿吃的食物
" 吐会上瘾。" 对小鱼而言,吐是一件很爽的事情—— " 类似于尖叫或者呐喊。" 食物对小鱼来说,没有好不好吃,只有好不好吐:豆沙面包、月饼、红薯干会坠在胃里出不来,并且很重;乳制品、酸奶吐出来的味道很恶心。
在社交媒体上,有不少像小鱼这样的女孩们,她们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一口气吃掉八斤的食物,然后去厕所吐掉;每天花十几个小时用来吃和吐;保持体重低于 25kg。写这些帖子的女孩们都很年轻,许多人不满 18 岁,她们称自己为 ED 妹(进食障碍 Eating Disorders 的缩写)。
进食障碍通常表现为强烈的害怕体重增加和发胖,患者会伴随着不可控地反复暴食,继之采用呕吐、禁食等补偿性行为防止增重。它是精神障碍中死亡率最高的疾病之一,并经常伴有严重的躯体并发症和心理痛苦。
但在现实中,医生、家人却难以发现他们。数据显示,全国外科医生对神经性贪食的识别率仅为 12%。在不知情的父母、朋友,甚至她们自己都认为这仅仅是 " 过度减肥 " 的同时,这些女孩也在不知不觉中被推到了另一个世界。
1.76 米的喆喆,体重最轻时只有 34kg
下午两点,室友都去上课了,这是小豆的进食时间。在食堂买来的烧腊饭、肉夹馍、包子,外卖送来的汉堡、炸鸡块、菠萝油面包、蛋挞、芒果千层蛋糕,还有自己煮的一锅螺蛳粉。
所有准备齐全后,小豆开始大口大口地往嘴里送。" 快一点,吃得再快一点 ",耳边有个声音仿佛一直在催促她。小豆来不及咀嚼,不停地用饮料把食物冲下去。吃到螺蛳粉的时候,锅里还冒着热气,但小豆等不及了,边吹边送进嘴里。吃完这些食物,小豆的肚子已经突了出来,她转身把之前买的饼干找出来,继续一块接一块地塞进嘴里。
呕吐是这场进食的高潮。饼干还没吃完的时候,小豆感觉食物已经顶到喉咙,自己像一个被塞满的罐子。扔下饼干袋,小豆冲进厕所。左手撑住马桶,右手戳进喉咙里捅。她忍住不发出声音,那些刚吃下去的食物变成一团又一团的糊糊从胃里倒出来。小豆的眼泪和鼻涕随着那些呕吐物一起掉进马桶,她感觉食道热热的,那锅螺蛳粉原封不动地冒着热气被她全部吐了出来。
结束是下一轮的开始。打扫完厕所,小豆回到桌子前收拾垃圾,抓起那半袋没吃完的饼干要扔进垃圾桶的时候,她却鬼使神差地再次塞进嘴里 ……
神经性贪食,作为进食障碍的一种,主要表现为不可控地反复暴食,继之采用呕吐、禁食等补偿性行为防止增重,发病年龄跨度一般为 12-25 岁。
没有人知道她们在生病,甚至包括她们自己。江苏师范大学心理学研究员于晓琳向深一度表示,进食障碍患者核心特征之一就是 " 缺乏病识感 " 或 " 否认疾病 "。 对于她们而言,极度的消瘦、严格的饮食控制并非痛苦的来源,反而被视为自己的一种自律和成就。
" 对我而言,身体只是暂时的容器。" 小豆的腿比正常女生的胳膊还细,但她仍然无法接受哪怕一粒米呆在自己的胃里," 听上去有点病态,但这就是我们这个圈子。"
小豆说的圈子里的女孩,在网上被称为 ED 妹。小鱼凭借暴食视频,在圈子里出名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吃完会去厕所全部吐掉,你介意吗?" 每次和新朋友一起吃饭之前,小鱼总会这样问,那个时候她 24kg,还没有超市里的一袋大米重。
每天眼睛睁开的第一件事就是吃。走进自助餐厅,坐下,把能拿到的所有食物都依次塞进嘴里,然后去厕所吐掉,再回去吃,再吐掉。这是当时小鱼生活里最重要的一件事,直到家附近的所有自助餐厅都认识她。
为了吐干净,小鱼尝试了所有的方法。指甲划伤喉咙出血对她而言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要看见胃酸、胆汁、肠液都出来她才安心。" 肠液的味道很臭很恶心,但要到 50 斤以下,就必须要吐出肠液才行。" 她说。
在小鱼最瘦的时候,去厕所吐的 20 米路上,她会摔四次跤。" 我这样会死的 ",于是在晚上 10 点,小鱼吃了两块炸鸡才入睡,这是她几个月来第一次在胃里留下东西。凌晨 3 点,胃里一阵阵疼痛让她不得不起身去厕所吐,然而吐出来的并不是胃液,而是完全没有消化的那两块炸鸡。
无法消化就代表着不会长胖。在看到那两块炸鸡之后,小鱼的第一反应是庆幸,因为这代表着以后不用着急吐了,反正不会消化。
喆喆第一次尝试吐是在一次烤肉自助餐之后
孩子在初高中阶段是进食障碍高发的时期。" 在身体发育期,体重和体型的正常变化,与 " 瘦 " 的理想美标准冲突,被错误地感知为失控和变丑。" 于晓琳对此解释道。
身高 1.7 米、体重 51 公斤的舞蹈生馨馨,总被老师说 " 太胖 "。在艺考前,她决定开始减肥。然而节食瘦了 10 斤之后,馨馨总感觉没有力气,成绩排名也从班级前几名不断下滑,于是要强的她开始焦虑,总是不自觉地开始吃东西。
每次 " 吃多了 ",对于正在减肥的馨馨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想着第二天课前称体重的环节,她选择通过催吐抹去这个错误。" 每次我都想着一定不能再这样了,但就是做不到。"
吐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于是四个多月之后,馨馨瘦到了 30 公斤。
19 岁的喆喆已经和进食障碍缠斗了三年,176 的身高,最轻的时候只有 34kg。喆喆仍然记得自己第一次尝试吐,是在一次烤肉自助餐之后,男友用手戳了戳喆喆说:" 你吃的比以前多了呀。" 这句随意的打趣却让喆喆害怕起来,从前那些因为胖受到的嘲笑像潮水一下涌来,再次淹没了她。
" 好没用 ",她听见有个声音在骂自己。于是她跑进厕所,把刚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由于不熟练,她嗓子被抠得很疼,身上也都沾了呕吐物,但害怕的潮水退去了、责骂的声音消失了,胃被清空后整个身体都变得轻飘飘的。
随着催吐次数的增加,什么样的食物对于喆喆开始变得不重要了。在一次家庭聚餐后,吃得不多的喆喆本没有去吐的想法。然而在大家离开后,她仍偷偷地把那些剩饭剩菜全部塞进了嘴里。
从此之后,她对食物的要求越来越低:剩饭剩菜、廉价的外卖,甚至去超市捡要扔掉的过期食品,这些东西对她而言只是要被吐出来的废料而已。
" 就算你吃完要吐掉,也吃点好的,让自己好受一些好不好。" 妈妈在发现喆喆捡过期食品后心疼不已,喆喆听得掉眼泪,却又无法克制住自己去抓食物的手。
" 吐会上瘾 "。在一段畸形的恋爱结束之后,小鱼发现,吐是一件很爽的事情—— " 类似于尖叫或者呐喊。" 食物对小鱼而言,没有好不好吃,只有好不好吐:豆沙面包、月饼、红薯干会坠在胃里出不来,并且很重;乳制品、酸奶吐出来的味道很恶心,甚至被母亲警告:" 随便你吐,但不要喝酸奶。"
" 食物为她们提供了一个幻想 ,即她可以立即拥有她所想要的任何东西,不受任何限制。而控制进食、呕吐也是努力要抗拒内在的空虚、厌倦、死寂带来的痛苦。"《进食障碍》一书的作者这样写道。
喆喆在医院治疗时喝的营养剂安素
小鱼在体重低于 30 公斤后整个身体感到彻底的麻木,没有情绪也没有办法思考,只剩一个念头,就是瘦。此时的她还患上了双向情感障碍、体象障碍——纤细的她看见的却是一个肥胖的自己,不只自己,她还会在内心攻击几乎所有体重正常的人,包括父母、朋友、路人,任何人在她眼里都胖得太恐怖了。
作为医学生,小鱼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 带我去看医生吧 ",在一个吐到累了的夜晚,小鱼打电话给自己的父母。
到了医院之后,小鱼没想到听到的第一句话是 " 你就是作的,不想活了 ",来自医生的训斥让小鱼不知所措。" 想住院的话就去宛平南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地址)",医生的建议只是让她转院—— " 像送瘟神一样 ",小鱼说。
喆喆被父母发现连续半个多月不吃东西之后,也被带去了当地医院。医生安排喆喆住院,下了营养不良诊断,然而在打了一段时间营养针后,她却出现了频繁的晕倒现象," 不知道为什么越来越严重 " 父母对于喆喆的情况万分焦急,最后和她一起去了北京。
一开始馨馨并不知道自己是生病了,她以为只是自己 " 太作了 "。爸妈也以为是学习压力大让她的体重骤降,但做教师的爷爷看出了她的问题,让父母带馨馨去了省医院。省医院把馨馨收进了普通精神科,被强制没收了所有电子设备,每天强制吃饭、打针。一个月之后,馨馨也在别人的建议下来到北京就医。
据公开资料显示,全国设有进食障碍专科病房的医院不超过十家,并且都集中在一线城市。以国内该领域的权威——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为例,进食障碍病房的床位常年紧张,等待入院的时间可能长达数月。
小鱼、喆喆、馨馨的遭遇,折射出许多进食障碍患者在诊疗上的现状。于晓琳向深一度表示,进食障碍是身心疾病,需要精神科、消化科、心内科、营养科等多科室协作。然而现实是,患者常因躯体并发症(如闭经、电解质紊乱、胃肠道问题)先去综合医院就诊,若接诊医生缺乏识别能力,很可能只处理躯体症状,而错过了根本的精神心理问题,导致病情被延误。
在确认自己是生病之后,馨馨不再责怪自己,在医院她看见了很多像自己一样的病人," 原来世界上真的有这种病 ",馨馨感觉自己好像不那么孤单了。
喆喆进过三次北医六院进食障碍病房,她并不抗拒在医院的治疗,她喜欢喝甜甜的安素(一种营养剂),吃饭的时候最期待病号餐里的红烧鸡腿,甚至看见那些藏饭不吃,以及饭后偷偷去吐的病友,她会假装喝药去找护士举报。
喆喆在医院最爱吃的鸡腿饭
回到健全人的世界
在生病的这些年,父母给喆喆办理休学,带着她天南地北地去旅游,为的是让她开心。在喆喆的进食障碍反复发作时,父母陪着她看医生、住院。直到父亲患食道癌住院,得知这个消息的喆喆,手里还拿着刚从超市捡回来的过期面包。
喆喆和妈妈一起去医院照顾父亲,一家人在一起吃饭,而这次,喆喆不再顾忌饭菜有多少热量,她感觉自己像回到了小时候,咬下的每一口食物都让她感觉幸福。
意识到自己正在康复是在父亲的生日宴会上。家庭聚餐是喆喆最容易失控的场合,吃到所有人都停下筷子后,她才会惊觉 " 吃太多了 ",于是去吐掉。但这次,在吃完一份主食之后,喆喆感到饱了," 当时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
支撑喆喆康复的另一个原因是她考上了大学。在休学一年半之后,喆喆不抱任何希望地参加了高考,令她没想到的是,成绩竟然超出预期近 50 分。" 我觉得我可厉害了!" 喆喆第一次觉得离那个理想中的自己这样近。
同样通过转移注意力康复的小鱼走入的是另一个世界。在第一次打完瘦脸针后,小鱼发现从前减肥怎样也瘦不下来的脸颊肉消失了。" 医美更有用,减肥就像为了一道错题不断地刷试卷,而医美是对症下药。" 在做完鼻子的手术后,她不再关注自己的体重了。
" 正向反馈能发挥作用,在于它帮患者重新建立了自我价值感。之前患者的注意力全聚焦在‘身材是否达标’上,而其他任务的成功让她意识到‘我的价值可以来自学业能力、努力后的成果 ',从而减少对身体外形的过度关注。" 于晓琳对此解释道。
谈及真正的康复,于晓琳给出的关键词是理解。" 目前大众对青少年进食障碍的理解仅将其简单等同于‘减肥过度’或‘暴饮暴食’,把行为归因于‘自控力差’‘矫情’,忽略了它是一种需要专业干预的心理与生理双重疾病。这种误解会使患者自我否定加剧,陷入更加极端的进食与自责的循环,求助意愿受阻,觉得说了也没人懂,以及社交支持缺失,让患者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 他们是健全人,不理解很正常。" 几乎所有受访的 ED 女孩都这么说,她们也几乎不会在被发现之前主动向身边人寻求帮助,仿佛和其他人处于两个平行世界。
在学校,小豆每次暴食催吐都会挑一个寝室没人的时间。因为担心室友怀疑,吐完之后她会把整个厕所打扫一遍,开窗通风,还要进去好几次确认没味道了才安心。" 健全人是完全无法理解的,只会觉得减肥减魔怔了。" 小豆不想引起麻烦。
" 我就问你,假如有人吃东西之前第一反应是把包装翻过来看热量,下一秒给你报这东西有多少热量,然后一克一克的数,多了要倒回去,你是不是看了也觉得很神经?"
因此,这些 " 不健全 " 的女孩选择在网络上抱团以获得理解。谈及当初自己在 ED 圈出名,小鱼说是因为在网上发布的一条自己暴食的视频,迅速吸引了几千名姐妹的关注。" 可能大家对她们在生活中表现出的失望更多,偶尔来一个人关心她们,她们就很感动。" 于是小鱼开始和她们一起玩,一起直播聊天。
然而在小鱼的世界里挤满 ED 妹之后,她开始感到无力。当小鱼体重增长,开始劝导同伴也尝试康复的时候,却收获了 " 背叛 "、" 因为胖了所以嫉妒她们 " 的攻击。此时的小鱼才意识到,被 " 要瘦到极致 " 裹挟着的 ED 妹们是无法互相依靠的,于是她注销了账号。
于晓琳表示,这种过度关注 " 我看起来怎么样 " 的自我客体化现象,会给这些女孩带来巨大的压力。" 这些充斥的理想美形象,不断加剧着青少年对自身的不接纳,并且会逐渐以一种观察者视角看待和监控自己,把自己当成一个被观赏的 " 物体 ",而不是一个完整的 " 人 "。"
从他人的眼光里挣脱出来并不容易。现在,小鱼和体重和解了,她不再苛求体重秤上的数字,但外貌对于她仍然是重要的。小鱼也会在社交媒体上关注一些偏胖的活力型女生,在评论里夸夸她们。" 或许是一种渴望,想着有一天自己长胖了,大家也会像这样肯定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