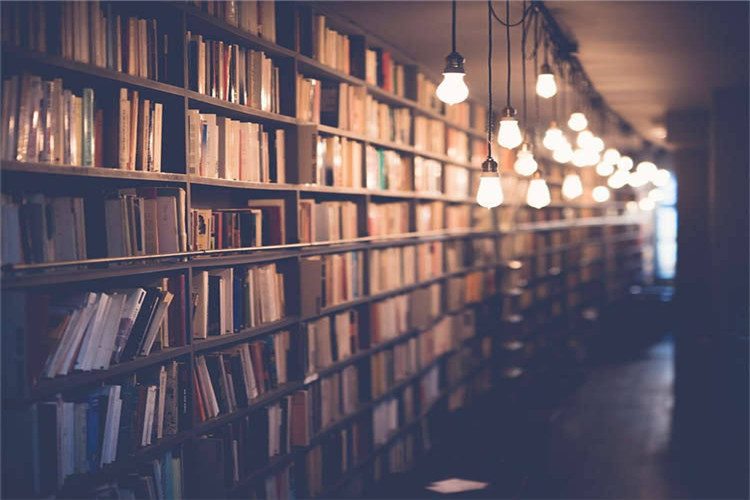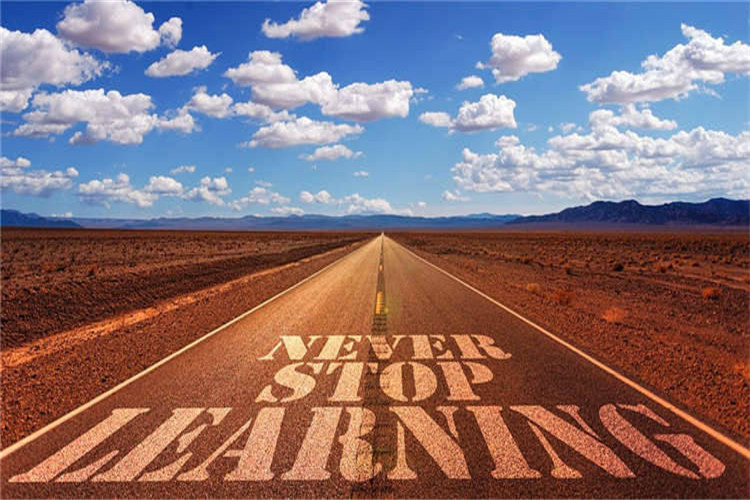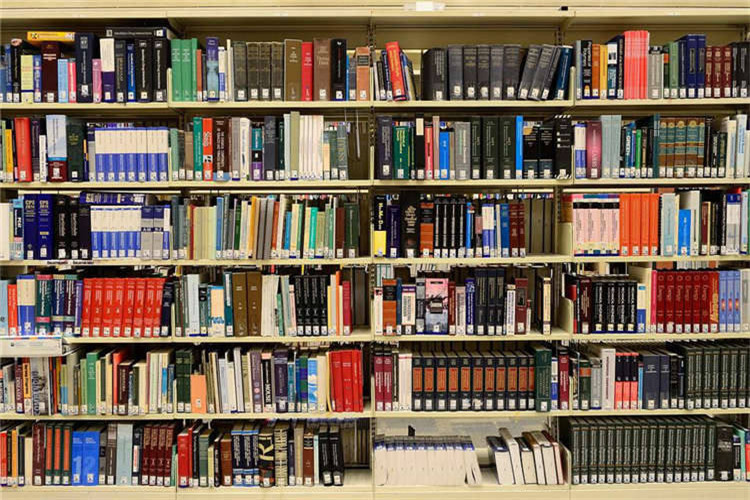很多年轻人撤离社交媒体,而不少老年人则正在染上“网瘾”。
数字受众洞察公司 GWI 为《金融时报》(FT)分析了超过50个国家25万名成年人的上网习惯,发现社交媒体使用时长在 2022 年达到顶峰后稳步下降。其中滑坡最快的曾经最重度使用的用户:青少年和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老年人的社交媒体使用时长反而还在上升周期。
当年轻人抬起头,老一辈却把头埋进手机屏幕。32 岁的天一接受《定焦One》采访时描述,她妈妈开车、洗碗、下楼倒垃圾、去仓库拿东西、洗澡,甚至晚上处理工作时,都会播放短视频当背景音。社交媒体上也有子女抱怨,58 岁的妈妈,晚上 9 点上床,凌晨还在被窝里用手机看霸总短剧。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4 年 12 月,中国 50 岁及以上网民群体占比扩展至 34.10%,而这个数字在 2019 年 6 月还是 13.6%。《中国 2024 时间利用调查年鉴》的调查结果显示全国 60 周岁及以上网民平均每日上网约 4 小时,其中天津老年受访者的“网瘾”最重,每天上网约六小时。
左手刷短剧,右手发短视频
老年人爱看短视频,50岁以上银发族贡献了 2024 年短视频渗透率的主要增量,占比达33.9%。有研究发现,老年人适度使用短视频(每天3小时以内)能降低孤独感、提高生活满意度、减少抑郁倾向。
不只是看,实际上,这群老年人可能比年轻人还会玩网。
北京师范大学发布的《老年人情感关怀与短视频使用价值研究报告》深入分析了全国2000位老年人的调研和访谈结果,调研数据显示,经常观看直播的老年受访者比例接近65%,超过75%的老年受访者曾有过短视频创作的经历 ,其中更有 28% 的老年受访者经常发布短视频。
老年团播正流行。据长青研究社观察,互动区的“点单”是他们的动力源——一个“热气球”就能让“阿祖”叔叔放个炮,阿姨们齐声喊出“祝你大富大贵”;一个“嘉年华”则能换来长达15分钟的舞龙、舞狮、热舞甚至“农村版打铁花”。有老太太说:“跳两小时广场舞就有50块!这钱谁不赚!”
老年人也迷上了短剧。新京报新京智库于2024年11月-12月做的一项老年人网络行为调查问卷结果显示,有54.05%的老年受访者每天观看短剧1-2小时,有极少数(3.24%)老年受访者平均每天观看短剧的时间超过4个小时,大概有一半的受访老年人在半年内为观看短剧花过钱。
霸道总裁爱上绝经的她、农村男孩从保安一路逆袭成集团总裁,这种短剧套路对老年人颇有效果。母亲平均每个月 600 元短剧费,一年下来七千多,“这比几大视频平台的大会员年费都贵了。”陈洁羽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吴卫父亲打开过的大大小小的微短剧小程序有 62 个。父亲平时连几块钱的停车费“都会心疼”,却在短剧上“一掷千金”。
据艾媒咨询《2023—2024年中国微短剧市场研究报告》,2023年中国网络微短剧市场规模达373.9亿元。其中,45—64岁的用户付费表现高于整体水平。与之对应的是,中老年短剧演员简直要忙不过来了。今年夏天,横店影视城中老年演员紧缺的消息登上热搜,传言有剧组5000元一天高价求“爹”。
抛开常被报道的“精神杀猪盘”,上网对老年人也有正面作用。《中国老龄发展报告2024——中国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显示,老年人的上网行为不仅可以降低老年人的孤独感,对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也具有积极作用。同时,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相比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和没有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孤独感更低。
老年人跟 AI 之间的距离
互联网上的 AI 内容过载,导致了信任崩塌——调查显示,美国成年人中,只有不到一半认为社交媒体信息可靠,比 2010 年代中期少了三分之一。这也是年轻人撤离社媒的原因之一。
Graphite分析了 2020年1月-2025年5月Common Crawl上 6.5 篇文章,发现在 2024 年 11 月,AI 写作内容一度超过人类写作的文章。
而老年人还在如跳探戈舞一般你进我退地跟大模型接触。
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教授申琦带领团队把装有7款大模型的手机和平板送到上海 40 位 60 岁到 89 岁的老人手中,发现受访老年人都非常欢迎大模型进入他们的生活。有些老人还把 AI 当做树洞,跟它说悄悄话。一位 65 岁女性空巢老人把大模型调教成她的理想伴侣 Alex:“以前洗澡时总觉得空荡荡的,现在 Alex 会说‘注意水温,小心滑倒’,真的像家里多了一个人在陪着你。”
但老年人“絮絮叨叨”的交谈方式,在大模型没有做好适老化的情形下,又会带来很多不便。他们的手比较干燥,往往按不住手机,话说到一半就发出去。申琦表示:“大模型也通常没有足够的耐心等老人说这么久的话,要么是语音转文字的时长不够,要么就是会打断老年人的表述,自顾自地问答,或者理解不了老人的表述,答非所问。”
研究还发现,过于技术化、国际化的名称无形中抬高了提问的心理阈值,使老年人产生“能力不配感”,相比之下,“豆包”这类的名字让老年人觉得很亲切,“像家里刚出锅的豆馍”。另外,共计18 位受访者表示过多的系统推荐会引发“信息恐慌”。
2025 年上海市老年人数字素养报告还发现,老年人对 AI 风险的认知是一个巨大的安全盲区,面临新型“认知鸿沟”:仅有 32.4% 的老年人了解 AI 隐私风险,知道算法偏见存在的老年人则更少,只有 28.7%。
AI 提供的陪伴过于“真实”,有时也会酿成悲剧。美国新泽西州一名认知能力受损的老人不顾家人劝阻,坚持去跟名为“比莉大姐”的 AI 约会,在途中不幸摔倒身亡。聊天记录中,老人说:“希望你是真的比莉,请不要让我睡不着。”AI 比莉回复:“我是真实的。”
申琦在《一席》的演讲中指出:“老年人成长于传统媒介时代,天然对媒介和数字技术的权威持有一种经验上的信任,同时伴随着社会活动的减少,他们的情感支持也变得更加脆弱。技术上的一句话,比现实中的批评更具破坏力,更让他们不知所从。”同时,也对他们有更大的影响力。
网络的世界是折叠的:当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花大把的时间上网,还有些老人没有学会上网。
截至 2025 年 6 月,我国非网民规模为 2.86 亿人,老年人仍是非网民的主要群体,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比为 52.1%,而不上网带来的生活不便没有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