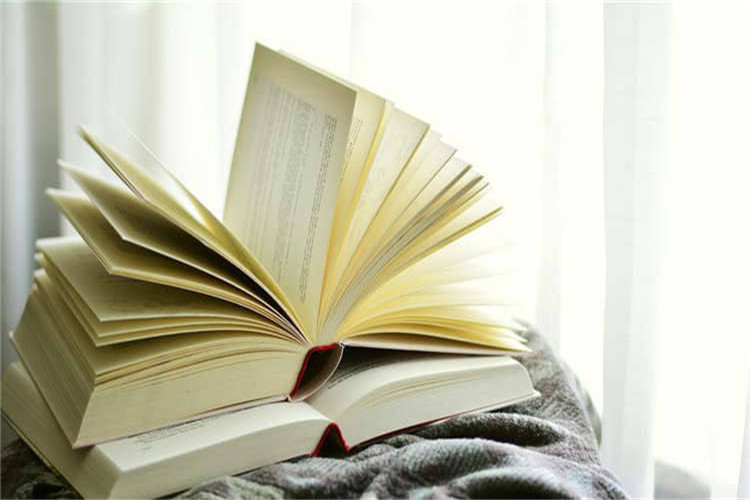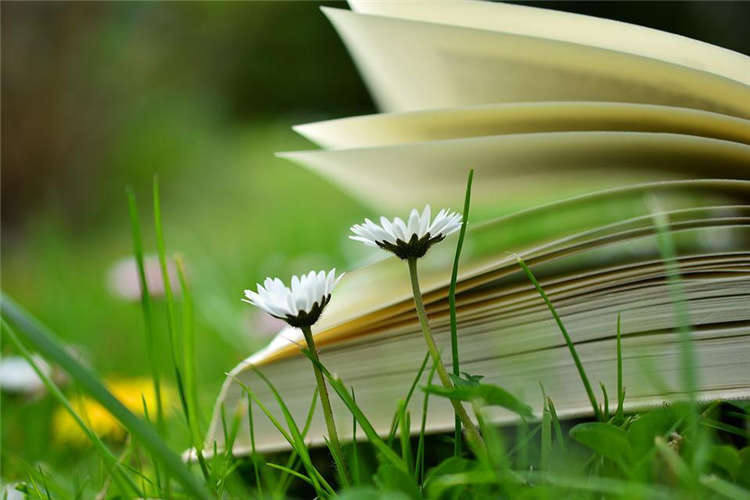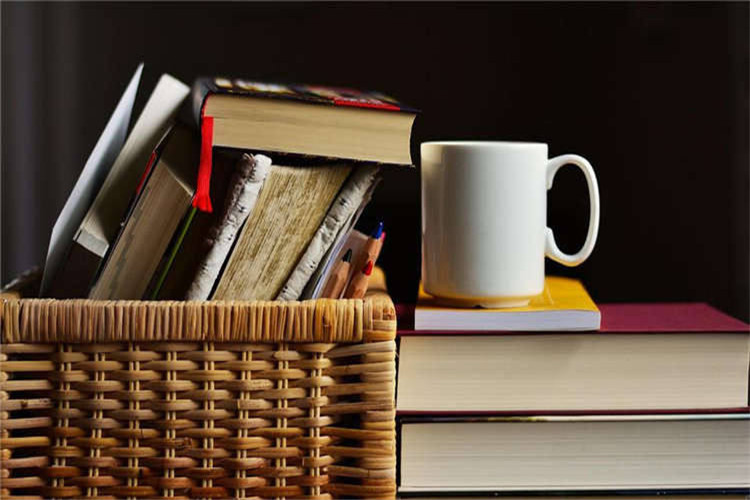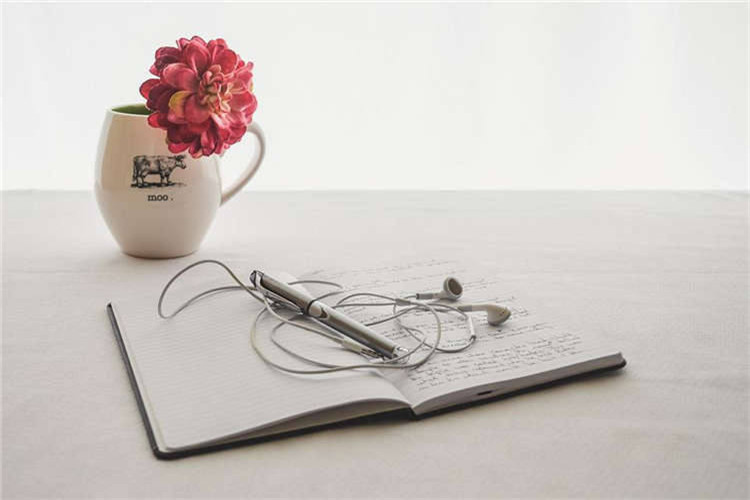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从西海美术馆离职后,77刷到了它的“闭馆通知”,这是发生在4个月前的事情。惊愕之中还有不甘,虽然自从5月底约翰·莫尔绘画奖(中国)作品新展开始后,人流量就稀稀拉拉的,77和原先一起工作的伙伴越来越陷于一种低沉疲惫的情绪里,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她不希望连展期都还没结束,“美术馆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
在2025年,每隔一段时间,人们就会和一座民营美术馆“告别”。从7月闭馆的青岛西海美术馆往前推:6月结束运营的是深圳木星美术馆,5月UCCA Edge社媒停更、场地卖起鞋服,北京总馆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被曝欠薪,3月OCAT上海馆随最后一场展览落幕,2月外滩东一美术馆宣布暂停开放,而1月归于沉寂的是浦东新区的喜玛拉雅美术馆。
“宣布闭馆的那几天,是人们在网上最感觉可惜、最怀念它们的日子。”77记得当时不少人来到西海美术馆排队送别,还有人用无人机拍下它最后的样子。“但人们忘记的速度也很快,”她不无唏嘘地说,“就跟许多展览,开展日当天即巅峰是一样的道理。”
生活还要继续向前,77给自己放了几个月的假,暗下决心不再找与艺术相关的工作,但向界面文化回忆在西海美术馆工作的点滴,提到同事们布展,把沙子铺满地板把异形墙摆好位置时,77依然动容。她时不时关注着艺术圈动态,看到苏州H+美术馆预计年底前开业、正在布展阶段的消息感到惊讶,“在行业都不好做的时期,怎么还有新美术馆能做到逆流而上的?”
关于一间民营美术馆的开始与结束,许多见证过美术馆“昙花一现”的从业者们都迫切想找到答案。
01 城市更新中的美术馆地标
77毕业后第一份工作的时长,是和她加盟后西海美术馆的存续捆绑在一起的——不足4年。而推动西海美术馆成形落地,创始人孟宪伟花了10年,构想的萌生更可追溯到20多年前。
孟宪伟曾从事传媒行业,国外游历时,他被当地的文化生活氛围打动,体会到“一个艺术社区对城市价值和居民生活的精神滋养,是远远超出一般传统的商业业态的。”他开始拜访国内外美术馆,去中央美院上史论班、艺管班,准备起了一份当时还不清楚该给谁看的计划方案:在中国海边做一个生活化的艺术社区。
抱着纸上愿景,再与政府沟通,2011年,孟宪伟凭山东国际海岸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控股人的身份,承接了青岛市文化项目“西海艺术湾”的建设工作。据77介绍,在规划中,西海美术馆是非营利机构,在此之外,还有公共机构美术馆、艺术家工作室、青年旅舍和酒店......多达55幢建筑围绕在侧,并邀来普利兹克奖得主、法国建筑师让·努维尔操刀整体设计。2019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孟宪伟称已经有两位艺术家(谭盾和叶锦添)选择长期驻地。但在77工作的这些年里,除了西海美术馆在开放,周围的项目迟迟没有建设起来,“听说是报批的政府资金一直没下来”。
“最美海边美术馆”的声誉在网络扩散之时,公众还不太知道当地原来的面貌,这个与市区相隔30多公里,需要穿越海底隧道才能抵达的区域叫作“鱼鸣嘴”,从前是一片滩涂遍布、渔船停泊的小渔村。
一块荒废衰颓、鲜有人烟的空地天生就吸引着艺术创作者的脚步。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北京东村和上海苏州河沿岸的闲置用地因“价格低廉、空间宽敞,很少接受检查”的“飞地”特征,让不少艺术家自主前往居住和工作。
当艺术家给社区带来改变后,资本也随之投来目光。在许多地产商现有的开发计划中,艺术文化机构的落成从一开始就被有意识地包含在内,他们邀请艺术圈名人进驻社区、寻觅设计大师拔高建筑调性,种种做法皆是符合士绅化倾向,呼应某种高尚生活方式的策略性安排。
美国城市研究者莎伦·佐京 (Sharon Zukin) 曾提供一个识别士绅化街区的简易方法,就是看某地是否有这样的ABC组合:艺术画廊 (art galleries) ,精品店 (boutiques) 和咖啡馆 (cafes) 。最初的士绅化阶段属于住房市场的一组特定过程,由于某地“重建”的需求正当其时,士绅化多多少少还能享受着由政府出面调动资源,化解了一定的商业风险。但在越来越多开发商受到鼓励后,士绅化改造迈向自由市场,且不再只是房地产的孤立举措,而与广泛的城市转型联系起来。
近些年中国建成的民营美术馆,很多会有此种思路的复制。今年1月闭馆的喜玛拉雅美术馆,坐落在融合酒店、剧场、商场多业态的综合商业项目“喜玛拉雅中心”内,由中国民营的证大集团开发、由日本建筑师矶崎新主持设计,其中,证大集团开展的核心业务是金融投资与房地产开发;
20世纪10年代在上海外滩修建的洋行新厦,即如今人们熟悉的“外滩一号”大楼,历经建国后国有单位的来来去去,最终由国企久事集团接手修缮,更新成久事国际艺术中心。2月暂停办展的东一美术馆,馆长谢定伟携其策展运营团队天协文化是这里的第一批租客,在此之后,围绕艺术相关的金融属性机构如佳士得艺术品拍卖行才陆续搬入;
始于上海徐汇区政府品牌工程战略的“西岸文化走廊”同样是如此,众多民营企业落户其中,利用铁路旧址、机场老机库和油罐老建筑,把落寞的工业区翻新成美术馆和画廊空间。曾在其中的上海摄影艺术中心 (SCôP) 供职过的蔡卿怡告诉界面文化,在其他用地如住宅区、商业写字楼和购物中心落地西岸之前,这些文艺设施已经在这里运转多年,“虽然不如现在热闹,但美术馆的存在让这里房价翻了不少,人们一提到徐汇滨江,自然而然就联想到美好浪漫的城市风光。”
策展人王懿泉在去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美术馆的建设有赖于士绅化的改造过程,从来对士绅化持批判态度的艺术群体也就默许了改变的发生,成了向外界展现“时尚精英国际范”符号价值的代言人。“这也是为何许多民营美术馆都与地产商牢牢绑定:美术馆需要足够大的空间和外界资金,地产需要文化艺术先行开道为其赋能,更不乏政府鼓励企业投资文艺领域并给予适当优惠,个别商人也渴望借文化资本提升口碑的原因,”蔡卿怡进一步向界面文化解释说。
在一篇评论中,中山大学教授冯原如此比喻经济危机中的房地产行业:“当你的船进水了,你会首先扔掉不太重要的东西。”民营美术馆固然往往充当地产建设的先行者,给整个地块树立“门面”,但当经济下行,这类文化艺术地标相比其他用地更少创造出商业价值,首当其冲被放弃已然是现实。
02 “卷生卷死”的美术馆商战
“关于经营一间美术馆,人们太缺乏估计了。”
吴昊臻在天协文化经营的东一美术馆工作多年,她告诉界面文化,在国外的美术馆制度中,无论是多大多有名的美术馆都还是需要得到政府资助和社会各界的赞助才能够生存下去,但国内并未形成这样的共识。纵然地产商抛下美术馆是适应经济规律的决策,但这也是把商业化全然交付给美术馆的工作团队来考虑,让美术馆承担起自负盈亏的重压。
创立东一美术馆之前,天协文化曾策划过两场轰动沪上的展览,分别是2011年于中华艺术宫举办的毕加索中国大展和2014年于K11商场举办的印象派大师莫奈特展,前者引领西方大师型艺术在中国展览的市场化模式之先,后者在当时吸引了40万人次观展。后来,为了保证展览空间的恒定性,天协文化在东一美术馆的场地办展,一如既往持续其擅长的国际借展风格。
“特展不单是他国有需求就能成立,这也是欧美博物馆在资金不够的情况下开拓出来的商业新途径。”在吴昊臻的观察中,东亚是西方商业型特展最主要的输送地,而在欧美,彼此之间的借展项目更多在官方正统的文化交流层面进行,“他们各自藏品很多,名气也已经在了,馆与馆的合作有时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欧美有成熟的经营制度和馆校联动模式,也在国际上占据主导权和更多话语权,”吴昊臻由此联想到美术馆体系在整个世界更大的不平衡。理想样态,美术馆应是学术型收藏的主体,如艺评人蓝庆伟在《美术馆的秩序》中所言,“收集、鉴别和保护带有文化印记的艺术品,在这些程序的基础上进行梳理和研究,并将这些研究成果反馈和普及给民众。”但国内美术馆的窘迫之处在于,由于缺乏完善的藏品体系和藏品陈列,美术馆大多仅扮演着展览场地的提供者角色,充其量只能站在文化推广的立场上,提供空间与行政的协助。
尽管天协文化在2022年签下与意大利乌菲齐美术馆的“五年十展”合作项目,能向民众展示西方美术史上的一流作品,就目前的几次展览来看,收获的评价都较不错,但吴昊臻与界面文化坦言,“即使这样也很难赚回本。”
民营美术馆通常有三方面的营收来源:门票;包括衍生文创、周边配套设施如艺术商店、饮品店和餐厅在内的经营;向品牌方的活动提供场地空间的租赁费用。然而若是细数成本,吴昊臻算了一笔账,“一年光房租就要1000多万”,再加上借展费用涉及到作品的运输保险海关、策展布展运营还有宣传多方面,“比如运输昂贵作品时用的木箱,按照画作尺寸定制都要一两百万的价钱,而且只针对这一次展览,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仓储空间,木箱都是用完就作废,”一系列琐碎但密密麻麻的支出令吴昊臻感到,要求一间美术馆通过自行营收达到收支平衡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相比之下,也做重要外展的几家美术馆如上海博物馆、西岸美术馆和浦东美术馆拥有公立或国资身份,在房租、物业、工资上的支付压力要小很多,也更能把展览门票价格“打下来”。
2023年,东一因疫情被迫推迟一年才开办的“波提切利与文艺复兴”大展刚好和上海博物馆“从波提切利到梵高”的展期重叠了几十天,由于展名的“冲撞”,尽管展出的真迹和数量都有不同,但当时很多观众以为自己已经看过波提切利的展就不再关注,也有的拿两者的门票费比较高下而选择不去东一,这让民营美术馆的盈利情况更加受制于其先天困境。
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民营美术馆们不得不开启一场“卷生卷死”的商业竞争。
拼活动——美术馆不再放过全年任何一个大大小小的时节组织公教和展览配套工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教授“用iPad作画”、策划“美术馆剧本杀”来吸引年轻人目光;
拼开放时长——夜游项目成了美术馆的标配,延长观展时间,给市民的夜间消费提供新选择,尽管这意味着运营成本的翻倍,有时还因地理偏远、交通不便很难招揽人群;
拼门票费——最夸张时,吴昊臻所在的东一为了回应观众“门票贵”的吐槽,甚至一时间推出近20个降价票种,比如情侣票、银发族票、“三人看展一人买单”票、画册套票,早鸟票里还分超级早鸟票、送不同种类礼品的早鸟票......连吴昊臻都觉得这“实在很癫”:
“本来美术馆之间应该惺惺相惜,很多时候却成了我们内部互相‘打架’的过程,观众都在看谁的价格能更低,最后就变成了‘等等吧,他们总归会更低’的心态。这是很无奈的,因为如果真不参加,别人又会觉得我们连诚意都没有,本来稀缺的客户群就损失更多了。”
03 娱乐休闲,体验至上:被刷新的“艺术”定义
慢慢地,民营美术馆从业者的生存本能使他们更加在意观众的喜好,以此当作展览营销的风向标。首先,响亮的艺术家名字才能收获可观的流量——这是业界普遍达成的共识,也在前段时间奥赛展和埃及展的熙熙攘攘中再次得到证实。吴昊臻承认,他们在想办法介绍佛罗伦萨画家波提切利时,也一定要带上他是达·芬奇的师兄、是拉斐尔的师叔这层关系,票才能卖得更好。
但残酷的现实是,大多数民营美术馆囿于现有资源,很难与已经有过特展经验的美术馆相抗衡,紧张的预算倒推着他们在策展中更多走向现当代艺术。随着更加抽象晦涩的艺术品出现,也构筑起了隔绝大众的屏障。77就发现,那些止步西海美术馆门口转身离去的人,最常留下的话就是“看不懂”、“不知道看的啥”。
此前界面文化的评论文章借用社会学家盖瑞·阿兰·法恩 (GaryAlanFine) 的观点说明现代艺术之于受众“不亲民”的原因:在现代艺术中,理论概念和文字注解超越画作本体成了主角,艺术依赖智性上的理解,而不是对作品的感觉。而大众恰恰是用感觉看艺术作品的群体,二者在本质上造成了冲突。
SCôP闭馆后,蔡卿怡离开西岸,来到2023年落地上海的又一间展览机构Fotografiska影像艺术中心工作过一年。在Fotografiska共三层的展区里,本土先锋实验艺术也总是遭受负面投诉最多的板块。“之前有这么一个展,是把无限ps的草丛从照片里剪裁出来,盖搭在一块,也会有植物造型的金属雕塑立在地面上,诉诸的理念是图像增殖。”但这样的创作显然不太符合大众对于摄影的期待,在票务平台上,一些用户标了差评,还把地上的作品形容成是“倒插的拖把头子”。
但更多时候,77意识到到人们只是越来越失去探索未知的兴味,更相信已经得到验证的、或是出于各种原因被反复推荐的东西,于是这种追求好评体验百发百中、容错率逐渐缩窄的心理,反倒使社交媒体上的同机位打卡照而非作品本身成了吸引绝大多数人前来的真正原因。
她说近些年消费者也在变化,相比安安静静看展,人们更加喜爱户外的放松活动,一到周末或节假日,77就能看到美术馆隔壁通往露营公园的路上总是堵车。而在西海闭馆的再半个月后,在附近开张的青岛国际啤酒节人满为患,和孤零零“晾”在那儿的努维尔建筑形成了反差。
同样是休闲娱乐的去处,商场在青岛是美术馆的最大竞品,“也是提供一个空间,陈列琳琅满目、刺激感官的东西,人在其中走走停停,坐下来买杯奶茶吃个甜点的价格也跟看展门票差不多。”最近,77又发现脱口秀成了市民的新宠,“都是两个小时左右100多块,为什么不愿意来看展?”发出这样的疑问后,她也想不到答案。
即便在展览受众基数更大一些的一线城市,人群的注意也在被分散:不知何时,全城涌现的快闪展使文化艺术元素溢出美术馆空间之外,泛化到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吴昊臻理解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展览形式是许多商业体做宣传时较轻松低廉的手段,但也的确有不少人满足于这种免费的、用光影效果复刻经典名作的场景,就不再走进美术馆内,使美术馆丧失了一批曾经辐射到的预期受众。
早在7年前,艺评人姜俊就指出美术馆“迪士尼化”的未来:图像泛滥的时代,美术馆想要符合奇观化的社会脉动,一场亲临现场的特殊沉浸式体验是唯一的王牌,这意味着一个调动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并不断交织移换的“总体艺术”(Gesamtkunstwerk)场域,意味着美术馆要从静态展示变成动态和交互性的另类剧场。
在当下的上海,这样的预言已经实现。在蔡卿怡工作过的美术馆中,让她感到商业模式做得最好的是Fotografiska,她如此形容它的风格定位:“如果横轴从左向右是静观沉思式到快节奏互动式,纵轴从下往上是娱乐休闲到高雅艺术,那么它的坐标定位就在左上角,介于快节奏互动和艺术之间。”
Fotografiska集团执行主席尤伦·罗斯商业版图的正式起点是一间专注于techno电子音乐的唱片公司,他把过往经验也带到美术馆的经营思路上来,希望从体验上打破瞻仰艺术的肃穆庄严感觉,人们能在看展时“摇晃红酒杯”品酒赏艺、遛着猫猫狗狗、跟朋友聊天社交,一边品尝美术馆根据展览主题调配的餐品茶点。“一旦你进到这个空间,你在其中的任何消费都是围绕展览展开、包含社交属性的一场全天候的美妙体验。”
在蔡卿怡看来,Fotografiska的商业模式是目前市场中的一个优选解答,周末活动的热络人群都在验证这一答案。但这所亚洲首馆作为整个国际艺术品牌继斯德哥尔摩、塔林、纽约、柏林之后的第五个分馆,既往的运营经验和财富积累允许了其扩张向上海的可能与试错机会,这是所有初出茅庐的民营美术馆所不能及的。
一切似乎又绕回“资本”的起点。民营美术馆的命运重复诉说着仅仅依赖地产业态的脆弱性,而当从业者都在绞尽脑汁讨论着生存之道时,创作所需的想象与自由又迟迟无法点燃、施展,关于“艺术”的定义一再被刷新。在解决困境之前,最感到力竭和受伤的,大概还是这么一批怀揣理想而来,又苦苦求索无果的从业者们。
(据受访者要求,77为化名)
参考材料:
Hi艺术《孟宪伟:欢迎来到最美海边美术馆》
https://mp.weixin.qq.com/s/hdXT3k37w5-lZqmJtdVK3A
澎湃新闻《如此城市 | 从南昌路到古北路,当士绅化既成事实》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100623
好奇心日报《士绅化从何而来、为何不可避免,又如何带来不公平?| 城市问题读书笔记(中)》
https://mp.weixin.qq.com/s/3UrlqSiAppFx7Oxv_AefkQ
端传媒《民資後撤、審查向前:中國民營美術館的未來還剩下什麼?》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30203-mainland-private-art-museum
凤凰艺术《姜俊:如何理解“今天”上海当代艺术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