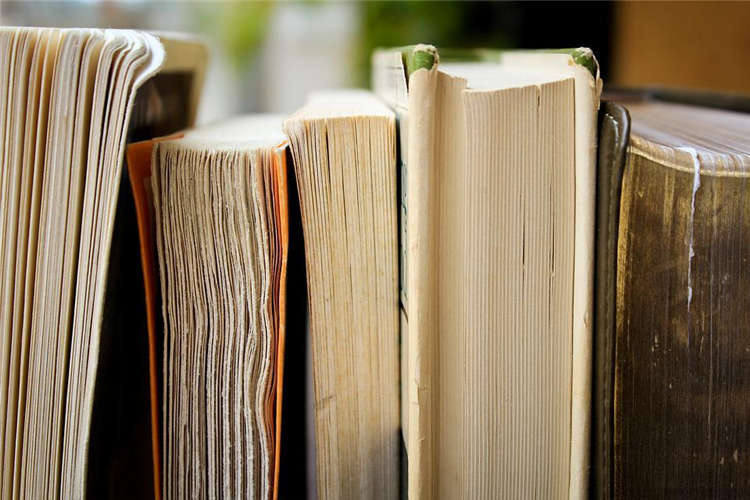诗人在存在的临界点上言说。—— 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
一、 引言
本文将会分析2023年时于全世界都广受欢迎的电子游戏作品《8号出口》[1],通过它来解析在都市空间内对“阈限空间(Liminal Space)”想象力的其中一面向,从而探寻在“后疫情时代”都市空间中“诗学”的可能性。
《8号出口》应当是受到了作为网络热潮“美学”——“阈限空间”的影响而制作的作品。
《8号出口》游戏画面
关于“阈限空间”的概念,将留至下节详述。这一词语原本指代的是都市空间中类似地下通道或是走廊等过渡区域的建筑类用词,也可以指代在都市中最不被人所注意到的边缘地带。与此相对,网络流行词“阈限空间”现在多指无人状态下的恐怖感,在网络上的流传也多以图像或短视频的形式存在。
《8号出口》是一款让玩家在地铁通道这一“阈限空间”行走的游戏。而玩家将尝试从永远循环的地铁通道中逃出,以从“8号”出口最终脱出循环。为此玩家必须要从每次循环的地铁通道中发现异变。如果玩家发现异变则必须折返,如果没有异变就可以继续前进,从“出口1”抵达“出口2”,也就是下一个循环空间。如果发生了异变但是玩家却没有发现并继续前进的话就会被移动至最初的“出口0”。换言之,这一游戏中玩家的任务就是从循环的“阈限空间”中小心寻找异变并进行应对然后采取行动。
最有意思的现象是,这款《8号出口》在被游戏主播纷纷直播后,许多的网民开始在现实空间里找寻“阈限空间”和在此发生的异变。也就是说,在“阈限空间”这一网络流行现象的影响下,《8号出口》开始流行,随后更是让这一想象力影响到了现实的都市空间。
本文将讨论“阈限空间”是在什么样的场合被想象出来的,又是通过什么样的媒介来传播的,借用了“阈限空间”这一表象的游戏是如何对其进行改变的,以及游戏又是如何改变人群对于都市空间的想象力的。
二、何为“阈限空间”?
上文已经提及,《8号出口》与其后续作品都受到了作为“美学”的“阈限空间”的影响。那么“阈限空间”究竟是什么类型的空间呢?我们可以从评论家木泽佐登志的讨论来简单地进行了解。(木泽,2021)从木泽的定义来看,“阈限空间”原本是建筑用语,现在指代“比如走廊、台阶、道路、等候室、停车场、机场大厅等”,“为了将人从一处场所移动到另一处场所而设置的人造建筑物”。(木泽,2021)
基于这一定义,2019年时作为“美学”的“阈限空间”在网络上出现,并逐步渗透到各个角落。这里的“美学”一词是指称某种特定的视觉和听觉形象在网络上成为热潮的情况。其他成为热潮的还有“小屋田园风”(英文:Cottagecore 日语:コテージコア)、“怪核”(英文:Weirdcore 日语:ウィアードコア)、“梦核”(英文:Dreamcore 日语:ドリームコア)、“伤核”(英文:traumacore 日语:トラウマコア)、“病娇核”(英文:yanderecore 日语:ヤンデレコア)、“合成器浪潮”(英文:Synthwave 日语:シンセウェイヴ)、“城市流行”(英文:City pop 日语:シティポップ)等。
作为“美学”的“阈限空间”虽然有种怀旧感,但是因为具有“无人”这一特征,所以给人“错位感”和“不寒而栗感”也是其特征之一。从这一点来看,“阈限(liminal)”是具有“临界点、边界、界限”的含义的。换言之,走廊、台阶、道路、等候室等只为让人通过而存在的场所自身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可以认为它们是为连接已经被明确定义、在文化上具有明确功能的空间与空间之间的“临界点”式的过渡性空间。
在都市空间中,“阈限空间”是最为压抑、被挤压至边缘的空间。究其原因,是因为其被认为是应该穿行而过的部分,即不应当被凝视的部分,极端来看甚至是应该被无视的部分。这里本应是通过的场所,如果在此停留的话其功能本身就会受损。(“请勿在走廊和平台逗留!”)
相对于其原本的过渡性功能,作为“美学”的“阈限空间”正是聚焦于其过渡性本身,也就是通过“滞留于此”的凝视,而将其应当称呼为“临界性”的性质重新成为一个分析的对象。由此,通行与空间上的连接这一性质也就被置于了追问之中。
例如,木泽从“无人”这一特征出发论证了“阈限空间”会引起“去语境化”。(木泽,2021)即“从被本来所刻意设计的语境中脱离而出”的状态。考虑到其本具有的“临界性”,也就是连接空间与空间的功能的话,因为“阈限空间”的“去语境化”,所以会引起类似于“这是哪里”,“这里究竟通往何处”,“这里真的能通往某处吗”,“为什么我会在这里”等强烈的实存性不安。反过来说,这种“实存性”正是由这些疑问所产生的对同一性(identity)的欲望所支撑的。从这点来看,这不仅产生了木泽所说的“去语境化”,也产生了对场所的认同(这是哪)和在场所中存在主体(在这里的我是谁)的寻求同一性的“语境还原”的失败或悬空。
三、游戏和“阈限空间”
有学者认为,作为网络热潮的“阈限空间”通过和照片这一媒介强绑定而进行扩散。(钱清弘,2021年)无论是“去语境化”的效果还是“语境复原化”的失败或悬空都是在照片这一媒介下成为可能的。照片中的“阈限空间”之所以让我们感到不安和恐怖,原因如下:
这片空间在其他时间时是一定会有人或者有过人的,但是现在是空无一人的人造空间。这片空间会促使我们去找寻其中的人的痕迹,同时也会让我们意识到这里并没有人。捕捉到这一画面的照片,就会产生出如上文所述的‘去语境化’和‘语境复原化’,在给予读者心理影响(想象、联想、推测)的同时,就产生了这种好像扭曲的图像。(钱清弘,2021年)
也就是说,因为照片这种媒介是一种能够留住过去的痕迹的静态媒介,他在可以强烈地唤起人类“在这里曾经有过什么”的疑问的同时,也因为并没有留下除却所拍下的东西之外的信息,因此对于这个疑问也是决然回答不上来的。读者想要知道在这里到底有谁做过什么或是有过什么,然而却不为所知,但依然还想知道,但依然不为所知……读者无法满足自己这种对语境还原的欲望,同时被置于不确定性中并被不安所折磨。与此相对,《8号出口》这款游戏允许和要求玩家在这种空间内行走和探索。在随时给予了玩家现今处在几号出口的信息后,在“前进”和“后退”这种主体行为下,最终也就有可能从“8号出口”逃出了。但是,笔者认为这并没有解决“语境还原”的失败和悬空,倒不如说是让这一问题变成了别的问题。
这个问题涉及游戏是何种媒介的重大问题,可能会导致问题的复杂化,因此此处笔者想简单地使用“游戏是行为主体性的艺术”(阮,2020)这一限定性的定义来继续接下来的讨论。在游戏中,我们可以体验在现实的身体上无法体验到的各种行为主体性。例如,在类似《超级马里奥兄弟》的横版卷轴动作游戏里,我们可以体验到跳得比自己的身高高好几倍,用头去破坏方块,还可以从手中放出火球这类根本性的异质行为主体性。
在《8号出口》这一游戏里,玩家被封闭于循环的“阈限空间”中,要找到每次循环时或许会发生或许不会发生的异变,然后必须采取对应这一异变的行动方法(是前进还是折返)。那么我们来详细地分析一下,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在现实的空间中,地下通道是不会循环的。这里的地下通道是将我们从A地点确实地连通至B地点或C地点等地的功能性的存在。在这一情况下,在循环的地下通道中行走的经历,就好像一种遇到了极为特殊的都市的交通功能受到阻碍的经历。
其次,在现实的空间中,也不会产生游戏中的异变。与此相对,《8号出口》中合计共有31个异变,其变化组合也非常丰富。例如,好似是上班族的“大叔”虽然每次都是从对面走过来,在无异变的状态下他会面无表情只是通过而已,但在有异变时他会“变成笑脸”,“死盯着玩家”,“脸上有异样”。还有其他类似于招募兼职的海报上描绘的人的眼睛变得让人毛骨悚然得大;写有“监控摄像头拍摄中”的海报上画着的眼睛在游动;天花板上有脸的痕迹;从换气扇中流出黑色的液体;门把手的位置发生了偏移;走过的招牌背后写有“回头吧回头吧回头吧”……总而言之会发生许多的异变。其中有比较容易找到的,也有相当很难找到的。
然后,玩家必须要在通道中走来走去,盯着墙壁和天花板来找寻异变。这是要求我们去做平时在地下通道这一空间中绝对不会做的行为。打比方来说,这就是在要求玩家好像文献学家一样被想要发现版本异同的这一欲望所驱使的主体性,或是像文学批评家一样精读文本,在这片空间之中努力找到其空间自身所崩坏的之处的“文本解构式”的行为主体性。[2]
最后,当玩家发现异变的时候,可以通过折返来保持前进。因为我们通常是不会在现实的地下通道返回的,所以有着“向后返回=向前进”这一语义前后矛盾的情况也不会在现实中出现。因此,这也是只能在游戏中才能体验到的行为主体性和空间认识。
总结来看,通过游戏这一媒介的特性,《8号出口》显著改变了我们如何认知空间和如何行动这一行为主体性。这一主体性不再是判断是否会妨碍通行,或通过还是停留的单一行为主体性,而是成为了一种包含多样化和多层次化的行为主体性。
当然,这里还包含着自我认知的问题。换言之,“这里是哪里”,“我是谁”,“我为什么在这里”的疑问依然还残留着,让人如鲠在喉,但这已经不是中心的问题了。那种不安和恐怖感也应该相比于照片减弱了不少,甚至消失。究其原因,是因为在《8号出口》中相较于这一自我认知的问题,如何发现异变和如何逃出,这些目标成为了更为中心的问题。
进一步来讲,在这里中心的问题并非“缺少”应有的信息,而是信息的“隐藏”。这里所说的隐藏的信息也并非用来确定(identify)对象和空间性质的信息,而是这一空间无法成立的阈限性(liminality)和破绽相关的“信息”。在这一意义下,相比于“信息”这一称呼,更应该称为“字里行间”或是“隐喻”。所谓字里行间就是文本在文字之外的含义,或者是超脱文字含义的空间,超越含义界限和临界点的空间,也就是“阈限空间”。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得知照片中的“liminality=临界性”和(《8号出口》)游戏中的临界性是拥有不同指向的。前者是不停地让读者回归到“即便如此仍想要了解一切”对同一性(identity)的欲望中(当然也让读者感到挫败),后者的特征则是从一开始就赋予了读者去寻找从同一性中偏离之物的欲望。
四、因“游玩之心”而造成的空间上的“再多义化”
下面再分析一下这种被游戏性所表象的偏离性指向。
《8号出口》是日本都市中随处可见的地下通道这一“阈限空间”的表象。它继承了作为“美学”的“阈限空间”的空间表象,解读了都市空间中的“字里行间”,产生出了想要“解构”的行为主体性。在这款游戏发布后,网络上出现了许多在实际中前往地铁的地下通道找寻异变的视频。这些视频也颇受欢迎。考虑到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事实,我们可以认为这是这款游戏给一般人群对现实的都市空间的想象力所施加的影响。
游戏让玩家所体验到的,所看到的“字里行间”的超越性,以及基于此进行行动的行为主体性,已经超过了作为游戏的“临界点”,影响到了现实空间。更严谨的说法是,像玩游戏一样在现实空间中游玩。笔者自己也在游玩了这款游戏之后,有时在通过地下通道时会放缓速度看看周围有没有异变发生。
那么,“游戏中游玩”这一行为主体性为什么会影响至现实空间呢?这是因为游玩的对象并非只是单纯的玩具或是在特定的规则下所被制定的游戏世界,更是囊括现实空间在内的所有物品。
游戏行为研究者米格尔·西卡尔(Miguel Angel Sicart)将“游玩之心(playfulness)”定义为一种“存在模式”,也就是定义为我们在面对世界时所采取的态度。
游玩与阅读言语的“行间”然后进行超越是相似的。如此,这种“游玩之心”会将世界“再多义化(reambiguate)。(Sicart,2019:54)
譬如,在“办公室”这一功能和意义都已经被确定的空间中,也就是通过进行交流、互相协作,处理任务而目的是产生利益的空间里玩“捉迷藏”的时候,在这一空间中的各类配置就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即参与者获得了将会从桌子的交流功能中脱离,将桌子当成为了隐蔽自己的遮挡物从而尽可能地避开和人的接触的新目的。从这样来看,也就是将“办公室”的物理性配置进行了“去语境化”,然后在“捉迷藏”这一新的语境中进行了语境还原。
从这种意义上来看,《8号出口》这一作品,通过借用游戏这一媒介特有的特征,也就是让玩家体验到使用空间来游玩这一存在模式的行为主体性,创造出了一种让这一模式扩散到了现实空间自身的可能性。
当然,“游玩”也有许多不同种类的“玩法”。例如,这里借用青木淳《空地和游乐园》中的概念来看,有作为自由的游玩场地的“空地”,还有作为应该专门用来游玩的,被告知规范玩法的“游乐园”。
这里的“空地”,可以想象为在《哆啦A梦》等作品中出现的“昭和年代”的空地。这一片空间本来的功能或是目的都暂时被放置一边,成为了一种不被定义的物品,然后再依使用人而进行改变。与此相对,“游乐园”有正确的玩法,只要遵从这个玩法就可以了。如果不遵从的话就仅仅会被请出游乐场,因为这片空间是有规范性的。也就是说,胖虎是不能在游乐园里开个人演唱会的。这里对于“再多义化”或是“去语境化”和“语境还原”的过程是封闭的,也就是说这片区域里也不存在“游玩之心”。
考虑到这两者和“阈限空间”的关系时,可以将“空地”认作在学校和家之间的边界上的区域;对于孩子们来说,学校和家都是被强制性赋予行为规范的空间,因此这片“空地”正可以说是一种“阈限空间”。在这里,孩子们会考虑该如何使用这片空间,也会再次想出和赋予这片空间意义。换言之,这里作为一种去语境化的空间,然后也在要求重新赋予其新的语境。这种语境赋予并非要确立同一性,而是展现了对这片空间进行创造的可能性。带来不安的“阈限空间”在这里就成为了一种拥有创造潜在性的空间。
这样来看,“空地”并不是单纯的供孩子们游乐的场地,更准确地说,是“能够成为游乐场地的场地”。换言之,赋予空间多重意义的并不只有“游玩之心”。《8号出口》确实是让人游玩的游戏作品,但是在游戏的中心玩法与其说是“玩”,更应该说是“走”,相较于所谓的动作游戏,它应当归入更为简单的一类。玩家能够在现实中实践游戏模式,正是通过“走”这个行为。“走”,让“日常的实践”和抱有“游玩之心”的游玩连接在了一起。
根据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所言,“走”这一动作也会依行走的方法而成为改变空间的“修辞”手段。也就是说,“游玩之心”只是诸多对空间进行“再度赋予多重意义”的方法或是模式的其中之一而已,《8号出口》更像是通过游戏而凸显了“走”这一动作赋予多重意义的能力。而且,无论何者都是用“语言”的比喻来表达的,也就是说它们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正朝着一种 “诗学” 层面的存在模式发展。
五、“行走”所诞生出的都市美学
塞尔托描述出了在都市空间中的一项对立关系。也就是“观察者”和“行走者”之间的对立。
从世界贸易中心110层俯视曼哈顿。……(中略)在视线下,巨大的人群会突然停止移动。这些人群会变为无数的文本,在这些文本中,物与人都会变得一致。野心勃勃和落魄不堪的两极,人种以及方式的激烈对立,昨天才刚刚建好的却已经变成垃圾场的大厦们和充满空间、热闹喧嚣的街道间的对比,这些都变得浑然一体,所有的一切都融合在了一起。(塞尔托,2021:232)
从上空俯视都市,这也是一种从整体性出发的“对都市的支配”。这种观察的视线会抹平差异和对立,会让城市变成一切都互相融合的“文本”。作为巨大的文本群的都市是一种“类似城市工学家和地图绘制者们所制作的复制品的类似品”,抑或是“虚构”。“这种虚构,变成了可以解读城市错综复杂性的东西,将都市持续变动的不透明性变成了透明的文本。”(塞尔托,2021:235))
所谓“透明的文本”,是指并未超越和脱离语言的涵义,文本中的一切都只有文字本身的涵义,其语言环境也固定,在这里没有“城市的错综复杂”,也就是没有“行间”的文本。这里所有的空间都严格履行着各自的功能,空间之间彼此顺畅地衔接着,加之没有杂音,信息也可以正确地进行传输。这是一种完全被合理组织,被人工设计的都市交通(空间交流)的存在形态。
这样的城市空间通过一览式观察将人群监视起来,实行规律训练,然后进行管理。“观察者”是这种能将透明的文本和城市固定成为高效传达信息、进行交流的场所的如同神一样的当权者的视角。在这里,“城市的错综复杂”被完全压制,对空间的同一性也就没有一丝一毫可以质疑的空隙。
与此相对,“行走者”则产生出了完全不同的空间性。这种空间性作为一种“日常性”,在 “可视性突然消失之处出现”。
这些行走者正在利用这些不能被观察到的空间。对于这些空间,若要说他们有什么了解的话,就好像互相拥抱的恋人虽然想要看到对方的身体却看不到一样,只是有着盲目的认识。在这种关联下,彼此应答、互相联通的一条条道路和一个个身体在其他的众多身体的印记上所刻写和编织出的一首首不为人所知的诗篇,几乎都是无法阅读的东西。(塞尔托,2021:236)
这里提出了一个概念,与“透明的文本”相对的“无法阅读的东西”,由行走者的身体性所编织成的“诗”。所谓行走,也就是盲目地写诗。塞尔托认为,行走者会“将相同的东西改造成其他的东西,对依事物的定义而规定的用法和界限都完全清除”,将“空间中的每一个能指都变为别的东西。”(塞尔托,2021:247)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这里笔者将举几个具体事例。我们在以不同的节奏于城市空间中行走。一边行走一边看来看去。有的时候还会绕路。也会发现偶然的际遇——遇到几十年前的老朋友;一直在找的旧东西、事故或事件;父母的仇人……在夕阳之下,拍下了奇形怪状的电线杆,然后上传到了社交网络上。走到筋疲力尽,然后找个地方坐下开始观察过往的行人。有人和恋人约会后还不想分别,一直在地铁的进站口前面互相拥抱。你一边走一边开着直播。在地下通道里高兴地玩着《Pokémon GO》等AR游戏……
在空间行走,并不是意味着只是从A地点到达B地点、交通和交流都能够无碍地进行。而是没有目的地促成各种各样的事情。不同的实践会改变空间的意义,会在其上附加历史、记忆和故事。以通行为唯一功能的地下通道也可以因情况和特别的目的而成为拥有各种意义的“分别的场所”,“游戏的场所”,“复仇的场所”。像《Pokémon GO》这样的AR游戏正是利用了技术而让空间的这种可能凸显了出来。因为是连续剧和动漫的取景地而变成“圣地”也是赋予了空间其他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空间本身具有多重意义的潜在可能性是一直都存在的。
行走会让城市中被管理的交通和交流中所拥有的整体性变得碎片化,将合理性置换为欲望和偶然性。对于正常的信息交流来说可能只是噪音的事物,但行走中可能会获得迄今为止尚未存在过的各种各样的其他的意义和价值。
行走就是“诗”,也正是基于这个意义。行走从词语与词语之间,信息和信息之间固定的联系,即从城市的语法中脱离;切断和打散了语言这一交流系统中词语的关联关系,意图重新组合后产生出新的意义关系。换言之,城市在像语言一样被结构化和系统化的同时,也有像语言一样有着“诗”这一超越语言界限和临界点的使用方法,即本文所说的行走。行走就是与“透明的文本”相对的“修辞”。
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说:“诗人在存在的临界点上言说。”如果套用这句话的话,可以说“行走者在空间的临界点上行走”。
另一方面,当代的城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管控。交通和交流可以毫无障碍地进行,消除偏离的空间已经得到了实现——或者至少是正在努力实现。自动驾驶正可以说是这种交通=交流的象征。如果这种完美的交流受到了少许阻碍的话,我们就会出现“路怒症”(Road Rage),这也展现出来了我们是如何期待平常的完美交流的。先前所说的《Pokémon GO》等AR服务,固然是与空间在游玩,但其信息其实在被严格地监视和管理,因此这些服务也仍然只是全体交通和交流之中的一部分而已。
支撑这种交通和交流的基础设施,正是《8号出口》中作为游戏环境的地下通道等这类空间。它作为被改造出的“阈限空间”(临界空间),是为了将行走这一“诗学”加以管理,服务于城市全体交通和交流(地铁、电车、道路)顺畅进行和信息传递的。在这一意义上,《8号出口》这一游戏作品借用了作为“美学”的“阈限空间”的表象,通过让玩家实际去“行走”的玩法,再次向玩家指明了在“临界空间”中超越“空间的临界线”的可能性。
六、代结语
作为“美学”的“阈限空间”而大范围流行的时间,正是Covid–19在世界中大范围肆虐,而现实空间实际上变成了“阈限空间”那样的去语境化的空间的时期。[3]
这也是一个城市空间中顺畅的交通和交流被前所未有的阻碍,几乎要注定面对失败的时期。这也这是我们人类的全体生活都因此而受到阻碍,面对我们在曾经的这片空间做过些什么,之后又将向何处去这种实存性的不安前所未有地高涨的时期。
伊藤亚纱通过分析保罗·瓦勒里(Paul Valéry)的诗论,认为“诗”只有在某种“失败”中才会出现。
例如,保罗认为“擦了火柴,火着起来了”并不是诗;但是“擦了火柴,没有着火”就是一句诗。……(中略)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语言之外的事物,一旦出现了诗的话,那就是“事物的自然连接”发生断裂的时候。而只有通过这些断裂,我们才有可能接近“我们所拥有的潜在物的总体”。(伊藤,2021:264)
“阈限空间”被定义为为了连接“事物的自然连接”而建构的场所。正因如此,如果切断了其“连接”的话就会发生断裂。所以,“阈限空间”并非是单由Covid-19所生成的阻塞空间的表象,而是一种“诗”的条件所显现的瞬间的空间表象。
正好在同一个时期,类似“Zoom”等代替了现实空间的网络会议服务作为交通和交流的基础设置快速普及,即使是Covid-19已经不再严重的今日也依然没有改变。其中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在Zoom这类空间里并不存在“阈限空间”。我们不会向别处偏离或脱轨,而且只能选择连接还是不连接。这里也没有绕远。这里的交通和交流也绝不会失败。
《8号出口》正是一款通过游戏这一形式,在“后疫情时代”中再次让我们感受到了这种失败的可能性,这种失败所产生出的“诗学”的可能性,这种“诗学”所展现出的西卡尔和保罗所说的城市的“错综性”的作品。
【本文经作者授权,译自伊豆原润星、山口直孝、松本健太郎主编《都市与后文学的诗学》(都市とポスト文学の詩学)、ナカニシヤ出版、2025年、第三章。】
*本研究受到了JSPS科研经费JP23K18684的资助。
【引用··参考文献(皆为日文文献)】
文内注释:
[1] KOTAKE CREATE,Steam版于2023年上市,Switch版于2024年上市。本章的讨论都基于Steam版。
[2] 在续作《8号站台》(KOTAKE CREATE,Steam 2024)中异变本身变得更加容易发现,但游戏不再要求玩家返回,而是强调对应异变寻找多样的行为方法这一部分,也就是让“文本解构”的部分变得更为突出。限于篇幅此处不再详细展开。但在本文第四节中所论述的“行走”的多样性中,续作较本作展示得更为明显,也是对本文内容的证明。
[3] 谷头和希(2024)也指出了这两个时期的一致性。
木泽佐登志(2021),《Column:Liminal Space是什么》,FNMNL,https://fnmnl.tv/2021/11/16/139203,最终访问时间,2025年1月9日。
钱清弘(2021),《Liminal Space当中的恐怖感是什么》」obakeweb,https://obakeweb.hatenablog.com/entry/liminalspace,最终访问时间,2025年1月9日
Nguyen, C. T.(2020),《Games Agency As Art》,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iguel Angel Sicart(2019),《Play Matters——游玩之心的哲学》,フィルムアート社
Michel de Certeau(2021),《日常实践中的诗学》,筑摩書房
谷头和希(2024),“游戏《8号出口》的火热与‘与日本悲惨的现状’》有密切的关系……” マネー現代,https://gendai.media/articles/-/124728,最终访问时间,2025年1月9日
伊藤亚纱(2021),《瓦勒里——艺术和身体的哲学》,講談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