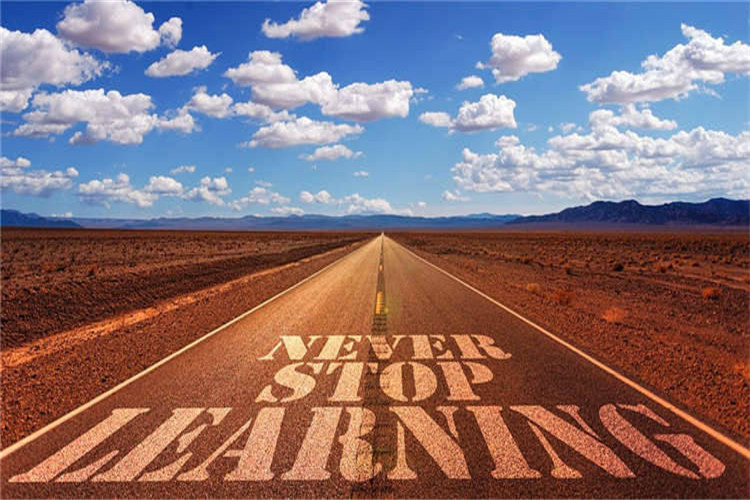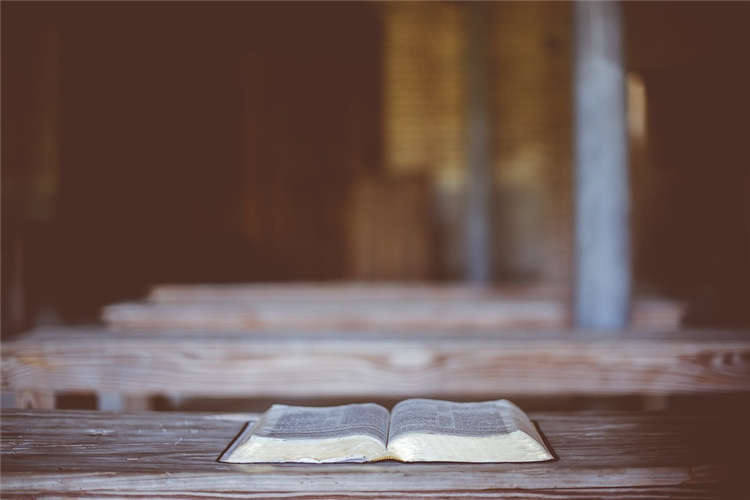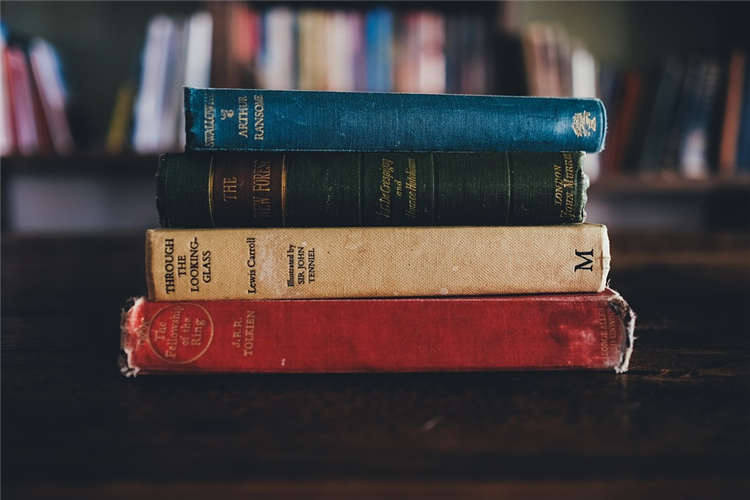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句在中文世界广为流行并衍生出不同主语的谚语,最初因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一次颁奖典礼发言上的引用而流传。
自80年代起,中国席卷过一场长久的发烧般的“昆德拉热”。他的大量作品被译介至中国,不同译本一次又一次出版,《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生活在别处》等作品为几代人所熟知。历史上中国读者与东欧文学曾有过紧密的关系,许多人现在仍能脱口念出捷克诗人裴多菲的那首“爱情与自由”。
然而,对于刚刚摘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以及他背后的东欧文学,中国读者却不甚了解。比如在讨论最初,大家弄反了这位诺奖获得者的名字与姓氏;相比他的书籍,更被人知道的是他参与编剧或由其作品改编的《都灵之马》与《撒坦探戈》等电影。在赫塔・米勒、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等获得过诺奖的作家之外,其他东欧当代作家则甚少被关注。
我们好像已经站在了距离东欧文学很远的位置。
回顾东欧文学在中国的百余年译介史可以发现,中国的关注者一直将其当做一盏具有相似处境的棱镜,透过其去寻找自身的位置。这种关注现在仍然存在。在翻译作品多元、社会生活多元的当下,伴随着“东欧”概念逐渐模糊,过去集中在文学上的目光也弥散开来。不过,东欧作家的抗争与流亡经验以及被标注为“斯拉夫美学”的各种媒介产品依然在产生影响。
它们对于我们的意义或许在于提醒,那种对于命运、自由与记忆的思考,从来不是别处的故事。
从红色到蓝色
在动荡的百余年里,东欧文学与中国读者几经交织,它是如何成为一盏关照自身的棱镜的?
因为东欧国家深重的民族抗争历史及其与现代中国相似的处境,中国文人自19、20世纪之交便开始译介东欧文学。在20世纪初期,鲁迅与周作人对包含东欧文学在内的“弱小民族文学”译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们推广“立意在反抗”的外国文艺,发表了诸多介绍东欧文学的文章及译作,并影响了第二、三代译者。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相关译介较为活跃。以文学研究会为核心力量的《新青年》杂志和《小说月报》是主要平台,茅盾、郑振铎、刘半农、冰心、许地山等许多作家参与其中,罗马尼亚、捷克、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更多东欧国家的文学作品进入中国。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一几代中国人都十分熟悉的裴多菲的格言诗的译本便诞生于这个时期,由烈士殷夫翻译,1933年鲁迅将其引录至著名悼文《为了忘却的纪念》中。
在建国初期,中国与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关系密切,文艺界倡导学习与介绍苏联及新民主主主义国家文学。许多东欧文学作品被译入中国,例如罗马尼亚小说家萨多维亚努的《斧头》《倔强的驴子》、剧作家扬·路卡·卡拉伽列的《失去的信》、波兰作家普鲁斯的小说等,形成又一次热潮。
现在留在生长于六七十年代的读者印象里的东欧文学则来自八十年代的翻译热。彼时“走向世界”成为社会的主流叙事,文化环境相对开放,国内大量引进西方现代文学,对东欧文学的译介也逐渐多了起来。捷克作家哈谢克的《好兵帅克历险记》、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南斯拉夫作家伊沃·安德里奇的《德里纳河上的桥》等作品以及来自东欧的电影成为一代人的记忆。
尤其是米兰·昆德拉,这位来自捷克的作家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中国掀起了一股持续数年的“昆德拉热”,其作品《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生活在别处》《不朽》《玩笑》等至今仍具有广泛的知名度。米兰·昆德拉凭借他对政治与社会现状的反思与批判以及独特的写作方式——幽默、机智、对性爱的大量正面展示等,吸引了中国读者的关注,并影响了一代寻根与先锋作家。
关注的消退
从出版数据来看,目前对东欧文学的翻译数量较少,对作家及作品的关注有限,并且在作品出版上有较大时差。以拉斯洛为例,他在80年代就以《撒旦探戈》与《反抗的忧郁》成名,这两本书分别在2017年与2023年才进入中国文学市场。
那这一与东欧文学间“关系冷淡”的情形是在何时出现?又是因为什么呢?
回溯至上世纪90年代,据《世界文学》原主编高兴告诉界面文化,1989年东欧剧变之后的几年时间里,中国和东欧的文学和学术交流不畅,资料匮乏。在21世纪初期,对东欧文学的翻译出版总体上较八九十年代有所减少,这与中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后受到国外作品版权限制有关。
其中,东欧文学的翻译断档问题是影响东欧文学在中国传播的一大因素。国内匈牙利当代文学的主要译者余泽民告诉界面文化,这一状况已经持续二十年了。“从‘文革’开始之后,各个语言基本上都断了。(‘文革’结束后)有些老翻译在做,老翻译不做之后就没人了。”一方面是语言专业培养更注重应用翻译,另一方面是当下的社会氛围并不提倡阅读,无法有效培养文学翻译人才。“我完全是一个特例,我不是作为语言学生被培养出来的。我是遇到了80年代特别饥渴的时候,突然放开之后主动地大量阅读。即使我学医了,还是读文学的。”
关于“现在中国读者是否对东欧文学感到陌生”的问题,高兴认为不能说陌生,而是阅读选择更多元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文学译介范围大幅拓宽,世界上所有优秀的文学作品几乎都能在中国找到译本。读者被不同的文学魅力吸引,他们的目光不再集中于东欧文学,还会关注美国、法国、英国等国的文学作品。”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现在社会生活的中心不再是文学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文学是社会生活的中心,80年代时,作家、翻译家、诗人会受到很多关注。但现在世界多元丰富,有音乐、美术等太多事物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分散了读者对文学的关注,这是正常现象。”高兴说。
面对“拉斯洛在中国受到的关注度和他的文学水平不相称”的评价,余泽民认为这是文学评价体系的原因:国内经常将书籍销售量与获奖情况作为其质量的衡量标准,这个尺度是有问题的。高兴也关注到了市场评价对东欧文学传播的影响:“出版界有时会受效益影响,往往等作家获大奖后才会关注、出版其作品,其实很多有潜力的作家早有优秀作品。”例如,余泽民早年就曾将拉斯洛的代表作推荐给中国出版社,但直到拉斯洛于2015年获得国际布克奖之后,他的作品才被逐渐译介到中国。
在社媒讨论方面,相比中国港台地区、日本、俄罗斯、英国等其他地区文学的bot账号,“中东欧文学bot”的粉丝数与其有数倍甚至数十倍之差,并且在仅运营了两年后于2023年8月停止更新,也可看作东欧文学当下在中国受到关注鲜少的体现。
但是,我们现在真的远离东欧文学了吗?
流亡与转移
在读书类bot中检索“东欧文学”,除了2018年诺奖获得者托卡尔丘克的《太古与其他的时间》和她的其他小说,评论区里经常提到的赫塔·米勒的《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以及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的《疼痛部》,近年来在社交媒体上小有讨论。一些读者说,他们知道这些作品,但并不知道它们也可以属于东欧文学。
《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收录了赫塔·米勒的九篇散文,讲述她从罗马尼亚的小村庄“出走”到德国的故事。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出生于前南斯拉夫,在1991年内战爆发后因公开反对战争与民族主义遭到国内舆论的猛烈攻击,于1993年被迫离开克罗地亚,后来定居荷兰。她坚持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写作,但拒绝承认自己是克罗地亚作家。在《疼痛部》中,她讲述了一个“一群来自于已经不存在的国家的没有身份的人,共同以一门灭绝的语言,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与文学”的故事。
这些经验都有关于流亡,这与“东欧”概念本身在逐渐变得模糊是同源的。
“东欧”并非一个稳定的地理实体,一般被认为是一个政治与历史概念。它的形成根植于多重帝国历史的交错影响,现代意义上的“东欧”概念诞生于二战结束后,在冷战时期被苏联统治与西方视角重新界定。在1989年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后,原东欧国家纷纷试图摆脱这一标签,如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更愿意被称为中欧或中南欧国家。
高兴认为,之所以依然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论和研究,是因为它们在历史背景等方面的共同点,在文学定位上,现在称其为“中东欧文学”更为合适。
在余泽民看来,“东欧文学”的概念在今天仍然成立。“东欧国家很晚才加入欧盟与申根,有的还没有加入,那它们肯定保持着原来东欧历史的遗迹,还是很沉重的。”
赫塔·米勒与杜布拉夫卡近来受到的关注还反映了东欧文学在中国传播的新情形。近四十年间,东欧当代作家进入中国大众的视野多是源自他们获得国际性奖项(特别是诺贝尔文学奖),关注度也随对诺奖讨论的减少而跌落。而赫塔·米勒获得诺奖的时间是2009年,杜布拉夫卡更是不因获奖而受到国内读者关注。她们的作品均是在中文出版后,借由社交媒体的传播被更多读者看到,也因“女性”身份引起话题性讨论。
此外,国内对“东欧文学”的关注的解离还在“文学”上。
相比拉斯洛这位新晋诺奖得主难以进入的“火山岩浆般缓慢流淌”的复杂长句,关注者们更愿意走进的是电影版《撒旦探戈》——当然,它也因7小时的时长让人望而生畏。今年瑞典文学院给拉斯洛的颁奖词是“他那富有感染力与远见卓识的作品,在末日般的恐惧之中重申了艺术的力量”,而“末日感”“末世感”是短视频平台中并不小众的标签。
这或许意味着大家对于东欧文化及与之相关的喜好从文学转移到了其他媒介上,并且更多表现为一种亚文化,对从前多与意识形态绑定的东欧文化进行了反收编。现在在爱好者间流传的“东欧”更多以这样的形态出现:名为Doomer的meme,具有阴郁、冷冽感的后朋克音乐,流行一时的音乐《布拉格广场》与《克罗地亚狂想曲》,废墟核影像,对历史及现实有深刻思考的游戏《极乐迪斯科》……
记忆与记录的使命感
纵向来看,基于相似的经历,中国关注者对于东欧文学的兴趣一直围绕着对自我存在的探寻而展开。20世纪上半叶是在民族生存焦虑中将其作为参照,试图从中获得振奋力量。80年代则是借这些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已经受到世界(主要是西方国家)承认的作家,来思考如何在世界中找到中国文学的位置。当下,即使承载媒介发生了变化,大家受触动的“大厦倾倒”后的流亡与颓废感也是一种当代人共享的症候。
东欧文学能在百年来持续散发这样的影响,与东欧作家“记忆历史”的创作特点息息相关,这也使他们享有相当的国际声誉。
“匈牙利文学在世界文学中是一线的,尤其是在现在。他们每个人都在通过不同的角度去看历史,做历史的记忆者。”余泽民说,“在20世纪,二战和冷战是欧洲最重要的两个事件,匈牙利作家所写反映的就是这两个时期。比如凯尔泰斯写二战,拉斯洛写冷战时和冷战后,马利亚什·贝拉的《垃圾日》写剧变时期的许多底层人物。东欧人所经历的跟西欧人完全不同,西欧人对冷战没有这么深刻的体验。这些体验本身给东欧人提供了文学素材,他们从经验里吸取养分,形成思想性。”
[匈牙利]马利亚什·贝拉 著 余泽民 译
花城出版社 2016-6
先后有10位东欧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高兴认为诺奖评委在他们身上看到的共通性是直面苦难的勇气、自由精神和独立品格以及将文学当做抗衡灰暗和严酷现实的武器的方式。余泽民认为他们都具有坚韧性与纯文学的信念,在长期写作生涯中往往能够咬住一个主题越写越深,保持自己的语言风格。他们思考的不是一个社会现象,他们是围绕着自己的哲学核心去组织素材。
具体来说,凯尔泰斯·伊姆雷关注集中营与大屠杀。他认为大屠杀是一种人类文化,始终与人类社会并存,即使奥斯维辛集中营被烧掉了,还有另外的集中营,可能还有没有围墙的集中营。拉斯洛四十年来一直在写人类困境,他通过冷战看人类的发展。他觉得人类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进步,无论社会表面多么光鲜,各种技术发展,但是人类都是从绝望到希望、从希望再绝望的轮回。“就像探戈一样,往前两步,往后两步。”
在记录历史之外,拉斯洛也一直保持着对社会的密切关注。在即将于国内出版的《温克海姆男爵返乡》(原版出版于2016年)译序中,余泽民写到这本书探讨了一些当下的社会问题,比如体制变革、难民危机、吉卜赛人问题、媒体不道德的运作方式等。比如他写一家报社收到了一封辱骂匈牙利人的非常犀利的匿名信,写一个人过马路,街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很多难民。这些让人联想到距离不远的两起事件:2011年,犹太裔匈牙利作家阿科什·凯尔泰斯在媒体上发表对匈牙利的批评文章,遭到了匈牙利右翼势力的围攻与恐吓,最后流亡到加拿大;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期间,匈牙利政府拒绝接收难民,约8000名难民被迫滞留在布达佩斯东站及周边街区。
如此,东欧作家从各自的视角书写历史,每个人的原创性组成了一个立体的文学景观。
[匈牙利] 凯尔泰斯·伊姆莱 著 余泽民 译
理想国 2015-8
在“历史之重”与民族认同的创作主题之后,高兴谈到新一代东欧作家发生的变化。“现在很多有实力的东欧作家早就突破了狭隘的民族主题,更多书写‘存在’这个人类大主题。他们作品的背景往往是模糊的,人物具有某种符号意义,追求作品的普遍性,希望写出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内容。在写作手法上,有‘跨界’‘杂糅’‘融合’的大倾向,作品会涉及心理学、哲学、音乐、地理学等多个领域,打破单一写法,也打破了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限。比如托卡丘克就是百科全书式作家,她的作品融合了多种领域的知识。”
但是在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东欧作家之外,目前知名度较小的中小作家仍面临着作品传播困境。“东欧很多国家的语言是非通用语言,比如捷克语使用者约1000万,波兰语约3000万,匈牙利语不到1000万,语言障碍影响了作品传播。很多东欧作家渴望作品被翻译,尤其是翻译成瑞典文,因为瑞典文是诺奖评委能直接阅读的语言。”
高兴观察到,现在东欧文学的传播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比如昆德拉、米沃什这样的大作家几乎没有传播困扰,而中小语种作家仍受语言与出版资源限制。“不过,也有许多作家在努力,例如罗马尼亚作家米尔恰·卡尔塔雷斯库长期被视为诺贝尔奖热门候选人,北马其顿作家戈采·斯米列夫斯基、罗马尼亚女诗人安娜·布兰迪亚娜等,也凭借自身创作与国际奖项的助力,逐渐引起世界的关注。”
参考资料
宋炳辉.(2017).弱势民族文学在现代中国:以东欧文学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赵玮婷.(2020).红蓝二重奏:学者聚焦东欧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https://www.chinawriter.com.cn/n1/2020/0402/c404090-31658637.html
高兴.(2020).21世纪东欧文学:复杂、夺目,边缘的光芒.中国作家网.https://www.chinawriter.com.cn/n1/2020/0826/c433142-31837844.html
姜妍.(2012).东欧文学 影响衰落源于译者断档.新京报.https://www.bjnews.com.cn/detail/155144439014430.html
Starosta, A. (2015). Form and Instability: Eastern Europe, Literature, Postimperial Difference (Vol. 22).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徐鲁青,董子琪.(2023).昆德拉逝世:诺奖错过了他,读者不忘记他.界面文化.https://mp.weixin.qq.com/s/0ePk5dJ9Lar9Bjt9mtE6fQ
潘文捷.(2017).沉寂二十余年,俄语文学为何再度成为读者们的宠儿?.界面文化.https://mp.weixin.qq.com/s/xmM1XW96AWN5p5SNLEhey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