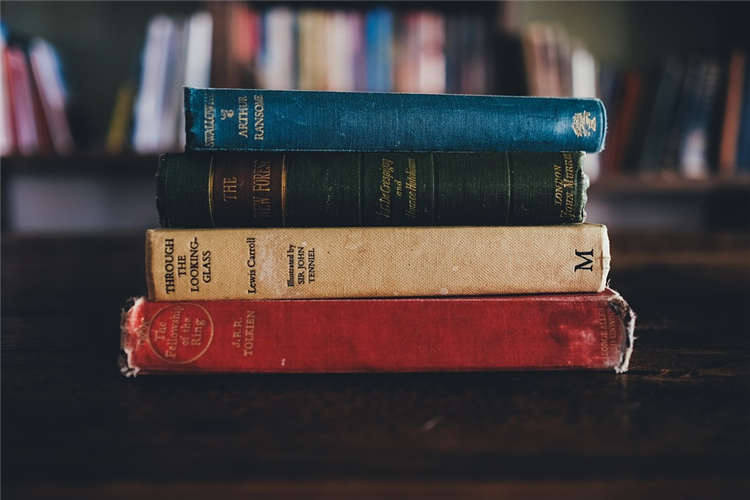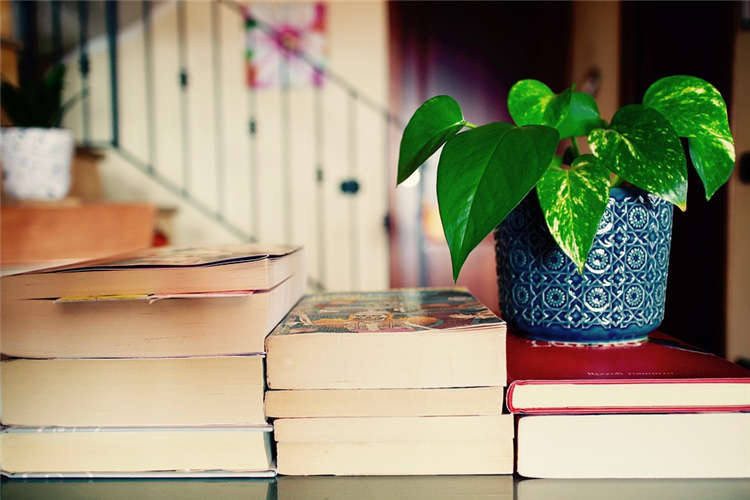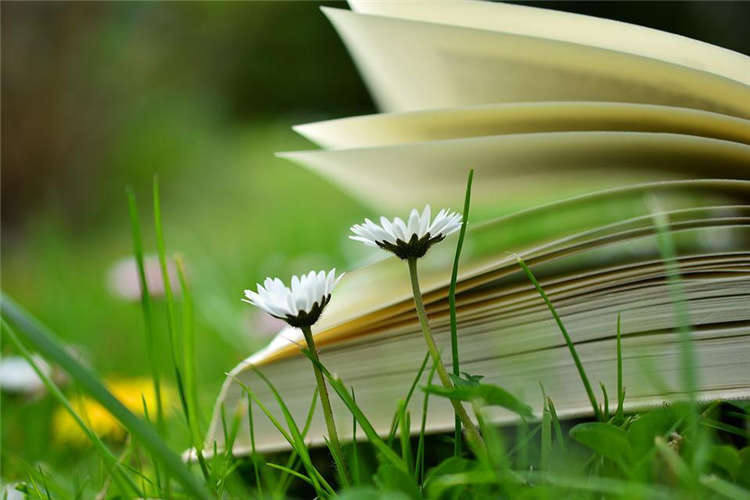10月13日,在法国勒科尔尼(Sébastien Lecornu)第二届政府成立后的第一次工作会议上,作为开场白,再度担任总理的勒科尔尼向所有新就任的部长们强调:“我们这届政府唯一的任务就是超越并且摆脱这场政治危机。”
当地时间2025年10月22日,法国巴黎,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在爱丽舍宫出席每周内阁会议后离开。视觉中国 图
他所提到的“政治危机”的开始时间可以有多种解读。最早可以追溯到2022年那场没有任何悬念,也没有任何活力的总统竞选和立法选举。在总统选举中争取连任的马克龙顺利击败了极右政党领袖马琳娜·勒庞(Marine Le Pen),连任成功。而在之后的立法选举中,马克龙的执政党联盟却没能赢得议会绝对多数。议会中出现左翼、中间派和极右三足鼎立的局面雏形。
这场危机也可以追溯到2024年夏天,在欧洲议会选举失利后马克龙出人意料地选择解散议会重新举行立法选举。在立法选举中,中间派丢掉了更多席位,议会中三足鼎立的态势彻底形成。而正是从那时开始,法国政治的重心开始从总统-总理二元逐渐移动向议会。
也正是因为这一三足鼎立的局势,从2024年9月以来,米歇尔·巴尼耶(Michel Barnier)政府和弗郎索瓦·贝鲁(François Bayrou)政府两次被议会推翻。到了今年9月,面对迫在眉睫的2026年预算案,马克龙不得不选择他一直以来忠心耿耿,有着“政治上的苦行武士”(moine-solddat)之称的勒科尔尼出任总理。
对勒科尔尼的任命创造了法国政治历史上的纪录,即在一个星期内出现一位“两任总理”。勒科尔尼第一次接受任命后,于10月5日晚间公布了第一批政府名单,这一名单引得其重要盟友共和党领袖布鲁诺·勒塔约(Bruno Retailleau)强烈不满,并且表示将会考虑带领整个共和党退出政府。这一决定成为了压倒勒科尔尼第一任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转天一早,勒科尔尼便宣布辞职,其政府存在的时间可以精确到以小时计算。4天后,马克龙再度任命勒科尔尼为总理。尽管10月16日第二任勒科尔尼政府在国民议会的两项不信任投票中过关,但这届政府恐怕还难言已经挺过“危险期”。
对民意的蔑视
马克龙对勒科尔尼的再次任命引发舆论强烈震荡,也标志着法国当前政治危机的暂时性收束与权力格局重组。
消息人士透露,马克龙意在“维持国家财政与行政连续性”,避免在预算案尚未通过之际解散议会。勒科尔尼则以“责任感”与“国家利益”为由接受再任命,但他提出两项条件:其一,新政府必须“与2027年总统选举脱钩”,不再沦为潜在候选人的平台;其二,他必须获得充分授权,主导与各党派的谈判,并有权独立提出人事任命。马克龙同意,声称将给予“完全信任与行动空间”。
但对勒科尔尼的再任命却并不能平息纷争。首先,勒科尔尼努力协商所达成的成果是相当脆弱的,参加协商的党派之间唯一存在的共识就是保证国家稳定,避免新的立法选举。而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进展。
此外,从历史轴线来看,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与勒科尔尼两度受命出任总理类似的情形,要追溯到1962年。当时的法国总统戴高乐试图恢复总统全民直选,但议会中各政党均担忧这一宪法改革有可能会导致独裁者上台,于是发起不信任投票,并且成功推翻蓬皮杜政府。
然而,戴高乐立刻解散议会,还在之后的立法选举中再次获得多数。戴高乐再次任命蓬皮杜担任总理。对蓬皮杜的第二次任命可以看做戴高乐对各个党派的复仇。但马克龙对勒科尔尼的再次任命就只能是权宜之计了。
甚至有声音说勒科尔尼是马克龙最后一个盟友。在某种程度上,马克龙第二次任命勒科尔尼也是对民意的再一次藐视和挑战。如果仔细品味这短短一周内勒科尔尼突然辞职到再次被任命的过程,其中任何一个步骤都少不了马克龙。毕竟如果马克龙不同意,勒科尔尼的辞职也不会生效。这一点也反映出马克龙在局势对他如此不利,面对反对派来势汹汹,甚至是自己党派内部的批评声时,依旧试图把握主动权。
议会彻底成为法国政治的中心
10月12日晚,总统府公布新的内阁成员名单。相较以往,名单中出现不少担任过政府职位的年轻议员以及来自民间团体的任命。但在野各方仍不满意,极左派与极右派均扬言提出不信任动议,社会党则尚未表态。勒科尔尼警告,如仍然无法获得支持,将考虑辞职。
10月14日下午,勒科尔尼在国民议会发表了他上任后的首次总体施政方针演讲(Discours de politiques générales)。以往来说,这一演讲是单纯仪式性,但面对议会中虎视眈眈的反对派,这场近一小时的演讲不仅是对政府存续合法性的考验,也标志着法国政治重心的再度转移——议会已彻底成为第五共和国运行的核心舞台。
演讲伊始,勒科尔尼重申政府的三大优先目标:恢复政治信任、重建财政秩序、与社会达成新的契约。他以一种近乎辩证的语调指出:“在多党共存的议会格局中,稳定不再来自服从,而应当源于对话。”这一表述被广泛解读为对马克龙长期“总统中心主义”的间接批评,也显示出他试图以“议会总理”的姿态重新定义总理职能。
在财政议题上,勒科尔尼承诺政府将在2026年前“恢复预算连贯性”,强调将在不诉诸宪法第49.3条(即通过抵押政府信用的方式强行通过法案)的情况下推动2026年国家预算以及社保预算的表决。他指出:“共和国的信誉取决于我们是否还相信辩论本身。”这句话获得了一阵掌声,但也伴随着左翼席位的讥笑。对社会党而言,这既是姿态,也是试探——他们在政治上保持距离,却仍可能成为政府生存的关键支点。勒科尔尼强调:“政府提议,我们辩论,你们(议员)投票表决。”
在社会政策层面,勒科尔尼宣布暂停实施退休改革中的延迟退休年龄条款,并承诺将启动一场“关于工作与社会公正的新协商”。他援引戴高乐的名言——“国家的力量在于其凝聚力”——试图将政策调整包裹在共和国传统的正当性叙事中。此举被普遍认为是向社会党示好,亦是对极左翼要求“立即废除改革”的温和回应。
这场演讲的意义已超出政策本身。对勒科尔尼而言,它是一次政治存续的战役;对法国制度而言,它是一次合法性重构的实验。正如宪法学者丹尼斯·巴朗热(Denis Baranger)所言:“当总统制的权力耗尽时,议会便重新成为共和国的唯一锚点。”
政治危机还是政体危机?
勒科尔尼的施政演讲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短期的不确定性。随着社会党表示将会“下注议会游戏规则”,希望通过议会的斗争来实现包括对富人加税等政策主张。极左的“不屈法国”(La France Insoumise, LFI)和极右的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 RN)16日提出的不信任动议在议会投票中被否决。但社会党一名党内高层也同时表示:“我们不是政府的盟友,但也不是混乱的同谋。”
但目前的措施并未消除结构性矛盾。事实上,这场危机已远远超出总统-政府与议会之间的权力对峙,而触及第五共和国制度的根基问题:在失去议会多数与社会信任的情况下,总统制还能否维系政治稳定?
第五共和国自1958年由戴高乐建立以来,一直被描述为以总统主导的垂直权力结构为特征。第五共和国宪政框架在制定之初就旨在避免第四共和国下议会造成的混乱,通过强化行政首脑、限制立法权来确保“治理的效率”。然而,经过六十余年的演化,这一模式正遭遇逆转:总统权威削弱,议会碎片化,政党体系重组,社会动员常态化。
这也让第五共和国的本质在某种程度上终于逐渐露出:其并不是一个总统制政体,甚至并不是一个半总统制国家,其实是一个“理性议会制”(parlementarisme rationalisé)政体。这一点尤其可以从2022年之后看出,当总统所依靠的执政党失去了在议会中的绝对多数地位,不仅其个人意志无法通过议会中的投票进而上升为国家意志,其所能做的事情和议会制国家的总统相比也只是多了一个可以解散议会的权力。
而如果我们回过头看第四共和国黄昏时候的样子,和当前也有几分相像。在回顾法国宪政史时,人们常将1958年视为一个断裂点,仿佛第五共和国的诞生意味着政治混乱的终结。然而,如今看来,1958年的逻辑正在以一种反向的方式重演。法国宪法学家本杰明·莫雷尔(Benjamin Morel)指出:当前的政治困局与第四共和国末期的议会分裂“有着令人不安的相似性”。面对当时出现的“议会专横”的情况,是戴高乐这一政治强人的回归,利用其高超的个人声望,通过在总统选举获胜以及议会选举中赢下绝对多数才打破了僵局。
不同的是,今天的法国陷入了“总统权威的耗尽”。1958年戴高乐上台时,提出了一种强行政、有限议会的宪法解决方案。第五共和国自此确立了“总统化”的政治文化:总统体现国家意志,总理执行政治方向,议会则主要承担合法化与监督职能。
第五共和国的黄昏
但2025年的危机正揭示出这一体系的反面:总统依然在宪法上居于高位,却在政治上陷入孤立。
自2022年以来,执政联盟失去议会绝对多数,总统不再拥有将个人意志转化为国家政策的路径;同时,反对党之间虽不共治,却形成了“消极联盟”,共同阻止政府立法而不承担任何执政责任。结果是,行政权与立法权同时陷入瘫痪,而社会不满被迫在体制外发泄。
正如莫雷尔所言,第五共和国的危机在于其制度逻辑已被耗尽。第五共和国建立在一个核心假设之上:行政多数与政治稳定相互捆绑;总统制的效率来自多数制的稳定。一旦这一假设崩塌,总统制就失去了支点。如今的法国总统虽然仍拥有解散议会的权力,却无法确保新的多数产生——这一点与1958年前的议会轮替形成了讽刺的对照:过去的问题是政府太容易倒,如今的问题是制度已无力产生新的政府。
更深层次的危机在于“代表性的断裂”。1950年代的第四共和国至少仍有强大的政党体系作为中介,能够在议会中反映社会结构的多样性。而当代法国的政党体系经历了长期的空心化:社会党与共和党被边缘化,极端政党取而代之,但并未形成稳定的执政文化。结果是,议会虽然重新成为政治中心,却缺乏结构化的政治语言来进行妥协。
这也解释了莫雷尔所说的那句意味深长的话:“当制度性手段被耗尽,体制危机便会出现。”换言之,法国当下的问题已经超出政治操作层面,而触及政体本身的可持续性。制度已无法再吸纳社会矛盾,只能在短暂的技术妥协中延缓爆发。
因此,当勒科尔尼在国民议会中宣称要“恢复对话的文化”时,他实际上是在承认一种更深的历史循环:法国再次回到了1958年之前的十字路口。不同的是,今天没有戴高乐,也没有阿尔及利亚危机作为制度重构的触发点。法国所面临的,是一种更为缓慢、内生,但同样深刻的政体疲劳。这样的情况下变革是必需的,只不过唯一的变数在于变革的将会是宪法还是总统的施政风格。
(张钰韬,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新闻学院,现为中国社科院欧洲学会法国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