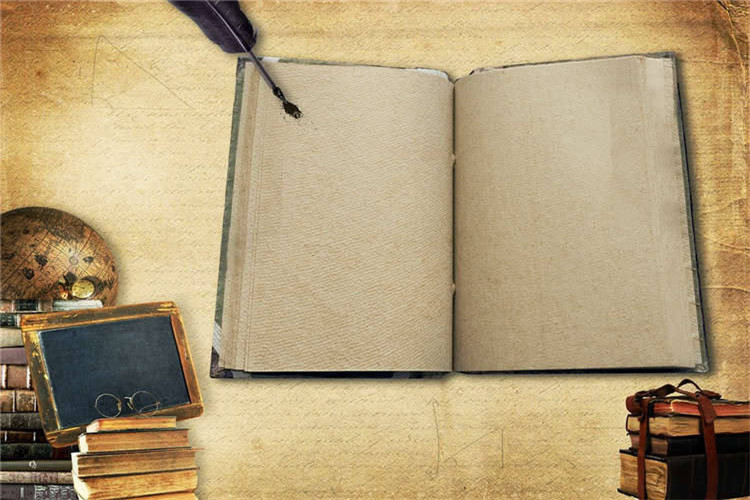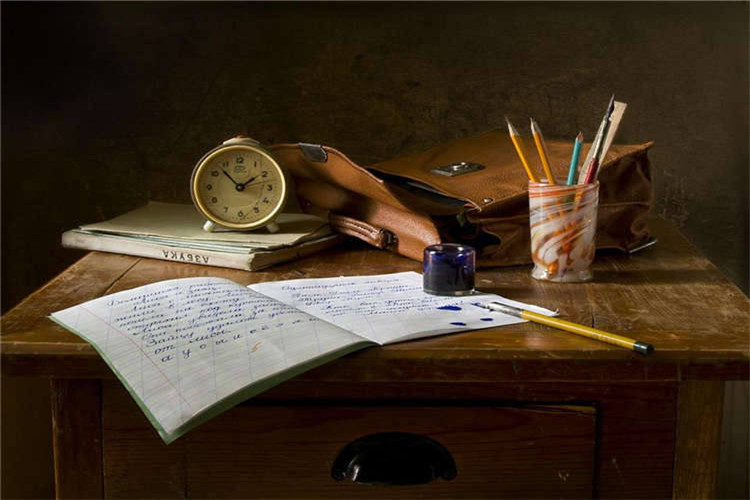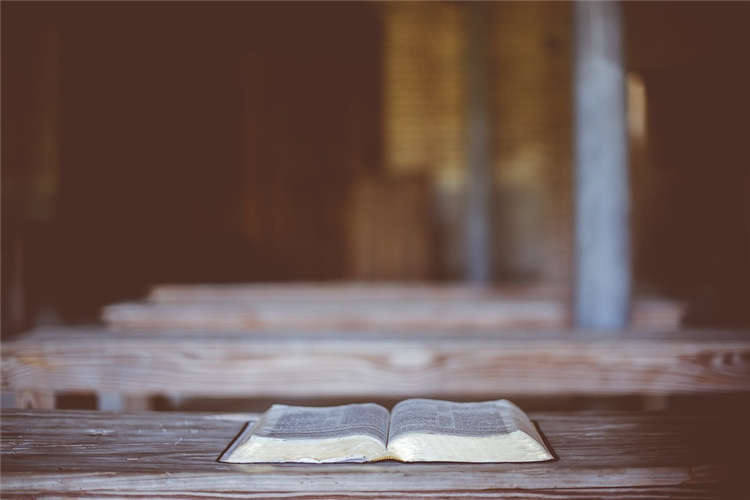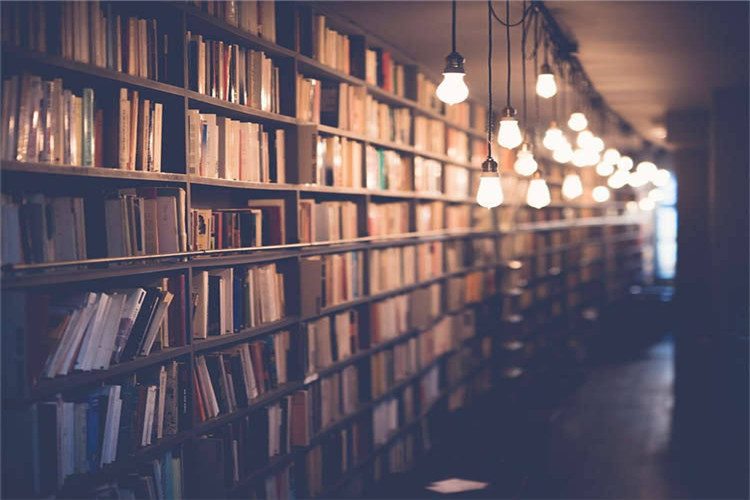自清代以来,学者留心搜访山西碑拓、编纂地方石刻专书。但叶昌炽在《语石》中认为,对山西碑刻的调查研究相较其他地区起步较晚,学术积累不甚丰厚。近年来,在考古工作者、文史研究者和众多文化机构的努力下,山西石刻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越发兴盛。其中,新出土或重新整理的山西古代碑志,为丰富历史文化、推进学术研究提供了坚实的资料基础。1979年,介休市洪山镇古窑址南面丘陵出土一通碑刻,梯形碑额,碑高95厘米,宽55厘米,厚19厘米;碑阳刻于贞元十一年(795年),碑额无字,无碑题,因碑文有“法兴寺”,故学者径称“法兴寺碑”;碑阴刻于北汉天会十四年(970年),额题《重修殿记》,碑首行题《洪山寺重修佛殿记》。此碑常年埋藏地下,目力所及未见前代金石学者著录,惟今人张晋平编著《晋中碑刻选粹》收录。原碑现存介休市博物馆,碑阳文字流传不广,碑阴文字虽偶见摘引,未窥全豹。笔者通读碑文,认为法兴寺碑对于研究唐宋佛教史、社会史、经济史以及山西区域史都有特殊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同时原石及碑拓皆具有较高文物价值。笔者不揣简陋,试在录文基础上,参证它碑,进而对唐宋时期介休地区的信仰活动与寺院经济进行初步分析,敬祈方家教正。
碑文录文与碑阳定名
碑阳文字简洁,主要内容为罗列法兴寺各项资产,故学者称之为《法兴寺碑》或《法兴寺界限碑》。现据原石及拓片(图一、图二),将碑阳、碑阴文字分别著录如下:
碑阳:
窃以成住坏空,古今兴废,是其常道。本寺魂识,恐终移失,议立碑文,开列于后。法兴寺四至:东至刘家山,南至沙河沟,西至麻儿沟,北至樊王道。洪簇寺窠一所,东至焦家山,南至沙河沟,西至麻儿沟,北自至。神峰北,地一所:东至大烟头,南自至,西至琉璃寺,北至石佛脚。神峰南,洪耀庄东、紫林,两处洪师道场。石佛堂,麻地一段,记地三亩七分:东北至大河,南至道,西至贾天祥。两水教村西北,庄子一所,记地一顷八十亩:东至贺秀,南至段顺祖等,西至李德玉,北至大河。崇贤村,庄子一所,记地一顷七十亩:东至道,南至张文俊,西至永润村宋祐,北至华门沟。木毕庄,炭窑一分。源神后,水磨一分。堡和沟,水磨一分。本村观音堂,地一所,内水碾磨□两盘:东至沟心为界,南、西、北至道。
当寺僧四十众。下院:武同村大觉院大约地两顷,西神村圆照庵大约地两顷。
时大唐贞元十一年月日,恒澄立石,石匠仇思义。
图一 碑阳《法兴寺产业记》拓片
碑阴:
洪山寺重修佛殿记 抱腹山白云岩沙门智泉奉命撰述
窃以为佛尊容重修古殿者,大哉清信守。若顺理益生、匡徒话道者,奇特洪师矣。洪师者,即是建置当寺住持之祖也。本不露姓氏,亦昧生涯,近代无以知其因由也。古老传言,沧波龙之种族。弈叶出缘,道成四果。咸言洪师罗汉和尚,始初示迹,从山东来至此,驻足紫林。后乃更居,栖心洪岳。两处各建立精舍,有同凡僧住持。和尚每将心印,应接详机。闻之者不落人天,悟之者咸升果位。女男奔凑,若市骈阗。僧道往来,如轮上下。精蓝盖就,寺额不祈。坛那随主,呼名唤作洪师之寺。和尚行标白雪,道峻青天。四众赞扬,声喧重闺。是时,后魏临朝,数闻师德。亦下征诏,遣使远移。特降天恩,并宣寺额。依山立号,改为洪山之寺。从昔至今,相继数百年矣。昨去天会十四年庚午岁,秋七月十五日,有当邑信士杨晖、李进等必是宿承佛教,深解梵空。知浮荣若石火电光,□色身似芭蕉□□。可谓倾心佛□,注想金园,屡届禅宫,每亲硕德,参问幽玄之理也。□嗟古殿梁栋年深,基□隳残,木植烂朽,虑其颓毁,伤损尊容。遂乃共议商量,重兴修盖。于是命良师选□,郢匠兴工。斤斧动而云路喧,锯凿交而嵠风紧。攒梁立柱,峥嵘倚天。□树昂飞,盘旋翳日。椽铺玳瑁,瓦甃琉璃。龙鳞盛千道青烟,凤羽横一溪秋水。丹青缋处,光皎寒空。赤白辉时,曜分素彩。功圆殿就,深似兜率移来;粉罢笔停,虑是娑婆化出。胜因广大,福报无涯。尘□□□,常居尊位。心身不久,佛寺永长。刊石标勋,留名金地。寺主僧谊靖、谊普、谊昭、惠繁
寺主讲四分律僧云□、云钦、云照、云秀、智琳、智丕、智江、智通、智全、智隐、智愿、智□、智谊
朝散大夫行介休县令兼监察御史李□ 将仕郎试大理评事守介休县主簿张□
西头供奉官检校□□尉兼御史大夫充介休镇使□□□ 汾州石匠郭兴德
图二 碑阴《洪山寺重修佛殿记》拓片
碑阳文字几乎没有虚言,主要是对法兴寺产业的记载,可视为石质“寺产清单”,颇有产权凭证之意义。纵观碑文,法兴寺产业主要分为以下几类:一、建筑六处,包括法兴寺核心建筑群,洪簇寺窠、两处洪师道场等小型宗教场所以及大觉院、圆照庵两处下院;二、田产七处,包括大片寺庄四处,小块田地两处及种植经济作物的麻地一处;三、手工业产业四处,包括生产燃料的炭窑一处,加工粮食的水磨、水碾三处。
在开列的寺产中,碑文明确记载了重要建筑及田产的四至。《金石萃编》录有开元二十八年(740年)石刻《记石浮屠后》,王昶在按语中称:“疆域之分四至八到,始见于《元和郡县志》,继见于《太平寰宇记》,后之撰地志者皆因之。此以寺记,而后列东西南北云‘四至分明’,后人田宅署券,亦同此式,盖昉于此也。”所谓“四至八到,始见于《元和郡县志》”,大抵据地志撰述而论。就传世文献而言,有关田地“四至”之规定,便有早于元和之记录。《册府元龟》载开元十九年(731年)四月敕:“天下诸州县并府镇戍官等,职田四至顷亩,造帐申省,仍依元租价对定。六斗以下者,依旧定;以上者,不得过六斗。”《唐会要》载天宝五载(746年)六月十一日敕:“自今以后,应造籍帐及公私诸文书,所言田地四至者,改为路。”可见,在唐前期的官方文书中,应当已经出现用“四至”指代土地边界的惯例。自石刻观之,备载四至以示经界,由来已久。王昶所论《记石浮屠后》便早于《元和郡县图志》,为开元年间石刻,法兴寺碑的刊刻时间也在元和以前。
叶昌炽在《语石》中论及“界至石刻”,称“癸巳、甲午间,莒州新出汉碑,四面刻字。隶书古拙,剥泐过半。即其词句相属者䌷绎之,盖经界碑也”,同书叶氏又论买地莂,引《释名》称“莂。别也。大书中央,破别之也。古人造冢,设为买地之词,刻石为券,纳之圹中”。则此类石刻,同为标记边界之用。叶昌炽例举“有建宁元年(168年)《马氏兄弟买山莂》,即冢中甎也。或大字摩厓,越中有汉《大吉山地记》,建初元年(76年)造”。叶氏所举《大吉山地记》,即东汉建初元年摩崖石刻《大吉买山地记刻石》,位于今浙江省绍兴市富盛镇乌石村跳山东坡。莒州新出汉碑当为光绪十九年(1893年)出土于山东莒县西孟庄庙的《宋伯望分界刻石》(又称《宋伯望租界碑》),刻于东汉汉安三年(144年),现存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大吉买山地记刻石》字数简短,并未出现具体边界四至记录。《宋伯望分界刻石》则有残损漫漶,学者对其性质莫衷一是。但无疑义的是,二石皆为标识位置及土地所有权的石刻,则地产类石刻早在东汉前期已经产生。
唐代明确记载边界四至的石刻相当常见,尤以佛教石刻居多。叶昌炽认为,佛教谓界至为大界相,并举唐永泰二年(766年)《丰乐寺大界相碑》、宋景祐五年(1038年)《明州保安院大界相碑》。阮元在《两浙金石志》中提出“界相即地形变文”,叶昌炽则称“此是禅家语,质言之,则四至而已矣”。唐代径以“四至”为名的佛教石刻,有长庆三年(823年)《特赐寺庄山林地土四至记》,现存山西省交城县玄中寺,碑文记载寺院历史及山林土地边界,有证明产权来源合法、边界清晰之义。此外,唐代还有单独为寺院田产立碑之例。《金石录》载:“唐育王山常住田碑,万齐融撰,范的行书,大和七年(833年)十二月。”此碑现存浙江省宁波市阿育王寺。据《宝刻丛编》引《复斋碑录》载:“《唐阿育王寺常住田记》,唐万齐融撰,范的行书,大和七年十二月刺史于季友重立,元碑乃徐峤之书。”徐峤之为书法家徐浩之父,亦精于书碑。考史籍所载,徐峤之活跃于武周至玄宗时期,则原碑最晚在玄宗时期已经建立。相较于单独记录寺院四至或寺田边界的碑刻,《法兴寺碑》更像是一份“寺产清单”,记载了法兴寺各类资产。《宝刻丛编》转引北宋田概《京兆金石录》载:“《唐安国寺产业记》,僧正言撰,大中五年(851年),刻于大达法师碑阴。”《大达法师碑》即《玄秘塔碑》,《唐安国寺产业记》指碑阴上部所刻《敕内庄宅使牒》与《比丘正言疏》,两则文书记载了安国寺包括屋舍、树木、菜园、家具等在内的各类资产及价值,故宋代金石书称之为“产业记”。此前将碑阳定名为《法兴寺碑》,则碑文无涉寺史;称之《法兴寺界限碑》则未涵盖寺产全貌。参照《唐安国寺产业记》,法兴寺碑碑阳文字或可定名为《法兴寺产业记》。
法兴寺寺院经济与文化遗存
在《法兴寺产业记》开列寺产中,值得一提的是“洪簇寺窠一所,东至焦家山,南至沙河沟,西至麻儿沟,北自至”。何谓“寺窠”?《宋高僧传》载僧人释全玼“隐衡岳中立华庵。木食涧饮,结软草为衣,伏腊不易。有赠玼诗云:‘窠居过后更何人?传得如来法印真。昨日祝融峰下见,草衣便是雪山身。’”“窠居”为简陋居处,指全玼隐居之立华庵。《明重修龙泉寺记碑》载“寺窠迫促,僧徒罕聚,莫如增其式廓为久大”,可见寺窠乃规模较小的佛教场所。碑文记洪簇寺窠北面边界称“北自至”,王昶曾论“《重修大像寺记》所载庄地果园四至,近他人者,著他人姓名。近本寺地,则曰自至”。《法兴寺碑》中,记麻地边界有“西至贾天祥”,记庄地边界则有“东至贺秀,南至段顺祖等,西至李德玉”等表述,即是与他人田地毗邻而著邻人姓名,洪簇寺窠“北自至”则表明,寺窠建筑北缘为法兴寺所属田地。
在法兴寺拥有的七处田产中,占地一顷以上的大片寺庄共四处,本寺直接管理两处,下院大觉院与圆照庵各管理一处。剩余三块面积较小的田地中,只有位于石佛堂的麻地,除了记载田地四至还写明土地面积为三亩七分。麻属于经济作物,商业价值大于粮食作物。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介休所属的汾州“贡、赋:开元贡:龙须席,石膏。赋:布,麻,菽,粟”。点校者在“布麻”后出校记称“今按:殿本同此分布与麻为二,它本作‘麻布’为一物。”不论是缴纳“麻”还是“麻布”,都说明麻是唐代汾州地区的重要物产,具有较高经济价值,此处麻地当为法兴寺重要经济收入之一。
在法兴寺产业中,尤需注意的是水磨、水碾等粮食加工设备。隋唐时期,寺院拥有水碾、水磨设施并从事相关经营活动十分普遍。隋文帝时期,晋王杨广作为京师清禅寺施主“前后送户七十有余,水磑及碾上下六具,永充基业,传利于今”。唐初,因寺僧助平王世充有功,“少林寺赐地肆拾顷、水碾硙一具”。一些地方小寺,包括偏远如敦煌地区的寺院也普遍拥有水碾。法兴寺拥有的三处水碾、水磨中,源神后及堡和沟,只记水磨一分,而观音堂的水碾及磨则位于法兴寺自有地中。前两处水磨或许主要用于经营活动,而自有田地中的碾、磨可能主要用于本寺田地所产粮食的加工。在水资源调配上,碾硙经营与农田灌溉存在矛盾。中古时期,因两种用水需求冲突发生的争讼屡见不鲜,严重者甚至惊动皇帝裁决。法兴寺是否存在类似纷争?根据碑文所载,法兴寺一处水磨位于“源神后”。此处“源神”为地名,夷考史料可知“源神”同样是介休一带影响深远的水神信仰。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年建立的《源神碑记》记载了至道三年(997年)介休官民在洪山重建神堂并于大中祥符元年立碑纪念之事。碑文称:“灵泉化出,古庙齐兴”,又言“浩辟沧江,滋浓汾介。护持国土,亨扶圣代”,“昔虑华宫,庙宇凋坏。将命雄标,重谋更改”。可见,源神是与水源灌溉、护佑农业有关的地方神祇,在北宋初年重修神堂以前已经建有“古庙”。据《法兴寺碑》,源神作为地名在法兴寺产业范围内。今源神庙坐落于介休洪山镇洪山村洪山泉(鸑鷟泉)源头。据庙内明万历《新建源神庙记》载,时任知县王一魁因原庙址“在山之西阜南向,位置奇侧,而南山当面墙立,瞻眺弗广。泉出左腋,陟庙则泉不可见。又基址狭隘,垣宇倾颓”,故选址重建。“顷之,见南山麓有平阜,马喜而登其上,则连亘诸峰,隆隆南负。左右盘礴崛起,若双阙逶迤。北下益蜿蜒暎带,不知其几里,豁然大观。而飞泉数道,泻出于平阜下两峰之间”,此即王一魁所选新址,即今庙所在地。根据碑文,源神庙原址坐北朝南,南山在庙南如墙耸立,遮挡视线,而新庙则在南山之麓,北面有蜿蜒谷地。结合当地地形,可知明万历以前源神庙址在现址隔河沟相望的北边山地。总之,源神庙的原址与现址都紧邻泉水源头,距离法兴寺碑出土地十分近,说明法兴寺建于泉水上游。
与之情形类似的是广胜寺的地理环境与空间位置。法兴寺属于汾州介休县,位于汾河东岸、霍山北缘,广胜寺属于晋州赵城县,同样位于汾河东岸,但在霍山南麓。两寺南北相对,正可互相发明。《太平寰宇记》载:“霍水,在县北三里。《水经注》云:‘霍水源出赵城县东三十八里广胜寺大郎神,西流至洪洞县。’”广胜寺地处霍水源头,而大郎神正是自唐代便在赵城、洪洞地区影响广泛的地方水神,宋代被加封为明应王。金正隆四年(1159年)刊刻的《平阳府赵城县霍山广胜寺莹山主塔铭》,在记述广胜寺僧宗莹生平事业时,有“争大郎庙一所”“前后住持,连绵三次,可十五余年”的记载,塔铭还记述了宗莹创修水磨、开发水利之事。争得大郎庙管辖权对于广胜寺及僧众而言,意义重大,也表明寺院占据有利地形可以控制水源,占据水利。法兴寺也是如此,凭借位于洪山泉(鸑鷟泉)源头的有利地形,设置多处水碾、水磨,利用水能从事粮食加工,获取经济利益。同时,因地处上游,方便截流水源,法兴寺在地方农业生产用水中也具有一定话语权。五代时期,法兴寺已更名为洪山寺。在《源神碑记》碑阳末尾,题名的第二行下半部分有“洪山寺尚座、讲《上生经》僧云秀,讲《百法论》、业讲《法华经》僧智皓,见充寺主僧智峦,僧智显、法敬、法蕴、法言”等人。在纪念重修源神庙宇的碑刻题名中,洪山寺共有七名僧人得以留名且排在相对靠前的位置。足可说明,唐宋之际法兴寺与源神信仰联系密切,甚至可能通过吸收利用源神信仰的方式,达成对水利资源的掌控。
此外,碑文记载了大量地名,在考证区域历史地理沿革方面也有特殊意义。康熙《介休县志》载介休县东乡有前樊王村、后樊王村,县志又载祭祀樊哙的樊王庙在樊王村,则前、后樊王村当为一村分化而成。北宋《源神碑记》碑阴列各村社题名,有“樊王社”。由此上溯,唐代“樊王道”得名当与樊哙传说或樊王信仰有关,同时“樊王”作为地名从唐代经北宋、明清一直延续至今,显示出地方文化的悠久传承和深远影响。康熙《介休县志》载东乡、南乡都有刘家山村,今刘家山村位于出土《法兴寺碑》的洪山瓷窑遗址以东,直线距离约2.5公里处,且位于樊王村与后樊王以南,方位与《法兴寺碑》所载四至吻合;南乡有崇贤村,位于今洪山瓷窑遗址西7公里处。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介休县将原有的45处坊里合并为24处,清顺治九年(1652年)又合并为12处,原有的45处坊里中有永润里和武同里,按同书载“在城曰坊,近城曰厢,在乡曰里”的原则,永润里、武同里实际为永润村、武同村,武同村作为村名同样出现在《源神碑记》上。康熙《介休县志》载“武同泉在县东三十五里武同村,溉地十五亩”,嘉庆《介休县志》则载:“武屯泉在县东三十五里武屯村,溉地十五亩。”今介休连福镇有东、西武屯村,说明武同村作为村名确实从唐代传承至明清时期,但在清代或许因音近而发生改变。东乡有木壁村,在今后樊王村、刘家山村以南,名称或沿袭自唐代木毕庄。
唐代法兴寺有下院圆照庵,明代洪武年间并入法兴寺的有圆照寺,从名称、规模及从属关系来看,明代的圆照寺很可能是在唐代圆照庵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此外,今介休洪山镇有焦家山、紫林沟、炭窑沟等地名(图三)。现地名未必全部能与唐代位置一一对应,但法兴寺碑的出土,为后人了解区域沿革及地名文化传承提供了实物资料,同时也证实部分地名历经千年传承,延续至今,显现出山西地区古代基层社会稳定传承的一面。
图三 法兴寺及周边庙宇、村落分布示意图(地图来源: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等5册《隋·唐·五代十国时期》,第46-47页“河东道”改绘)
法兴寺沿革与介休地方社会的互动
成化《山西通志》记载山西境内法兴寺有四,“一在介休县东南二十里洪山翠微,宋政和元年(1111年)建。国朝洪武间,并禅觉、圆照、十方三寺入焉”。法兴寺碑的出土,修正了方志中关于寺史的记载,唐代贞元年间法兴寺已经颇具规模,绝非始建于北宋政和元年。碑阴刻写的《洪山寺重修佛殿记》,为后人了解法兴寺的历史沿革及其在介休信仰世界中的位置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细节。
首先,北汉重修佛殿时,法兴寺已更名为洪山寺。据《重修佛殿记》载,法兴寺建寺祖师为北魏时期的洪师和尚。洪师从山东地区到洪山传法,分别在紫林和洪岳建立精舍,此即《法兴寺产业记》所载“洪耀庄东、紫林,两处洪师道场”。洪师在当地赢得男女信众争相供奉,信徒共同为其建造寺院并命名为“洪师之寺”。随着信徒宣扬,洪师声誉日隆,被北魏皇帝征召并赐寺额为“洪山之寺”。据此记载,似乎自北魏赐额直至北汉,该寺一直名为洪山寺。考诸佛教石刻,唐代北方寺院,特别是太行山区佛寺,在追溯寺史时附会北朝高僧乃至皇帝,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距离法兴寺不远有抱腹寺,据《有唐汾州抱腹寺碑》载:“后魏太和中,高僧迪公之经始之。迪公昔因乞食,尝至介山,喟然□叹曰:兹地贤□□居,宜修塔庙。遂杖锡而往咨冥搜……魏明览而休□,特诏置寺。则抱腹之号,由兹而作。运更□隋,额有兴替。”碑文不仅叙述了抱腹寺为高僧迪公于北魏太和年间创建,又指出寺名为孝明帝所赐,而随着政权更替,寺额也曾多次改易。位于太行山以东的邺县修定寺,有开元七年(719年)建立的《大唐邺县修定寺传记》,碑文记载“修定寺者,后魏兰若,沙门释僧猛之所立也”,还详述了寺名沿革:北魏孝文帝赐额“天城寺”,东魏权臣高澄改寺名为“城山寺”,北齐文宣帝又改为“合水寺”。至唐开元年间建碑时,已改为修定寺。可见,无论是宣称前代高僧创建,还是寺名为皇家颁赐,是地方大寺惯用的叙事模式。而寺名更替变化,更是寻常。据此推测法兴寺史,其初创于北魏时名作洪师寺,或许北魏曾赐额为洪山寺,至唐代寺名则更为法兴寺,北汉时又改回洪山寺。《山西通志》载介休法兴寺为宋政和元年建,或许政和年间将寺名再次改为法兴寺,故方志误记创寺年代。
北汉天会十四年七月十五日,当地信众杨晖、李进等人,看到洪山寺大殿年久日深有倾塌风险,于是发心重建。根据碑阳所载法兴寺产业,法兴寺的信仰辐射范围覆盖周边众多村庄,寺田与众多民田相邻。继承法兴寺而来的洪山寺应当同样如此。杨晖、李进等人“屡届禅宫,每亲硕德”,是与洪山寺往来密切的虔诚信徒。同时,他们也是提议重建的发起人和出资人,在信仰活动和经济往来上都与洪山寺联系紧密。而在碑末题名中,出现了介休县令、主簿和镇使三位地方主要长官的名字,说明此项营建工程并非信众自发的民间行为,而是得到官方认可和支持的举动。五代时期,洪山寺经过长期发展,影响力及于官民不同阶层。以杨晖、李进等为代表的富庶信徒,是洪山寺重要的供养人和经济往来对象。通过立碑等仪式性活动,富民、官员等地方重要人物齐聚洪山寺,创造了寺僧与不同阶层往来互动的机会。官、僧、民三方,出于权势、名声、经济或纯粹的精神信仰考虑,通过题目刻石的方式达成阶段性的利益联结。洪山寺凭借这项影响,在介休地方社会的信仰世界中更加牢固地占有一席之地。
仔细分析碑阴僧人的题名序列,可以发现洪山寺的发展处于上升期。题名僧人以寺主谊靖为首,同辈僧人有谊普、谊昭;谊字辈后有僧人惠繁,其后为云字辈僧人四人,最后为智字辈僧人九人。有字辈的僧人,同辈皆有数人,且字辈排名越靠后人数越多,说明此时洪山寺僧众传承有序、地位尊卑分明:辈分最长的谊字辈担任寺主等管理职务;中壮年的云字辈僧人,已经具备相当的佛学造诣,可以主讲经律;最年轻、地位较低但人数最多的智字辈僧人,则是寺院的后备力量。至于惠字辈,仅有惠繁一人,多半是不入洪山寺僧行辈者。天会年间,洪山寺老中青三代僧人字辈从高到低依次为谊、云、智。《源神碑记》建立时,距离重修洪山寺大殿已经过去三十余年,《源神碑记》碑阳所载洪山寺僧人的题名顺序已经变成“洪山寺尚座、讲《上生经》僧云秀,讲《百法论》、业讲《法华经》僧智皓,见充寺主僧智峦,僧智显、法敬、法蕴、法言”。其中上座云秀曾出现在《重修佛殿记》题名中,天会年间云秀只是寺内第二代的中层僧人,未担任寺内要职,且在同辈僧人中排名最末。大中祥符年间,云字辈的僧人已经是洪山寺年纪最长、辈分最高的一代,昔年身份地位相对靠后的云秀也已经成长为洪山寺领袖并负责经义传授。依此类推,天会时期尚且稚嫩的智字辈此时也成长为寺内中坚力量,第四代法字辈僧人则成为洪山寺的新生力量。可见,数十年间洪山寺的僧人群体新旧更替、序列分明,处于良性发展阶段。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撰写《重修佛殿记》的作者为抱腹山白云岩沙门智泉,他自称奉命撰述。那他奉何人之命?诚然,题名中出现了介休县令、主簿、镇使等官员题名,他们作为地方官员自然有权力命令智泉撰文。但疑点有二:一是本寺僧人更加熟悉寺史,且具备文化修养者不在少数,为何舍近求远从其他寺院找不相干的僧人撰述?二是重修佛殿乃洪山寺之事,寺僧谊靖等为主人,介休众官员为受邀之贵宾,立碑刻石为纪念大殿落成配套之事,理应由主人一并操持,岂能交由贵客费心?因此,智泉所受只能是受洪山寺掌事僧人之命。智泉法号同为智字辈,而在碑上留名的洪山寺智字辈僧人中有智江,其与智泉不仅行辈相同,法号也都与水有关。种种迹象表明,抱腹山白云岩沙门智泉是出自洪山寺门下第三代智字辈的僧人。如此,他受命撰文则于情理皆合。
抱腹山为介休当地另一处有名的宗教圣地。开元二十年(732年)建立的《有唐汾州抱腹寺碑》,记述抱腹寺建寺历史,现存介休市绵山景区棋盘洞前。碑文称北魏太和年间,高僧迪公创建寺院,孝明帝赐额“抱腹”。《续高僧传》载,隋唐之际有榆次僧人志超于“武德五年(622年),入于介山,创聚禅侣。岩名抱腹,四方有闻……又于汾州介休县治立光严寺,殿宇房廊,躬亲缔构,赫然宏壮,有类神宫。故行深者岩居,道浅者城隐”,志超在山中与介休城中分别建立修行场所,山中道场在抱腹岩下;同书又载:“近武德初年,介山抱腹岩有沙门慧休者,高洁僧也。”《法苑珠林》亦载:“唐汾州光严寺释志超,俗姓田,同州冯翊人也。精厉不群,雅度标远。至武德七年(624年),止于汾州抱腹山。”可见,在隋唐之际,介山之中已有抱腹山之名,则《有唐汾州抱腹寺碑》所载抱腹山的佛教活动始于北魏,大致可信。唐宪宗时期,汾州开元寺僧人无业望著朝野,为避俗务“逍遥绵上抱腹山”。抱腹山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声誉日隆;僧人志超则在后世逐渐演化为空王佛,成为介休当地影响深远的信仰对象。
抱腹山是北魏时期已经扬名、在后世介休地区长期占据重要信仰地位的佛教圣地。北汉洪山寺刻碑之际,抱腹山在介休当地信仰世界中必然也有重要影响。咸平五年(1002年)建立的《抱腹山回銮寺及诸寺院灵境之碑记》记载了抱腹山的佛教发展历程和回銮寺得名由来。碑后题名有“寺主、讲诵《法华经》《百法论》僧智玄,念《法华经》僧智严,殿主、讲《上生经》僧智海”,另有“僧讲《上生经》智谕”和其他智字辈僧人两名。前引《源神碑记》题名洪山寺尚座云秀讲《上生经》,洪山寺僧智皓讲《百法论》、业讲《法华经》。从擅长的经律来看,抱腹山回銮寺智字辈僧人与洪山寺僧人几乎一致,不外乎《上生经》《法华经》和《百法论》三类;两碑建立时间仅相差5年,两寺智字辈诸僧为同时代人,对比法号,回銮寺智海与洪山寺智江、回銮寺智谕与洪山寺智谊,两寺僧众在取名方式上高度相似,极有可能是师出同门的同辈师兄弟。而洪山寺上座云秀作为年辈最高、地位最尊的师长,教导了包括洪山寺僧众与抱腹山白云岩智泉、回銮寺众僧。这些受业于洪山寺的僧人,不但成长为本寺的中坚力量,还向外发展,在抱腹山这处寺院林立、底蕴深厚的佛教圣地开辟了洪山寺法脉的新据点,甚至担任一寺之主,成为领导核心。这足以说明,唐宋之际洪山寺在介休地方的信仰世界和知识世界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而自唐中期贞元时代开始,已经积聚颇具规模的寺院产业,是法兴(洪山)寺持续不断发展并向外进行知识和人员输出的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
结语
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建设与文物考古工作的深入推进,以碑志为代表的各类地下文物不断出土。追踪新材料的同时,充分利用原有资料,综合深入地挖掘历史信息,无疑是进行解读的关键。以介休出土的法兴寺碑为例,碑阳刊刻的唐贞元年间《法兴寺产业记》,一方面可以增进对唐代寺院经济结构的了解,特别是对中晚唐时期河东社会经济的认识;同时作为实物例证,也丰富了唐代寺产碑刻乃至中国古代契证石刻、经界石刻的类型。同时碑阳留存大量村一级的唐代地名,结合宋碑和明清方志记载,有助于深化对区域地理沿革和聚落分布的探讨。其中,部分地名历经千年延续至今,体现了乡土文化的韧性与生命力。
碑阴《洪山寺重修佛殿记》是前人未曾完整录文的石刻文献,具有较高文献价值与史料价值。记文构建了洪山寺发展史,结合唐代河东地区其他寺院碑刻关于寺史的记载,可以发现寺史建构模式的共性。特别是太行山区沿线,因处于北朝几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晋阳、邺城、洛阳之间,留下大量与北朝皇帝和高僧有关的传说与遗迹。因此这一区域的地方名寺,大多会将创建历史追溯到某位北朝高僧,将寺额确立附会至某位皇帝。历史真实与传说糅杂,构成区域佛教文化的叙事特色。
唐宋之际的洪山寺,依托自贞元时代已经积聚的颇具规模的寺院产业,不但在介休信仰世界占据一席之地,在地方公共事务中也掌握一定话语权。在充足的物质保障前提下,洪山寺僧人潜心佛教经义研读与传授,培养了大量佛教人才,不仅维持了寺院的有序传承,还向邻近寺院输送精英僧人,开辟法脉的新据点,成为区域佛教中心和知识中心。凭借广泛的社会影响,洪山寺僧人积极参与地方公共事务,一方面是为保持寺院对地方水利等经济利益的长久占有;另一方面则强化与本地富民和地方官员的联系,拓宽寺院的社会网络,从而维持寺院在地方社会结构中的优势地位。法兴寺碑的出土填补了介休佛教史的一段空白,揭示了唐宋之际河东区域社会发展的局部面貌,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物价值。
附记:本文系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中古华北信仰空间的社会治理功能研究”(项目批准号:ZX20240276)阶段性成果。法兴寺碑碑阳、碑阴拓片高清图片由介休市博物馆提供,谨致谢忱。
(本文首刊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5年第9期,作者史正玉[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