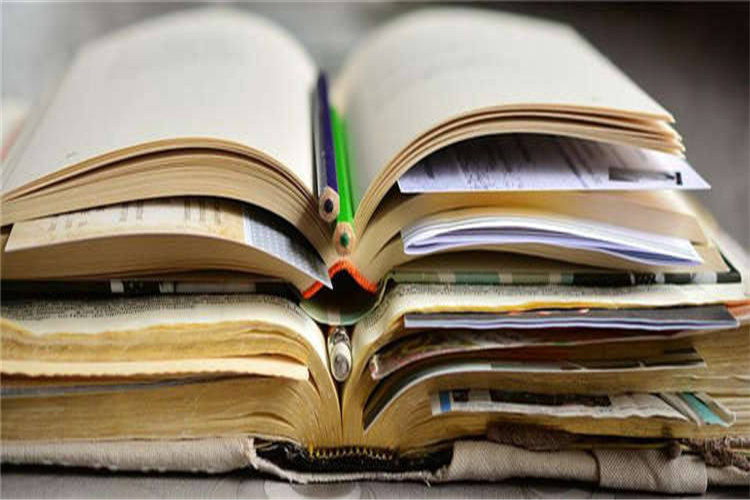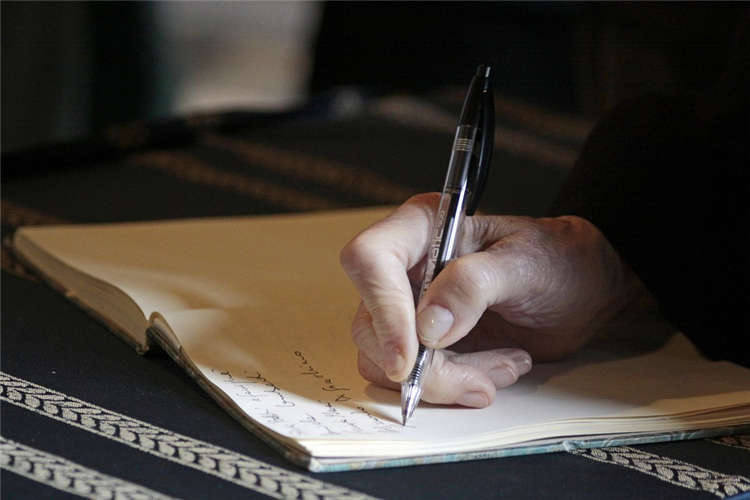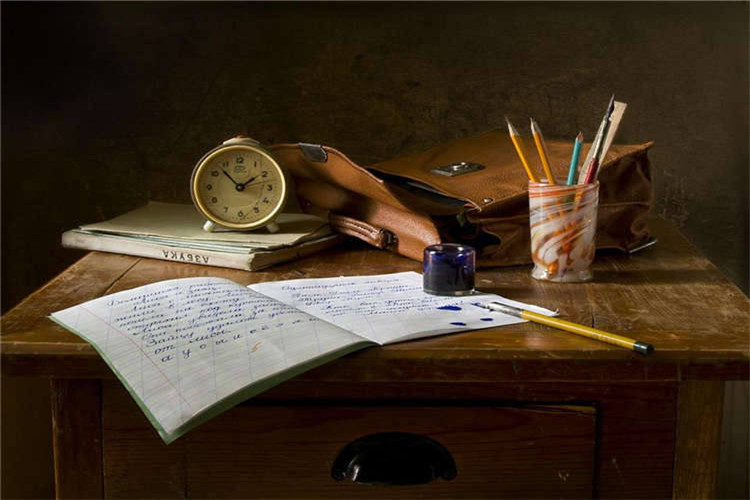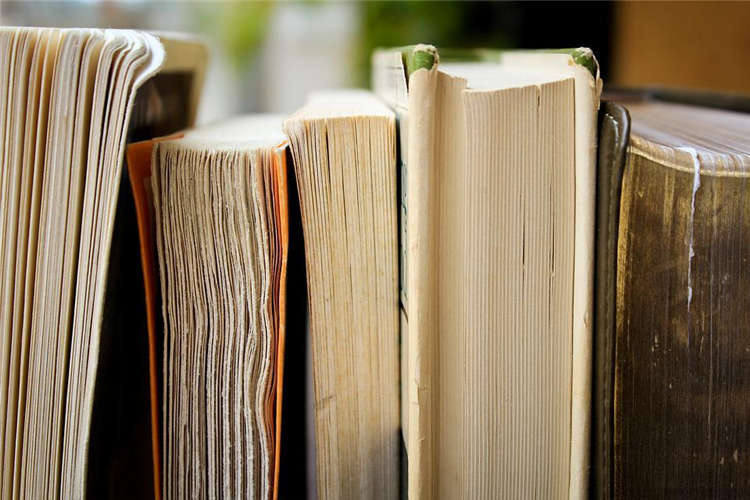人类学从西方(欧美)扩展到亚洲的百余年过程中,不同区域和国度有不同的历史进程。不论是本土学者开展的研究还是西方学者来这些地区开展的调查,基本上都是延续性的,即在学理上没有与西方的发展脉络中断。如果说有变化的话,那也只是人类学学科内部随着理论模型、 问题意识和观察视角的更替而发生的转变。但是对于中国大陆而言,情形却颇为不同,给人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感。
约略来说,从晚清到民国时期,中外人类学家在中国经验中进行的中国人类学实践基本遵循西方的脉络,尽管少数学者融入了部分国学的智慧和线索。但自1949年以来,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乃至80年代中期,中国人类学(主要指以民族学形式开展的文化人类学)总体是在社会主义框架下发展的,其突出特点是以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为指导,突出“阶级”“剥削与压迫”“社会性质”“社会制度”“社会类型”等内涵或议题,广受苏联民族学范式影响和渗透。然而自1979年中美建交,尤其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把自己放在世界范围内谋求发展,遵循市场经济的逻辑,中国人类学由此获得了跟西方人类学再接触乃至再亲密的机会。加之西方各种哲学思想被译介进来,中国人类学由此突破了单一理论指导下的研究范式,变得五花八门,甚至极为驳杂。
马丹丹选择了中国南部三个省份的三所大学,即东南沿海的厦门大学、中山大学(这两处在太平洋西海岸)和地处喜马拉雅山脉东南麓深处的云南大学的人类学作为考察对象,结合全国总体的形势和其他地方学者的探索,举例式地说明了中国人类学的这段发展历程,展现了各方行动者的心思与努力,当然也有曾经的焦虑和苦恼,以及成功后的欣慰和喜悦,描绘出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面。打个比方说,她假定一部机器熄火了,然后着重考察了该机器如何再次被启动。因而,文章具有极强的可读性,引人入胜。叙事之后,她不忘作理论的探讨,即试图在三家单位之间区分出不同的人类学发展路径和模式,显示出其总体的俯瞰与把控能力。
选择中国南部尤其是东南沿海作为考察对象,可能具有特别的意味。我们知道,中国近现代化的启幕就是从这一地理区域开始的。也就是说,来自西方的所谓近代化或现代化浪潮就是从这一海岸线登陆中国的,由此将古老的中国从传统叙事轨道里拖出来,使其迈入了近现代征程。而西南的云南是作为东南沿海的一翼或战略纵深被纳入这个历程的,在近代中国的叙事里,云南往往作为广东的响应而出现(比如蔡锷在护国战争中对孙中山革命的响应与配合)。反观中国北部和西北地区,由于地处广袤的亚洲内陆腹地,其现代化的步伐总是慢了一步。之所以选这三所学校,可能在作者的意识里也潜藏着这样一种她意识不到的认知图式。如果作者没有这种图式,那么中国40多年来重建的人类学就是分有了中国近现代化发展的图式。于是,《轮廓:中国人类学南派的重建伊始》就有了西方人类学家或人类学的影子,如武雅士、德国哥廷根科教电影研究所及留学西方的中国学者等。在学科史文本中,这些被作者视为中国人类学重建的启动引擎之一。当然,另外的引擎就是本土的学科发展诉求及已有的历史积累和传统。可以说,中国人类学40多年来的重建是这三股力量互动的结果。
当今中国大陆许多人类学从业者喜欢用“重建”或“重建以来的中国人类学”这样的词汇或短语来指称40多年来中国大陆人类学的开展,我不这样认为(按:我以往的论述也有过这种糊涂认识)。我觉得,这只是中国人类学在不同时代场域里的实践或表现。不能说集体化时代搞的民族学就不是人类学。在我看来,中国实践的民族学只不过是某一理论主张下的文化人类学实践之一种。所以,要意识到“中国人类学”没有死亡,更没有腰斩和中断,它只是因应不同时代氛围和场域穿上了不同衣服,用不同眼睛或从不同视角打量世界,本质上还是有作为实践者的“中国人类学”存在,哪怕是在集体化时代。语言名称上的暂时隐形或被取缔,并不意味着它消失了。就像一个人有没有名字都在世界上存在一样,我们不能因为没给他起名字、暂时取消其名字或换了名字,就以为他消失了。至于本书中提到部分学者和单位在学科开展中把民族学与人类学分开,即持有分别之心, 那也只是想发展自己心仪的某种人类学样态,或者在一个全国性的氛围内刻意跟一些单位和人相区隔,这只是做事的一种策略或借口。但这种策略和借口却反映出了一种狭隘之心,由此失却了人类学的包容胸怀。人类作为在地系统的一个物种,在全球各地有不同的社会与文化,理解他们、尊重他们、包容他们,是人类学最本真的追求和精神。我们不该存有分别之心。
既然是举例式的说明,那就不是全景式的梳理、回顾与建构。只有明白作者的这个思路,读者才不至于因没有提到自己、自家单位或心仪的学者而指责作者的不对或不当。我思考中国文化人类学史习惯于从民族志入手,或以民族志为线索,以各项议题为焦点,去探讨中国人类学的起承转合,尤其习惯于将其放在一个世界知识生产的平台与脉络链条里,看中国人类学家都取得了哪些理论成果。具体而言,包括发明了什么概念和什么样的理论解说模型(不是事后的工作思路总结。国内学者这些年抛出的许多所谓“理论”就是这种工作总结或心得,要不就是自己设计的空架子、空概念,与西方人类学建立在民族志基础上提炼理论学说的方式与逻辑不同)。从这样一个思路出发,我觉得马丹丹遗漏了上述三个单位的许多民族志专著和学者,即便提到也未作深入的理论分析和探讨。相反,她的同代人被介绍得过多,而一些资历更深的学者没有被提及,担心书出版以后,会被读者指责有失衡问题。但如果明白了她的视角和思路,可能这样的困惑和内心的不满就会消失。
客观而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就作者而言,可能是:①没有访问到一些重要的学者;②对于过往的情况,作者的阅读范围和兴趣点未及;③由于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无论是科研经费的情况还是结项时间的要求,都使其无法充分地开展调查、访问和研读;④与她对“南派”的语义理解有关。这些年来,马丹丹致力于梳理和总结40多年来中国人类学学科重建历程。作为一个40多岁的青年人类学学者,她没有与这段历程相始终的经历,即很多事情她没有经历过。此外,当聚焦于一个地域性学派恢复、重建与发展史的时候,她不是局内或圈子里的人,很多事情只能靠文献阅读(出版的和没有出版的)、事后口述访谈和当下的参与观察去了解。当然,被访谈者提供什么样的信息,也会影响到学科史的撰写。
写学科史是最难的事情,尤其是撰写当代学科史,因为被写的人都健在,教学单位和研究机构还在运转。他们可能会因种种原因而对作者充满怨言,甚至有与学科史专家从此不往来者。有的当事人觉得写自己太少,写别人太多,且不愿意让作者分析自己的得失,指出存在的问题,目的是想在学科发展历程中留下更多关于自己的集体记忆和美好形象。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会在接受学科史专家采访时只讲自己的东西,故意夸大自己的成就,刻意隐瞒自己的问题及同行的作为和观点,甚至个别人可能恶意贬低同行,对同行进行丑化乃至扭曲。书成稿以后,交给不同的当事人审阅,他们在看到有关同行的文字时,可能产生对比、攀比甚至嫉妒之心,于是对作者的抱怨之情会更加浓重,常常弄得作者内心很窝火。当然,被访谈者也可能确实对他人或同事的情况不了解,这种情况下也会造成疏漏。更为普遍的一种现象是,中国人忌讳说他人,以免给自己带来麻烦。
鉴于上述种种情形,我们不难想象和理解马丹丹在撰写这部学科史时遇到的困难和遭受的委屈。我想,“出力不讨好”不仅是她当下的一种感受,也是她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抹不掉的心理阴影。马丹丹受业于中国民族学与文化人类学学科史专家王建民先生,王建民以著作《中国民族学史》(上、下卷)闻名国内外学术界,个中甘苦他是最有体会的。正因如此,他才不建议弟子们纂修学科史。马丹丹知难而进,其勇气可嘉、可佩。她用种种办法核对被访谈者提供的各种信息,努力辨别真伪,去伪存真,辨义析理。读者了解到这份辛苦后,就不得不尊重这份出版的文本。我想,不管存在怎样的争议和不满,但有一点是可以为大家所共同接受的,即这部作品为我们提供了大量而丰富的信息,借此可以了解中国南部(以三个点为例)人类学恢复、重建与发展的缘起与历程,满足中国人类学学者的好奇心。这正是本书出版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最后我想谈谈南派的问题。从已有学科文献看,最早提出“南派”概念的学者是中国台湾地区的唐美君。1976年,他在《人类学在中国》一文中指出,南派以台湾“中研院”为中心,与历史学派有深厚的关系。而后是黄应贵,他在《光复后台湾地区人类学研究的发展》一文中认为,“南派即历史学派”。我们根据南派重要人物芮逸夫于1972年出版的《中国民族及其文化论稿》(上、中、下)来看,确实符合这个特征。在这个认识基础上,王建民后来于《中国民族学史》上卷第五章中提出了“中国历史学派”的看法。该学派不仅仅是以“历史的方法”对民族的具体材料进行描述和整理,而且注重引用和研究中国历史文献资料,强调运用民族学的各种理论和方法解释中国的材料,解决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难题。“中国历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以进化论作为主要的理论观点,较多地利用法国民族学派收集资料的方法,吸纳了美国文化历史学派的研究框架和步骤。王建民列出的代表性学者有凌纯声、陶云逵、卫惠林、芮逸夫、林惠祥、马长寿、杨成志、杨堃、徐益棠等人。从王建民的分析来看,他显然接受了唐美君、黄应贵之“南派”的历史意蕴,但又突破了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南”字意义。
那么,如果沿袭唐美君和黄应贵的语义,并结合王建民的具体理解和阐释,本书用“南派”作为书名关键字眼,倒也不是不妥,毕竟现在的厦门大学人类学追认林惠祥为鼻祖;中山大学人类学追认梁钊韬(杨成志的学生)为重建人类学系的开基祖;云南大学把杨堃、方国瑜(曾在北京师范大学读本科,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读研究生,1934年进入“中研院”史语所工作,后至云南大学)、江应樑(20世纪30年代曾经在中山大学研究院工作过,后至云南大学)作为重建人类学系的系谱祖先,而且江应樑还于20世纪80年代在云南大学主导重建了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指导林超民等开展学科筹建工作,当时杨堃也在这里。
但是,从另一角度来看,又存在一定的问题。本书中的“南派”可能在人类学重建初期还有个影子,因为那时梁钊韬、江应樑、林惠祥的弟子们如陈国强、蒋炳钊等都还健在,还有进化论和民族史的探求在里面,但后来随着西方人类学各种理论流派的引进及多元师资力量与研究力量的加盟、汇入,历史的诉求开始从该学派的主线上滑落下去,所以“南派”已经名存实亡。当然,也可以用“新南派”来称它,就像一粒土豆烂掉后,新的土豆才能从中发芽。又,若从谱系学追溯,“南派”这个字眼也应该包括飘零到台湾去的凌纯声、芮逸夫、卫惠林等人及其弟子、再传弟子系列;还应该包括江应樑的学生如杨庭硕一系,他们回到贵州和湘西,在那里开枝散叶。但作者没有涉猎这些人物。若要细细考虑,可能厦门大学历史系、中山大学历史研究中心和云南大学历史学院也可以列入考察之列。故,本书不妨看作一部托名为“南派”的区域人类学学科史著作,或者如上所云“是举例式的说明”。即便澄清到这一步,我想也并不能否定本书的学术价值。我坚信,读者在阅后自会有所收获,对作者有所感激。
语义学上的“南派”或“中国历史学派”之所以在作者的笔下和被访谈者的口述中脱漏,大致有两个原因。其一是理论演化的结果。最近几十年来,中国大陆人类学学者集体性地排斥和抵制进化论思路,批评其线性的思维方式,有时对进化论的批评隐藏在对现代化思路的反思中。其实我个人认为,进化论揭示的思路在一个社会中不是绝对没有存在的道理,因为一个社会总要有个理想类型去牵引,没有方向感,我们就会变成无头苍蝇。试想,有一个历史学家认为人类是不断进步的,从低级到高级;另一个历史学家认为,人类社会越来越倒退;还有一个历史学家认为,人类的历史是循环往复的(如汤因比);最后一个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人类社会是停滞不前的。那么,如果你有孩子,你愿意让他相信哪一种呢?我想多半你会选择第一种,即进化论思想,否则,后三种就会让他产生没有前途、没有进步和没有光明的预期,他的一生都可能处在抑郁而灰色的状态中。所以,进化论作为一种价值学说,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二是,当文化人类学被置于社会学范畴来想象和发展的时候,就会被国家对社会学的期待所塑造。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现代化和市场化的推行产生了一些社会问题,国家希望社会学能够调查清楚这些问题,并提供解决问题的方略。这样,人类学转为应对社会问题之学、研究民间疾苦之学,而再也不像五六十年代那样是一种国家顶层设计之学(指各民族社会性质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参与中华民族的国家构建)。所以,中山大学出现了都市人类学、移民人类学,云南大学出现了民族文化生态村实验和建设(当然,我不是说人类学不该对新生事物产生敏感性)。这些从事应用人类学、行动人类学的学者可能觉得历史维度的思考对于解决中国当下现实问题不是太贴切。殊不知,20世纪30年代之所以出现大量民族史著作,南派或中国历史学派登场,均是因应时代重大问题的结果。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的边地有被分裂出去的危险,日本觊觎满蒙、沙俄觊觎新疆、英国觊觎西藏,云南也遭遇了同样危机,等等,这使得中国人类学家要从历史出发,深入论证这些边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疆土,其中最响亮的呐喊就是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所以,当我们批判南派或中国历史学派的时候,一定要弄清楚我们的人类学前辈何以要做那样的学问,不一定非得按照自己的人类学理解而将这个研究方向排挤出去或压缩其发展空间。
上面说到,南派或中国历史学派的影子要到今日一些历史学院或历史研究机构来寻觅,不是没有证据的。就中国的西南地区研究而言,近年来出版了纪若诚的《亚洲边疆:清代中国云南边疆的转型(Asian Borderlands:The Transformation of Qing China’s Yunnan Frontier)、乔荷曼的《云雾之间:中国在贵州的殖民,1200—1700(Amid the Clouds and Mist:China’ s Colonization of Guizhou,1200-1700)与《西南边疆的合作与反抗:18世纪初清朝的两线扩张(Collaboration and Resistance on the Southwest Frontier: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Qing Expansion on Two Fronts)、戴沙·莫滕森的《中国统治下香格里拉的历史:滇西北藏区的记 忆、认同与控制权争夺》(The History of Gyalthang Under Chinese Rule:Memory,Identity,and Contested Control in a Tibetan Region of Northwest Yunnan)、埃洛伊塞·赖特的《重写大理:建构帝国的边疆地区,1253—1679》(Re-Writing Dali:the Construction of an Imperial Locality in the Borderlands,1253—1679)等,这些书呈现的是中心对边缘的扩张。相反,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从“无国家”概念出发,在《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一书中提出“佐米亚”理论。而中国年轻的历史学人杨斌的博士学位论文《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试图从“全球视野”来思考云南与中国的关系。这些研究引起了云南大学林超民、罗群与李淑敏等人的批评(具体见林超民的《云南与内地:和谐共融的整体》、罗群和李淑敏的《警惕“去中国化”陷阱——评西方学者的中国西南边疆史研究》等文章)。
可以说,林超民和罗群等人的反击继承了方国瑜等人的成就和思路。在20 世纪上半叶,方国瑜等中国学者就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及日本学者展开过学术争论。以伯希和等为首的西方学者主张,南诏是泰族建立的独立国家或泰族王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出于侵略目的,不仅在政治上极力支持“大泰国”形成,怂恿暹罗鼓吹“泛泰主义”,并将“暹罗”改名为“泰国”,而且在学术上也唆使日本学者论证“泰族起源于云南,南诏、大理为泰族”,以及“元世祖政府后泰族南迁说”。由此引起暹罗内部一些民族主义分子鼓吹“大泰族主义”,宣称中国的云南、贵州和广西的一些非汉民族,尤其云南的摆夷人等都是泰族。以上主张实为意欲“抢夺我们的国土”或分裂中国西南。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保卫祖国边疆、捍卫国家统一,方国瑜发表考证文章认为,诏是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白子(僰人)建立的臣属于唐王朝的地方政权(具体可参见潘先林的《家国情怀 书生本色:方国瑜先生的中国边疆学研究》、葛兆光的《当“暹罗”改名“泰国”——从一九三九年往事说到历史学与民族主义》等文)。类似的学术实践也见诸当今厦门大学历史学学者的研究中。面对“台独”势力及相关的学术观点, 厦门大学历史学家陈支平发表了《本末倒置的台湾“南岛语族”问题研究——驳“台湾南岛语族原乡论”》等文章。显然,陈支平继承了林惠祥有关石锛的研究思路和精神,因为林惠祥发现,台湾地区的新石器类型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是一样的,由此证明了两岸的同源性或文化共享性。
所以,如果我们到人类学系之外去寻找历史维度的人类学研究,即不墨守今日学科建制之藩篱,也许就会发现,南派或中国历史学派没有绝迹,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突破当今学科划分的限制来考察中国人类学的南派。那么,如何思考中国人类学南派在当代的延续及演变?本书无疑会给我们提供思路和启发。
马丹丹丐序于我,余小子眼界有限,加之才识不足,纡徐曲折地写了以上文字,只能勉强为序。请方家指正!
杜靖谨识于青岛崂山金家岭下
甲辰龙年农历冬月初六
(本文为杜靖为《轮廓:中国人类学南派的重建伊始》一书撰写的序言,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