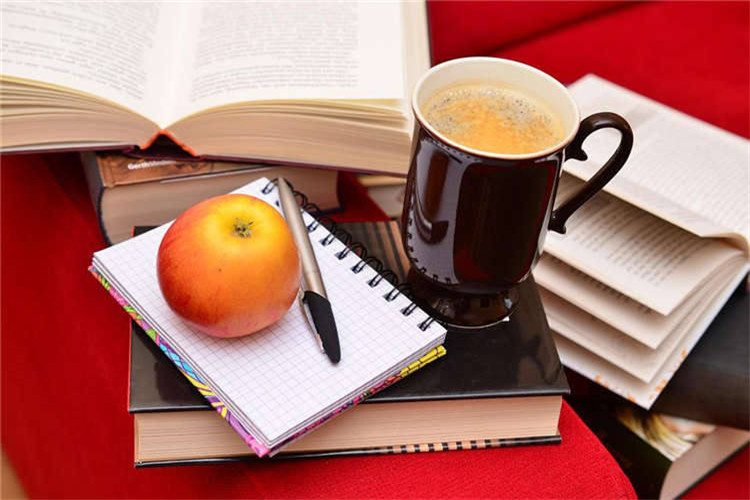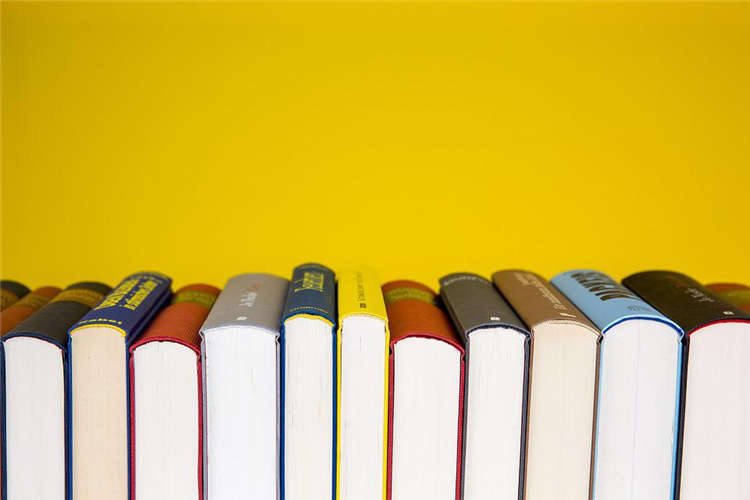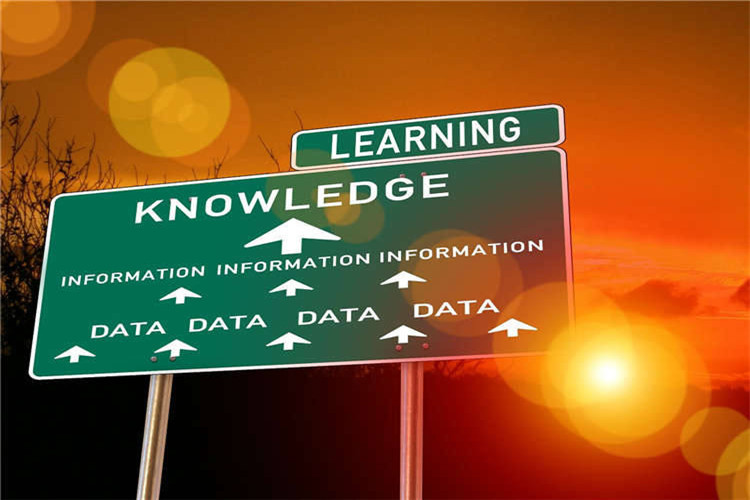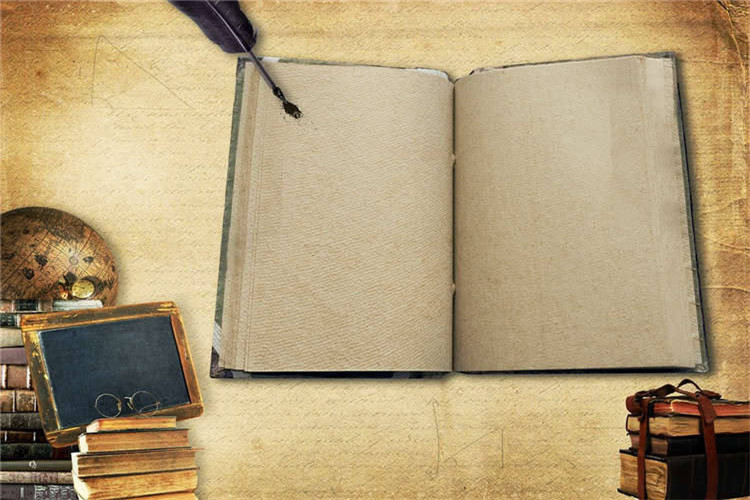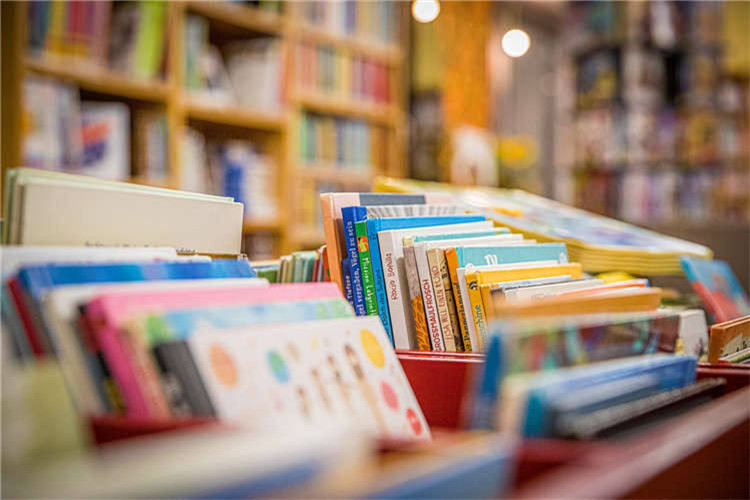又一年中秋。当此夜,人们举家团圆,分食月饼,共赏皓月,这般景象似乎千古未变。而当我们翻开明清时期的笔记,会发现中秋节在明清文人笔下有着千般风情。它不仅是“人月两团圆”的温馨祈愿,亦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家国之思,也是寄托生死别情的儿女情长。这些散落于明清笔记中的零篇碎墨,如同一面面古镜,不仅映照出彼时的风土人情,更折射出文人心中那片或清朗、或幽暗的月光。
天涯共此时:天南海北的中秋风物
中秋作为传统大节,其习俗在明清笔记中留下了丰富的记录,南北风光,各有异趣。
身居京师的晚明士人刘侗,在其《帝京景物略》中记下了京城中秋的景象。节日的仪式感,从祭月开始:
八月十五日祭月,其祭果饼必圆,分瓜必牙错瓣刻之,如莲华。纸肆市月光纸,缋满月像,趺坐莲华者,月光遍照菩萨也。华下月轮桂殿,有兔杵而人立,捣药臼中。纸小者三寸,大者丈,致工者金碧缤纷。家设月光位,于月所出方,向月供而拜,则焚月光纸,撤所供,散家之人必遍。
这种被称为“月光纸”的木刻版画,是彼时京城中秋最具特色的物品之一。祭拜之后,分食供品,月饼之大,“有径二尺者”。中秋作为“团圆节”也已是市井共识:“女归宁,是日必返其夫家,曰团圆节也”。
月光纸
目光转向南国,风俗则更添几分旖旎与活泼。清代学者李调元久官广东,其《南越笔记》便记录了岭南独特的节俗。中秋之夜,儿童们的乐事是燃灯为戏:
八月十五之夕,儿童燃番塔灯,持柚火,踏歌于道……塔,累碎瓦为之。象花塔者,其灯多。象光塔者,其灯少。柚火者,以红柚皮雕镂人物花草,中置一琉璃盏。朱光四射与素馨茉莉灯交映。
与柚灯的“以色胜”不同,素馨、茉莉灯则“以香胜”。色与香的交织,构成了岭南中秋夜独特的感官体验。
在某些地方,中秋还是女子生命中重要的节点。如香山一带,“中秋女始笄”,是夜,少女在亲族的见证下加笄,完成从女孩到成年女子的身份转变。长乐的妇女则有“拜月姑”的习俗,伴以歌谣。
除了风俗,笔记作者们还留意到自然万物与月亮的神秘感应。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便记下了珠蚌与月光的传奇关联:“中秋蚌始胎珠,中秋无月,则蚌无胎。”他相信,每当秋夕月明,海天闪烁如赤霞,便是“老蚌晒珠之候”,蚌“得月光多者其珠白”。这种近乎神话的记述,为中秋的月光增添了一层万物有灵的瑰丽色彩。
《广东新语》
而到了江南水乡的苏州,中秋则是一场全民参与的游赏盛会。苏州人好游,明人袁宏道有诗云:“苏人三件大奇事,六月荷花二十四。中秋无月虎丘山,重阳有雨治平寺。”可见虎丘山夜游与中秋节的紧密关联。顾禄在《清嘉录》中对此有更细致的描写:是夜妇女“盛妆出游,互相往还”,名为“走月亮”。而除了陆上游玩,水上则更为热闹。人们“或携瞽妓,或挈友朋,泛舟赏月,笙歌彻夜”。虎丘一带更是游人如织,“远而竞集,多至数万”。明清之际文人张岱在《虎丘中秋夜》中对此有非常形象的记述,然而,他笔下的繁华盛景,已是故国的往事梦影。
故国月明中:易代文人的家国之悲
京师庄重,岭南活泼,苏州喧腾,笔记所载,皆是升平气象。而在明清易代,月光之下,则更多了几分故国之思与存亡之感。对于明末清初的遗民文人而言,“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不仅是他们人生的写照,也成了他们笔下月光的底色。曾经的热闹与今日的寂寥,在清辉下形成巨大的反差,使节日的欢愉染上了浓重的悲凉。张岱便是其中的代表。
这位明遗老,在“国破家亡,无所归止”后,在追忆中寻找往昔的梦影,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文字。他在《陶庵梦忆·自序》中自陈:“五十年来,总成一梦。”他笔下的中秋,便是一场盛大、永不落幕的旧梦。在《虎丘中秋夜》中,他描绘了一幅全民狂欢的画卷,在他笔下,虎丘中秋是一场从极动到极静的听觉盛宴:
虎丘八月半,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傒僮走空之辈,无不鳞集。自生公台、千人石、鹤涧、剑池……皆铺毡席地坐,登高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天暝月上,鼓吹百十处,大吹大擂,十番铙钹,渔阳掺挝,动地翻天,雷轰鼎沸,呼叫不闻。更定,鼓铙渐歇,丝管繁兴,杂以歌唱……二鼓人静,悉屏管弦,洞箫一缕,哀涩清绵,与肉相引,尚存三四,迭更为之。三鼓,月孤气肃,人皆寂阒,不杂蚊虻。一夫登场,高坐石上,不箫不拍,声出如丝,裂石穿云,串度抑扬,一字一刻。听者寻入针芥,心血为枯,不敢击节,惟有点头。然此时雁比而坐者,犹存百十人焉。使非苏州,焉讨识者!
在《闰中秋》一文中,此等狂欢更被推向顶峰。崇祯七年(1634年),此时明朝统治已岌岌可危,山西、河南等地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但江南的中秋一如往昔,张岱在蕺山亭会友,“在席者七百余人,能歌者百余人,同声唱‘澄湖万顷’,声如潮涌,山为雷动”。酒酣之后,演剧至四鼓方散,此时“月光泼地如水,人在月中,濯濯如新出浴”。这些文字写于清顺治年间,当张岱在“瓶粟屡罄,不能举火”的窘迫中追忆这一切时,旧梦的繁华越是真切,现实的凄凉便越是刺骨。
与张岱齐名的“明末四公子”之一冒襄,其《影梅庵忆语》虽是悼亡爱妾董小宛之作,却同样处处透出故国之思。此书作于顺治八年(1651年),董小宛新丧未久,距甲申之变(1644年)不过七年。冒襄在回忆中明确提及“甲申三月十九日之变”与乙酉年间的流离,故国之痛是其情感的底色。他追忆崇祯十五年(1642年)与董小宛在秦淮水阁的中秋之夜,观赏新剧《燕子笺》,当演到男女主人公离合之景时,“姬泣下,顾、李亦泣下”。一场戏,牵动的岂止是儿女私情,更是所有经历离乱之人的共同悲歌。董小宛爱月,常对冒襄言及月之气静,可以“仙路禅关,于此静得”。对于这位曾“奔驰患难,终保玉颜无恙”的奇女子而言,对这静美的月光下片刻安宁的喜爱背后,又何尝没有山河破碎的影子。
冒襄画像
晚明文人的精神气质,即便不在中秋,也常在月下显现。张岱的名篇《西湖七月半》便是绝佳的例证。此文虽非写中秋,却将那种末世的狂欢与遗民的孤高刻画得淋漓尽致。他将看月之人分为五类,前四类皆是俗人:有“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者”的官府豪绅;有“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者”的名娃闺秀;有“欲人看其看月者”的名妓闲僧;更有“装假醉,唱无腔曲,而实无一看者”的市井无赖。张岱将自己与同好归为第五类,于孤寂中自认清高:
其一,小船轻愰,净几暖炉,茶铛旋煮,素瓷静递,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树下,或逃嚣里湖,看月而人不见其看月之态,亦不作意看月者,看之。
这份不与俗同流的姿态,在众声喧哗散尽后,才真正显现。当官府席散,游人赶门,繁华落尽,月夜便成了他们的王国。“吾辈始舣舟近岸……此时,月如镜新磨,山复整妆,湖复颒面。”在他们眼中,真正的月亮,不属于那些追逐热闹的“好名”之徒,而属于能在万籁俱寂中品味其“苍凉”之美的“吾辈”。繁华已然落尽,他们是月下最后的看客,守着一个时代的余光。
两面《红楼梦》:同人文里的中秋月
在诸多描写中秋的笔记中,一部名为《林黛玉笔记》的稿本显得尤为特殊。此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史料或见闻录,而是清末民初文人喻血轮(别号“伤心人”)的寄情之作。作者在弁言中自述“余既伤心人也,则作伤心语”,于是“爰取《红楼梦》一书,就书中林黛玉一生之言行,代为立言”,化身黛玉,以第一人称的口吻,重新记叙了她自入贾府至魂归离恨天的所见所感。这种独特的体例,使其与曹雪芹的原著形成了有趣的对照。
民国版《林黛玉笔记》
《红楼梦》第七十六回“凸碧堂品笛感凄清,凹晶馆联诗悲寂寞”是书中一处重要转折。此时的贾府已显颓势,元宵省亲时的盛景不再,中秋家宴上人员寥落,贾母亦不禁感叹“可知天下事总难求全”。此情此景,在曹雪芹笔下是通过环境、氛围以及人物间的对话来烘托的,是一种客观呈现的凄凉。
到了《林黛玉笔记》,这一经典场景几乎被完整地复现,但视角的转换,将外部的萧条景象直接转化为黛玉内心的波澜。当贾母感叹世事无全时,原著中仅以“黛玉、湘云二人不免对景感怀”一笔带过,而笔记的作者则为黛玉补上了一大段心理独白:
余闻语,不禁牵起愁绪,出倚长栏,仰望一轮明月,方挂天空,丹桂数十株,扶疏山左,袅枝敲玉,飘粟绽金,微风吹之,清芬拂面。回忆去年今日,吾侪集宴缀锦阁时,赌酒赋诗,其乐何如。乃忽又一年矣,流光易度,时不我留,吾人由少而长,以逮衰老,曾不瞬耳。思及此,不觉凄然泪下。
这一差异在随后的凹晶馆联诗中表现得更为淋漓。在原著里,黛玉与湘云的联诗是一场才情的自然流露,意境的层层递进。“寒塘度鹤影,冷月葬诗魂”的诞生,更像是一种诗兴与谶语的交织,重点在于诗句本身的凄绝和不祥之兆。《林黛玉笔记》则将这场联诗处理成了一次黛玉内心激烈挣扎与情感宣泄的过程。当湘云吟出“寒塘度鹤影”的佳句时,笔记中的黛玉先是为对方的才华所折服,不禁“顿足呼曰”佳句天成,“余当偃旗息鼓矣”。然而,她并未就此罢休,而是“戚戚不安,遐想半日”,最终在一种不甘与被激发的状态下,吟出了自己的对句:“冷月葬诗魂”。
作为《红楼梦》庞大同人创作的先声,《林黛玉笔记》体例固然有趣,但把林黛玉心声一一模拟,相较于原著含蓄隽永的笔触,读起来显然有些刻意。不过,若是同样痴迷《红楼梦》的读者读到,或许也不难理解这份痴意。
今年异去年:月下的悲欢离合
张岱与冒襄的中秋记忆关乎家国,沈复在《浮生六记》中所描绘的月光,则纯然是个人情感的结晶,温馨动人,却又因其追忆的性质而带着无可挽回的伤感。
沈复并非显宦世家,亦非名士巨擘,他的一生,在幕僚生涯与琐碎营生中度过。他留下的自传体散文《浮生六记》,被誉为“小红楼梦”,以其真率自然的笔触,记录了与妻子陈芸相守二十三年的悲欢离合。此书的魅力在于将平凡的夫妻生活写得情趣盎然,意蕴悠长。在颠沛流离之中,他们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与文人的雅趣,这种于苦难中提炼出的温情,尤为动人。书中所记的月夜,便是这种情感的集中体现。
《浮生六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9月版
《浮生六记》开篇《闺房记乐》,便记下了新婚不久与陈芸在沧浪亭的中秋之游。那时的沈复大病初愈,陈芸新嫁半年,一切都带着初愈的清新与新婚的羞涩:
中秋日,余病初愈,以芸半年新妇,未尝一至间壁之沧浪亭,先令老仆约守者勿放闲人,于将晚时,偕芸及余幼妹,一妪一婢扶焉,老仆前道,过石桥,进门,折东,曲径而入。叠石成山,林木葱翠。亭在土山之巅,循级至亭心,周遭极目可数里,炊烟四起,晚霞烂然。……少焉,一轮明月已上林梢,渐觉风生袖底,月到波心,俗虑尘怀,爽然顿释。芸曰:“今日之游乐矣。若驾一叶扁舟,往来亭下,不更快哉!”时已上灯,忆及七月十五夜之惊,相扶下亭而归。吴俗,妇女是晚不拘大家小户皆出,结队而游,名曰“走月亮”。沧浪亭幽雅清旷,反无一人至者。
没有盛大的宴席与喧闹的鼓吹,只有夫妻二人与家人席地而坐,在几乎无人的沧浪亭,独享一份清旷的月光。陈芸“若驾一叶扁舟”的提议更显出夫妻间的灵犀相通。沈复写下这段文字时,陈芸早已亡故。这看似平淡温馨的记述背后,是“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无限哀思。他在追忆中秋之乐时,笔锋一转,忆及七月十五鬼节之夜的经历,那一夜的月亮,似乎成了他们爱情的谶语:
七月望,俗谓之鬼节。芸备小酌,拟邀月畅饮,夜忽阴云如晦。芸愀然曰:“妾能与君白头偕老,月轮当出。”余亦索然。但见隔岸萤光明灭万点,梳织于柳堤蓼渚间。余与芸联句以遣闷怀,而两韵之后,愈联愈纵,想入非夷,随口乱道。芸已漱涎涕泪,笑倒余怀,不能成声矣。觉其鬓边茉莉,浓香扑鼻,因拍其背,以他词解之曰:“想古人以茉莉形色如珠,故供助妆压鬓,不知此花必沾油头粉面之气,其香更可爱,所供佛手当退三舍矣。”芸乃止笑曰:“佛手乃香中君子,只在有意无意间;茉莉是香中小人,故须借人之势,其香也如胁肩谄笑。”余曰:“卿何远君子而近小人?”芸曰:“我笑君子爱小人耳。”正话间,漏已三滴,渐见风扫云开,一轮涌出。乃大喜,倚窗对酌。酒未三杯,忽闻桥下哄然一声,如有人堕,就窗细瞩,波明如镜,不见一物,惟闻河滩有只鸭急奔声。余知沧浪亭畔素有溺鬼,恐芸胆怯,未敢即言。芸曰:“噫!此声也,胡为乎来哉?”不禁毛骨皆悚,急闭窗,携酒归房。一灯如豆,罗帐低垂,弓影杯蛇,惊神未定。剔灯入帐,芸已寒热大作,余亦继之,困顿两旬。真所谓乐极灾生,亦是白头不终之兆。
“妾能与君白头偕老,月轮当出”,这是陈芸天真而深情的祈愿,随即月亮冲出云层,但惊吓与疾病也接踵而至,沈复追忆至此,不禁发出了“亦是白头不终之兆”的叹息。月圆与否,竟真的成了他们爱情与命运的预言。
这种将个人生死爱恋寄托于月夜的笔法,在明清笔记中并不鲜见。陈裴之的《香畹楼忆语》是悼念亡姬紫湘之作,其中有挽诗写道:“金灯照夜月初圆,往事分明在眼前。……相看大妇怜中妇,岂料今年异去年。”蒋坦的《秋灯琐忆》亦是追怀亡妻秋芙的作品,他记下与秋芙泛舟湖上,在苏堤月下鼓琴听曲的往事,清雅绝伦,却也只剩追忆:“其时星斗渐稀,湖气横白,听城头更鼓,已沉沉第四通矣,遂携琴刺船而去。”
这些笔记中的中秋,多不是在描绘节日本身,而是在借节日抒发个人的离愁情怀。当沈复在琉球度过中秋,虽有“月光澄水,天色拖蓝”的异域风光,心中所念,仍是“回忆昔日萧爽楼中,良宵美景,轻轻放过,今则天各一方,能无对月而兴怀乎?”
月华流转,佳节又至。今天的人们再度举头望月,或许也还能从那清辉之中,读出古人的心事与叹息,以及月亮背后古今共通的人间情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