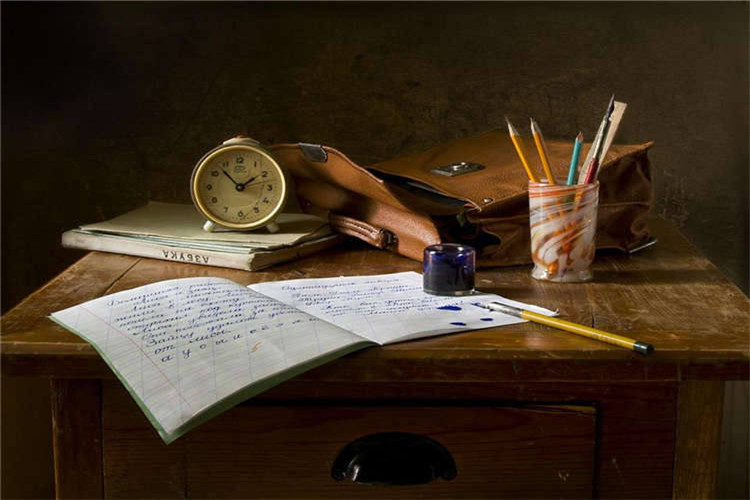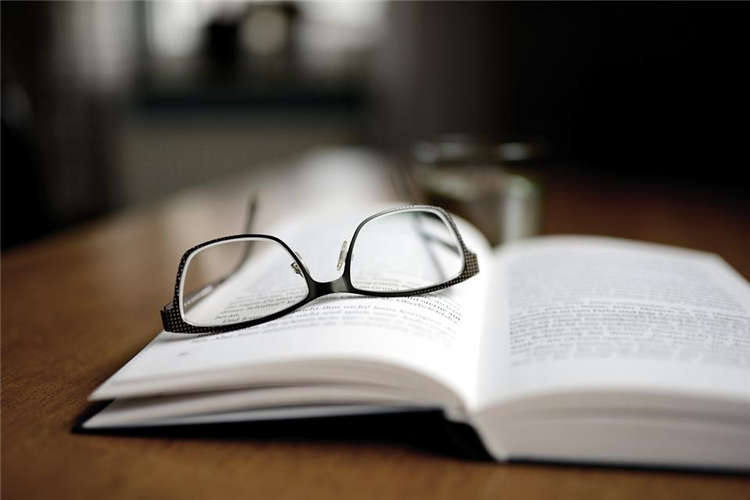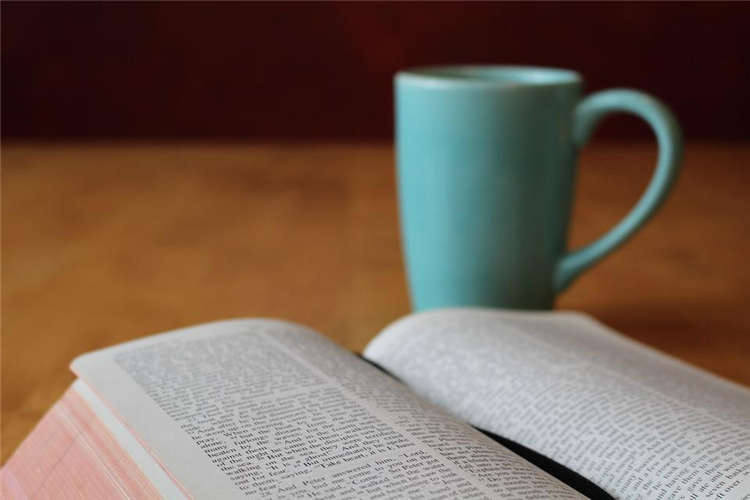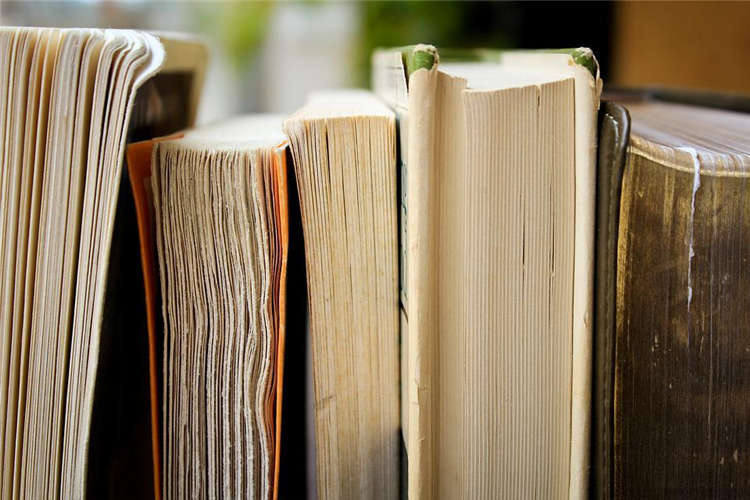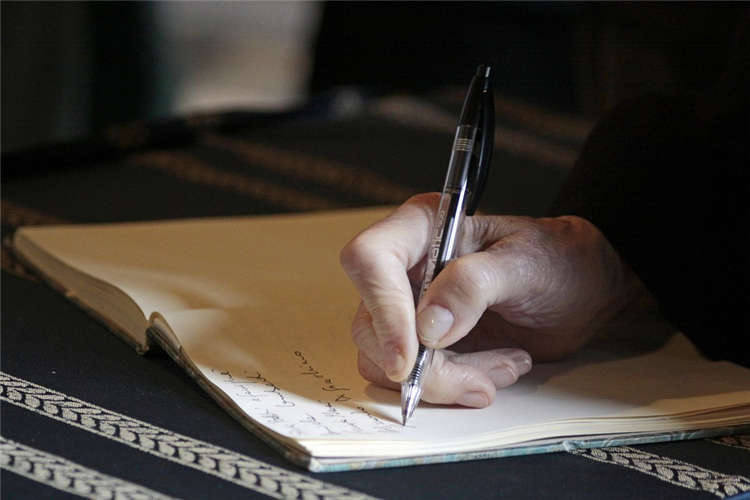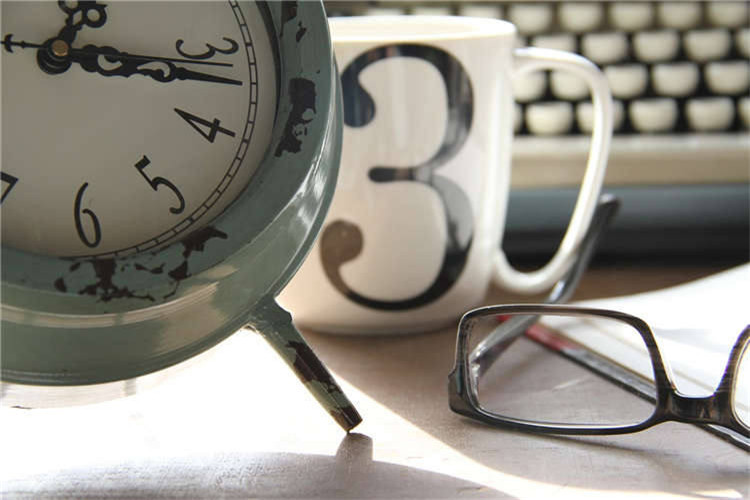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科尔姆·托宾的嗓门很大。
宾馆房间里,他朝我们走来。他的手掌大而有力,紧紧握住几秒,深绿的眼睛看着我们。他穿鲜蓝色衬衫,两颊之间的肉坠下来不少,但脸庞仍然是紧实的。还有他的声音,果决、饱满,语速很快,不像70岁的声音。
电梯间里,责编说,从落地上海开始,托宾就没有停过,先是签书、拍视频,再是记者采访,一个接着一个。他随和、热情,乐于接受各种各样的邀约。打开B站,你能看到他抱着娃娃说,“各位好,我是科尔姆·托宾,我今天正式入驻B站了。”
“这是你第几次来中国?”架相机时,我们闲聊。
“第五次,” 他看着我们,哈哈大笑。
上一次是十年前,2015年。他问,那时候你们多大?那时候,他继续回忆,中国的建筑更少,严肃读者也更少——所谓严肃读者,在他看来是愿意阅读一些“奇怪地方”小说的人,比如冰岛、挪威,还有他,这个来自爱尔兰的作家。
去年,托宾告诉他的图书策划人彭伦,2025年的一整年,他不用去哥伦比亚大学“上班”,能够找时间来中国看看。彭伦与托宾合作多年,在来中国之前,彭伦翻看云盘上的旧文件,发现自己出版的第一本托宾,是2006年夏天签约的《大师》。从那一次合作以后,他的出版便紧跟着托宾的写作,一晃已经过去十九年。2016年,彭伦写邮件告诉托宾,自己打算从公司辞职,“我将创办自己的出版品牌。”托宾回他:“I will follow you.”
十年后,他们再次见了面。9月19日的晚上,托宾拖着行李,从浦东机场走出来,彭伦在到达处向他挥手,远远给他拍了几张照片。他告诉托宾接下来的活动行程,过几天,会安排他和一位脱口秀演员(鸟鸟)对谈,托宾听后高兴地搓手,那我可以尽情说笑话了。
托宾经常说笑话,采访时,思维总是从一个地方跳到另一个地方。彭伦则在一边给他递苏打水,他一听接一听打开,喝光,壮实的脖子上架着一副细眼镜,和大块头体格形式了鲜明对比。不说话的时候,他似乎也在微笑,沉静的绿眼睛看向你,像好脾气的森林巨人。
一旦见过他的真人,就很难再把他和他的文字联系在一起。小说里,托宾总是写独处的、漂泊的人,但他看起来却如此快乐,如此年轻。比如他提起自己爱看电影,看了很多遍小说改编的《布鲁克林》,“许多人会把爱尔兰人描述成醉鬼,沉思的、忧郁的,但这部电影不是这么演绎爱尔兰人的。”比如他曾写过《论詹姆斯·鲍德温》,于是我们想让他谈谈为何鲍德温在近几年开始更受欢迎了?是否有一些时代症候暗含其中?他想了想,说,可能是因为Youtube。“鲍德温那么迷人、聪明,能脱口而出一句句金子般的断言,Youtube上都是他的视频。”
当提问来到文学,托宾开始变得认真。他总能在听完提问的下一秒立刻作答,甚至都不等问完。他举出一连串的名字,将讲述引回更漫长的文学史,有时你以为他讲偏题了,或是在故意反预设地回答,但他又总能绕回到最初的问题。就像他的书一样,不论是写小说还是评论,托宾的文字总是展现出一种知识的密度,以及叙述背后一闪而过的思维火花。
过去十年间,托宾得过癌症,又康复。他说自己在那六个月里什么都没做,只是为意大利作家娜塔莉娅 ·金兹伯格的一本书写了序言。今年年初,托宾亲历了洛杉矶山火,他和《伦敦书评》的朋友说到自己的遭遇,编辑问,你今晚能写好吗?于是他开始在火灾的阴云下赶稿。在文章里,他想象自己变成一个非常老的女人,站在水池中央躲避四处的火焰和烟雾。采访中,他回忆起那段时间,仍觉得不可思议,灾难与私人生活之间的距离如此微妙,“它(大火)离我们的房子这么近,可一旦它没有蔓延过来,我们就在房子里继续生活。”
群岛图书·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3-4
相比更显性的“政治“,“爱”是他谈得更多的事情,比如他会说鲍德温的特别之处,是他总是谈及“爱”。
“他认为唯一重要的改变是每个人在私人领域内的改变。当时的公共领域人们总是说,我们要立法,要改革,没有人像他这样呼吁,我们需要做的是彼此相爱。”
如何书写“爱”则成为采访里他思考最久的问题。“我认为在有些时候,爱情的一个元素是交易性(transactional)。在小说中,你有时候会看到这样的交易,它比单纯源自激情的、气喘吁吁的爱情故事要有趣得多。”《长岛》中,南茜想要嫁给吉姆,因为”你在酒吧楼上的房间对我来说很好。”在《魔术师》里,托马斯·曼与她的妻子结婚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场交易。
“这和流行歌里唱的不一样”,聊到这里,他唱了几句披头士的She Loves You,又笑起来。最后他回忆,在所有这些故事里,只有一次写到了非交易性的爱,那是在《布鲁克林》里托尼真正坠入爱河, solid,他如此形容这样的爱。
01 我不想再写关于小镇的故事了
界面文化:和十年前相比,这次访问中国有什么新的感受?
科尔姆·托宾:你能明显感受到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更多的高楼大厦,更高的城市化程度。另外我也发现,中国正在涌现一群非常认真的读者,他们受到良好教育,对世界充满好奇,会从一本小说里获得极大的满足感。他们不会去区分小说家的国别,一本爱尔兰小说可以令上海的某个读者产生共鸣,这与一本意大利小说或冰岛小说是一样的。小说如今不太受到国界的限制,有时候,哪怕来自最遥远地方的小说也能触动你的情感,让你觉得,天啊,这就是我能理解,或者是想要读更多的内容。
比如你想读萨莉·鲁尼的书,不是因为她与你有一样的身份,而是因为她书中的故事,里面描绘的世界在吸引着你。那些女孩在都柏林的经历,她们上学,去派对,回家,思考自己的生活、与他人的关系,这与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正在发生的事情都没有那么遥远。
界面文化:在这种全球性的语境下,文学传统还重要吗?
科尔姆·托宾:当然。写一部小说并声称它是全球性的,这毫无意义,因为没有什么是真正全球性的。人们总在谈论全球化,但这在小说里不存在。我的小说总是发生在特定地点,如果我开始在这方面妥协,想要写一本关于世界任何地方的小说,它可能最后什么也不是。对于读者来说,特定地点变得重要,因为在其中你能够想象某些“不是你”的事物,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根本性的理念。
界面文化:但你同时也拒绝被定义为某个国籍的作家。
科尔姆·托宾:对,这来自我的阅读经验。当我在阅读托马斯·曼和亨利·詹姆斯时,我仿佛感觉他们就属于我,即使他们一个是德国人,一个是美国人。我对国籍之外的他们感兴趣。所以我也不会说,我是一个爱尔兰作家,我必须专注于描述爱尔兰的天气,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不想再写关于我的小镇的故事了,我发现有其它想要描写的东西,这一切都是开放的。
02 今天的移民故事可能会发生在社交媒体
界面文化:为什么会在十五年后续写《布鲁克林》的故事?
科尔姆·托宾:《布鲁克林》改编为电影后,我要参加不同场次的映后座谈,按理说电影放映的时候我可以去外面待着,但我没有,我留下来看了好多次,真的看了好多遍。慢慢地,我开始感受这部电影,与它发生情感共鸣。我原本以为这本书早就写完,已经是过去式,与我没什么关系了,但这部电影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我。
我开始意识到,如果二十年后,在美国,某件糟糕的事情发生,它可能会毁掉她(艾丽丝)的一切。因为她的生活建立在极少的事物上,她没有亲近的朋友,只有一份小差事,她与一切的关系都很脆弱。我意识到你可以将一件小事变得多么戏剧化,特别是她的丈夫,如果她的婚姻出了状况,她将一无所有。这个想法出现,我开始写它,就是这样,这不是什么重大决策。我不知道我将去往哪里,只是一次试探。
界面文化:在你看来,移民故事到今天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科尔姆·托宾:在爱尔兰,19世纪中期以来,每个家庭、每个世代都会有人离开,去往美国或是澳大利亚,这是非常典型的爱尔兰故事。但它也成为了许多其它国家的故事,比如中国,也有很多中国人选择搬到大城市生活,这是很相似的。很多去到美国的爱尔兰人都来自小农场,过去他们整日挖土,但到了美国,他们不再从事农业,有人成为警察,或是消防员。中国人也是如此,他们待在城市里,喜欢那些街道,而不会走进广阔的美国景观中。他们不想再在田里挖掘、劳作,凄风冷雨,他们想要城市生活。这是不是很有趣?
今天的情况又会有所不同。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有不少中国学生,他们非常聪明,可能在来之前就已经获得学位,或是有工作经历,他们在美国待几年后可能会回到中国。这是一种更多孔的关系,你不再是去到美国,住在唐人街,待上一辈子,他们能够与父母保持联系,来回往返,去不同的地方学习。所以如果今天再去写移民故事,我可能会写社交媒体上的各种消息,这些屏幕截图。
界面文化:你似乎很喜欢电影版的《布鲁克林》。
科尔姆·托宾:我时常会想起电影里的吉姆这个角色,饰演他的是爱尔兰演员多姆纳尔·格里森。在过去,很多爱尔兰电影、戏剧、小说都倾向于将爱尔兰男性描摹为不稳定的、喝醉的,但同时又是迷人的、沉思的、忧郁的。但他(格里森)并没有表现得像那样,他没有发疯,也没有喝醉酒大喊大叫,他将吉姆演绎成一个更平常的人物,他可以在自身周围创造一种光晕,即使他很平常。我对在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很感兴趣。
界面文化:你怎么看改编自萨莉·鲁尼小说的剧集《正常人》?康奈尔也不是一个充满攻击性的角色。
科尔姆·托宾:噢,它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因为它播出于疫情期间,当时我在洛杉矶,和我的伴侣一起,他不是爱尔兰人,我跟他说,这个爱尔兰故事要在电视播出了。每个人都看了,这非常特别。你说的很对,保罗·麦斯卡饰演的康奈尔确实有一种有趣的魅力,但我不想要魅力,也不想要微笑,格里森在《布鲁克林》里做的就是这样。
03 任何小说都需要有一个孤独的角色
界面文化:你曾经做过政治记者。这段经历对你的小说写作有何影响?
科尔姆·托宾:我从来没有真正写过新闻消息,我总是写更长的文章。这段经历让我意识到,你是为读者而写作的。那是一段很美好的时光,但我不想继续做下去了。问题在于,在爱尔兰这样的国家,政治阶层是如此之小,如果你要写关于某个政客的文章,并且写得具有敌意或批判色彩,支持她的人就不想再跟你说话了,你不再是他们的朋友。但如果我不这么做,转而成为支持者,我的读者又会觉得我在为政客写作,不再独立。所以这是非常困难的,你最好在年轻的时候做几年,然后停下来。
界面文化:不过政治在你的小说里仍然很重要,像是《魔术师》。
科尔姆·托宾:在《魔术师》里,公共生活变得非常重要。他(托马斯·曼)最早是怎么听到希特勒这个词的?这需要显得平常,不能太政治化,它是关于私人生活和个体的,比如来自他的儿子从报纸上剪下的插条。但也有其它时刻,比如当他发表演讲时,人们开始冲他大喊大叫,向他扔东西,这个男人的生活正深深地被政治所影响——你需要通过展示他的生活而非政治来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不会在书里的某个时刻让希特勒出现,而是托马斯·曼从不同途径得知他。
界面文化:很多人觉得你的人物都在孤独中挣扎。你怎么看这种孤独感?
科尔姆·托宾:我认为任何小说都需要有一个孤独的角色。简·奥斯汀在200年前会这样写,你去跳舞,接下来的一天,你会感到孤独,并持续思考这场舞会。你会有一种感觉,孤独越深,你能赋予角色的强度就越多,让他们拥有很丰富的生活体验,这是他们去迪斯科舞厅或跟朋友吃饭所无法获得的。但不要一直这样,在那之后你还需要做点什么。而在电影里,人们总是倾向于让事物快速进展,我认为这是小说比电影或戏剧能做得更好的地方。
群岛图书·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5-1
04 爱情的一个元素是交易性
界面文化:你写过不少关于詹姆斯·鲍德温的文章,《纽约客》上个月发表了一篇关于鲍德温的评论,里面写到,鲍德温写作中的核心讯息是对爱的恐惧——“在参与民权运动的同时,他也在私人生活中追寻着稳固、真挚的爱情关系。”你怎么看这个观点?它似乎与当代生活息息相关。
科尔姆·托宾:鲍德温的人生是从传教士开始的,那是他十一二岁的时候,他的观念总是关于拯救你的灵魂,他认为唯一重要的改变是每个人在私人领域内的改变。所以,鲍德温会使用“爱”这个词汇,当时的公共领域中人们总是说,我们要立法,要改革,没有人像他这样呼吁,我们需要做的是彼此相爱。在此基础上,他广泛地写作,用小说、随笔、诗歌、戏剧这些不同的形式,并在美国、巴黎和法国南部之间奔走,这是一种非常有吸引力的生活。
界面文化:近几年,不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鲍德温似乎变得越来越受欢迎。
科尔姆·托宾:如果你在YouTube上搜索詹姆斯·鲍德温,会看到大量有关鲍德温的演讲视频,这些片段是如此有趣、睿智而尖锐。鲍德温在美国最为人熟知的形象就是电视中的,如果你要辩论某个话题,请来鲍德温,他总能说出比其它媒体更聪明的东西。很多年轻人在YouTube上发现了这些内容,这太惊人了,于是人们开始搜寻他的书,他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像马丁·路德·金那样的时髦人物,但不同的是,人们并不是引用鲍德温的话,而是喜爱他,希望能够见到他。他也与当下流行的文化特质有关,既是酷儿的,也是少数族裔的,他拥有所有这些身份,却并没有声称自己是受害者,而是将它视为自己写作、发声的特殊视角。
界面文化:你在讨论鲍德温的作品时,会谈论身体、欲望和政治,这些主题也出现在你自己的小说当中,你是怎么书写爱的?
科尔姆·托宾:我认为在有些时候,爱情的一个元素是交易性(transactional)。比如《长岛》里,南茜想要嫁给吉姆,但这里面有交易的成分,而不是激情之爱,你在酒吧楼上的房间对我来说很好。同样在《魔术师》里,托马斯·曼与她的妻子结婚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场交易,这不仅仅是因为她很富有,也因为这能为他解决许多问题。我认为唯一一段非交易性的爱情是《布鲁克林》中,很明显托尼坠入了爱河,那将会是可靠的。在小说中,你有时候会看到这样的交易,它比单纯源自激情的、气喘吁吁的爱情故事要更有趣,因为很多时候你分不清这些感觉,哪部分是激情,哪部分是交易。
界面文化:你怎么看待爱情与政治的关系?当下的读者似乎对此越来越有兴趣,萨莉·鲁尼的小说就探讨了大量这样的问题,很受欢迎。
科尔姆·托宾:如果你是同性恋,你出生在哪一年、哪个国家,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是一名女性,那又取决于你能接受什么程度的教育。在过去的某些时代,男性掌握了如此多的权力,以至于他们笨拙地行使它。但在今天,比如我教书的大学,如果一个男人表现得令人厌烦,只知道谈论自己,或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没有人会愿意靠近他。所以男性也开始学习倾听。相对应的,在萨莉·鲁尼的故事里,女性开始拥有如此多的内在能量,她们受过非常好的教育,与此同时她们又会有些神经质,关于她们的外表,或是她们所处的关系,但她们本身又非常强大,在各种方面。
界面文化:你接下来的写作计划是什么?
科尔姆·托宾:我写了两部歌剧。其中一部是一个基础的爱情故事,尤其是我们前面谈到交易性,歌剧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来创造浪漫而充满激情的爱,四个人感到孤独而悲伤,遇到另外四个同样孤独而悲伤的人,他们在歌剧中走到一起,歌唱爱情,这是如此甜蜜,所有复杂性都不见了,只有爱。我已经写完了,它很蠢,这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