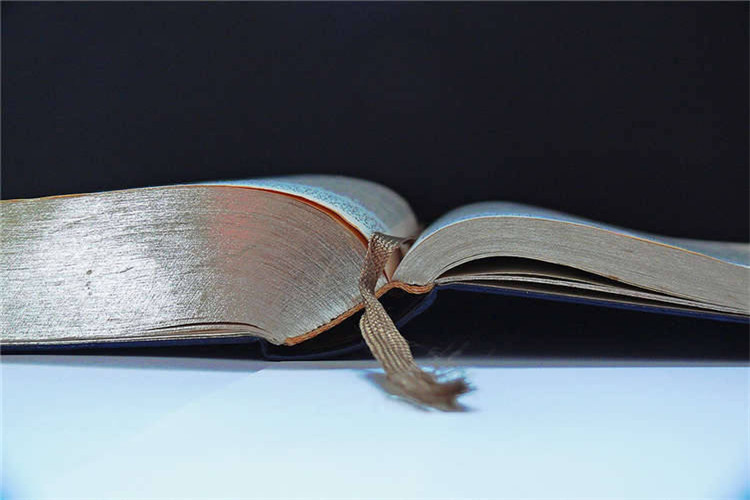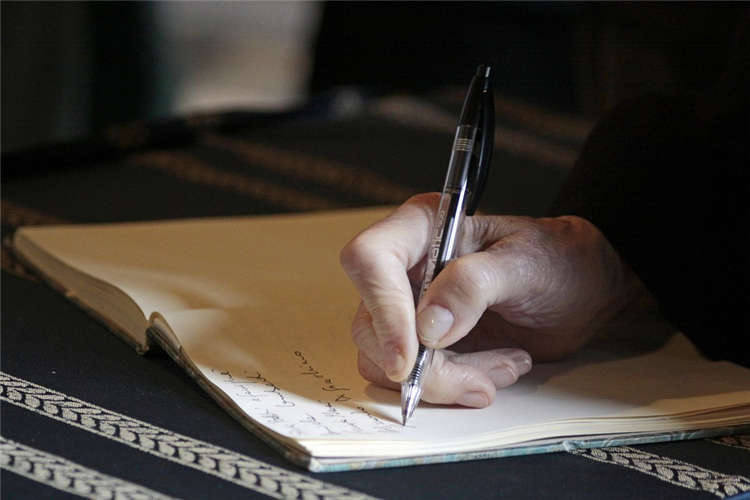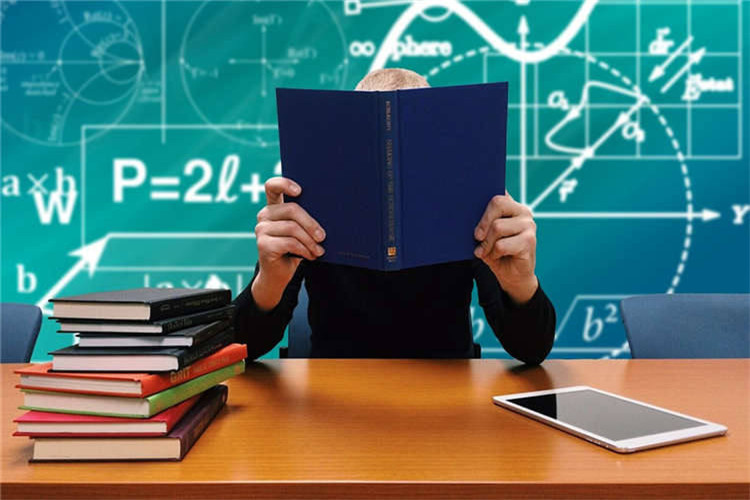《江山胜迹:人文风景的建构与传承》,商伟主编,韩笑副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即将出版,322页,148.00元
《江山胜迹》汇集了五篇文章,分别从一台(金陵凤凰台)二山(泰山、天台山)二城(北魏的都城洛阳和东晋、南朝的都城建康/金陵)入手,深入探讨“人文风景的建构与传承”这一主题。什么是胜迹?何为人文风景?它又是怎样建构与传承的?这些都是贯穿全书的基本问题,因此有必要略做梳理。同时也借此对全书的主旨做一次初步介绍,交代问题的由来和论述的取径,以供读者阅读时参考,也希望能对读者有所启发。
一
这本书的书名取自唐代诗人孟浩然的名篇《与诸子登岘山》:“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胜迹”一词源远流长,蕴含丰富。从字面上看,“江山留胜迹”一句将胜迹定义为自然风景。然而这首诗的尾联“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却将江山胜迹聚焦在了羊祜碑或堕泪碑上。
据宋代欧阳修的《岘山亭记》,岘山原无出众之处:“岘山临汉上,望之隐然,盖诸山之小者……”可是,山不在高,有“人”则名:“而其名特著于荆州者,岂非以其人哉?其人谓谁?羊祜叔子、杜预元凯是已。”欧阳修进而解释道:“而二子相继于此,遂以平吴而成晋业,其功烈已盖于当世矣。至于风流余韵,蔼然被于江汉之间者,至今人犹思之,而于思叔子也尤深。盖元凯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为虽不同,然皆足以垂于不朽。”欧阳修借用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范式来解释岘山为何因羊祜和杜预二人而名著于荆州。羊祜身后无子嗣,唯以德行和文章名世。《晋书·羊祜传》曰:“襄阳百姓于岘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庙,岁时飨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预因名为堕泪碑。”杜预命名的堕泪碑既是为了纪念羊祜,也是对纪念行为的一个见证与物质标志。它因此成为后人心目中的历史遗迹,而岘山也随之变成了纪念先贤的一个场所。
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部分,飨祭的仪式隐含了羊祜的另一个面相。《晋书·羊祜传》:
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尝慨然叹息,顾谓从事中郎邹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犹应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闻令望,必与此山俱传。至若湛辈,乃当如公言耳。”
羊祜不仅因其德行文章而名世,更以其登山临水的游览者的形象而被后人所追念和怀想。这位游览者热爱岘山,死不瞑目:“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犹应登此也。”历史上登览岘山的“贤达胜士”何止成百上千,但都早已被人遗忘,羊祜何以独传其名?立德说显然不足以回答这个问题,也无法遮蔽这段文字所蕴含的另外一个想法和预设:一个人可以像羊祜那样,由于对岘山的刻骨铭心的热爱而名与此山俱传。正可谓: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爱山者留其名。至于杜预呢,他是因为纪念羊祜而为后人所纪念。
岘山今貌
孟浩然的《与诸子登岘山》为我们揭示了江山胜迹从江山到人对江山的介入和参与的多重涵义。借助羊祜的先例来感受岘山的风光,意味着我们与岘山的关系是以羊祜为中介而达成的。而羊祜的中介作用,首先体现在为我们与岘山的关系带入了一个时间与历史的维度。这也正是为什么《与诸子登岘山》的开篇,便设置了人事代谢和古往今来的时间框架:“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而这岂不正是当年羊祜登临岘山的感叹吗?孟浩然在他第一人称的陈述中融入了羊祜的声音。更重要的是,其中“我辈复登临”一句也在事实上实现了羊祜的生前愿望。虽然主语已变成了“我辈”,但“登临”的行为却是重复性的,故此以“复”来修饰。这个“复”字显然并不意味着我辈曾经来过,而是应验了羊祜离去后,魂魄“犹应登此也”!的确,“我辈复登临”有如羊祜的魂魄附体,再次回到了岘山。此时此地,我即羊祜,羊祜即我。由于“人事有代谢”,“我辈”不仅指此时此刻登临岘山的我们,而且是向每一代的登临者开放。他们像我们一样,为了纪念羊祜而来,同时也兑现了羊祜的允诺,将每一次登临变成“复登临”。也正是因为如此,登览者与登览之地的关系被一劳永逸地内在化了。岘山出自我们灵魂深处的共同记忆:它不再是外在于我们感知经验的客体或对象,不再是那座“望之隐然”的“诸山之小者”,而早已成为我们所熟悉所热爱并且可以被明确指认的一处“江山胜迹”。
如何定义胜迹取决于我们与它的关系。自宋代以后,这些被确认为胜迹的地点已经变成了地方知识和历史记忆的内在组成部分。它们被纳入方志,并且加以分类,分别置于“古迹”“山水(山川)”“形胜”“寺观(庙宇)”“祠墓(冢墓)”“园亭”“疆域”“城郭”等名目之下。然而对于胜迹研究来说,指认胜迹固然重要,更为重要的是描述和解释胜迹是如何成为可能的,一处具体的地点又是怎样变成胜迹的;也就是说,描述和解释胜迹是如何被构造出来,并且得到了普遍的确认,从而形成绵延不绝的传统。如上所见,孟浩然的《与诸子登岘山》不只是题写胜迹,而且对此做出了富于洞见的评论。
二
从书的正题引出了副标题,即“人文风景”的概念。人文风景首先是与人的活动分不开的。人的活动在物质空间中留下了印记和标志,又称“迹”。而迹既包括自然之迹,也包括人的足迹、手记、笔迹和墨迹,以及地标性和纪念性的建筑及其遗址,如堕泪碑和欧阳修笔下的岘山亭。早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关于“文”以及“天文”和“人文”就已经形成了体系化的论述。人文包含书写,但又不限于书写,而是涉及任何人类文化活动所创造的标记与图式。正像希腊文中的topos既指一处地点或场所(locus),又指话题(topic),我们也可以通过“文”与“迹”的交错互动来定义和理解胜迹书写。
在中国这个以书写为中心的文化传统中,所谓胜迹是难以脱离书写而独立存在的。书写之“文”不仅题写胜迹,塑造了我们对胜迹的感知,而且反过来通过题诗板和石碑等媒介载体进入胜迹遗址或遗址所在的空间,从而转化为它所题写的胜迹的一部分。这提醒我们在一个动态的时间过程中来考察胜迹、胜迹书写,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从而超越主体与对象、主观与客观、内在与外在、文字书写与物质世界等一系列一成不变的二元对立关系。此外,“迹”字本身就包含地点或场所的用法,为我们与欧美学界关于地点/场所(place)和空间(space)的论述展开建设性的对话,提供了本土的话语资源与理论依据。
“人文风景”可以译作“cultural landscape”(文化风景),泛指一切经由人的活动所塑造的风景。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文化风景”产生于二十世纪初期,但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纪欧洲的风景画。毋庸置疑,这一概念有其历史特定性,而这并不妨碍我们将这本书所涉及的名山和都市放在广义文化风景的范畴内来讨论。名山和都市由更小单元的胜迹所组成,例如寺庙、宫殿、墓碑和亭台楼阁,但又不等于它们的叠加与总合,而是囊括了堪称为迹的任何空间、地点与风景。以名山和都市为主题的文化风景或人文风景研究因此提出了更为复杂多元的问题,相应地在方法论上也形成了更具有跨学科和跨领域的综合性特征。
就研究领域而言,尽管文化风景往往与历史风景、政治风景和宗教风景等概念并举,但它们之间并不构成相互对立或舍此即彼的排除关系。实际上,这些领域通常不过是侧重不同,方法有别,而在研究对象与内容上,彼此之间不乏重合之处。文化风景研究蕴含了时间和历史的维度,有别于通常意义上的地理景观学。而无论是何种意义上的圣山(如泰山和天台山)和历史上的都城(如洛阳和金陵),都无不深刻地嵌入王朝政治和宗教文化的脉络与肌理之中,因此研究者无法也不应该刻意地将它们切割开来。
从学术方法来看,文化风景学与人文地理学、景观人类学、建筑史、制图史、文学艺术史、空间诗学和城市史等相关学科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系统地分梳这些学科分支的来龙去脉及其相互关系,不免有些令人生畏。但实际的学术研究往往都是从一个具体的学科出发,而进入有关空间、地方/场所和风景的讨论。例如,著名的麦克米伦(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地理批评与空间文学研究”(Geocriticism and Spatial Literary Studies)丛书,其中包括2019年推出的一本《苏格兰文学中的空间与地方诗学》(The Poetics of Space and Place in Scottish Literature),对于从文学作品出发进入地理和空间诗学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文学研究以文本为依据,可以分为纪实性的和虚构性的两大类,此外还有出自经验与冥想之别。例如天台山原非出于虚构,但孙绰的《游天台山赋》却是一篇神游之作,它的作者未曾亲临其地。无论从哪一个具体的学科出发,人文风景或文化风景研究都离不开对物与空间的探讨。但文字书写是线性的和时间性的,而绘画、雕塑和建筑则是空间的艺术。近二三十年来的学界出现了“空间的转向”“物的转向”与“视觉的转向”等说法。任何以文本研究为主的学科,都以各自的方式对此做出了回应。其中图文关系已经发展成为跨媒介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在中国这样一个以书写为中心的文化传统中,这一系列的转向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人文风景的研究具有怎样的启示?对于研究者来说,如何处理书写与物、空间以及空间艺术和视觉艺术的关系,变成了一个难以回避的迫切问题。
《苏格兰文学中的空间与地方诗学》(2019)
有鉴于上述回顾与总结,我们将从事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史和广义历史研究的学者聚集起来,一同探讨包括胜迹在内的人文风景的建构与传承这一核心问题。如果中国古典诗文和绘画中的风景的确如柄谷行人教授所说的那样,首先是一个“理念”,那么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便是这一理念是如何建构出来,并发生作用的;也就是首先需要解释它的构造与运作机制。同样,在对人文风景进行探究和分析时,我们想要知道的是:一处胜迹、一座名山和都市的人文风景是如何形成的?其中涉及了哪些因素?在历史上产生了什么作用,又是怎样产生作用的?
人文风景并不外在于人和人的活动而存在。相反,它构成了历史记忆的来源,同时也塑造了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W. J. T. 米切尔(W. J. T. Mitchell)在《帝国的风景》中指出:
风景是以文化为媒介的自然景色。它既是再现的又是呈现的空间,既是能指(signifier)又是所指(signified),既是框架又是内容,既是真实的地方又是拟境,既是包装又是包装起来的商品。(见米切尔编《风景与权力》)
W. J. T. 米切尔编《风景与权力》(2002,2014)
他的这段论述有其特定的所指,但其主旨却不失参考价值。人文风景是人类的创造物,但是人类又不得不借助它来认识自然、历史和自我,以及参与塑造了自然、历史和自我的那个文化。
三
在唐人题写胜迹的例子中,金陵凤凰台似乎是一个例外。它在当时的文字记载中难得一见,与金陵的众多胜迹相比,显得颇为冷落。而最负盛名的李白那一首《登金陵凤凰台》诗,又是一篇“竞仿”之作,并且有唐一代几乎无人回应。直到宋代,才出现了大量题写凤凰台的诗词作品,一举而将这首诗推到了凤凰台题写系列的奠基之作的位置上。这一现象已足以耐人寻味,但更令人惊奇的是,正是在凤凰台缺席或面目全非的情形下,产生了宋代之后的凤凰台诗词题写系列。自五代之后,凤凰台周围的地貌和金陵的城市格局都发生了巨变,被指认为凤凰台的所在地被城墙遮蔽,李白诗中的景观已不复可见。凤凰台胜迹于是被永久性地封存在李白的笔下,印证了“地以一诗传”的说法。
李白这首诗的作用还不仅限于将凤凰台的风景保存下来和传承下去,它在事实上创造了它所题写的凤凰台胜迹。后世的文人不断地通过诗文和绘画等媒介形式,将李白书写的凤凰台召唤出来,形成了超越时间和具体地点的一道永恒的风景线。此外,正像岳阳楼“欲使久而不可废,则莫如文字”,凤凰台在久废之后,也正是因为诗歌题写,尤其是李白的那一篇奠基之作,才得以重建。物质形态的胜迹变成了胜迹书写的衍生物。与文字相比,它更脆弱而难以持久,不仅周期性地被废弃和替代,而且与时俱变。因此,正是高度文本化的胜迹风景维系了凤凰台的历史记忆。它为凤凰台的重建提供了证据和动机,也为凤凰台的文字书写和视觉呈现提供了孵化器和滋生场。不仅如此,书写创造胜迹的故事还可以落实到物质的层面上: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曾经以墨迹和碑刻等形式介入凤凰台所在的物理空间,从而构成了凤凰台胜迹的一部分。
商伟著《题写名胜:从黄鹤楼到凤凰台》(2020)
我在《书写胜迹:诗人李白与金陵凤凰台》一文中,以金陵凤凰台的诗歌书写和图像呈现为主题,集中探究了胜迹书写与物和景观,以及地点/场所和空间的关系。我对李白诗作的细读与语境化分析表明,不仅文字参与了对胜迹的创造,而且文本化的胜迹还被内化为具有普遍性的感知模式。这一感知模式一方面呈现在诗歌写作的更为广泛的互文关系中,另一方面又被贮存在历史记忆的深处而形成了内心的风景。在关于胜迹的论述中加入凤凰台的绘画系列,无疑有助于展示内心风景的建构与变奏。几乎所有现存的凤凰台图像都是对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的演绎与诠释,但演绎与诠释不等于图解。重要的是,这些图像以不同的方式将诗的文字转译成视觉艺术的语言,在画面的三维空间中去呈现书写的风景。有的图绘在李白诗歌的凤凰台景观与凤凰台江面视野被城墙遮蔽的现场之间反复协商,通过操控视角和画面空间的特殊安排,达到以前者克服后者的视觉效果。有的画家对李白“三山半落青天外”的诗句也做出了有趣的处理:或将“三山”简化为远景中的标志性符号,以此来帮助指认画面前景或中景上的凤凰台,或索性在凤凰台的标题下,展开对长江对岸三山的正面描绘,并以之替代久已消逝的凤凰台景观。
明 文伯仁《凤凰台》
明 文伯仁《三山》
对胜迹风景的研究也有助于理解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发展变化。自宋代尤其是明代之后,出现了胜迹地方化和都市景点化的双重转型,分别呼应了南宋开始的文人地方化和宋代都市商业化的发展。胜迹不再是对远方的向往和孤独行旅的目的地,而是构成了当地文人聚会交往的家园景观,被收入城市的旅游胜览手册和贮存在地方书写的历史记忆中。宋代之后的凤凰台书写以及明代之后的凤凰台图绘,都可以在这个大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脉络中来加以考辨和说明。
薛龙春教授的《点缀山林:题刻、拓本与胜迹的塑造》以泰山为对象,探讨书写与胜迹的关系。这与上一篇《书写胜迹:诗人李白与金陵凤凰台》具有一些连续性,尤其是对书写的考察更为深刻地揭示了它的物质性。泰山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与王朝政治和道教的关系尤为密切。但就实地观览的视觉印象而言,最令人称异的,又莫过于泰山自身构成了文字书写的天然载体。经过世代累积,泰山山体上至今存留了两千五百多处摩崖石刻。薛龙春教授所探讨的正是这一独特的书写胜迹和文字风景。他关注的是石刻的形式而非内容,是石刻的制作及其复制、观览和脱离泰山原境的移动与传播。
泰山的摩崖石刻风景是在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薛龙春教授因此以石刻的制作与观览为主要线索,致力于重构摩崖石刻景观的历史时间维度。在他的论述中,制作与观览是一个双重的过程,从石刻的制作到拓本的制作,从泰山现场的观览到拓本的流传与阅览。正是在制作和观看的双重过程中,泰山的摩崖石刻风景展现出它丰富多彩而又变化不定的面影。
作为一位训练有素的书法家和书法史家,薛龙春教授采用了刻工的角度来观察和思考摩崖石刻的制作过程,从选择地点时考虑石头的质地和石面的大小,到刻写之前打磨石面,准备刻写的技术工具和物质条件,以及决定书法的字体与风格。在他看来,摩崖石刻的形成既受制于外在的地理和技术条件,又充满了意外的变故与偶然性。因此,应该避免从今人的视点和感受出发,将其视为完美的整体设计。在历史的每一个时刻上,人们在泰山上所见到的石刻风景都不尽相同。例如,唐玄宗的《纪泰山铭》被刷上金色和红色,很可能发生于二十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此前并不如此醒目。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也只有在水漫过石面后才变得可以辨识。由此可知,从观览的角度来描述泰山的石刻风景,不应该假设一个理想的观众,而务必首先考虑石刻的物理状况及其周围环境所经历的变化。不仅如此,薛龙春教授还利用清人的游记来再现文人的泰山游览体验。他发现,文人的游记叙述往往在欣赏自然奇观与观览题刻文字之间往返交替。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在泰山的观览经验与书写中,山水与金石形成了一种相互衬托与提示的关系。
唐玄宗《纪泰山铭》(薛龙春摄)
除了实地观览,摩崖石刻还可以通过拓本的形式来传播和阅读。拓本脱离了泰山的固定地点,为我们展示了“移动的胜迹”,尽管这移动的胜迹只能让我们看到泰山石刻风景的局部或片段。在乾嘉金石学盛行的时代,围绕着拓本的制作、摹刻、把玩、校订、鉴赏与阅读,发展出了一整套的规则与法度,同时也成就了书法界的碑学革命和推进了学术范式的转型。正如巫鸿教授和白谦慎教授在各自对石刻拓本的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拓本往往比石刻原件承载了更丰富的历史信息。千百年之下,如欲复原石刻从前的面貌,舍拓本别无他途。石碑和摩崖石刻风景都并非一成不变,从刮补、重刻、增刻到涂色,以及周边空间出现新的石刻,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此外,石刻不仅会经受自然的风化,还在拓墨的过程中受到损耗。从这个意义上说,复制本是以损害原作为代价而制作完成的。它一方面改变了原作,另一方面又保存了原作身上逐渐模糊的旧日面影。因此,在泰山现场观览石刻与通过历代拓本阅览石刻,不仅体现了观看行为的两种媒介方式的差异,也标志着当下与过去的时间导向的不同。即便有一天摩崖石刻已无法辨识或不复存在,拓本仍旧可以让我们看到石刻胜迹的面貌及其历史演变的痕迹。
天台山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座名山,虽未跻身于五岳之列,但在文学、宗教和广义的文化史上,却占据了一个无可替代的地位。同样是将山作为人文风景来考察,也同样强调书写的重要性,薛龙春教授着眼于镌刻在泰山山体上的文字风景及其拓制,流传和观览,陆扬教授则关注于文学写作如何呈现对天台山的感知和想象,从而塑造了天台山人文风景的多重面向与不同品格。他引用了“一座天台山,半部《全唐诗》”的说法,因此在《洞仙与诗神: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天台山》一文中,以文学为主要素材来破解天台山的奥秘:天台山是如何从人迹罕至的地理空间逐渐转化成为一个人文地理学意义上的“地方”;它怎样在“先道而后佛”的层累构成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一座具有兼容性的宗教“圣山”;最后但几乎同样重要的是,从孙绰《游天台山赋》,到《搜神后记》中袁柏、根硕的遇仙故事和《幽明录》中刘晨、阮肇的传说,以及浙东“唐诗之路”的题咏和僧人的诗歌写作,中古文人如何合力将天台山打造成一座文字书写之山和文化史上的丰碑。为此,陆扬教授借助了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空间的生产》中所阐述的“意念空间”的概念。他将天台山描述为三个相互关联的空间:物质之境、意念之境和文化之境,并且在这个框架下展开他历时性的历史重构与文本分析。
天台山隋塔
这篇文章的内容非常丰富,在此我只想聚焦在两个问题上:首先是作为地理空间的山是如何进入人的经验视野而被感知和接受的;其次是怎样通过天台山书写来理解山水诗的兴起。
陆扬教授引用段义孚教授《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中的论述,指出西方世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山感到恐惧,将其视为难以亲近的异己物,甚至是邪恶力量的化身。然而,山所唤起的恐惧感,被朗吉努斯(Dionysius Longinus)尤其是后来的康德等人,纳入了“崇高”(sublime)的范畴来加以解释,并且形成了崇高与优美的二元论的美学论述。人类在面对具有巨大威力的自然现象时,首先被恐惧所压倒,但继而凭借理性认识而将其转化为升华的力量,并最终获得了精神主体对自然力的超越。这样一种崇高感的心理体验在中国古典山水诗中是难得一见的。李白《望庐山瀑布二首》中“初惊河汉落,半洒云天里。仰观势转雄,壮哉造化功”二联或庶几近之,但也不具备本质上的可比性。早在先秦思想,就已经将大自然当作人类生活的一部分而予以接纳并且安顿下来,而不是对其采取拒斥和否定的态度。具体落实到山水诗的兴起,刘勰的一句“庄、老告退,山水方滋”引起了学界的持续争议。陆扬教授拈出孙绰的《游天台山赋》,以揭示它对天台山书写和山水文学的贡献。的确,今人所说的“玄言诗”已所存无多,反倒是这篇赋堪称玄言文学集大成的代表作。如前所述,孙绰笔下的天台山之游实际上是一次内心之旅。其中虽然容纳了心灵之眼所见的天台山瀑布和赤城山等标志性意象,但更重要的在于它将佛道观念融入了对天台山的整体性感知和理解,从而达到了“悟遗有之不尽,觉涉无之有间”和“浑万象以冥观,兀同体于自然”的境界。在山水诗出现之前,首先需要回到内心去寻找接纳和安顿山水的内在资源,孙绰以其神游天台山的内心冥想,完成了对它的“意念之境”的建构,为诗人接触和状写天台山的“物质之境”做了必要的准备。由此看来,玄言文学与山水文学分别呈现了以山水为主体的人文风景的两个不同层面和发展阶段,而不是像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二者之间形成了此消彼长、相互排斥的关系,也大可不必过于计较山水诗何时并且以何种方式正式登场。即便是在山水诗成熟之后,胜迹的创造与书写也仍然离不开将其内在化的过程。胜迹之所以成为胜迹,正有赖于此。上文所举的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和李白《登金陵凤凰台》,都可以说明这一点。
段义孚著《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2014,2021)
作为一门相对成熟的学科,城市史的成就有目共睹。但能否将其纳入胜迹与人文风景的视野而有所拓展,同时弥合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史、宗教史和城市建筑史的分野,从而围绕着都市人文风景的多重面相,形成一个综合性的历史叙述?魏斌教授在他出版的《“山中”的六朝史》一书中,已经对人文风景的概念做了深入阐发。而在本书的《北魏洛阳的汉晋想象:空间、古迹与记忆》一文中,他又将这一概念延伸到了都市空间。魏斌教授将中国的古都风景划为三个层面:王朝权力空间、民众生活场所,以及由废墟和古迹构成的历史记忆空间。这三个层面交织错落,自汉代以降便在京都大赋中形成了相应的书写模式,而在北魏重建洛阳的话语与实践中,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魏斌著《“山中”的六朝史》
古都洛阳是一座空间叠压的城市,尤其是北魏政权在汉晋旧城的层累之上重建了它的都城。被掩埋在地下的古都遗迹,至此被重新“发现”和“指认”出来。这些发现和指认包括物证、人证,以及文字记载和口头传闻,令人真假难辨。无论如何,地下遗迹与地面上残存的建筑和旧物一起,加入了当下的都市空间,并且在与政治权力中心和日常生活场域的互动中,营造了时空交错的多维度的都市人文风景。北魏拓跋氏于洛阳建都时,距这座西晋都城的废毁已经有一百八十余年了。重建洛阳意味着在几种不同的政治文化资源和理念之间做出选择:是恢复周制,还是沿用汉晋制度?是照搬平城的设计,抑或借鉴南方的方案?这些选择直接关乎北魏政权的自我定位与自我想象,与北魏王朝的合法性诉求也密不可分。魏斌教授指出,除此之外,实用的考量也是一个决定性因素。无论是哪一种方案或者是多种方案的综合,都受制于当时洛阳的物质条件和实际需求。
在魏斌教授看来,北魏重建的洛阳景观在两个方面出现了变化:其一是改变了旧都的政治空间以铜铸物为主要象征物和装饰物的特色。古都洛阳残余的前朝旧物包括象征和炫示宫廷权威的铜铸物,其中已多有损坏或被熔铸成它物。但魏斌教授注意到,北魏王朝并没有在汉晋铜铸物的基址上回收或重铸这些象征物与装饰物,而是致力于收集作为王朝权力合法性象征的石经,并将其运回洛阳。北魏洛阳景观的另一大变化,体现在王公贵族将大量的资财投入佛教寺院的修建。旧都的铜铸物被熔铸之后,有的化为铜钱,有的则流向寺院,用于佛教的造像和寺院建筑的装饰。洛阳的铜铸风景因此为之改观,从政治空间转向了宗教空间。如果引入南北对比的视野,不难看到北魏的洛阳和南朝的建康都历经了佛教景观化的洗礼。魏斌教授认为,与东晋以后南方的佛教发展相比,北魏佛教寺院与宫廷权力的关系尤为密切。于是,在新兴的佛教与汉晋旧制之间产生了不小的张力,而这一张力又以最直观的方式呈现在了北魏洛阳的都市风景中。
北魏洛阳内城的空间格局复原示意图(钱国祥《北魏洛阳内城的空间格局复原研究》,《华夏考古》2019年第四期)
从重建洛阳到营造建康,人文风景的主题还在继续,而且来得顺理成章。田晓菲教授的《从白门到紫陌:营造建康》将目光带回到了建康即金陵。其中写到紫陌这一地名如何逐渐蜕变成为普通名词,以此说明即便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如果缺乏文本尤其是诗歌文本的经营,最终也难免被人所遗忘。这个例子从反面印证了贯穿全书的胜迹书写的主题。文章标题上的“营造”具有双重意义,既是指建康城的设计与营建,也包括关于它的书写,尤其是诗赋对建康城的文字营造。而文字营造的建康,比作为实体存在的建康更坚固也更持久。
田晓菲教授指出,作为一个地方,建康在东晋之前就已经有了将近六百年的历史,但在文化史上却几乎没有存在感。自宋文帝开始,建康的双重营造才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建康从“江左地促,不如中国”的“纡余委曲”之地,变成诗歌中的“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就发生在公元五世纪这一关键时期。究竟应该怎样来理解建康的实地营造与文字营造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
关于建康的诗赋写作发生在构筑建康的这个黄金时代。它们的出现与许多因素相关,包括作者的身份及其与宫廷和诸侯王的关系,写作的地点如宫廷与皇家园囿,写作的场合如宫廷仪式和郊外游览,以及写作的性质,如侍游之作或在仪式和其他场合上应诏、应教和应令而作。不难理解,为什么其中的不少作品分享并重申了建康都城的营造理念与帝京的自我想象。诗赋不能代替建筑说话,建筑有自己的语言,但无法像诗赋那样直接诉诸文字的表达。我们不清楚正在建筑中的建康是否真的成为“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因为谢朓在诗歌中表述了一个关于金陵的愿景。在这件事情上,恐怕只有诗歌而非建筑说了算,而诗歌是不接受反驳的。田晓菲教授举颜延之《车驾幸京口侍游蒜山作》为例,让我们看到他如何巧施妙手,点石成金,将蒜山——这座长江边上因野蒜丛生而得名的平顶小丘——写进了气象万千、壮观天地的帝京风景。而“流池自化造,山关固神营”一联固然是对建康形胜的礼赞,又何尝不是诗人的作者自赞?
田晓菲著《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与文化》(2010,2022)
田晓菲教授在文章中将诗赋中的建康书写置于“文化江南”的语境中来加以阐释,强调了它们之间相互依存和相互塑造的关系,同时也揭示了江南的南朝定位,以及江南的文化意义与地理意义之间的不相一致。唐诗中的江南大于地理意义上的江南,金陵怀古也变成了对东晋和南朝的追忆。她还指出,尽管隋文帝在589年征服了江南之后,下令毁掉建康的所有宫殿,将这座城市化作废墟,但这并没有将金陵景观从唐代诗人的心目中抹去。杜牧在由宣州经江宁(金陵)赴扬州的途中写下了《江南春绝句》中的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他极目望去,满眼依旧是南朝的烟雨与楼台。无论这是一句问话还是感叹,江南都被永久地定格在了南朝。因此,唐诗中的江南风景有其自身的空间指涉与时间标志。它们出自诗人的文字经营,却变成了历史记忆的来源和言说与书写的根据。
四
这本书是在北京大学文研院2022年主办的“江山胜迹”线上讲座系列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中的四次讲座的讲稿经过修改,曾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上。这次结集成书,也是以讲稿为底本加写补充而成的。学报有篇幅规定,编书不受限制。这使得我们可以更充分地展开对问题的论述。以我自己的文章为例,除了修改之外,还增加了凤凰台图像的部分,结语也做了重写,与学报的论文相比,篇幅几乎翻倍。
我们在编辑的过程中,始终抱着这样一个心愿,那就是将讲座的特色保存下来。为此,我们收录了讲座时使用的大量图像,并且还做了一些增补。而最大的一个特色是在每一篇文章的后面都收录了主持人和评议人的评论,以及作者的回应。书的这一部分既保留了讲座的现场感,又经过了全部参与者的修改补充,因此是讲座以及讲座之后持续性对话的结果。相信这一部分可以让读者读到充满知性乐趣的对话,看到学问和思想在碰撞之下灵光闪现,火花迸射。这本书围绕着一些共同的问题展开,但并非所有的作者都持相同的观点,或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而评议人也往往对同一个问题提示了其他的思路与视角,读者完全有可能从中引发新的想法,甚至新的话题。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今年4月至6月,我有幸应邀作为访问学者,在北大文研院驻访了两个月。在这两个月中,我也对文研院有了真切的体验。北大文研院秉承涵育学术、激活思想的宗旨,将校内外不同学科的学者聚在一起,以各种方式推进学术的讨论与交流。这在全国高校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的领域中,率先建立了一个新的范式,同时也为多少有些沉闷的学界带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每一次走进文研院的园子,都可以感受到它弥漫着活力和喜悦的氛围,令人如有所待。而在结束了一天的活动后,你又会体会到它的另一面,或许是更深的一面,那是屏蔽了一切喧嚣的宁静。这让我想到了契诃夫《樱桃园》中安尼雅所幻想的那座新的花园:
你会看得见它的,你会感觉到它有多么美的,而一种平静、深沉的喜悦,也会降临在你的心灵上的,就像夕阳斜照着黄昏一样。
愿文研院这座花园芳华永驻,四季长春。愿它为我们保留一方净土和一个可以称之为心灵家园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