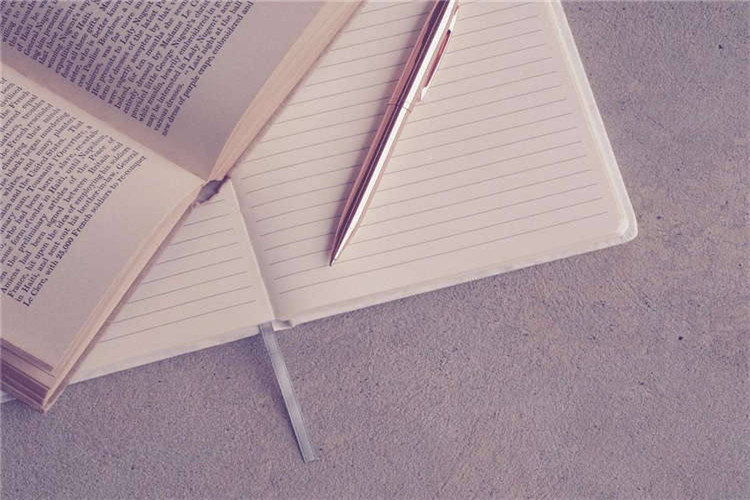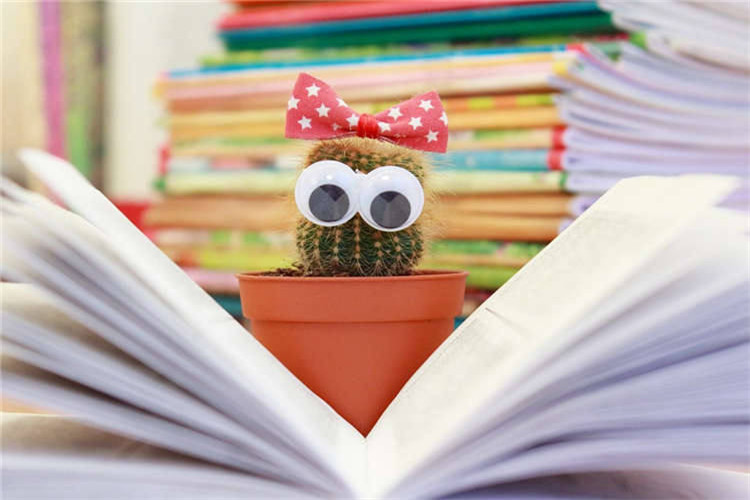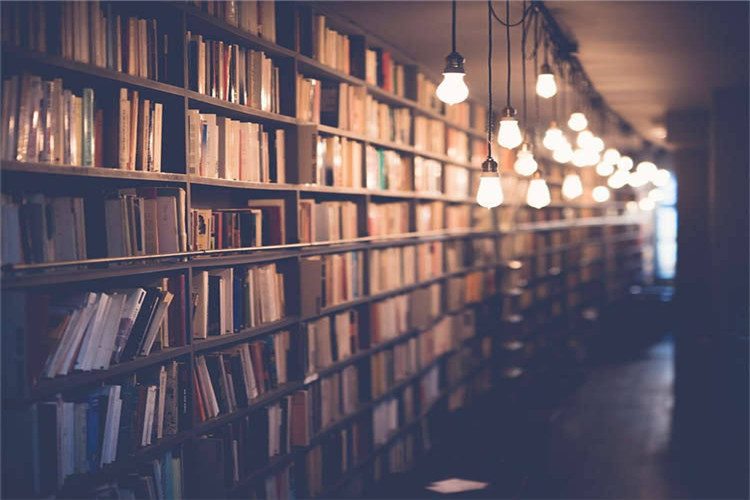当下,大型演唱会在二三线城市(77%)的票房占比远高于一线城市(10%),大型演唱会已成为多地拉动文旅消费的关键点。而体量更小的Livehouse演出,则深入一线城市的“毛细血管”,正持续在大城市的日常生活里制造着丰富多样的音乐现场。今年暑假,上海各类演唱会、音乐节和Livehouse演出超过200场,其中,中小型Livehouse场次占到3/4,呈现出一派细微、活跃的市场氛围。
网友分享台湾乐队康士坦的变化球在蜚声livehouse的演出
Livehouse:音乐产业的“毛细血管”
根据近期中国传媒大学音乐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2025年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总报告》,2024年全国音乐演出市场规模达387.33亿元,同比增长46.61%,远超数字音乐(15%),影视、动漫、游戏音乐(15%)等的增速,演唱会场次数同比增长49.9%。其中,大中型演唱会、音乐节票房收入达296.36亿元,同比增长66.5%。与作为音乐演出市场核心驱动力的大型演唱会、音乐节相比,Livehouse主要为中小型演出,大部分场馆属于演艺新空间范畴。据灯塔专业版统计,2024年全国中小型演唱会达450余场,观演人次近50万,同样呈现欣欣向荣的态势。
据@魔都live指南 不完全统计 仅9月1日一天上海就有近20场livehouse演出
在这类数据报告中,一处细节值得注意。当下,大型演唱会在二三线城市(77%)的票房占比远高于一线城市(10%),大型演唱会已成为多地拉动文旅消费的关键点。而体量更小的Livehouse演出,则深入一线城市的“毛细血管”,正持续在大城市的日常生活里制造着丰富多样的音乐现场。
今年暑假,上海各类演唱会、音乐节和Livehouse演出超过200场,其中,中小型Livehouse场次占到3/4,呈现出一派细微、活跃的市场氛围。
就在前不久,燃烬感十足的乐队康士坦的变化球,乡村雷鬼风的五雷王乐队,年过古稀的日本传奇Citypop乐队Bread&Butter,生于1990年代末的摇滚乐队虎啸春,生于2019年的摇滚乐队帆布小镇,以及“旧燕归巢”的LOFT BEACH等三支从上海起步的乐队,纷纷在上海开启专场。一时间,囊括了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音乐现场,呈现出潮流与冷门并置,复古与动感交织的景象。同时,一些偶像新人或虚拟偶像的线下音乐会,从影视、动漫或音乐剧领域跨界而来的各类演出,同样精彩纷呈。
专业与跨界、多元与小众的并存,在Livehouse等中小型演艺空间的身上成为标志,呈现出既矛盾又自洽的一面。
地下偶像团体StarWink在万代南梦宫上海文化中心未来剧场
虚拟偶像泠鸢线下live上海场 回响之地
从被埋没中破发
Livehouse这类演出形态与独立音乐的兴起与发展关系紧密。回到二战刚结束的年代,音乐产业的核心圈层以唱片等音乐出版物和专业剧院中的音乐演出为主导。专业剧院为音乐表演者和观众均设置了高门槛,工业化驱动下的唱片业使音乐转换为工业产品,引爆巨幅商业版图,也使得资本对音乐形成垄断之势。
由此,音乐产业欣欣向荣的一面背后,还有底层与新兴音乐人的无助。必须要依托娱乐业糊口的现状,会带来随市场风向而逐流的无力,甚至遭受不平等待遇。他们被商业娱乐的精致景观埋没,却依旧对音乐艺术本体发起探索与追求,创造出爵士、蓝调、民谣、早期摇滚与朋克等不同质地的音乐与态度。
二手玫瑰 上海Mao livehouse
破高门槛、破工业化、破娱乐至上的理念,给了底层边缘艺术家一个释放活力的平台,“独立”成为一种带有态度的音乐标签,影响着全球音乐产业的发展。随着独立音乐的崛起,独立音乐人的表演场地,从早期仍依赖Pub、Club这类餐饮酒吧或带社交属性的展演场所,到Livehouse的出现。表演场地逐步抛弃了传统剧院式的任何装饰,撤除以餐饮或社交为主角的空间盈利模式,反向以低廉的场地成本和灵活的空间组成,强调音乐的现场表现力。这正是当下许多Livehouse选择以废弃仓库为改造对象,可容纳百人至千人的场地不设固定座位,却花重金打造音响设备的原因。人们可以在黑暗的空间里,自由走动,近距离与台上人共同沉浸在音乐氛围里。
Keren Ann在上海Mao livehouse
在中国,随着摇滚乐兴起,独立音乐人从北京的马克希姆西餐厅、上海新天地ARK等演出场地,逐渐衍化出MAO Livehouse、摩登天空、育音堂、瓦肆。随着2019年《乐队的夏天》,2022年《我们民谣2022》等综艺开播,引发公众对中国独立音乐40年发展史的追忆,新裤子、痛仰、达达、周云蓬、万晓利、重塑雕像的权利等被更多人认识。历经时代的“米店”“给给”“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等歌曲,成为当下年轻人歌单里的必备。
据海外媒体的数据统计,2024年全球(已发布作品的)独立音乐人超700万,产生的市场价值达307亿美元,并预计在2029年升至456亿美元,是音乐产业未来发展的一股强大动力。
上海育音堂演出现场
体验经济:中间空间的符号体验
当下,音乐产业的结构性变局已经发生,原本占产业核心大份额的唱片等出版物被数字音乐替代。2024年中国的数字音乐产业规模达1027亿元,占整体的1/5。经济学家艾伦·克鲁格曾强调,打造超级明星艺人的两个关键要素是规模和不可替代性,无论传统的唱片还是当下数字音乐的蓬勃之势都证明,成功的艺人往往会覆盖规模巨大的受众群体。由于演出本身不具备所谓规模巨大的属性,因此在过往很长一段时间,音乐演出只是艺人推销唱片的互补商品。
但就在2017年,这一形势彻底改变。在美国,艺人的收入大头转向巡回演出(平均占比80%),来自唱片占15%,来自版税占5%。克鲁格强调“巡演为他们挣来了绝大部分的钱,(而且)对大多数音乐人来说,只有现场演唱会才能挣钱”(《摇滚吧,经济学》)。
正是在这样的产业变局下,中小体量的Livehouse演出有了理所当然的立足之本。近年,像陶喆、胡海泉、南拳妈妈,以及在海外流媒体热火一时的欧美新人歌手都把巡演场地设置在专业剧院或Livehouse。同时,更多年轻乐队的涌现,将时下或新潮,或小众,或实验性的音乐填满大大小小的场地,培育起更多样化的音乐产业生态。原本在流行音乐中,少数头部艺人强势顶升,随后长尾效应绵延悠长的格局,也在长尾变化出多元样态,而显得不同。
越来越多的歌手巡演场地设置在专业剧院或Livehouse,图为2023年陶喆“欢迎光临”上海专场在前滩31演艺中心。
同时,克鲁格还提出“演唱会卖的是体验,不仅仅是音乐”(《摇滚吧,经济学》),似乎引出了当下音乐产业必须面临的新问题。
Livehouse如今已在音乐产业的大格局下不再边缘,它架起了音乐演出的不同面,成为核心支柱。而它以音乐为本的原初使命,在不同的需求面前被不断冲刷。在体验经济的背景下,Livehouse的观众已不只是来听音乐的。
日本歌手BENI中国首场演唱会在上海瓦肆VAS est
无论五条人或是草东没有派对,两支深受年轻人喜欢的乐队都有着对传统流行音乐工业化生产的解构气势。从方言叙事诗到创造塑料袋美学,从数字化切分到静默与嘶吼夹杂的干枯情感描画方式。如今,音乐现场给人的体验与传统的情感抒发,悠扬的氛围渲染已大为不同。颠覆性的音乐描绘手法和美学理念充盈其中,让人不得不脱离惯常表达逻辑,重新建立感知体验的维度。
暗黑的Livehouse空间像一道裂隙,横亘在日常生活中间,给不变的生活带来各种变量。这些变量类似城镇的节庆狂欢、主题乐园里的各类演出,冲破常量带来的预期停滞,补充着新鲜感。
庞麦郎在上海星临天下Star world的演出海报
此外,无论朋克、说唱这类音乐风格,还是方言叙事中的地域性、机械律动带来的感知感受,都是一场不同文化符号的融合与碰撞。Livehouse之于当下的年轻人,更像一场体验不同文化符号的熔炉。互联网时代下,文化符号一直在流变,时而兴起时而衰减。但活在当下,去感受去体验,用符号与个人的志向相碰撞,其乐无穷。据统计,Livehouse中单人观演的比例达73.1%,远高于大型演唱会、音乐节或音乐剧等其他演出类型。独来独往的现象,或许是因为社恐等心理因素,或许是因为一场小众演出,但以孤立个体的身份进入充满变量的时空裂隙中,沉浸感会加倍。我们不只是消费者,更是文化符号碰撞下的体验者和现场激烈情绪的制造者。
可坐可站甚至可以躺,松弛感拉满,让livehouse沉浸感加倍。图为上海INS复兴公园地下的livehouse绿洲OASIS。
如今,Livehouse更像一个中间空间:它充满可变性,填满不同的符号元素。音乐像一条牵引线,聚拢了台上与台下的不同个体,并在嘈杂中释放情绪,碰撞花火。体验常量生活之外的不同感,重建与陌生世界的心底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