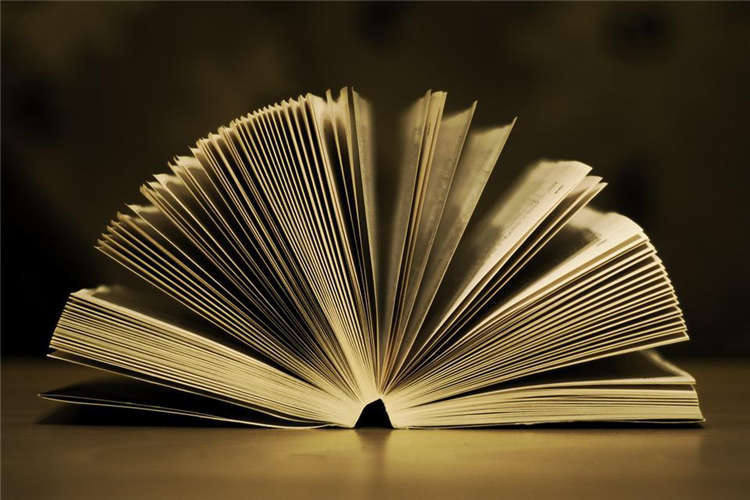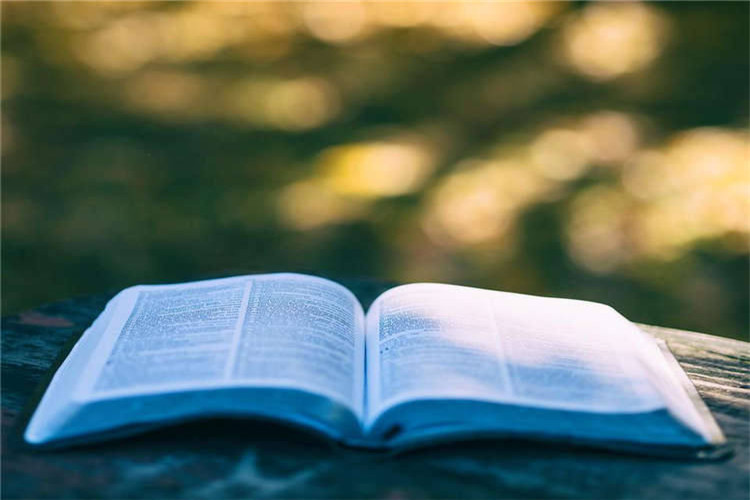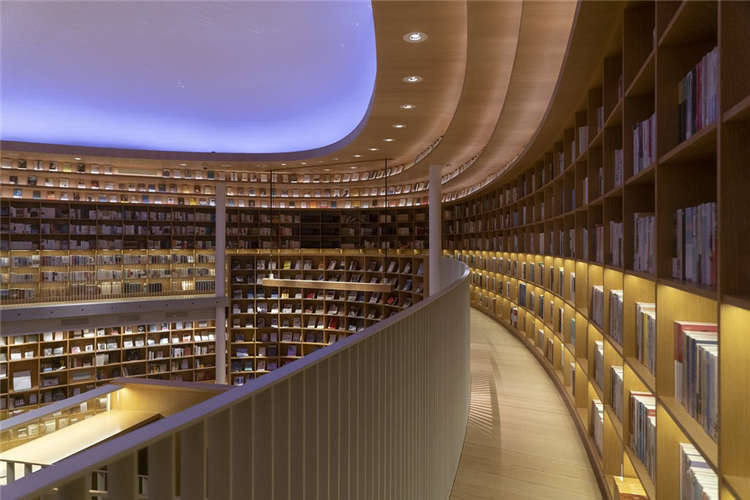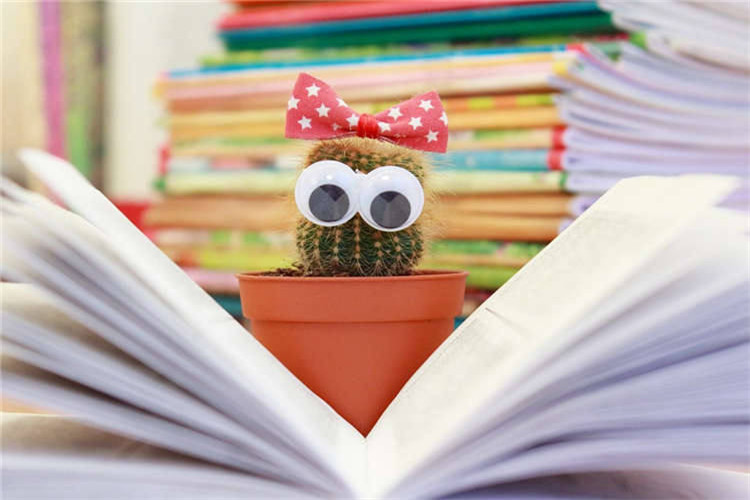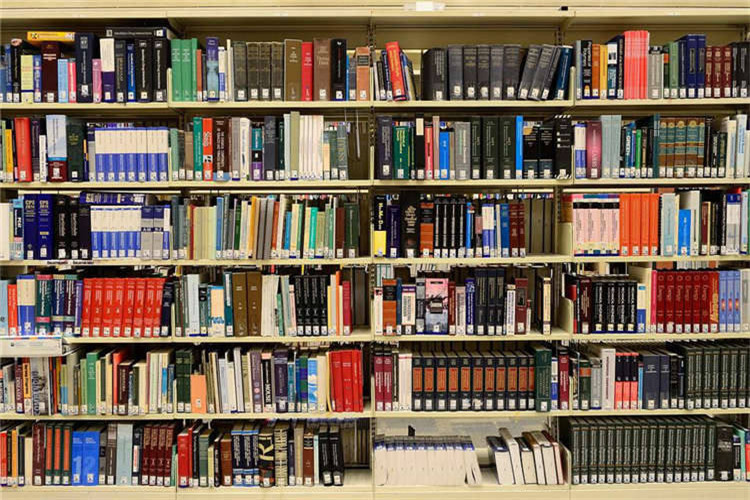袁枚《随园食单》里的三百二十六道菜,是他四十年美食江湖的总结,按他自己的说法,“每食于某氏而饱,必使家厨往彼灶觚,执弟子之礼”,如此不耻下问,终成美食大家。
《随园食单》里记录的美食,言简意赅,短则十几字,长则几十字,就把一道菜讲完,惜字如金,但这道“鳆鱼豆腐”,他却讲了两次。当时称鲍鱼为“鳆鱼”,也许是这道菜中的鲍鱼和豆腐都做得绝妙,让他老人家爱不释手,所以才反复念及。第一次出现是在“海鲜单”里的“鳆鱼”条目:
鳆鱼炒薄片甚佳,杨中丞家削片入鸡汤豆腐中,号称“鳆鱼豆腐”。上加陈糟油浇之。
“杂素菜单”里的一道“杨中丞豆腐”,讲得更详细些:
用嫩豆腐煮去豆气,入鸡汤,同鳆鱼片滚数刻,加糟油、香蕈起锅。鸡汁须浓,鱼片要薄。
做法大概是:先将鲍鱼切薄片;再将嫩豆腐焯水去豆腥;接着用浓鸡汤与焯过水的豆腐、鲍鱼片焖煮,水开后再滚片刻,加陈糟油和香菇,起锅。
貌似简单,其实复杂得很,这道菜有几个关键点。一是嫩豆腐要先焯水去豆腥味。豆腥味主要是由于大豆在粉碎加工的过程中,自身的脂肪氧化酶遇到空气被唤醒激活,将其中的部分多不饱和脂肪酸氧化,再降解为醛、酮类等小分子化合物,这些小分子化合物沸点不高且溶于水,简单焯一下水后,这些小分子化合物基本也就去掉大部分了;二是要先煲出鸡汤,至于用何种鸡煲鸡汤,他在“选用须知”中说了,“蒸鸡用雌鸡,煨鸡用骟鸡,取鸡汁用老鸡”。
更为关键的是鲍鱼要切成薄片,焖煮时水开后再滚一阵就行。我们吃鲍鱼,吃的是鲍鱼的软体部分,即一个宽大扁平的肉足,鲍鱼就是靠着这肉足和平展的跖面吸附于岩石上,爬行于礁坪和穴洞之间。鲍鱼肉足的附着力相当惊人,一个壳长十五厘米的鲍鱼,肉足的吸附力高达二百公斤,任凭风吹浪打,都不能把它掀翻。这个力大无比的肉足,由纵横交错的结缔组织构成,主要成分是胶原蛋白,其肉质之坚韧,也就可想而知了。动物胶原蛋白在四十度左右变性,肉质变软,但如果继续加热,它又会变硬,要再让它变软,必须经过长时间的炖煮。鲍鱼由纵横交错的胶原蛋白组成,换句话说,经过加热,外层的胶原蛋白的温度超过四十度,开始变性变软,里层的胶原蛋白由于热量还没传导到位,依然坚如磐石。当里层的胶原蛋白超过四十度,外层的胶原蛋白却因为温度过高而重新变硬。所以,烹饪鲜鲍,先切成薄片在烧开的鸡汤中焯几秒,都是为了控制合适的温度,让鲍鱼均匀受热。袁枚说让鲍鱼片与豆腐一起在烧开的鸡汤中“滚数刻”,再放香菇,这并不是最好的方法,应该是先放豆腐和香菇“滚数刻”,调好味后再放鲍鱼片,且马上熄火,用鸡汤的余温把鲍鱼片汆熟,这样做出来的鲍鱼片才又鲜又嫩。
袁枚说的陈糟油,也很有讲究。糟油是在甜酒糟中加入丁香、月桂、玉果、茴香、玉竹、香菇、白芷、陈皮、甘草、花椒、麦曲等辅料,让其继续发酵,发酵时间越长,风味物质越多,香味也越浓郁,所以袁枚强调要用“陈糟油”。糟油为江苏太仓特产,始创于清乾隆年间,创始人是酿酒商李梧江,先在江浙一带流行再逐步外传,太仓出产的最为出名,因为这里空气中的微生物最适合糟油风味的产生和累积。这道菜是典型的苏帮菜,糟油的应用就是最好的证据。
鲍鱼和豆腐的组合,即便放在今天,也是罕见,主要是一贵一贱,通常不会想到把它们放在一起。在袁枚生活的时代,鲍鱼还未实现人工养殖,名贵得很,夏曾传在《随园食单补证》里对鲍鱼和豆腐的组合,打了个比方:“设有一富家儿,一寒儒,一则乘舆赴宴,一则提篮买菜,两人相遇若无睹也。一朝入闱应试,同一号舍,题纸既下,题极艰难,富家儿彳行风檐,方思索破题而不得,瞥见寒儒已将脱稿,于是乞而观之,并且出重价而购之,则寒儒可以有才,而富家儿亦有文矣。知乎?此乃鳆鱼滚豆腐之妙。”他把鲍鱼比为不会作文的富家儿,把豆腐比为善文的寒儒,将鲍鱼滚豆腐比为两人在考场作弊,富家儿出重金买下寒儒的试卷,结果是双方各自获益。夏曾传屡试不中,清末科考作弊也很严重,所以他有此感悟,但鲍鱼和豆腐这两个清淡之物组合在一起要出效果,其中的关键其实是浓鸡汁和陈糟油。
这又不得不提到袁枚与杨中丞之间的关系。《随园食单》里不乏达官显贵,这些人请袁枚吃饭,遇到喜欢的菜,袁枚都会“问其方略,集而存之”。在这里面,“杨中丞”出现最多,除了这道“杨中丞豆腐”,还有“羽族单”里的“焦鸡”,袁枚明确指出“此杨中丞家法也。方辅兄家亦好”。此外,“点心单”里还有“杨中丞西洋饼”,也是出自杨中丞家,这个“杨中丞”家的厨师确实十分了得。
中丞一职,始于汉代,当时御史大夫下设两丞,一称御史丞,一称御史中丞。东汉以来,御史大夫转为大司空,以御史中丞为御史台长官。唐、宋两代虽然设御史大夫,也往往缺位,而以中丞代行其职。明代改御史台为都察院,都察院的副职都御史相当于前代的御史中丞。明、清两代常以副都御史或佥都御史出任巡抚,清代各省巡抚例兼右都御史衔,因此,明、清巡抚也称中丞。
有推测这“杨中丞”为与袁枚有交往的浙江巡抚杨廷璋,我认为这不可能。杨廷璋在乾隆二十一年(1756),被授为浙江巡抚,但乾隆二十四年(1759)就被授闽浙总督,后来更加授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袁枚出版《随园食单》时,他早已作古,袁枚对官员的称谓,只往其高的职务叫,不可能选巡抚这一低职位叫。
更大的可能是袁枚的好朋友杨潮观,字宏度,号笠湖,江苏无锡人。袁枚与其相识于乾隆元年(1736),当时袁枚进京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杨潮观中了新科举人到京旅游,两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在京相遇,自此结下了一段很深的情谊。两人志趣相投,袁枚喜诗词,杨潮观善戏曲,也都喜欢美食,在宦海沉浮时,两人声气相通,互相鼓励;袁枚准备辞官时,杨潮观时任邛州知府,“在邛州特寄金三百,属置宅金陵,将傍余以终老”,需知袁枚当时买下江宁织造隋赫德留下的随园,也才花了三百金;辞官后的袁枚有几次去找杨潮观玩,说杨潮观“闻余至必喜”;杨潮观有一回出公差,特地转道金陵来会老友,袁枚激动地写了一首诗《喜杨九宏度从邛州来,即事有作》,说“蔗味老弥甘,交情久更挚,不信扪胸中,三十六年事”。也是这回,袁枚让宝贝女儿阿能认杨潮观做干爹,并将其寄养在杨潮观家里。两人如此深的交情,交流美食心得时,当然和盘托出。杨潮观虽为知府,比巡抚“中丞”还差一级,但翻看《随园食单》和《随园诗话》,把官员往高一级职位叫,并不少见,比如袁枚称肇庆府高要县县令杨兰坡为“明府”,明府是汉代人对太守的尊称,比县令高一级,看来用前朝官职往高尊称官员,是袁枚所处时代的习俗。
说回袁枚与杨潮观,关系好到这个程度,算难得吧?但就是这样的朋友,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事因杨潮观曾向袁枚讲了一个梦,说他有次主持考试,阅卷前“梦有女子年三十许,淡妆,面目疏秀,短身,青绀裙,乌巾束额,如江南人仪态”,梦中这位美女“揭帐低语”,“拜托使君,《桂花香》一卷,千万留心相助”。杨潮观阅卷时真就发现有一老贡生作了《桂花香》,文笔还可以,想到女子梦中相托,于是就把他录取了。杨潮观认为“疑女子来托者,即李香君”。这一朋友间的闲聊,被袁枚写进“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的短篇小说集《子不语》中。
在袁枚眼中,这是趣事一桩,于是大书特书。《子不语》写成后,他还寄给老朋友讨彩,没想到,却讨了个没趣。杨潮观见后大发脾气,去信袁枚,说:“所称李香君者,乃当时侯朝宗之婊子也。就见活香君,有何荣?有何幸?有何可夸?弟平生非不好色,独不好婊子之色,‘名妓’二字,尤所厌闻……不知有何开罪阁下之处,乃于笔尖侮弄如此?似此乃佻达下流,弟虽不肖,尚不至此。”
袁枚觉得是趣事,杨潮观觉得是丑事,矛盾就是这么来的。这事本是小事,若不高兴,把文章删了就是,即便是印刷出来了,毁了也不值几个钱,可杨潮观来了这样一封不客气的信。袁枚收到信后估计心情也不怎么样,于是气冲脑门回信三千余字,说阁下艳梦之事,“亦君所说,非我臆造”,你现在不准我说,恐怕是:“目下日暮穷途,时时为身后之行述墓铭起见,故想讳隐其前说耶?”大意是“你怕是快要死了,要墓志铭好看,所以要隐去前面跟我说的话吧?”诅咒都出来了,又继续挖苦杨潮观:“伪名儒,不如真名妓!”将杨潮观骂了个痛快,自此两人可谓互相“拉黑”,互不往来。
杨潮观名气虽没有袁枚大,但官声极好,还是著名的戏曲家,两位文坛老人,惺惺相惜这么多年,却因一个梦而交恶,太可惜了。杨潮观去世后,袁枚后悔了,受杨潮观子女之托,给老朋友做了《邛州知州杨君笠湖传》,对自己的行为有所检讨:“君与余为总角交,性情绝不相似。余狂,君狷;余疏俊,君笃诚。”这个检讨虽然来得晚了些,但总比没有可能好些。
《论语》里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朋友之间交往,也当“亲亲互隐”,不该说的事,有可能影响朋友名誉和前途的事,或者朋友介意的事,打死也不能说。这个道理袁枚也是懂的,他在《随园诗话》中就说:“凡人各有得力处,各有乖谬处,总要平心静气,存其是而去其非。”道理谁都懂,但却不易做到,袁枚这个“大嘴巴”就是这样。
嘴大吃四方,嘴大也惹事,不如好好吃鲍鱼滚鸡汤豆腐。
本文摘自《袁枚的讲究:趣读随园食单》,林卫辉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8月。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