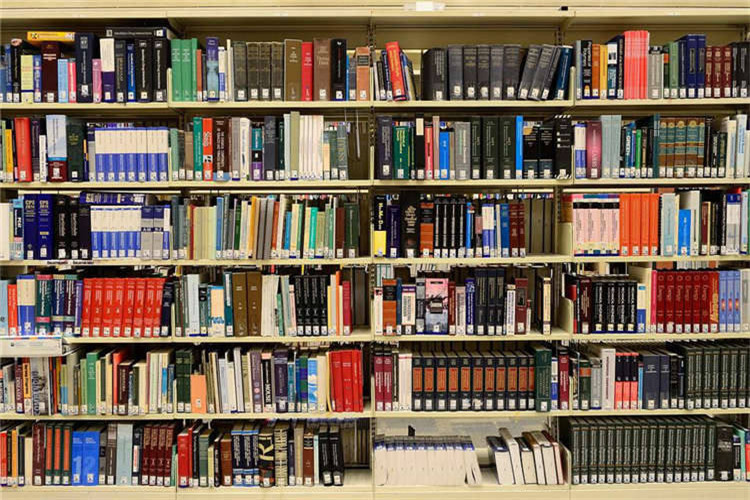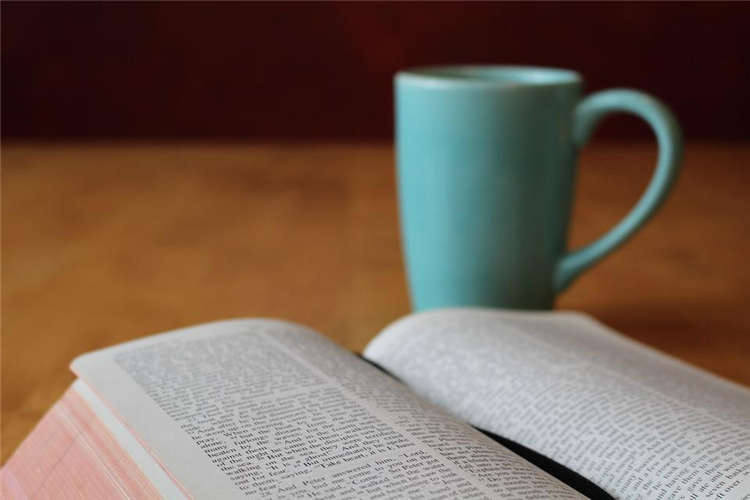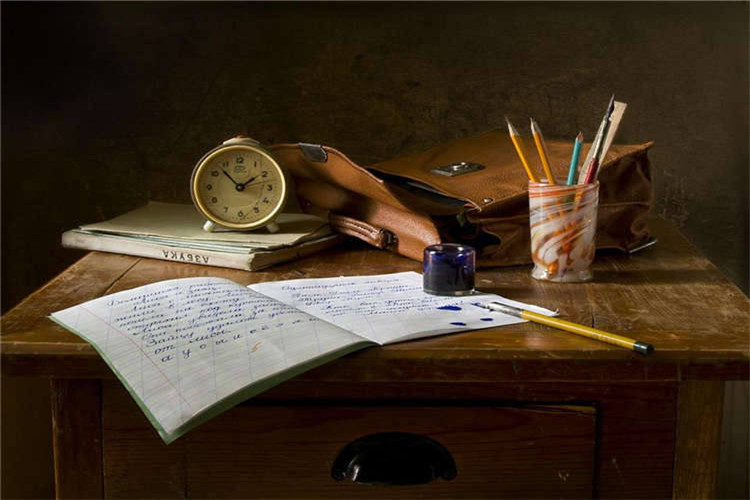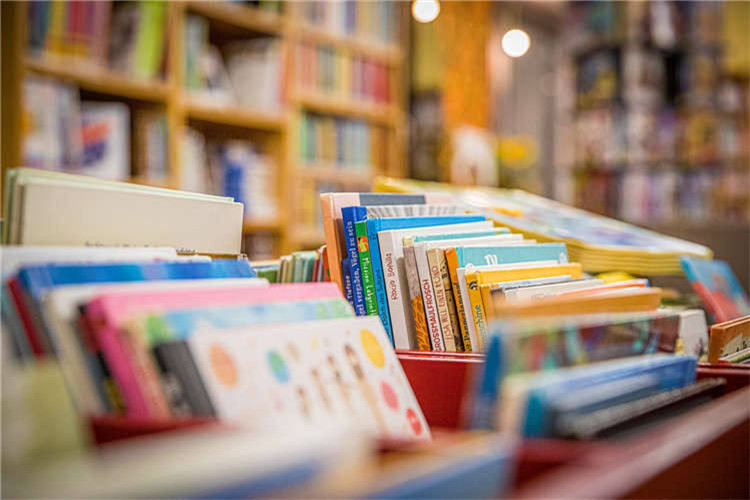唐代乐舞文化发达,崔令钦《教坊记》、段安节《乐府杂录》和孙棨《北里志》等书颇能反映唐代以曲艺为生的女子的精湛技艺和生活情状。其中的御前表演者,不免让读者联想到汉代的卫子夫与赵飞燕姊妹。似乎哪位女子一旦被皇帝青睐,“一朝选在君王侧”,就意味着锦衣玉食、飞黄腾达。
唐代后妃中,有此传奇经历的实在寥寥。两《唐书·后妃传》所录后妃数量寡少,其中未见有此种际遇的女子。陈丽萍《贤妃嬖宠:唐代后妃史事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补充了相当数量的唐代后妃资料,笔者倒是从中寻觅到两位。
一位是唐玄宗的赵丽妃。临淄王李隆基为潞州别驾时,张暐“潜识英姿,倾身事之,日奉游处。及乐人赵元礼自山东来,有女美丽,善歌舞,王幸之,止于暐第,生废太子瑛”。(《旧唐书》卷一〇六《张暐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247页)《新唐书·王琚传》述张暐事,作“山东倡人赵元礼有女”,(《新唐书》卷一二一《王琚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4332页)二书所载赵元礼身份一致。赵丽妃虽一度深得玄宗宠爱,开元十四年去世后获得“和”之谥号,这在唐代后妃中是很罕见的。(《贤妃嬖宠》,第125-126页)然而“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㢮,爱㢮则恩绝”,(《汉书》卷九十七上《外戚传上》,中华书局,1964年,第3952页)以明皇之好色多情,恐怕赵丽妃也不能久得君王欢心。
第二位是唐代宗时之张昭仪。大历(766-779)中,歌女张红红与父歌于衢路以求食。将军韦青“闻其歌者,喉音寥亮,仍有眉首,即纳为姬”。韦青“乃自传其艺,(红红)颖悟绝伦”。张红红很快名动长安,甚至传到皇帝耳中——“寻达上听。翊日,召入宜春院,宠泽隆异,宫中号‘记曲娘子’,寻为才人”。韦青去世的消息由代宗告知红红后,红红“不忍忘其恩,乃一恸而绝。上嘉叹之,即赠昭仪也”。(段安节撰,亓娟莉校注《乐府杂录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3-54页)陈丽萍于张昭仪事后加按语“张昭仪事出自小说,其人其事有待考证。但唐代规模庞大的宫伎群体确实有不少来自民间,其中因色艺出众而被宠幸并得封嫔妃者也是可能存在的”。(《贤妃嬖宠》,第156页)
虽然有得到皇帝宠幸的微弱可能性,但宫廷伎乐女子养在深宫,其活动殊少自由。近日浏览墓志,恰见一位出于唐代筝乐世家的女子,因为母亲的着意安排,摆脱了深受禁锢的命运,开启了与其他大部分女性一样的婚姻生活。该方墓志前半对于唐代音乐史(特别是补充筝乐人资料)很有价值,后半所涉及唐代士人与妾室、妾室与丈夫正妻子女关系亦是社会生活史的极佳史料。
高氏墓志并盖,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新入藏墓志》第98页
为便于研究,今将墓志全文(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新入藏墓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拓片在第98页,录文在第289页)分前后两部分移录如下:
大唐前监察韦公故高氏墓志铭并序
前监察御史里行韦廙撰
有唐元和十二年二月廿九日,高氏殁于长安亲仁里之私第,生廿七年矣,实可痛哉!其先代晓音律,世服朱紫。有亲姊三人,皆艺皃﹝貌﹞绝代。长姊歌启齿而梁尘暗落,次姊指拂弦而秦声动天,并为君命所求,殁身怨非吾偶。第三姊复因公主抑奏,今贵宠无比。 上欲制置新曲,必先错综于其筝。唯此姊与兄三人同出于李氏,其母尝叹三女拘限宫禁,每仲夏之朔方遂一面。况小女孤幼,倍所钟爱,变易姓氏,养于他族。而天假艳丽之质,生知丝竹之音,凡乐有经耳之声,我筝必随而尽得。密亲听其清响妙绝,知酷似同母之姊矣。
志主高氏于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去世,年二十七岁,则其生于德宗贞元七年(791)。高氏出自一个世代通晓音律的家族,三位姐姐因艺貌绝代而选入宫廷,其中三姐凭借公主的推荐,深得皇帝宠信。这位向宪宗进献女乐人的公主是谁呢?很可能是宪宗爱女普宁公主。宪宗有十八女,“梁国惠康公主,始封普宁。帝特爱之”(《新唐书》卷八十三《诸帝公主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667页)元和四年,“于頔入朝,悉以歌舞人内禁中,或言普宁公主取以献,皆頔嬖爱”。(《新唐书》卷一一九《白居易传》,第4300页)当时传言普宁公主从于頔处取歌舞人献于宪宗,可见其平素对乐舞的留意,那么高氏第三姊很可能也是因为宪宗最宠爱之普宁公主的推荐而受到皇帝赏识的。
从“次姊指拂弦而秦声动天”及“我筝必随而尽得。密亲听其清响妙绝,知酷似同母之姊矣”来看,高氏出自一个筝乐世家。学界关于唐代筝乐的研究中,对筝人搜集颇为完备,(谢明《唐代筝乐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51-62页;李国平《唐时期筝的历史地理探索》,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99-106页)然未见有著录高氏姊妹者。
《教坊记》载曰:
楼下戏出队,宜春院人少,即以云韶添之。云韶谓之“宫人”,盖贱隶也。非直美恶殊貌,佩琚居然易辨,内人带鱼,宫人则否。平人女以容色选入内者,教习琵琶、三弦、箜篌、筝等者,谓“搊弹家”。(崔令钦撰,吴企明点校《教坊记》,中华书局,2012年,第12页)
李氏的三位女儿应是“平人女以容色选入内者”之“搊弹家”,非如贱隶之“宫人”。
宫廷乐人的生活处于极度封闭的状态。《教坊记》的记载恰可与墓志内容对照:
妓女入宜春院,谓之“内人”,亦曰“前头人”,常在上前头也。其家犹在教坊,谓之“内人家”,四季给米。其得幸者,谓之“十家”,给第宅,赐无异等。初,特承恩宠者有十家,后继进者,敕有司:给赐同十家。虽数十家,犹故以“十家”称之。每月二日,十六日,内人母得以女对,无母,则姊妹若姑一人对。十家就本落,余内人并坐内教坊对。内人生日,则许其母、姑、姊妹皆来对。其对所如式。(《教坊记》,第11页)
入选宜春院的女伎,虽家在教坊,同家人相见亦非常困难。仅每月固定在二日和十六日,其母得与女儿相见;若遇其生日,则其母、姑、姊妹皆可同来相见。李氏三姊妹虽非入宜春院之“内人”,但其身份之不自由当无二致。墓志写出宫之难,此处则描述乐人家人入宫相见难。
高氏之母姓李,而唐代最著名的筝乐世家即出自李氏。《乐府杂录》“筝”条载:
筝者,蒙恬所造也。元和至太和中,李青青及龙佐。大中以来,有常述本,亦妙手也。史从、李从周皆能者也。从周即青孙,亚其父之艺也。(《乐府杂录校注》,第93页)
元和年间,善弹筝者中有名李青青者。《乐府杂录》原文谓从周为青青之孙,亓娟莉推断“孙”为“子”之讹,李青青活跃于元和至太和间(806-835),李从周(吴融《李周弹筝歌》结合吴融的经历,推算宣宗大中时,李周处于青少年时期,从所工技艺、身份、活动时间等判断,似与李从周为一人)活跃于宣宗大中(847-859)以来,二人似当为父子。(《乐府杂录校注》,第93-94页)亓氏观点可备一说。高氏去世于元和十二年,元和年间正是其三位姐姐在宫禁活跃的时期。这个筝乐世家不但“其先代晓音律”,则唐代音乐世家,不仅男子世承其业,女子也得以传其术。高氏筝乐师承既有先世通晓音律,或许其母李氏有来自李青青家族这一筝乐世家的可能。
唐代教坊女乐来源有多种途径,地位普遍卑下,命运亦堪称凄惨。(刘梦姣《唐代教坊女乐研究》,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14-18、32-38页)教坊艺人的生活中,屈辱和眼泪自然是占据绝大部分,虽然也伴随着些许欢乐时光。(岳永逸《眼泪与欢笑:唐代教坊艺人的生活》,《民俗研究》2009年第3期)有研究注意到唐代宫人女乐往往需到年长色衰后方能出宫而重获自由,其主要出路不外乎“入道”或“归家”两种。(张咏春、郭威《武德内教坊与云韶府(院)——唐代内廷用乐管理机构的后宫类型》,《人民音乐》2016年第9期)高氏的两位姐姐在深宫孤寂离世,没有盼到出宫的曙光。即便有幸重获自由,也已是年光老大,嫁人谈何容易。
李氏苦于与三位女儿见面困难,哪怕是付出“变易姓氏,养于他族”的沉重代价,也绝不让小女儿步三位姐姐的后尘。三位姐姐在得知母亲把自己的妹妹改姓寄养,从而可以避开自己这种几无自由的命运时,她们的情感或许是欣慰中夹杂着羡慕。在母亲的汲汲努力下,终于有一位女儿逃离了“拘限宫禁”的命运。高氏被母亲养于高家(可能与李氏或其夫家有姻亲关系),虽然也与姐姐们一样接受了音乐技能的修习,但终究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墓志又载:
女工妓巧,样出于心,新眉愁嚬,鬓藂于顶。年十六从于韦,虽非正礼,尝主中馈,无威以制,律己服之。顷韦于荆南滞留,黔南从事,中间暂会,复又南行,相继五年,托以家事。韦之儿女互染重疾,躬亲药物,口尝手授,适其寒燠,皆遂痊平。□年冬中,韦方旋反,如﹝而﹞新知之乐,每联步以游。才经周岁有余,未报辛勤之节,正月中而遘疾,二月终而奄谢。母及第二兄同执药饵,名医术士,无所施力。有行一纪,而无其子,遽长往矣,可不哀哉!以其年三月廿五日窆于长安县义阳乡任贾村韦庄之西北。恐陵谷之变,故勒石以纪。铭曰:
柔而干,丽而聪,秋之翠,春之红。三星耀兮人去室,九原归兮花辞风。廿七兮寿太促,十二年兮欢遽终。神福善兮言何谬,奠无主兮事如空。帝城南兮,故园之西北;临穴一恸兮,路人为悲塞。
高氏在十六岁时嫁给京兆韦廙。高氏是韦廙丧妻后续娶之妾室,不过实质上已成为家庭女主人,地位也不算低。但高氏毕竟非正妻,所以墓志强调了“无威以制,律己服之”的略显尴尬的处境。高氏未获正妻地位,或是因其家世低微,不能与京兆韦氏对等的缘故。
韦廙其人,传世典籍未见其传记资料。试秘书省校书郎崔周冕于大和元年(827)撰《唐故乡贡进士京兆韦府君墓志铭并序》,(拓片见《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13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7页;录文见《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099-2100页)志主韦行素,“曾祖彬,皇蜀州青城县令;祖克勤,皇河南府汜水县令;考廙,皇河南府汜水县尉。公即廙之幼子”。韦行素父名廙,京兆人,与撰高氏墓志之京兆韦廙时代相同,或即同一人。据韦行素墓志,知行素母(廙妻)为高阳齐氏,卫尉少卿齐煚是行素之舅,行素娶齐煚长女。若韦行素父韦廙与为高氏撰志的韦廙是同一人的话,那么韦廙是在正妻齐氏去世后,再娶高氏。“韦之儿女互染重疾”,当即是齐氏所生,高氏悉心照料的韦廙之子应该就是韦行素。据墓志载,韦行素卒于大和元年(827),享年卅五,则其生于贞元九年(793),仅比继母高氏小两岁。
韦行素墓志,见《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13册第87页
不过,史籍中还有另一个韦廙。《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郧公房有韦廙,太原府参军,与韦行素父韦廙非同一人。其高祖太仆少卿韦爽与武后、中宗时为相之韦巨源为同辈,则其时代亦与撰墓志之韦廙相合。因此不能遽然排除此人是高氏之夫的可能性。
高氏嫁给韦廙后,因韦廙常年仕宦他乡,二人聚少离多(“顷韦于荆南滞留,黔南从事,中间暂会,复又南行,相继五年,托以家事”)。高氏除了高超的音乐素养外,还是一位贤内助。韦廙常年在外为官,前妻之儿女身染重病,多亏高氏悉心照料,才得以痊愈。
元和十年冬,韦廙回到家中,二人度过了幸福的时光(“韦方旋反,如﹝而﹞新知之乐,每联步以游”)。可惜好景不长,高氏很快重病,虽有母亲和二哥的悉心照顾,还是在生病月余后去世(“才经周岁有余,未报辛勤之节,正月中而遘疾,二月终而奄谢。母及第二兄同执药饵,名医术士,无所施力”)。韦廙感叹高氏“有行一纪,而无其子,遽长往矣,可不哀哉”。
还可以提及的是,浸润在乐舞文化的环境中,不少唐代女性的音乐素养颇高。墓志中还有士族女性善弹筝的记载。华阴县尉苗纾为其妻撰《唐故夫人荥阳郑氏墓铭并序》载“夫人讳溶……善弹筝鼓琴,凡声成音律,珠贯心手。又善文字,能属诗。或尝游他方,时遇清明节,寄诗二首,见酬四篇。其词美丽,怨而不失其正。虽皇甫氏之礼宗,不独称矣。宝历二年,自博陵,从不时调集,闲关岁月,恨未果归。由是怨望,郁愤生疾。以大和二年二月戊戌终于定州宁国里之私第,享年廿”。(拓片及录文见赵力光主编《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线装书局,2007年,第670-671页)苗纾笔下的妻子温婉贤惠,音乐诗文俱佳,可惜因为丈夫在外求官,长久分别而郁愤生疾,才二十岁就去世了。
郑溶墓志,见《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第670页
张冏为其叔母撰《唐故九华观书□师藏形记》载“仰维叔母……加以雅好书史,一览无遗。善妙秦筝,备该曲调。爰自疾亟,神用不亏”。(拓片见《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2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4页;录文见《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795页)张冏叔母秦筝技艺高超,即使其病重时弹奏也是“神用不亏”。
张冏叔母墓志,见《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2册第24页
唐代士族家庭女性的音乐才能,一方面作为取悦丈夫的工具,同时又成为繁琐、单调家庭事务之外的调剂,是其自娱的手段。除了在与夫君相聚的短暂时光中给对方带来听觉享受之外,筝这种乐器对这些家庭女性更多意味着是与丈夫分别的漫长岁月中消磨时光、排解孤寂、自我愉悦的情感寄托。
因为母亲的安排,高氏没有走上她三位姐姐那般极度缺乏自由的人生之路。那么,她到底是走出围城,去到了更自由的天地,还是从一个围城短暂逃离后又步入另一个围城?不同读者可能会有迥异的看法。也许高氏在刚嫁给韦廙因聚少离多时曾憧憬过三位姐姐那般的生活。不过我想,在经历了大姐、二姐在宫中孤独度日,尚未嫁人就去世的悲剧后,她的憧憬就变成了对姐姐们的怜惜。真实的感受只有高氏自己冷暖自知,或者她身处其中,也曾犹豫过、怀疑过,却又难以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