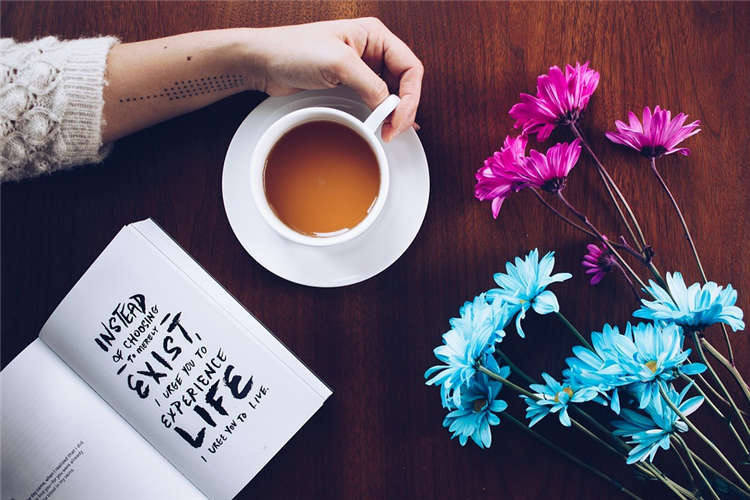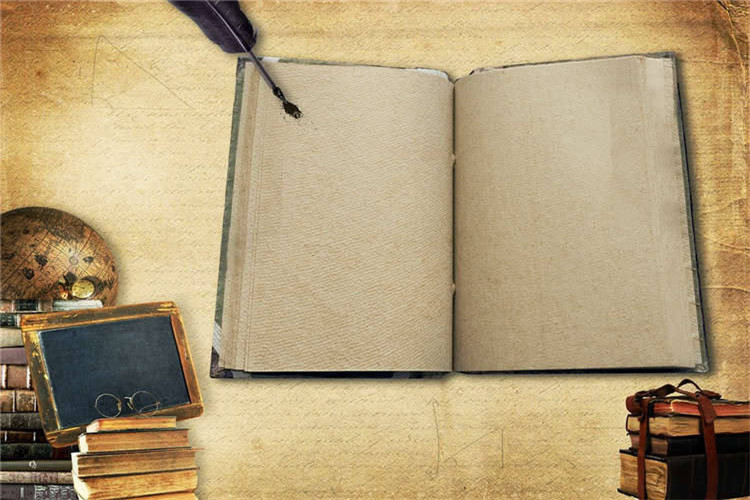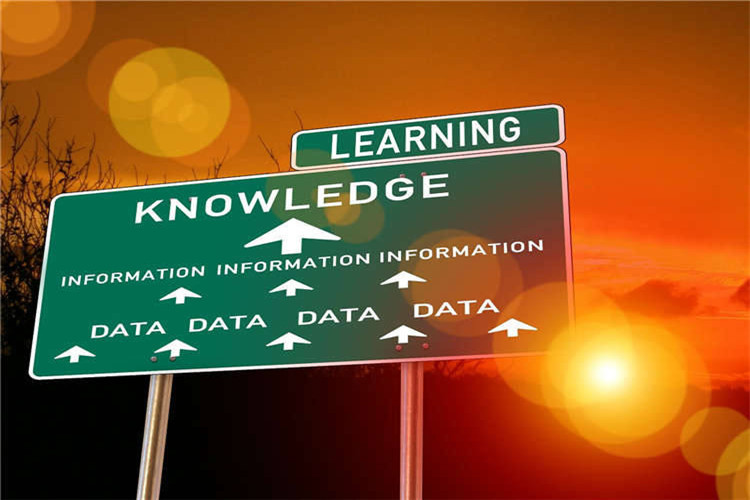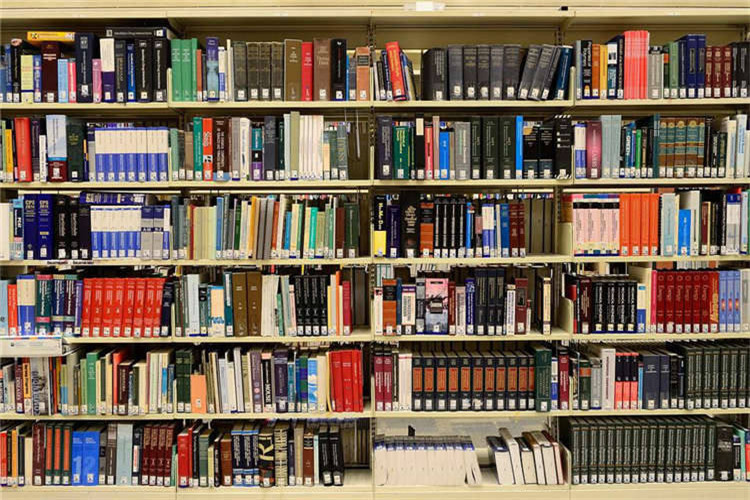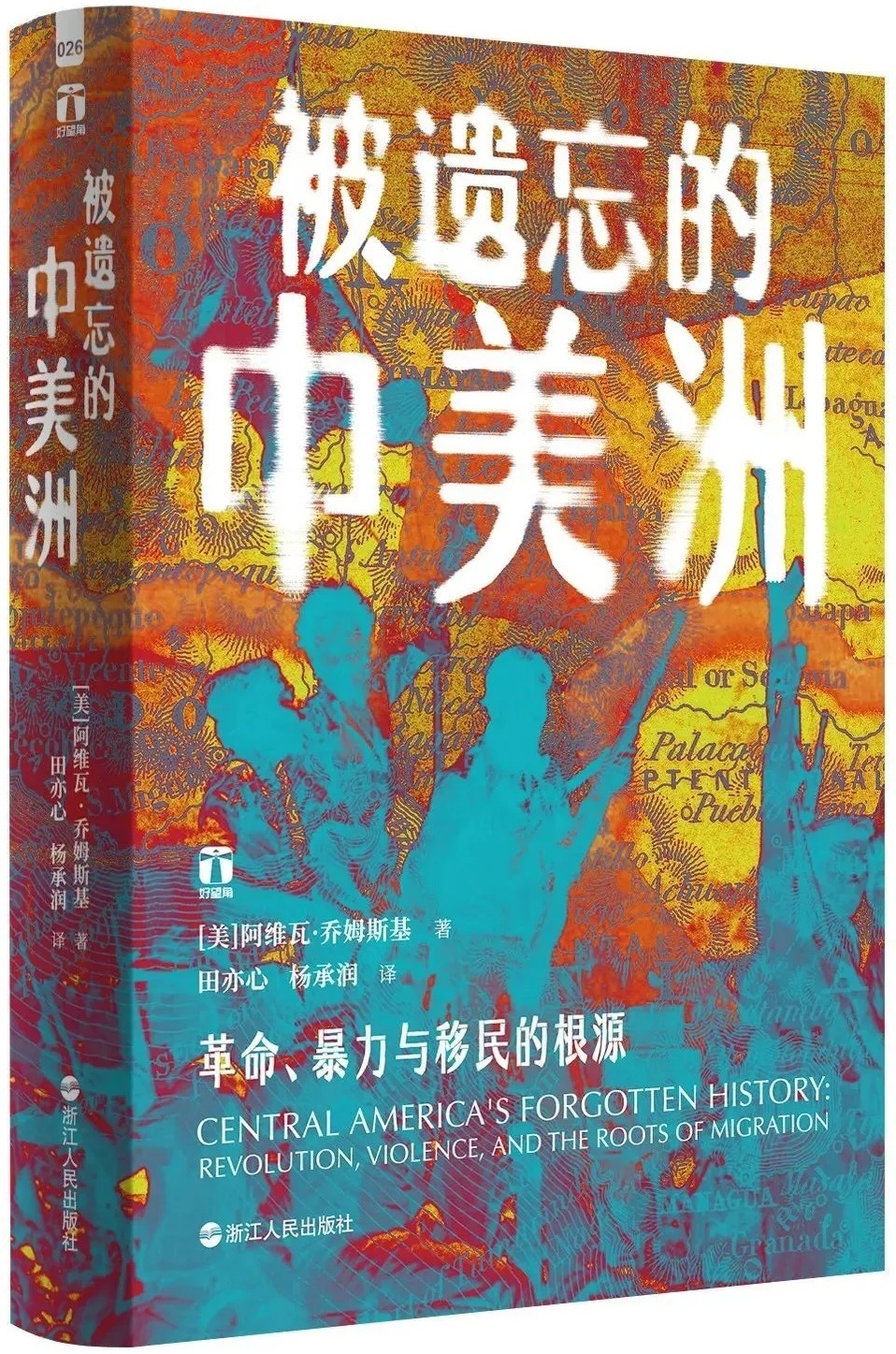
《被遗忘的中美洲:革命、暴力与移民的根源》,[美]阿维瓦·乔姆斯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好望角,2025年5月出版,404页,108.00元
关注到中美洲移民问题并非偶然。2019至2024年间在古巴三年的实地调研中,我的日常充斥着身边朋友的“出走”——有人在筹备,有人刚启程,有人已到达。五年间,超过十分之一的古巴人离开(古巴国家统计与信息局[ONEI]:《2024年人口统计指标》)。2025年春,我前往西班牙访学,这是中美洲移民除美国外的另一个重要落脚点。短短三个月,我的生活圈就被各类“流动者”所填满:古巴的舞者,墨西哥与尼加拉瓜的教授和同事,委内瑞拉的程序员与退役军人,洪都拉斯的司机,厄瓜多尔的厨师……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却在咖啡馆、图书馆、课堂和集会中相遇,构成了我理解“被迫迁移”的另一图景。
2025年初特朗普再任。紧接着6月12日,即宣布取消对古巴、海地、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移民的合法保护身份。这一政策的终结,意味着自2022年10月来,约五十三点二万依赖“临时保护身份”(TPS)或“人道主义假释”等政策居留美国的四国移民,将面临身份失效与被迫遣返的风险(“Trump Administration Tells Immigrants from Cuba, Haiti, Nicaragua and Venezuela They Have to Leave,” AP News, 13 June 2025)。他们不仅可能失去合法工作,也将陷入身份不确定、权利受损的处境。这一系列政策变动再次凸显了当前美国治理体系中的底层逻辑——移民问题被反复当作“危机”来处理,却鲜少被正视为历史责任的产物。
在这一背景下,阿维瓦·乔姆斯基(Aviva Chomsky)《被遗忘的中美洲:革命、暴力与移民的根源》的引进和出版,无疑为中国读者理解该现象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视角。阿维瓦提醒我们:中美洲移民的大规模出走并非危机的“结果”,而是权力系统下的“见证者”;它并非一场孤立的危机,而是美国数十年来地缘干预、新自由主义政策输出与国家失败政体共同作用下的被迫迁移。更重要的是,她揭示了“为何他们无法回去”的深层结构,将移民现象与国家、帝国、资本、毒品战争、殖民遗产等因素勾连起来,绘制出一幅远比“贫穷—移民—再贫穷”更复杂的暴力政治地图。阅读这本书,或能为中国读者提供一面镜子,映照出理解世界与自身处境的另一种可能。
《被遗忘的中美洲》其书
阿维瓦·乔姆斯基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移民问题专家”,而是一位立足历史学科、长期活跃于草根人权与移民正义运动的公共知识分子。她是美国塞勒姆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同时兼任拉美研究项目协调人。在其代表作《他们掠夺了我们的工作》(They Take Our Jobs!)与《全球劳动阶级的交织史》(Linked Labor Histories)中,阿维瓦坚定地站在“帝国的盲区”立场上,揭示结构性不平等如何被制度性掩盖和合法化。《被遗忘的中美洲》延续了这一书写传统:她不满足于“解释移民”,而是致力“追问责任”,将中美洲四国(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大规模移民潮还原为美国殖民逻辑与全球资本暴力的历史性产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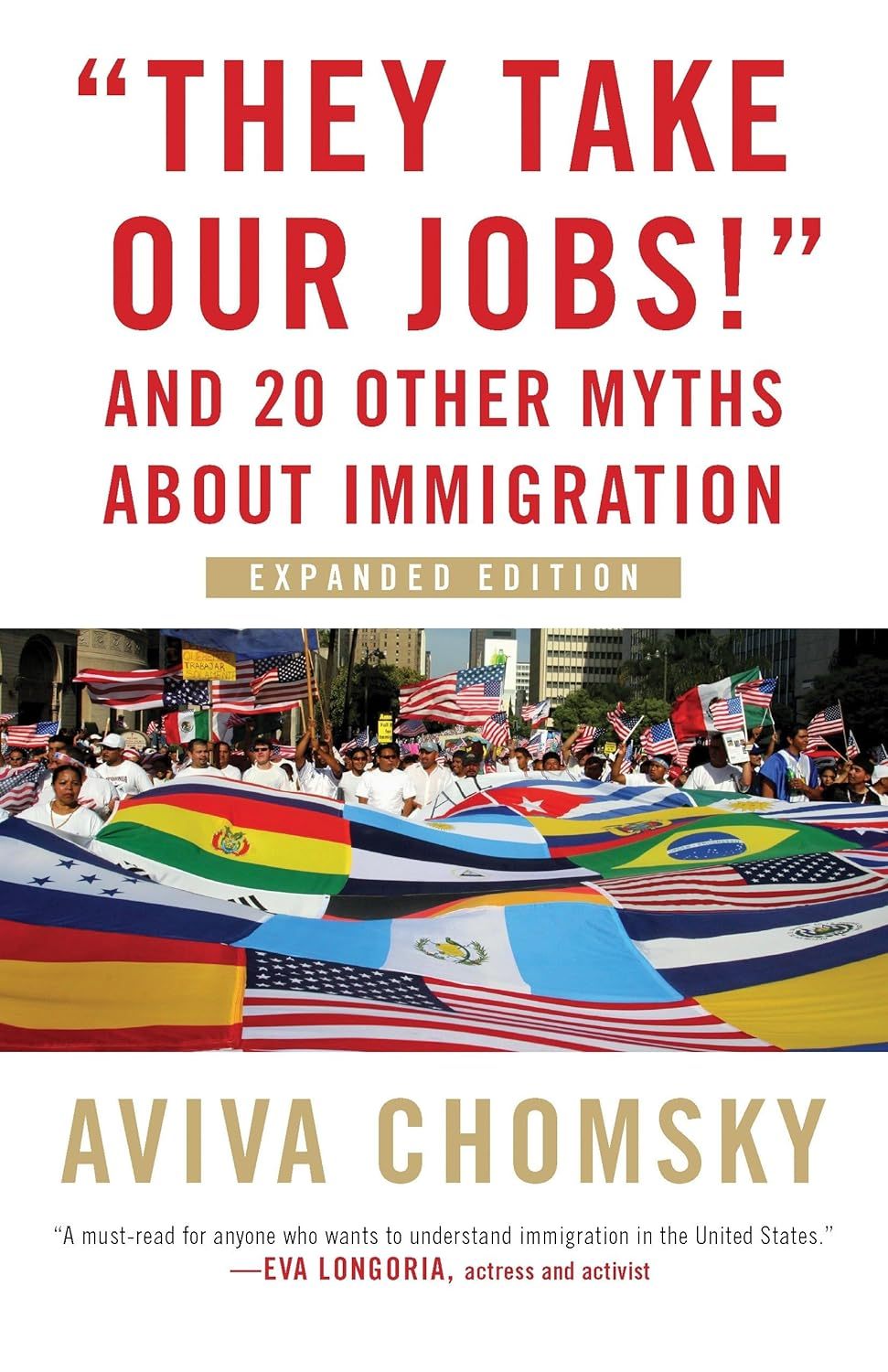
阿维瓦·乔姆斯基著《他们掠夺了我们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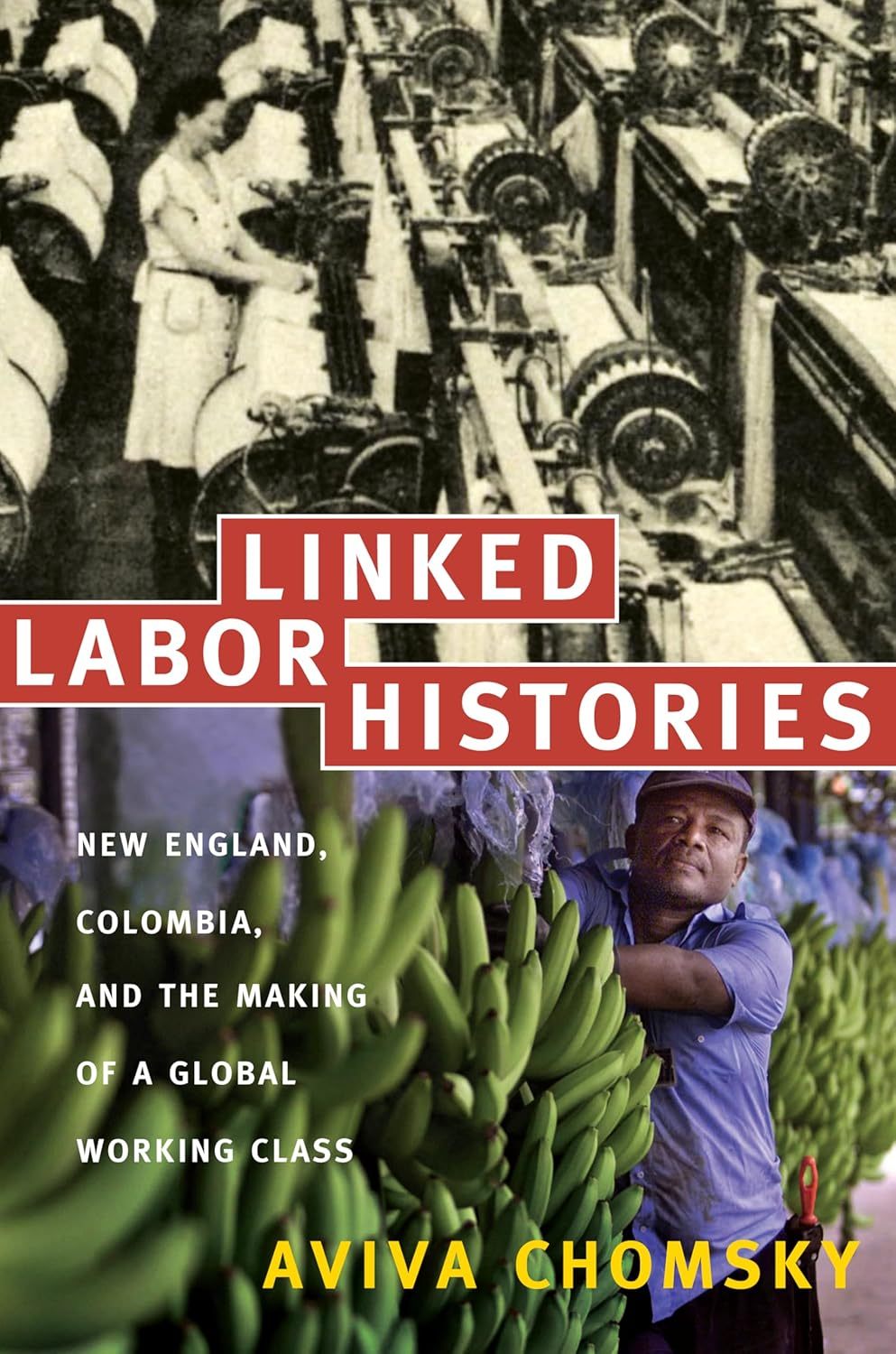
阿维瓦·乔姆斯基著《全球劳动阶级的交织史》
全书分为三部分。在第一部分,阿维瓦追溯“帝国的起源”,指出中美洲自西班牙殖民统治崩解后,迅速被美国纳入地缘扩张逻辑。从“香蕉共和国”的建立到军事干预常态化,主权不断被美国资本与安全战略蚕食。第二部分聚焦冷战期间的反共战争,细致揭示美国如何通过中情局、美洲学校等机构,为右翼政权提供军事训练与财政支持,以打压左翼工人、农民和宗教基层运动。阿维瓦强调,这并非简单的“内战”,而是一场在帝国保护伞下的“国家恐怖主义”。战争造成数十万民众流离失所,数百个村庄被毁,构成今日中美洲移民结构的制度性起点。第三部分则是全书对当代问题的回应。作者指出,冷战后的移民潮已不再依赖枪炮驱逐,而是通过新自由主义逻辑下的经济掠夺完成:结构调整计划迫使各国削减社会保障,解除农业补贴,引入自由贸易协议(如CAFTA),导致农业崩溃与失业激增,迫使农村人口“破产式”迁移。在此基础上,美国又以“反毒战争”名义加深中美洲治安危机,却未能强化法治体系,反而加剧了黑帮与军警勾连,使离开成为青年群体的唯一生路。
阿维瓦试图打破“移民危机源于今日”的叙事幻象。她强调,美国当前的边境困局并非偶发事件,而是深植于长期的外部干预与压迫结构之中(序言,第1-2页)。沿着这条历史线索,读者可以看到移民问题的根源如何层层积累:它最初源于殖民主义残余对中美洲国家主权的持续蚕食;随后是冷战期间国家暴力的制度化与合法化;接着是新自由主义改革对本土经济与社会结构的瓦解;最终,又在“反毒战争”的名义下演变为治安驱逐机制,进一步加剧了结构性的被迫迁移。更值得注意的是,阿维瓦尖锐指出,移民的标签与意义往往被媒体和政策话语所操控。主流叙事一方面将中美洲移民污名化为“非法入侵者”,并将原因简化为“腐败政府”“家庭解体”或“帮派暴力”等标签;另一方面,却系统性地隐去了美国在制造这些移民潮中的结构性角色。当美国政治领导人、媒体和教育体系共同选择“遗忘”时,对不平等根源的关注就被有组织地边缘化,移民问题随之被去政治化、去历史化,转化为治安管理和边境控制的问题(338页)。这种制度性的“选择性遗忘”不仅帮助美国逃避其应承担的道义和物质“债务”,也为强硬移民政策的合法化提供了话语基础(19-26页,338页)。
因此,在历史叙事、政治经济批判与制度追责的多重视角下,阿维瓦引导我们重新理解当下的移民问题,将其还原为帝国结构性暴力的延续与后果。正如她在书中所强调的:“要了解今天发生的事情,我们将挑战这种(被遮蔽的)叙事,强调我们交织在一起的共同的历史”(第8页)。

阿维瓦·乔姆斯基
“被迫迁移”的另类叙事
尽管《被遗忘的中美洲》的核心关注点是历史记忆的选择性遗忘与扭曲,研究范围集中在中美洲四国,但其提供的分析框架远超出其地域限定,为我们理解拉美及加勒比地区,乃至整个全球南方“被迫迁移”现象的结构性根源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
作为政策与学术语言中的核心术语,“被迫迁移”(forced migration)在联合国难民署、国际移民组织(IOM)等主导的政策话语中,常被用来指称因战争、自然灾害或政治暴力等“外部冲击”所导致的突发性人口流动,呈现为一种人道主义紧急状态。这类表述虽强调保护与援助,但在很大程度上将移民现象脱离了其深层的结构性成因。在学术研究中,“被迫迁移”常被理解为灾难或暴力造成的直接后果,较少追问其中所嵌套的制度性排斥、全球不平等与帝国治理机制。《被遗忘的中美洲》一书很大程度上提出了对“被迫迁移”概念的突破性修正。在阿维瓦的叙述中,中美洲的移民潮并非国家失控或偶发危机的自然产物,而是帝国治理逻辑下长期制度性暴力的延续。正如她所言,“体面就业的崩溃让贫困青年别无选择”(293页),中美洲移民不是逃离“无政府状态”,而是在逃离一个由美国主导,以安全、秩序与发展之名所合法实施的“有序暴力”体系。
若将这一逻辑延展至加勒比地区的古巴,我们不难发现类似的结构性被迫机制在其移民路径中也同样成立。自1959年革命以来,古巴移民始终置身于地缘政治与制度安排的交叉点。美国于1966年出台《古巴调整法》,赋予古巴移民特殊的合法化通道,使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拉美地区“最受欢迎”的移民群体。这一政策不仅服务于美方的冷战话语,也构成了一种“选择性庇护”的制度性安排。然而,随着冷战结束与两国关系反复变化,尤其是近年来美国持续冻结签证、收紧“人道主义假释”与“临时保护身份”等合法通道,原有的庇护逻辑正在崩塌。再加上近些年来古巴国内经济困境加剧、物资短缺、社会信任滑坡,促使越来越多古巴人不得不从尼加拉瓜出发,经洪都拉斯-危地马拉,以“走线”方式穿越中美洲抵达美墨边境。这条原本不存在于古巴移民想象中的路线,迅速成为一种在多重制度排斥下的生存策略——他们并非自由选择,而是别无选择。
在更广阔的全球南方语境中,因战争、气候危机、市场化改革或制度性排斥而被迫迁移的人口持续增加。然而,美国主流叙事却常将这些移民描绘为国家安全和经济秩序的“威胁”与“负担”,将自身塑造成全球危机中的“受害者”。在这一话语结构中,《被遗忘的中美洲》提供了一种具有批判力的反向叙事,通过对“被迫迁移”的三重重写,引导我们重新思考一个根本问题:为何世界的中心国家不断面对来自边缘的移民压力?
第一,阿维瓦有力地挑战了“自由选择”的迁移叙事,强调制度性约束在移民决策中的关键性作用。传统移民理论往往侧重于个体基于“发展落差”所进行的成本—收益计算,或国家政策对迁移路径的塑造。然而,她指出,拜登所称的中美洲“贫困、暴力与腐败”,并非自然状态,而是美国长期通过军事干预、产业重组和市场化改革所共同制造的结构性结果(序言,第1-2页)。因此,中美洲移民并非主动追逐“美国梦”,而是在制度性绝望中被迫谋求出路。例如,书中对萨尔瓦多帮派暴力的分析指出,这一问题本质上是美国“安全化治理”逻辑在中美洲的延伸:一种将结构性不平等简化为治安危机的治理模式。在这种逻辑下,MS-13等组织应运而生,成为青年在国家崩溃与市场破产夹击中的“替代性保护机制”(290-294页)。
第二,阿维瓦将“被迫迁移”嵌入帝国治理的历史脉络中进行剖析,梳理出三种“驱逐机制”:其一是军事驱逐。冷战时期,美国扶持中美洲右翼政权,镇压左翼工农组织与解放神学运动,制造大规模流亡潮,使移民沦为战争中的“剩余人口”;其二是经济驱逐。新自由主义改革削弱国家福利、摧毁本土农业,迫使大量民众流离失所,尤其《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CAFTA)的签署,构成“和平时期的制度性驱逐机制”;其三是安全驱逐。表面上,毒品战争与帮派暴力构成地方治安危机,实则根源于美国禁毒政策的外溢效应。最终为此买单的,是那些在本国失去立足空间、在美国又被污名化为“非法越境者”的中美洲青年。这三条种驱逐机制通过拉长历史时间线,再次揭示出一条贯穿殖民遗产、冷战干预与新自由主义治理的结构性迫迁路径。
第三,阿维瓦也对“苦难叙事”提出了质疑和批判。近年来,以个体情感为中心的移民故事日益成为一种为大众所接受的表述方式,然而,阿维瓦提醒我们,若缺乏结构分析,这类叙事很容易落入“自我选择”的逻辑陷阱。更可能掩盖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究竟是谁,剥夺了移民在原乡生存与安居的基本权利?例如当前很多媒体报道中,一位母亲携子徒步穿越边境的经历,常被塑造成“母爱与勇气”的象征。这种叙述虽富有感染力,却往往有意无意地回避了一个关键提问:她为何别无选择,只能踏上这条充满死亡风险的迁徙之路?
为警惕这种苦难经验被情绪化、商品化的伦理困境,阿维瓦延续了结构性民族志的写作传统,始终坚持将个体经验置于更宏大的制度结构之中加以理解。例如她笔下的移民个案——如逃离萨尔瓦多帮派暴力的青年何塞、因《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CAFTA)失去土地而北上的危地马拉农民家庭,以及被遣返回洪都拉斯后再次踏上迁徙之路的前“梦想生”马里奥——从不被孤立呈现,而始终嵌套在国家政策、历史进程与帝国秩序交织的背景中。通过这种结构性书写,阿维瓦试图将移民重新置回帝国治理与全球不平等的生产体系中,赋予移民叙事以更强的政治穿透力与伦理反思力。
介入式写作的边界与挑战
除了建设性地批判帝国干预与制度性暴力,《被遗忘的中美洲》的介入式写作策略也为移民研究带来了富有穿透力的结构性分析框架。然而,如所有介入式写作一样,它也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些方法与表达上的边界与挑战。以下问题的提出,希望与读者们共同展开更开放的思考与反思。
首先,我们或需重新思考对“单一帝国”视角的依赖,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会压缩了对区域国家内部复杂性的呈现。在书中,阿维瓦持续聚焦美利坚帝国的地缘政治干预与制度性排斥,将其定位为中美洲危机的核心制造者,这一立场无疑有助于揭示长期被遮蔽的结构性责任。然而,在强化帝国批判时,书中对中美洲国家自身的历史路径、政治精英与军政集团的合谋机制关注相对有限。例如,洪都拉斯的军政府、萨尔瓦多的右翼政党、危地马拉的军阀势力等,若读者稍有了解,便能知晓其虽有美国支持,但也有其内在的阶级逻辑与统治需求。此外,诸如族裔歧视、性别不平等与宗教保守主义等内部社会结构,也同样在塑造迁徙动因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这一点上,我们或需更多关注这些制度张力中的具体差异与能动回应。进一步探索本地政治如何与外部权力交织,构成多层次的压迫机制。
其次,在制度分析上,阿维瓦有力揭示了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的破坏性后果,但相较于她对冷战干预与军事暴力的历史追溯,对新自由主义作为制度逻辑的分析则稍显粗略。她明确指出自由贸易协定(如CAFTA)、结构调整政策与市场化改革对中美洲农业与公共服务体系的冲击,但在具体机制层面,如关税设计、补贴削减、国际金融组织在不同国家的嵌入路径等方面,讨论较为有限。在面对不同国家制度经验时,我们或可进一步区分这些改革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多样性与地方化路径。例如,尼加拉瓜与洪都拉斯在回应市场化压力时的政治选择、社会动员与抵抗形态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如何影响了移民结构与国家治理,也许值得更多展开。
第三个问题关乎写作风格本身。作为一位深度参与移民正义与历史记忆运动的学者,阿维瓦的写作姿态极具政治情感与道义力量,这种高度介入式的表达有效地推动了公共理解与政策介入。然而,这种风格也可能在材料选择上体现出某种立场偏向。例如,书中主要选取那些能支撑其批判立场的移民故事,较少呈现移民在制度缝隙中展现出的策略性选择、区域内的再迁移路径,甚至对“美国梦”仍抱有想象的群体声音。这种叙述方式可能无意遮蔽了移民主体的多元能动性。
更为重要的是,这本书向读者和研究者提出了一个须严肃面对的问题:在移民研究与政策建构中,我们是否真正追问了结构性责任的来源?阿维瓦提出了一个深刻的伦理自省:“如果我们(美国人)愿意或能够真正意识到我们所拥有的权力,认识到我们国家对遥远的、无形的、和(被我们)遗忘的人民所产生的影响,那么我们就是唯一能够改变这一切的人”(231页)。这一返身自问的写作姿态下,阿维瓦或为我们打开了一条重塑学术责任与知识伦理的路径:面对历史的沉默,记录只是起点,更要关注的是这其中谁拥有发声的权利,谁被纳入叙述,谁又持续被排除在外。
延续这一追问,《被遗忘的中美洲》也为读者留下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当我们强调“反遗忘”时,是否真正倾听了那些在场者的声音?阅读本书后我们不难发现,尽管书名强调“被遗忘”,但书中来自中美洲本地的知识者、社运参与者与普通民众的声音仍显稀少。阿维瓦主要依赖美国档案、英文媒体与边境经验来构建文本,西班牙语文献使用仍显不足。这一叙述方式会不会又在无意中强化了“由中心讲述边缘”的知识路径?一本旨在抵抗遗忘的书写,是否也应更加积极地为那些被边缘化的声音创造表达的空间?
结语:记住“被遗忘的中美洲”
总体而言,《被遗忘的中美洲》不仅是一部富有政治洞察力的作品,也为我们如何讲述和理解移民问题提供了新的可能。在肯定其结构性批判的深度与勇气的同时,它也邀请我们思考:在继续展开对迁移、帝国与不平等的讨论时,是否还存在一些未被充分触及的维度——比如地方的复杂性、制度的细节性、声音的多样性等问题。这些探索的空间,不是某种“更好”的替代,而是一种彼此激发、共同进退的研究可能性。
对我而言,这样的提醒也有着切身的现实感。正如开篇所述,2025年初,我在西班牙遇到的一些中美洲移民朋友们,思念亲人,却难以想象重返祖国生活与工作的可能。他们既有因变动被迫离乡的人,也有在困境中奋力谋生的人,还有寄望于新生活的“追梦者”,以及被困于全球发展秩序与安全话语交织之下的普通人。他们“用脚投票”的决定,远不是单纯的自由选择,而更多是对本国政治失序与社会希望逐渐消退的回应。正是在与他们朴实的交流中,我切实感受到了“结构性暴力”的具体面孔。
远方不远。中美洲的苦难,不仅是美洲政治共同体中被有意遗忘的一部分,也是全球南方“被迫迁移”现象最具代表性的缩影。《被遗忘的中美洲》不仅是对特定区域记忆的重构,更是一种方法论上的提醒:若要理解当下的流动、伤痕与反抗,我们必须跳出民族国家的叙事框架,回到资本、帝国与权力交织的历史现场。因此,这本书的意义远不止于理解中美洲。它也为中国读者,尤其是那些日益走向国际现场的青年学者与叙事者,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批判镜像和认知入口。在这个愈发不确定的世界中,它提醒我们:历史从未远去,暴力从未终止,而正义的追问,必须从重新“记得”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