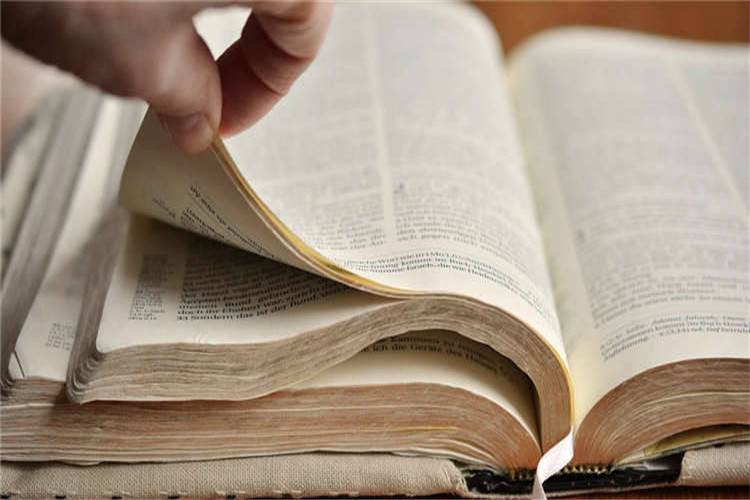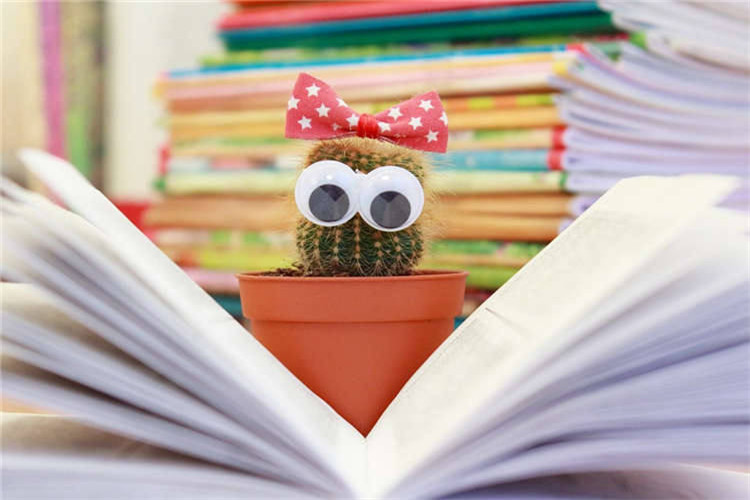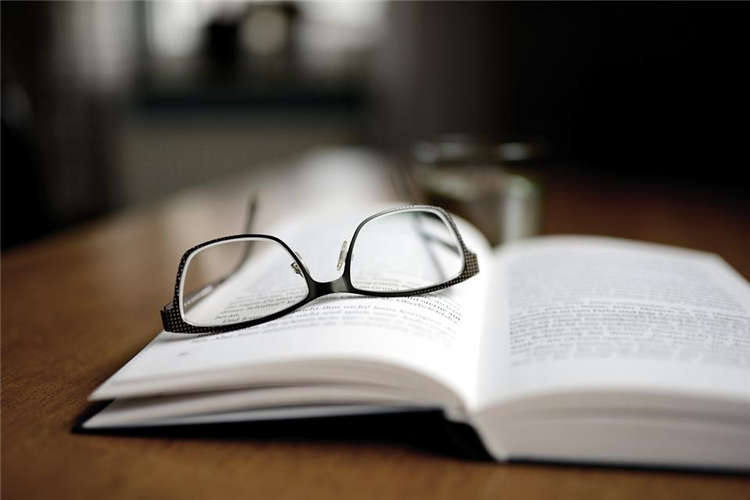8月19日,由刘家成执导,王贺编剧,杨幂、欧豪主演的年代剧《生万物》在央八酷云实时关注度最高破4%,创央八今年最高。同日,该剧在爱奇艺站内热度值达10762,升至爱奇艺史上第二。8月20日,《生万物》云合单日有效播放破亿,为今年首部单日有效播放破亿剧集。
接到《生万物》这部剧时,刘家成导演正处于转型期。
有很长一段时间他的作品以京味剧为主,《情满九道湾》《芝麻胡同》《正阳门下小女人》《情满四合院》……提起这些热播剧,我们脑海中就会情不自禁响起儿化音。“当时也是好的剧本集中爆发期,后来发现没有明显能够超越之前的剧本。我希望我的作品一步一步能往上走,如果拍来拍去再重复,或者还不如之前,这不是我想做的。所以,在这个转型期,我就希望能够放一放,能够拍一些其他题材。”于是刘家成刻意去拍了一些差异比较大的类型。正在做军旅剧《海天雄鹰》后期时,《生万物》找来了。“一听题材就比较吸引我,它跟我之前拍的剧差别很大。”
刘家成一直认为,所谓的题材是没有壁垒的,“能拍好现代剧,就一定能拍好农村剧,也一定能拍好历史剧。这里边的创作是相通的。”
导演刘家成在《生万物》拍摄现场。
《生万物》根据作家赵德发的长篇小说《缱绻与决绝》改编,以鲁南农村土地变迁为背景,讲述了以宁绣绣、封大脚、费左氏为代表的宁、封、费三个家族、两代人的生活史。原著小说曾获第三届人民文学奖。
《生万物》在爱奇艺站内热度值破万海报
刘家成的作品,收视创佳绩并不令人意外,有意思的是,这次“农村题材年代剧”居然吸引了不少年轻观众追看。是什么吸引了被短视频包围的年轻人去追一部关于土地与人,离大家日常生活遥远的长剧?
“首先,农村的这种真实感,你得让他们感受到。”刘家成导演说,观众见多了绿幕、棚景,要让观众真切感受到与他们生活不同的环境、状态,“要让观众看到那种庄稼,那种麦浪,那种山峰,还有那种大雪”。这种与众不同的新颖,才能够刺激观众,大家才觉得新鲜。
“最主要的是,让人物的命运来打动他们。人物在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困难,跟命运的抗争,这种不服输的精神,还有生存的智慧,这些都会深深打动他们,与自己连接在一块儿。我们不管历史剧、年代剧,都对现实要有关照。”
在这次现实主义题材创作中,刘家成导演还少见地尝试了浪漫主义表现手法。其实原著中人物众多,时间跨度大,命运也是极为坎坷冷峻的,剧本创作依据影视创作规律,做了大刀阔斧的改编,并在写实的现实主义的基础上,糅进了一种浪漫主义色彩,这不仅是创作者对剧中人物的温柔关照,也是对观众的一种心理安慰。而这种创新的表达方式,也吸引了更多圈层的观众,包括一些年轻的观众。
杨幂 饰 宁绣绣
无论开播前还是开播后,《生万物》的主演杨幂都是舆论暴风眼。和刘家成导演一样,杨幂也正寻求转型。上次演个反派,她遭遇全网群嘲。这次她能演好一个村姑吗?
谈到与杨幂的首次合作,刘家成透露,在开机前三四个月,杨幂就主动去农村体验生活,学干农活,后来拍一人挑两桶水她都能自己来,“她这么认真,这么刻苦,这么能吃苦,也得到了大家的信任和尊重。”同剧的秦海璐也是第一次和杨幂合作,她近日在直播中也大赞杨幂的认真、聪明,剧本台词能做到一个字不差,称她摸到演员的门道了。
对于观众吐槽绣绣出嫁前太白净,不像农妇,刘家成回应说,“她一开始就不是农妇,是一个家里有700亩地的大小姐,那种富贵,那种知性,在她身上得有。”随着剧情的发展,绣绣嫁入封家前后的妆造形成鲜明对比。导演也直言,拍到后期,有些客串的演员到现场拍了半天,都没在一众演员之中把杨幂认出来。“我们的一切,都得符合这个人物的成长脉络。”
《生万物》是每天播三集,对于这样的排播,开播前有人不怀好意暗示说这是不被看好、想赶快送走它,而开播后观众却吐槽“一天三集不够看”,虽然剧情信息量大,但意犹未尽。这种“长剧快播”的方式,刘家成觉得是好事,给观众的追剧爽感不一样。而不管怎么播,更重要的还是剧集本身的品质,无论长剧、短剧,都必须得符合人物逻辑,符合故事的逻辑。拍摄让观众欣赏,有回味,有思考的作品,是他擅长也是一贯秉持的创作理念。
“我相信,任何一个剧,都有它的天时地利人和。谁也不敢说,我这个剧就得爆。没有那种奢望。我想的是这个剧得是一个品质过得去的剧,得是一个让观众认可的剧。现在这个结果,可以说也在我们预料之中,天道酬勤。”刘家成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时说。
导演刘家成
【对话】
谈改编:要抓住原著精神的核,不能丢
澎湃新闻:聊聊拍摄《生万物》的契机?剧本最吸引您的地方是?
刘家成:首先,它是农村剧,这种题材在市场上很稀缺,特别是农村年代剧里,能够写得这么深刻的少之又少。
它写的是农民,还有中国的农耕文明,人跟土地的关系,以土地为核心,写的是人。它不是立了一个宏大的主题,让大家看到很空泛的东西,它写的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具象,个性鲜明,完全能够改成一部吸引观众的作品,我当时就觉得要做。
老实说,我们当时的剧本,尤其是前10集写得非常精彩,10集之后偏弱,后来我们就重新捋,重点提升之后的这些情节,进行了一些调整。我觉得,冲着前十集打下的这个基础,它就弱不了。
澎湃新闻:原著小说《缱绻与决绝》出版于上世纪90年代,从改编的角度来说,最大的难度是什么?
刘家成:看完剧本,我就去看了原著小说。原著也有一些东西,在我们剧本当中体现得不足,我觉得要进行一些展现和扩充;有些东西在剧本当中展现不合适,就去掉了,比如特别灰暗的、消极的。
比如男主人公,原来剧本当中,大脚不是现在这样个性鲜明的人物,他身上没有太多的光彩,他对绣绣也是嫌弃的,是被迫地接受她,而绣绣也是被命运驱使嫁给了大脚,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没有现在我们看到的那种真情真爱。
绣绣和大脚
我们把人物提亮的原因是,你得考虑到电视观众。作为一个男主,他不光得让绣绣爱,还得让观众也爱。虽然他没名没利什么都没有,但他有的是真诚,有的是担当。
后来我们在剧本中,设计他到马子窝救绣绣,围城的时候也舍身相救。土匪问他,你能活着回去吗?他说,我就没想过,只要我媳妇活着就行。当没有人要绣绣的时候,大脚说俺要,然后用八抬大轿敞敞亮亮地围着全村转三圈,把她娶回家。这种磊落的爷们儿,谁不爱?有不少观众发弹幕说,嫁人就嫁大脚。这就再次验证,我们这个改编的方向是对的。
在原著当中还有另一对,苏苏和郭贵耀(即郭龟腰),他俩就是一种性的吸引。从郭贵耀来说,就是玩弄女性;从苏苏来说,就是一种生理需求。现在我们把这条线改得合情又合理。虽然当时有封建压制,我们不回避这种丑恶,但是在关键的节点上,我们还是要保留一些情义和情理,不能让大家过得过于撕裂,包括人物的命运,但不是有意地去美化。
你要抓住原著的精神的核,这个不能丢。第一,是唤起了我们中国人,农民跟土地的这种关系。大家离不开土地,对土地的那种崇拜和依赖,唤起我们现代人深植内心的那种土地情。
另外一个关键是,让我们看到这些主人公面对生活的打击,那种敢于跟命运抗争的乐观精神,那种一定要把苦日子过成花的信念,它也会对我们当下有一种影响,传递这种生命力,传递这种希望和温暖,让我们有一种通过险阻,能够继续面对任何困难,有勇气生活下去的力量。这都是我们要表达的。这个魂抓住了。
把苦日子过出花,是《生万物》坚持的内核。
后来,我们把很多想法跟原著作者赵德发老师沟通,他非常支持,也相信我们会做得很好。他也理解,电视剧作为一种影像的表达,跟书面的东西一定不一样。小说当中写的一句话,观众可以展开任何的想象,但是变成影视剧就具象了,你的选择就要考虑大众化,要更多的观众能接受。
此外,原著的跨度太长,小说当中写了四代人,这个也是拍影视剧最忌讳的,就是观众不可能移情别恋好几代人。我跟很多编剧聊剧本创作,我说最多写两代人,就到极致了。因为这个创作理念,我们把剧本压缩到前20年的故事,以绣绣和大脚为主线。从1926年到1947年,这20年的故事也最精彩。可喜的是,这也得到了原著作者的支持和理解。
谈演员:像朋友,又像战友,谁都不掉链子
澎湃新闻:绣绣是全剧立住的关键,她最突出的个性是什么?
刘家成:在面对命运的打击下,她身上有一种不认命、不服输的精神。虽然嫁给大脚是赌气,但她从那么优渥的环境里,到这个相对贫穷的家庭里,这个转化过程,她就凭着一种坚强和智慧在成长。与此同时,她又是一个知识女性,上过私塾,毛笔字写得也很好。她不光是坚强勇敢,还有一股倔强,知性和智慧。这种智慧,延续到她整个的生命线。
澎湃新闻:说到绣绣一开始和家人赌气,马子围城那场戏,等于向全村人宣告,她当初是清白之身。当时宁学祥他们几个人得知后的表情也很精彩。这个前后呼应的设计是怎么构想的?
刘家成:这也是我们从原著做了一个提升。这件事在当时的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原著小说是几乎到结局的部分,她才跟大脚他们说,没被马子坏了。我们原本的剧本,这个情节也是放到比较晚的节点,但我们觉得,这块到那个节点已经失去了一个作用,所以我在中间一直在找点,怎么把谜团讲给大家听。这个心结,怎么解,是一个重点。
最后我们的处理是,绣绣先跟大脚解开这个心结,这两个人之间有了这种理解之后,再利用马子围城,马子自己喊出来——你是唯一的一个从我们手里逃出来的——全村人瞬间就知道了。这样的设计,我们觉得也很有意思。
澎湃新闻:聊聊与杨幂首次合作的感受?
刘家成:我跟杨幂第一次聊完剧本,她就给我留下一个特别好的印象。她说导演,我得去体验生活,我说你需要剧组做什么,她说需要剧组帮忙联系好那个地儿,她自己去。然后她就真的到我们拍戏的山东莒南找了一个农家的院子,她在那儿体验了二十多天。
那会儿离开机还有三四个月,我们刚确定演员。她当中还给我发微信,说导演你还有什么要求不,我现在已经学会烧火做饭了。我说,你再学学劈柴担水,干点农活。这段时间的锻炼,对她有很大的帮助。有一场戏,她在井台边一人挑了两担水,虽然有大脚在边上,但是主要是她挑起来的。如果没有当时那种历练,那种她从小姐转换成农家妇女的劲儿会差很多。
这一点挺打动我的。我觉得,她走到今天,能够这么认真,这么刻苦,这么能吃苦,也得到了大家一种信任和尊重。
她对剧本也很认真,我们经常在剧本当中沟通,大家拍起戏来,彼此建立了信任。我永远忘不了,就是我们拍了大概一周,拍到绣绣跑出来,家里的仆人追她,她就大骂他。骂完她说,那一种发泄,她觉得演得很顺畅。那天她还给我发了一个微信说,导演,今天我感到我无比的自信,我也无比的痛快,戏演下来以后,我似乎能把握住这个人了,我能找准她了。
前几天晚上,杨幂还给我发语音说,导演,我也在看,我把自己感动哭了。她说,导演,我感谢您那场戏让我重拍了一条,多亏用了。
那场戏是土匪围过来,她决定把自己牺牲的时候,她哭得特别好,很委屈,所有人都觉得好。我喊了一句停,我说再拍一条,不这么哭,不要那么多的泪,因为你面对的不是亲人,你跟谁委屈,现在是马子,是要你命的土匪,所以你更多的是恨,你的眼泪也是恨。
绣绣与马子谈判
我们这种碰撞、合作、沟通,彼此是建立在一种完全信任的基础上。因为导演就是第一个观众,我永远跟演员讲,我是最挑剔的观众,你们好就是好,你们不好就是不好,要是我不挑你,观众会挑你。
我跟我们的演员,大家特别像交心的朋友,又像战友。近半年的时间内,我们拍了两个场景,战严寒斗酷暑,我们最后全剧杀青时拍的东北部分,零下三十度,可是之前在山东拍摄,气温是零上四十多度,在没有一个遮挡的地方,你想田地哪有遮挡,大家都在那儿坚持。大家心特别齐,我也一定要拍好这个戏,不能辜负这么多人的努力。
关于剧本,我们也是反复打磨修改,最后发现还有一些问题不满意,要是一般剧组已经足矣,但我们又把编剧调到组里,拍摄之余,我跟编剧还在沟通,对哪场戏还有新想法,如果不好就推翻重写。一直坚持到最后都是这种创作状态。
演员之间也是比较卷,我们卷的是创作上,卷的是表演上,大家都不甘落后,就是你的戏我得能接住,我们需要百花齐放,不需要一枝独秀。在这当中,氛围就带起来了。不管是大红、永健,还是现在大家反响非常好的“大脚娘”迟蓬、“绣绣娘”沈丹萍,这些人谁都不掉链子,一到现场,你一听词,他们都是带着充足的准备来的。
我相信,任何一个剧,都有它的天时地利人和。谁也不敢说,我这个剧就得爆。没有那种奢望。我想的是这个剧得是一个品质过得去的剧,得是一个让观众认可的剧。现在这个结果,可以说也在我们预料之中,天道酬勤。
澎湃新闻:剧中有些群像戏也很有意思,尤其是老戏骨们的交锋。在拍摄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
刘家成:特别多。比如倪大红第一天跟秦海璐的对手戏。原来剧本里,他们俩是面对面的说词,商量让苏苏代替姐姐嫁到费家。但是到了现场,我说这个调度我想好了,你们俩就背对背演。
我大概这么一说,他们领略得特快。秦海璐直接走过去,奔到轿子边,两人就形成了背对背,大红不回身,他就能够预知准确的时间节点——就在海璐一伸手,刚要撩轿帘的时候,他的话就到那儿了。他说:费家嫂子,你想好了这人你要不要,你再撩轿帘。海璐一听,她的手“啪”就停在这儿了——她懂了这个弦外之音。这么一小段戏,通过一个没有脸对脸的表演,张力会更足。这种镜头的调度和表达,让人觉得,她不光是一个霸气的人,这个女人还聪明,所有的事情无需说透。
倪大红与秦海璐的对手戏
还有大红跟永健,都是喜欢有戏剧效果的人,所以我们会给他们一些规定情景,这场戏要达到什么效果,调度是什么样的,剩下的,他们中间会塞很多非常准确的小零碎,可能一两句话就恰到好处。因为我跟这两位都合作了很多次,彼此太有了解了,也太默契了,大家在戏上是知己,这种戏磨合下来,就很享受。
谈创作:坚持你认为对的事
澎湃新闻:剧中有不少名场面,您最喜欢的三场戏是?
刘家成:如果说喜欢的戏,可能我场场都喜欢,因为都出自于自己之手。要说印象深刻,像昨天刚播完的土匪攻打土围子的戏,就是一场,因为它太艰难了,四十多度,拍了七天。演员最痛苦,镜头角度多,我拍城上的人,远处要带着土匪,我拍土匪的时候,镜头要带着城上的演员,谁都跑不了,主演跟群众演员一样,一候场就是一天。
我们又得把那种气势,那种真实感拍出来。这里边不光是一场武打,如果我们只要攻城就很简单,但里边还有每个人的人物性格、人物命运,各种人物关系,人性的纠结,每个人身上都有戏。群像戏里边每个人都找准了以后,会非常精彩。
我们还有一些大场面,虽然费劲,但有一种成就感,比如最后我们的组能够拉到东北再拍。很少有剧这样拍,4月份开机,拍到8月份停机,到11月份大家重新建组,就为了到东北拍10天的雪戏。所以也是特别感谢我们的总制片人戴莹,她非常支持创作,还想办法跟演员沟通留时间去东北补拍。
现在反过头来看,当初的决定无比正确,所以我们才会拍出那种大雪纷飞,山顶守护着天牛庙村的天牛,才会看到大家说的白雪皑皑当中的一抹红。
绣绣倒在雪地里
第三场戏,我觉得是出殡那场戏。快拍到那场戏时,我们听到当地人讲他们的民俗,那个年代不准女人小孩送葬到墓地。我们决定要符合民俗民风,就临时改戏,没让宁学祥去送。我们找了一个城门,让所有妇女小孩都留下,但是恰恰男人们去了以后,绣绣突然追上去跟娘告别,更显得悲壮,这个女人已经不顾一切,冲破所有的约束要跟娘见一面。所以我们才出现了这样一场戏,让她有一种幻觉,与刚逝去的娘相见。这也是我过往现实主义创作当中很少的一种浪漫的表达。
一开始,就着出殡那场戏的环境就把这场戏拍了,回过头来一看,怎么都不满意。后来我就跟演员商量,能不能春暖花开,两个月以后有绿色了,我们再把这场戏补拍一下。我就想要绣绣的服装不变,还是穿的孝袍,但周边的季节变了,有草有树都是绿色。有一种寓意,有一种温暖,春天是希望,是万物生的季节,所以她才跟娘有这么一段温情的戏,给人物的心理,包括观众的心理一种安慰。演员们毫无怨言,春天后再次重拍,没有留下遗憾。
绣绣在幻觉中与娘告别。
像这种有幻觉的戏还有很多,这也可以说是在写实的现实主义的基础上,糅进了一种浪漫主义色彩。别把自己的现实给捆绑住手脚,偶尔浪漫一下,偶尔思想放飞一下。我觉得,这种创新的表达方式,也吸引了更多圈层的观众,包括一些年轻的观众。
澎湃新闻:怎么看待剧中女性角色面临的挣扎与成长?
刘家成:还是要根据每个人物的性格来确定,有些也很残酷。比如费左氏,天天待在那个祠堂。我们故意把那个祠堂的光线压得昏暗一些,她经常跪在里面,那就是一种象征,她被困在这种封建的牢笼里,突出了三从四德对女性的那种限制。她作为一个牺牲品,包括她对苏苏的控制也是,把自己害了,再害别人。她把自己陷在其中,会把别人也拉进来,因为她认为她是对的。
比如绣绣娘,她对佃农,对家里的佣人都非常善良,对自己的女儿,对大脚,让人觉得是一个慈母。
还有大脚娘,虽然贫穷,但是她会给所有人都带来真实和温暖。这样的婆婆也是稀缺的,对儿媳妇百依百顺,永远站在儿媳妇这边。婆媳剧斗来斗去太多了,我们这儿公公跟儿媳妇斗,也是一种颠覆,然后碰到一个好婆婆,处处维护绣绣。她对女人的那种天然的尊重,你能从这个女人身上感受到温暖、善良、朴实。
我在现场经常夸“大脚娘”迟蓬。她的表演有时候跟别人不太一样,在表演的节奏上,封二他们是快,她是稳,她有一些晚一步的反应。大家有点分歧的时候,我就特意找到她说,你要坚持自己的表演风格,我很认可,你的表演是对的,我在机房剪辑的时候这个表演节奏感很舒服,然后给她奠定了信心。迟蓬老师的表演也很朴实,现在果然不出所料,得到观众的普遍认可。
迟蓬 饰 大脚娘
还有蓝盈莹演的银子,那是正儿八经的佃农,连起码的生存都维持不了。面对父母,面对有病的娘,面对兄弟姐妹,她怎么办?最后,她只能把自己给豁出去了。她那种泪往肚子里咽,那种委屈,还带着一种倔强。她本来也是不认命的,开篇就设计她跟老地就闹别扭打架,互相呸。那么倔强的女人,在现实面前不得不低头。蓝盈莹把那种对命运的无奈,不是谁想挣扎就能挣扎出来,表现得淋漓尽致。
每个人身上,你都能看到人性,看到善恶,有的是无奈,没有办法。这都是一个个立体的人。
谈观众:让人物的命运来打动他们
澎湃新闻:《生万物》在台网的数据都很好,这类农村题材的剧集要如何吸引年轻观众?
刘家成:首先,农村的这种真实感,你得让他们感受到。要让观众感受到与他们生活不同的环境、状态,恰恰是这种不同,这种新颖,才能够刺激他们,大家才觉得新鲜。那种绿布、棚景他们见多了,所以要做实打实的,要让观众看到那种庄稼,那种麦浪,那种山峰,还有那种大雪,让观众被自然环境深深吸引。
最主要的是,让人物的命运来打动他们。人物在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困难,跟命运的抗争,这种不服输的精神,还有生存的智慧,这些都会深深打动他们,与自己连接在一块儿。我们不管历史剧、年代剧,都对现实要有关照。
《生万物》很质朴,我们最终要回归到,深扎到泥土里的那种真情实感,回归到艺术最本真的力量。小人物的真情实感,他们的挣扎与成长,这些永远是观众喜欢看的。
澎湃新闻:《生万物》每天三集的播放方式,也是适应时下观影节奏的选择吗?
刘家成:主要是央视很早就有抗战题材的排播计划。确定每天播三集以后,当时网络上很多种声音说,不需要播那么快那么多,但我觉得这恰恰是件好事。大家现在观影习惯都不一样,尤其是年轻人不可能再走到电视机前准点准时。我就看你这三集,可能攒在一块看,也有可能下班回来晚上12点才看。你要一下给大家看三集,那种爽感一定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就吊着观众,吊3天5天,大家可能就没有耐心再补看了。恰恰三集给的信息量也大,这种长剧快播是好事。
果然,我们的戏刚播没多久,广电总局的新规就出来了,以后不限制几集播放,电视台的排播没准以后都这样了,我们在无形当中成为了第一部。
一天播一集,要是剧不好看,本来撑40天,可能第四天就没了,是不是?但像之前有几个爆的剧,《我的阿勒泰》那种,该爆还得爆,还是取决于剧的品质。
澎湃新闻:您未来会考虑拍一些短剧吗?比如《我的阿勒泰》这种体量的剧集。
刘家成:我不反对拍。有很多短剧只要爽感不要逻辑,这个肯定不行,在我们这都过不去。我们拍戏,必须得符合人物逻辑,符合故事的逻辑,要过了我自己这道关。即使长度只有8集、10集,只要逻辑都对,在各方面都能表现,我们为什么不拍?
将来有可能播放的剧越来越短了,也有可能是集数缩短。我老跟他们说,将来像《红楼梦》那种小说,120个章回,不就是120集吗?那一集就10分钟一个章回,什么都有,文化信息量极大,也是有可能的。
有些只有爽感的微短剧、短视频,它的存在是有道理的,但它跟电视剧是两股道上的车,互相不干预,打发观众的碎片化时间。短视频刷完了,你翻过头来想,刚才我看的是什么,可能当天就忘了。但一部长剧,它能让你在欣赏的同时,让你回味,让你反思,让你对过去、对当下有思考,这一点只有长剧能完成。所以我们的重点应该还是做这些剧,这是我们的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