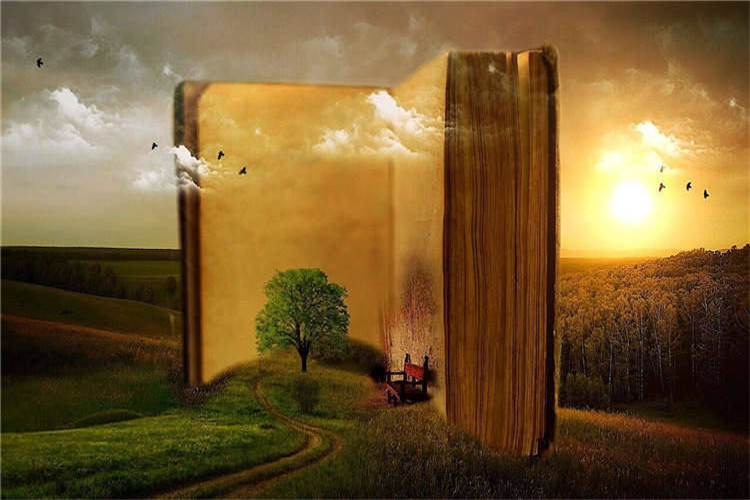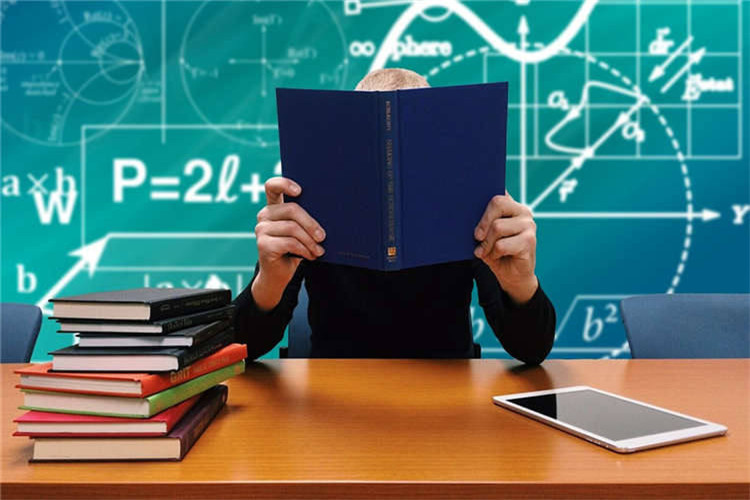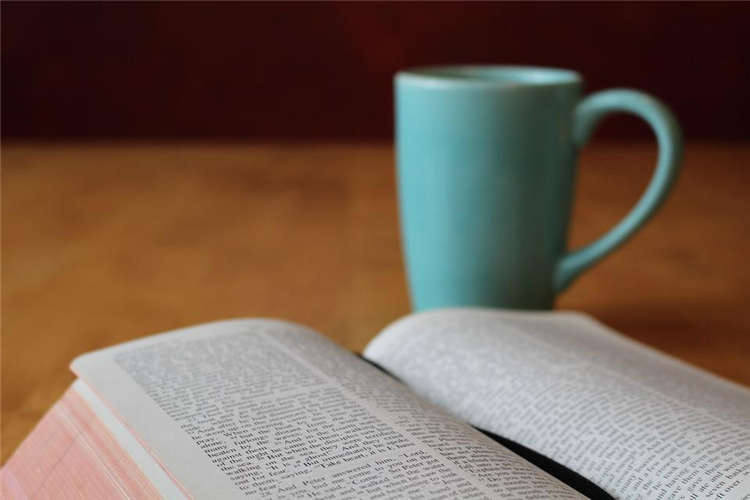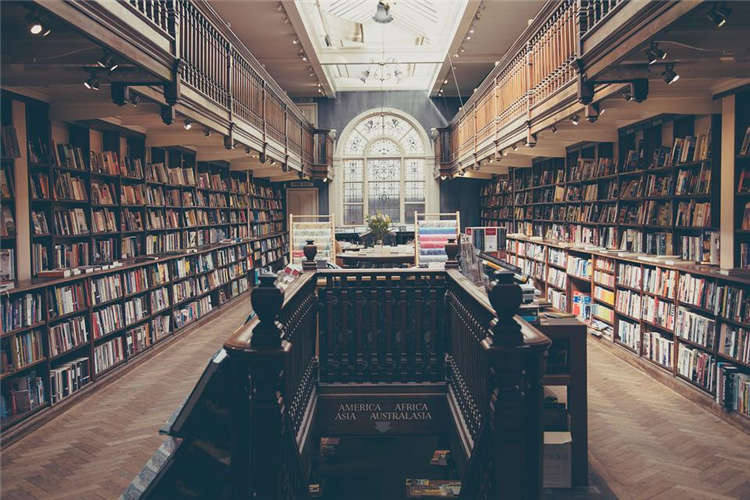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
占有兵至今记得,1995 年冬天,他第一次站在广州火车站广场时的眩晕感。22 岁的退伍兵背着褪色的军用背包,被人潮推搡着向前移动。高楼、立交桥、霓虹灯,这些在鄂西北农村从未见过的景象,让他 " 像被雷击中一样 " 呆立原地。
30 年后,他还留在广东,亲历了中国制造的轰轰烈烈、发财梦的若隐若现,仍未能摆脱打工人的身份。但是,他积累下 150 万张照片,和 6 吨打工实物。
占有兵可能是最对中国打工人记录最全、理解最深的人了。就在这个月,他入围了全球最权威的摄影奖项之一 LOBA(徕卡奥斯卡 · 巴纳克摄影奖)。
真故从一年多前开始做占有兵的书,今天终于出版了,书名就叫《如此打工 30 年》。每一代打工人都有自己重复的宿命,而占有兵记录下的,是中国第一代打工人的历史底片。
我们的父母当年有多拼
占有兵引起外界关注,就是因为摄影。
2000 年在电子厂上班,他用攒了半年的工资买了台二手尼康 F601。" 最开始只是想显摆。" 占有兵在书中坦白。他左拍拍右拍拍,镜头里有厂区的消防演习、年终聚餐、帅哥美女,发在博客上,显得很时髦。直到有一天,网友在评论区留言:" 你拍的烟花美女毫无价值,为什么不记录工友们真实的生活?"
这个质问像一记耳光。原来摄影和拍照不是一回事。
他开始把镜头对准和自己一样的打工人。就像现在的北上广一样,当时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等珠三角城市,吸引了以亿计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他们出身不一,刚刚从土地和地域的捆缚中挣脱出来,目标一致——赚大钱。
这是中国最早的打工族,当下 80、90 后的父母辈。
占有兵自己就从酒店保安开始干起,从一家工厂换到另一家工厂,拿着 450 元的月工资,当时已数高薪。他会拍摄女工们蹲在厂房角落快速扒饭的场景,记录发薪日 ATM 前排起的长龙,捕捉年轻情侣在工业区树荫下牵手的瞬间。
很平常,事后看来却很震撼。
2012 年,他创作的照片《工休》获得全国农民摄影大展金奖。电子厂女工们在更衣室进行工间休息。电子厂的工作一天只有两次休息,上午和下午各一次,每次 10 分钟,女工们可以短暂脱离无尘车间,走出去喝喝水上个洗手间,脱掉帽子和鞋子,让被紧紧包裹了几个小时的身体得以短暂放松。
这样的细节在书中比比皆是,没有在其中生活过的人,写不出来这种感受。
比如,吃饭对打工人来说是一场快速完成的硬仗。从拿到饭菜到走出餐厅,超过 10 分钟的人会被称为 " 老磨 ",就是磨磨蹭蹭的那种人。打工人常常是菜、汤、饭搅拌在一起,闭上眼,嘴贴着餐具,用筷子不停地扒,然后咽下去,接着再扒,直到光盘。占有兵回忆说:" 食堂的米饭,发黄,粗糙,还有细沙,胃里饿得翻江倒海的时候,可以吃一大盆,只敢狼吞虎咽,不能细嚼,米饭中的细沙,会把牙齿咬烂。"
这种被挤压到极致的 " 时间经济学 ",正是中国制造业奇迹背后最真实的注脚。
占有兵从多年拍摄的 150 多万张照片中,精选了 127 张,放入《如此打工 30 年》书中,并写下它们背后的故事。
翻开全书,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个体命运,更是社会的转型轨迹。从暂住证到社保卡,从 BP 机到智能手机,从 " 打工妹 " 到 " 新产业工人 ",这些变化都有具象的呈现。
但占有兵记录的不是苦难,而是苦难中迸发的生命力——工余时间学电脑的年轻人,用 QQ 空间写诗的女工,在网吧通宵与老家孩子视频的父母。这些画面让我们理解,为什么数以亿计的普通人能够忍受如此艰辛的生活,因为他们心中始终燃着改变命运的渴望。
由于持续记录时间长,这些影像和文字本身也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在书中 " 当保安那些年 " 章节里,占有兵就记录了自己在 SL 电子厂 12 年的见闻:非典时期的体温检测、金融危机时的裁员风波、年轻女工们下班后换上花裙子的瞬间。就像一部微观史,让我们看到在 " 世界工厂 " 的光环下,一个个具体而卑微的生命如何挣扎、适应、生存、奋斗。
打工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必须承认,所有的打工人起初都是信心满满的。
占有兵到广东后的第一张床,是两块红砖垫着草席。房间里,一个褪色的 " 健力宝 " 易拉罐格外醒目——那是接济他们的老乡咬牙买下的 " 奢侈品 "。这个易拉罐后来成了占有兵最重要的收藏品之一,他说:" 那晚我们十几个人分着喝一罐饮料,每个人只能抿一小口,但那甜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2009 年开始,占有兵在东莞某厂的车间和宿舍区,拍下了后来屡获大奖的照片:密密麻麻的饭盒、密密麻麻的钥匙串、密密麻麻的衣架和人群。这组照片被命名为《密集的打工生活》。
在几乎没有隐私的宿舍里,工人们喜欢张贴明星海报和风景画报,打工人们把愿景贴到墙上,伴着脚臭味、呼噜声、放屁声,在昏暗的灯光下审视了一次又一次,慢慢产生幻境,带入梦乡,忘掉流水线上的疲惫,身体得到短暂的放松,为第二天重新投入流水线积蓄力量。
也正是因为满怀希望,打工人们甘于忍受现状,并试图在逼仄中寻找尊严。网吧舒适的大班椅可以提供这种尊严。生产线上不许讲话,打工人上班时一律 " 静音 ",加上人员流动频繁,即使是同一条生产线上的打工人,也不都认识。但在网吧,不仅可以和恋人、同学、朋友、亲人联系,还可以玩游戏、听歌或者看影视剧消遣。白天在生产线上忍受的委屈,在网络上可以得到充分的宣泄。
然而,每天辛苦干活的打工人,随着青春逝去,得到的回报却极少。" 用这些回报,无法照顾好老人,无力亲自抚养孩子,更无力为自己的疾病买单。" 因此,在工业区,彩票投注站随处可见。憧憬着一夜暴富的打工人,就在买彩票、盼中奖、开奖落空中重复。
和今天的年轻人并没有什么分别。
52 岁的占有兵,站在 30 年后回望,一直在思考,打工给自己这一代人带来了什么。他现在不仅关心具体的上班环境,目睹制造业转型造成的厂区萧条,也开始担心自己的退休金、医保和养老问题。
因此,他将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命名为," 人为什么活着 ",收录了他历年来对 20 余位工友的访谈实录。
54 岁的女工阿琴说:" 在厂里过了 20 个春节,每次看春晚听到《常回家过年》就想哭。但看着存折上的数字,又觉得值了。" 这些朴实的话语道出了打工潮最深层的精神动力——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
但是在全书的结尾,从初二就开始打工的邹 PP 却说," 以前活着就是为了挣钱 "," 现在我感觉很多人为了房子、车子,挣钱,然后还贷款,好累呀。"
占有兵得出了认识,过去打工就是为了讨生活,现在这一代人则把打工当做一个临时过渡期," 可大部分人永远在临时过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