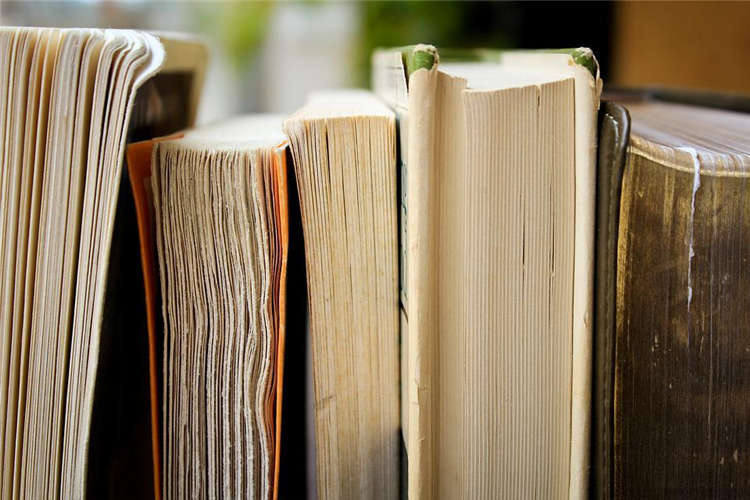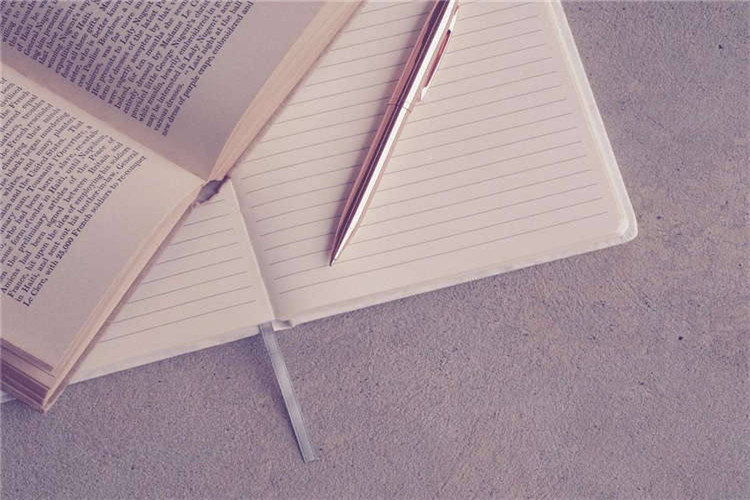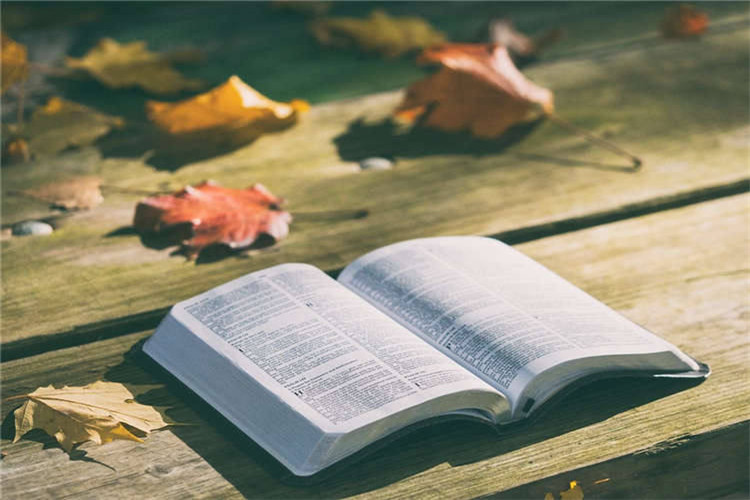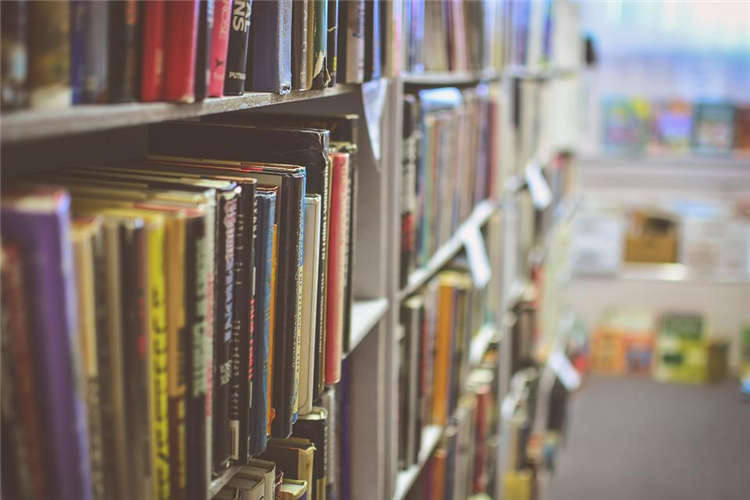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朝统一天山南北,中国历代王朝自汉、唐、元统一西域以来,中央政权恢复西域的重新统一。清朝统一西域后逐渐以新疆定名,施行军政合一的军府制度,最高军政长官为伊犁将军,驻扎伊犁地区。另外,又设置归伊犁将军节制的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乌鲁木齐都统和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管辖天山南部塔里木盆地边缘各绿洲,“天山以南是为回疆。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后,建城八”,总管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阿克苏、乌什、库车、喀喇沙尔八城事务,改革回疆传统伯克制度,成为清廷对回疆“因俗而治”的基本体制。
清代新疆治理的大规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即为遍布天山南北的城池设置,其表征即为“城池为官守之责,庙宇亦风教之征”,儒释道庙宇及其承载的文化逐渐交融于新疆天山南北。儒释道庙宇主要指儒家坛壝、祠庙、佛教寺庙、道教宫观,以及儒释道融合一体的各种民间信仰庙宇。回疆维吾尔人逐渐熟悉儒释道庙宇及其社会文化形态,只与清真寺相互区别,一概认知为偶像庙宇,喀什噶尔人阿布尔·瓦西提·阿洪德指出崇拜偶像的人“用木头、泥土、铜、铁、石头和黄铜建造各种模仿人、动物和鸟类的偶像,并对它们顶礼膜拜”,“有时,他们会把神像抬到城市的街道上,当神像穿过(所有)通道过境,在城市中流传时,它就会对(城市)有益”,把庙宇演戏描述为“自古以来,在(中国)皇帝的国家里,偶像崇拜者就有这种被称为‘唱戏’(戏剧表演)的习俗,它类似于穆斯林的说书人和在集市上游荡布道的毛拉”。儒释道信仰的多样性、包容性和人文世俗性创造了与伊斯兰信仰相互尊重习俗的社区环境,共处同一宽容的社会空间。
远迈汉唐的阿克苏道儒释道庙宇
乾隆年间至嘉庆九年,阿克苏城有4座庙宇,包括北城楼观音阁、关帝庙、万寿宫、风雨神庙。晚清温宿府城的庙宇总计有9座,包括万寿宫、文庙、社稷坛、神祇坛、武庙、城隍庙、龙神祠、刘猛将军祠、方神庙。1922年,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斯科拉因游历阿克苏,自称“最喜欢去的地方是中国(道教)的白云观”,得知“白云之神通过神文与他的信徒交流,或者说直到最近还在通过神文与他的信徒交流”,“自从12年前两位天津商人离开后,神就再也没有向他的信徒们传达过任何书法信息”,认为“阿克苏的白云圣地却是一个宁静和令人肃然起敬的地方”。晚清温宿县城的庙宇总计有8座,包括万寿宫、文庙、武庙、文昌宫、城隍庙、龙王庙、马王庙、方神庙。
阿克苏戏剧表演(马达汉,1907年)
乾隆年间,喀喇沙尔有3座官修庙宇,分别是万寿宫、关帝庙和龙神庙。民间历史记忆指出,乾隆年间修建的有关帝庙、龙王庙、八蜡庙、山神庙、财神庙,嘉庆年间修建的有马王庙、鲁班庙,道光至光绪年间陆续修建的有城隍庙、娘娘庙、方神庙、观音阁、文昌阁、文庙等。而晚清焉耆府乡土志记载的庙宇总计有9座,包括万寿宫、关帝庙、城隍庙、龙王庙、圣庙、文昌阁、刘猛将军、方神祠、文庙。晚清婼羌县的庙宇总计有4座,包括庆祝宫、社稷坛、城隍庙、定湘王庙。晚清轮台县的庙宇总计有4座,包括武庙、城隍庙、龙王庙(两座)。
喀喇沙尔舆图(局部)中的关帝庙与龙王庙(乾隆)
乾隆年间,库车有两座庙宇,分别是万寿宫和关帝庙。沙雅县有一座三尊庙。宣统元年二月十五日(1909年3月6日),野村荣三郎在沙雅发现三尊庙“祭孔子、文昌、关帝”。晚清库车直隶州的庙宇总计有9座,包括万寿宫、圣庙、文昌阁、关帝庙、城隍庙、刘猛将军庙、昭忠祠、龙王庙、方神祠。方神祠位于城北,不仅在库车民间社会香火兴盛,且影响力遍及回疆。库车地方社会流传的故事显示:“考方神原湖南善化人,姓黄名桂芳,道光间官喀什,偏裨黑水之围,张逆等灌城急独,慨然忠义愤激,投城赴水誓以身殉,须臾下流缺口,开城保无虞民,德而祠祀之,辄祈祷无不灵验。南路各城汉缠争奉香火,地方官朔望行香,亦为民请命之意也。”方神信仰融合儒释道信仰三教杂糅的文化形态,共同塑造了方神民间信仰,成为儒释道文化回疆在地化的显著社会事实。
库车方神庙(Gttfried Merzbacher,1902-1903)
乾隆年间,乌什城有7座庙宇,集中在韦陀山,包括万寿宫、山川社稷坛、关帝庙、马祖殿、火神殿、观音阁、韦驮殿。“韦陀山”即为当今的燕子山,仍然是地方风景名胜,可谓承载了千年不绝的儒释道文化内核。晚清乌什直隶厅的庙宇总计有6座,包括万寿宫、文庙、城隍庙、关帝庙、龙神祠、昭忠祠。晚清乌什韦陀山又称乌赤山,韦陀山的命名源于儒释道庙宇群的上山,持续有清一代,山上刻有石碑,刻字“继超追宪”和“远迈汉唐”,中华传统的文化遗迹铸就地方胜景。
乌什“韦陀山”“远迈汉唐”与“继超追宪”碑刻
德被群生的喀什噶尔道儒释道庙宇
乾隆年间,喀什噶尔徕宁城有两座庙宇,即万寿宫和关帝庙。地方官员个人纂修方志记载道光年间喀什噶尔城内庙宇已经有5座,分别是万寿宫、关帝庙、龙王庙、城隍庙和昭忠祠。清季疏勒府乡土志记载的庙宇有8座,包括庆祝宫、城隍庙、文庙、武庙、忠义祠、方神庙、观音阁、刘襄勤祠。刘襄勤祠即刘锦棠祠,斯坦因于1900年8月参观刘锦棠祠,称之为“一座雄伟的综合性建筑”,指出“毗连大门面向最里层院子的是一座精致的木构戏楼”,纪念祠的主体大厅“左、右两边的整个墙壁上贴满了一系列描述刘锦棠的胜利历程、政治活动及个人生活的大幅绘画”,并与祠堂祭司交谈并拍照。中国儒教庙宇给斯坦因留下深刻印象,直观感受到中华古典文明的情调。
疏勒刘锦棠祠主持(斯坦因,1900年)
疏勒刘锦棠祠戏台(斯坦因,1900年)
事实上疏勒的儒释道庙宇众多,近现代疏勒县城文物遗迹及地方口碑流传的历史记忆表明,至十九世纪初疏勒城庙宇林立,号称有十大庙宇,分别为城隍庙、财神庙、观音阁、方神庙、文庙、武庙(关帝庙,又称三圣庙)、娘娘庙、龙王庙、药王庙、鬼王庙(地藏王庙)。晚清伽师县有一座城隍庙。晚清疏附县的庙宇有7座,包括社稷坛、先农坛、神祇坛、文昌庙、龙王庙、城隍庙、耿公祠。清末民初瑞典传教团的传教士陶伦奎斯特是一位摄影大师,他敏锐地捕捉到喀什噶尔一座古庙院内大殿的横幅上书“德被群生”,昭示着庙宇承载的中华文教。喀什噶尔回城疏附有一座耿公祠,是纪念东汉明帝的西域戊己校尉耿恭的祠堂,属于典型的儒家纪念性文化形态。耿公祠附近有泉水带出露,水池小溪相连流入吐曼河,相继建有佛寺、茶馆、旅店,民间俗称九龙泉,又称为耿公泉或耿公井,成为喀什噶尔回城疏附的儒释道风土胜景。
喀什噶尔庙宇院内(陶伦奎斯特,清季民初)
喀什噶尔耿公祠(马达汉,1907年)
乾隆年间,叶尔羌城有5座庙宇,包括万寿宫、显忠祠、关帝庙(两座)、龙王庙。叶尔羌是回疆大城,曾经是总理回疆参赞大臣驻地,“内地商民,山陕江浙之人不辞险远,各携货资,购觅宝玉,以至其地,故店铺馆舍辉煌齐整”。万寿宫中建有碑亭,所刻立的碑正是“御制平定回部勒铭叶尔奇木之碑”,而显忠祠对阵亡满汉官兵的崇德报功,都明确树立了清王朝国家统治权合法性的祭祀文化标识。
叶尔羌关帝庙(马达汉,1906年)
晚清莎车府乡土志记载的庙宇总计有7座,包括万寿宫、武庙、火神庙、龙神祠、昭忠祠、城隍庙、方神庙。事实上莎车庙宇数量更多,根据白合提亚尔的采访口述与历史记忆,莎车有14座儒释道庙宇包括玉皇庙(又称玉皇阁)、三官庙(又叫三清宫)、文庙、火神庙、药王庙、土地庙、财神庙(又叫财神楼子)、王爷庙(即定湘王庙)、观音庙(又称观音阁)、娘娘庙、马王庙、龙王庙、城隍庙、武庙(关帝庙)。晚清巴楚州乡土志记载的庙宇总计有5座,包括龙神庙、城隍庙、火神庙、文武庙、昭忠祠。晚清蒲犁厅的庙宇总计有4座,包括武圣庙、城隍庙、风神庙、龙神祠。晚清叶城县的庙宇总计有5座,包括武圣庙、文庙、文昌庙、城隍庙、方神庙。晚清皮山县有两座庙宇龙王庙和火神庙。
乾隆年间,英吉沙尔有4座庙宇,包括万寿宫、关帝庙(两座)、廒神庙。晚清英吉沙尔直隶厅乡土志记载的庙宇总计有6座,包括关圣庙、龙王庙、万寿宫、城隍庙、方神庙、托公祠。晚清洛浦县乡土志记载只有一座大庙,供奉的牌位包括先师、文昌、关帝、龙神、城隍、社稷、先农、神祇。晚清于阗县乡土志记载的庙宇有3座,包括文庙、武庙、城隍庙。晚清和阗直隶州的庙宇总计有11座,包括文庙、武庙、城隍庙、文昌庙、社稷坛、神祇坛、龙神祠、昭忠祠、先农坛、刘猛将军庙、方神庙。斯科拉因1922年发现“和阗城并不大,但却繁华热闹,让旅行者充分感受到了它的魅力”,和阗新城里“有官府衙门、兵营和弹药库、道观和几条商店街”。斯科拉因对回疆道观有清醒认知,专门数次记载。方神庙于回疆民间社会神明卓著,和阗方神庙“庙貌偏南疆,推当日御患之功”,以至于地方官员认为“似在应升祀典之列”。和阗地方“至民间善举,惟额籍汉民建有方神庙,集公费千余金。奉神外,兼施棺木及中元属祭等事”,和阗方神庙成为地方社会慈善活动的民间重要力量。
英吉沙新城城东建筑(马达汉,1906年)
儒释道与伊斯兰的文化共生
“回”属于中国元明清时期对伊斯兰教信徒穆斯林的专称,其定名原则依据穆斯林社会的伊斯兰风俗。清代新疆回疆社会的宗教信仰以伊斯兰教为主,清真寺成为城乡居民生活的社区中心,呈现出伊斯兰文化的整体面貌。伊斯兰教在清朝被称为“回教”,清代新疆的穆斯林社会据此被称为“回部”,天山南部八城所在地域被称为“回疆”。伊斯兰教对回疆维吾尔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生活习俗产生全面影响。清代回疆“每城设礼拜寺”,维吾尔居民“每七日赴礼拜寺诵经一次,务集四人合诵,不论贵贱贫富皆然”。《西域图志》编纂者以儒释道的文化经验描述“回人通经典者曰阿浑,为人诵经以攘灾迎福”,信仰伊斯兰教的“回人尊敬造化之主,以拜天为礼”。清真寺为清代回疆普遍的社会景观,规定着穆斯林的生产与生活节律。清代在作为大一统王朝重要表征的意义上继承了中国历史中的“礼治”传统,特别强调跨越语言与族群界域的同文之治。清王朝确立对西域新疆的合法统治,随之建立起军府制治理体系,而其治理方略的核心要义在于“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充分尊重回疆伊斯兰风俗,追求“旷然更始而不惊,靡然向风而自化”的礼治。清王朝在新疆的中华礼治首重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城池与儒释道庙宇由此遍及回疆,儒释道庙宇成为中华政教文明的标识性载体,构成与葱岭(帕米尔高原)以西中亚绿洲穆斯林文化区的根本区别,造成回疆儒释道与伊斯兰一个半世纪的文化共生。
清代新疆回疆儒释道庙宇主要分布于驻防城镇、军台、道府州县城市和交通驿站等空间要地,数量有限,远不及遍布城乡的伊斯兰清真寺数量级,但其包容开放的信仰风俗与国家政教的双重属性在回疆具有较高的社会显示度。清代新疆回疆与清真寺共存的儒释道信仰习俗是三教混融的,具体表现为围绕庙宇为载体的社会空间文化形态,伊斯兰与儒释道风俗的碰撞、交流就此发生。西方学者的域外观察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西部的省区新疆是汉文化和突厥——伊斯兰文化的交汇之处,这种交汇使具有各自文化(特别是在戏剧方面)分野特点的两种宗教系统发生了冲撞。清王朝的回疆治理首重喀什噶尔,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的驻地比较稳定地设在喀什噶尔,喀什噶尔徕宁城“既具庙之丹碧与城池之庄严,俨然为回疆之一都会矣”。儒释道庙宇成为回疆都会的标志性表征。中古以降伊斯兰化大规模东进的历史进程至清代一统新疆结束,清王朝“大一统”的中华礼治又把回疆融入中华文明体系,重塑了内陆欧亚的文明版图,葱岭(帕米尔高原)成为清代以降中华文明体系与域外文明的分野。清代回疆社会经历英国与沙俄的渗透及阿古柏侵略的战乱破坏,发生军府制到行省制的转型,而儒释道庙宇得到重建并进一步发展。回疆儒释道庙宇军府制时期以官修为先,逐渐向民间社会弥散,行省制时期的则以民修为主,祭祀仪式以及庙会尤其是演戏酬神等社会活动构成多种族群共享的社会交流空间。
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初的拜城县赛里木人毛拉木萨·赛拉米用察合台文记载清代中国“国强地广的另一个原因与秦可汗实行的爱民和公正政策是分不开的”,尤其认为“他们绝不勉强让别人学习自己的习惯,允许宗教信仰和教派林立。只要你坚持自己的信仰,他们不会让你改宗”。毛拉木萨·赛拉米对清中国爱民政策、疆域和宗教政策的叙述反映出中华政教的文明特性,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其时一般穆斯林民众的国家认同。19世纪末,瑞典传教团进入回疆传播基督教,瑞典传教士发现儒释道庙宇中经常有戏剧表演,观众中有大量的维吾尔人。喀什噶尔人阿布尔·瓦西提·阿洪德经常去儒释道庙宇参观祭祀仪式,并观看戏剧表演。阿布尔·瓦西提·阿洪德基于伊斯兰教禁止一切形式的偶像崇拜,他用察合台文详细描写儒释道庙宇及其神像和所进行的祭祀仪式。贡纳尔·雅林指出一般的穆斯林很显然对儒释道庙宇及宗教中的“不敬神”行为不大在乎,相反充满了好奇心。由此表明,回疆儒释道与伊斯兰一个半世纪的文化共生已经产生交融与对话的文明会通。伊斯兰教与儒释道都在回疆产生各自的民间风俗形态,正是普遍的民间风俗实践促成儒释道的回疆在地化。清代新疆回疆的儒释道与伊斯兰风俗在民间社会文化层面实现长期的互动与交融,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的文明会通道路。清代新疆回疆的社会运行经历军府制到行省制的转型,儒释道庙宇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命运与共,成为清王朝“大一统”边疆治理秩序社会风俗交融的公共基础设施。清王朝面对广阔疆域和多元族群的“大一统”政局,“因俗而治”不是孤立的治理体制,而是与儒释道庙宇承载的风教共同结构成整体的中华政教,“风同道一”的回疆治理呈现的是整体的中华政教文明统治方略。
(原文《清代新疆回疆儒释道庙宇的中华政教》刊载于《学术月刊》2025年第4期,本文经作者大幅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