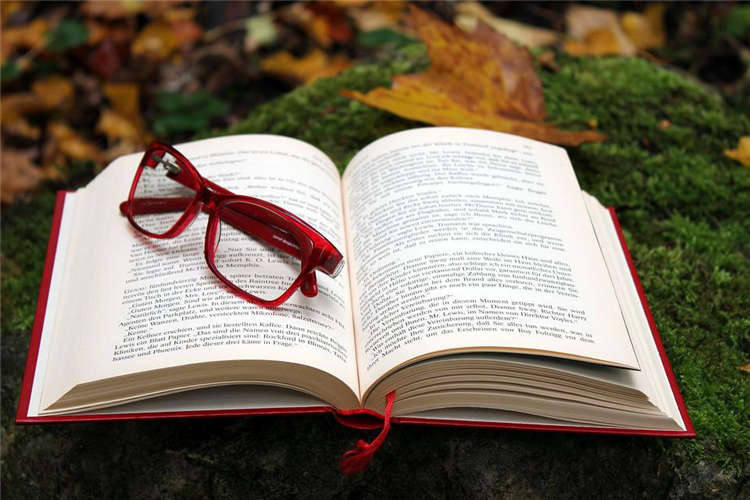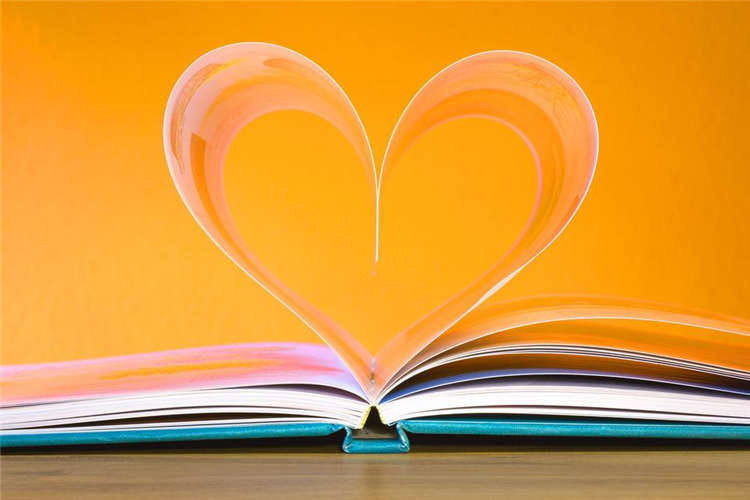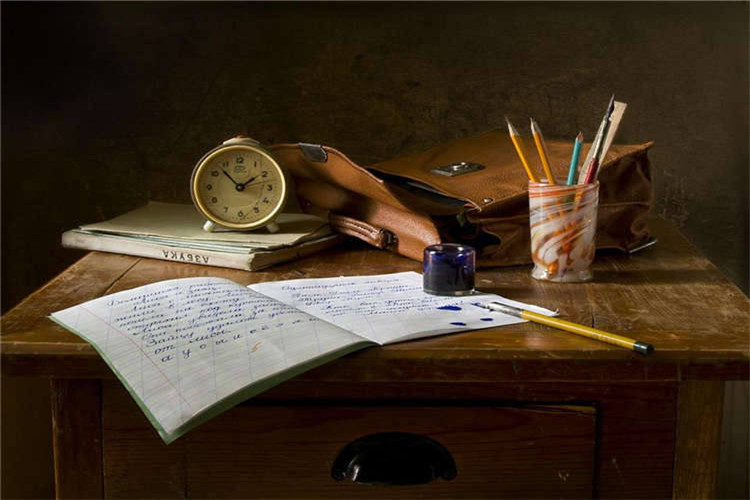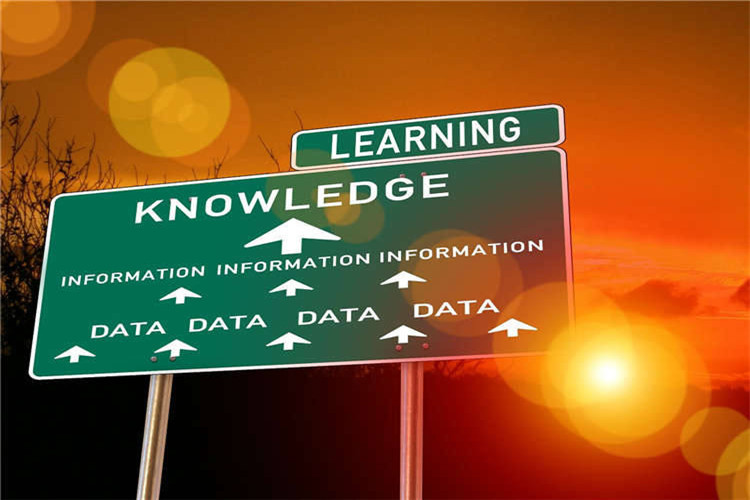双城之间的李维
李维全名提图斯·李维乌斯(Titus Livius),我们仅知晓他的名字和氏族名,对他的第三个名字,即家族名(cognomen)一无所知。我们从圣哲罗姆(St. Jerome)的记载中推断,李维生于公元前59年,即共和国后期的罗马内战时代,是向帝国转型的重要时期,他卒于公元17年,即罗马皇帝提比略继位的第三年。
提图斯·李维乌斯(Titus Livius)
李维出生在意大利北部波河北岸山南高卢地区的帕塔维乌姆[Patavium,今意大利东北部的帕多瓦(Padua)]。李维的家乡帕塔维乌姆以盛产羊毛驰名远近,富甲一方,是意大利略逊于罗马的富庶之地。帕塔维乌姆民风淳朴,古时的道德操守多有留存,与当时世风日下的罗马相比,帕塔维乌姆已然是古代美德的汇聚之地,传统的道德观念从该城的政治立场及亲元老院的态度上反映出来。公元前43年,元老院宣布安东尼为公敌,该城拒绝安东尼的副将来访,在腓力比战役后甚至受到站在安东尼一方的阿西尼乌斯·波利奥(Asinius Pollio)的严厉报复,遭到征收严苛税收的严重制裁。李维早年的生活背景为其道德观和政治观打下了鲜明的烙印,他极力颂扬共和国伟大人物所奉行的道德规范,流露出传统的道德观和共和观,折射出家乡的传统政治文化氛围给他带来的影响。
我们对李维的家庭背景所知甚少,和多数古代历史学家类似,他没有留下家庭出身和个人生活的只言片语。在帕多瓦发现的铭文中有获释奴李维乌斯的字样,还有一篇墓志铭是纪念提图斯·李维乌斯和妻子卡西亚(Cassia)及两个儿子的,经推测是这位历史学家的墓碑。具有深厚知识背景的李维也许并非元老贵族的后裔,而是出身获释奴阶层。
李维早年在家乡求学,接受基础阶段的家庭或学校教育后,也许在12岁时进入当地的中学学习,跟从文法老师学习词语的正确发音及用法,阅读希腊罗马诗人及史家的作品。我们不知道李维的恩师名讳,但他们显然激发了这位学生对历史研究的兴趣。古罗马的学生通常会在学校教育的最后阶段,通常在16岁以后,前往罗马深造。时局变乱、内战不息的现实也许打消了李维去往罗马求学的念头,他安心留在家乡潜心学习修辞学。他在演说术理论方面受过严格训练,这从他在史作中创作演说词的精湛技巧可见一斑。除了罗马,希腊也提供了学业深造的极佳选择,罗马学生通常会以留学雅典或罗德岛为自己的正规教育画上完满的句号,他们在那里可以结识极负盛名的哲人和修辞学家,聆听教诲,共同讨论。公元前1世纪40年代的罗马世界并不太平,庞培之子塞克斯图斯·庞培(Sextus Pompeius)控制着罗马的海路要道,以拦截首都的粮食供应来遏制对手屋大维。诚然,海路的险途并不能阻挡所有年轻人前往希腊的憧憬,然而,李维在其作品中对希腊语不甚熟稔和对地理问题认识模糊都透露出他很少游历,很可能没有在雅典或罗德岛接受高等教育。他也不曾服役军旅,他对战争的记载暴露出他对军事实属外行。
在家乡求学期间,他对历史和哲学兴趣颇浓,创作了一些哲学对话录,其中有一些带有浓重的历史意味。西塞罗的多篇哲学对话录在公元前45-前44年问世,与李维的求学时期正好吻合。这些作品,如《论神性》(De Natura Deorum)和《论占卜》(De Divinatione),促进了李维的哲学世界观的形成,西塞罗的哲学观点正合李维的兴趣,无疑会成为李维效法的典范。李维的这种哲学兴趣若要追溯,可能要追溯到斯多亚派代表人物波西多尼乌斯(Posidonius)的影响。李维或许也读过柏拉图、色诺芬等人的哲学原著,但他历史著作所蕴含的哲学精神主要渊源于深深扎根罗马史学传统的斯多亚派伦理学思想。他所从事的哲学研究对后来汇集史料展露哲思的影响尤为强烈,对他撰写罗马早期历史部分的影响尤其明显。
李维大约在而立之年即公元前30年左右来到罗马,得出这一猜测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李维为一个和平的国度撰写历史,通过彰显共和国英雄人物的操守来引导当代人的行为。因此,李维很可能在公元前31年亚克兴战役后,屋大维攘除安东尼和克里奥帕特拉的祸患后,才来到罗马的;其二,《建城以来史》卷一出版于公元前27年至前25年间。试可猜想,李维来到罗马,搜寻在帕塔维乌姆无法获得的书籍,再进行初步研究和准备工作。他与罗马的官场和文坛都是比较疏远的,他不曾担任公职,与麦凯纳斯(Maecenas)和麦萨拉(Messalla)为主的两个文学圈子没有联系,不在他们资助的文人之列,也非奥古斯都资助的对象。我们猜测,李维开始撰史时名不见经传,《建城以来史》的前言和第一卷出版后,奥古斯都对他的作品有所耳闻,乐于资助这位前途看好的著作家,希望他报之以投入这个新生“共和国”的文化建设,李维婉言谢绝。尽管如此,他与这位罗马最高政治人物奥古斯都关系融洽,被聘为日后成为罗马皇帝的年少克劳狄的老师。他曾鼓励克劳狄撰写历史,克劳狄撰写埃特鲁里亚人历史的兴致可能源自这位导师的启迪,他的演说词带有与李维相似的风格。
李维有二子一女。一子创作了有关地理方面的专著,一子撰写修辞学方面的文章。女儿嫁给一个名叫路奇乌斯·马吉乌斯(Lucius Magius)的修辞学家,老塞涅卡(Seneca the elder)曾心有不悦地暗示说,此人以其岳父的声名招揽听众,吸引大众关注他的朗诵。
李维也许后来一直在罗马定居。按照李维写史的平均进度推算,他在公元前2年之前一直居于罗马,或者,直到公元8年克劳狄长大成人,他才离开罗马回到家乡,亡于家乡。根据哲罗姆的记载,他于公元17年过世。帕多瓦发现有一段墓志铭,归属于奥古斯都时代,以纪念一个名叫提图斯·李维乌斯的人。
我们对李维这位伟大历史学家的个人情况所知甚少,似为全面了解他留下诸多遗憾。不过,正如李维的注释家奥吉尔维所言,即使我们知道更多李维的生平,对我们更好地欣赏他史书的伟大之处别无裨益。他全身心投入写作,不论琐屑日常,终成传世巨作。
《建城以来史》的内容结构
李维集四十年之力,广采史料,苦心研究,写就《建城以来史》(Ab Urbe Condita)。他从传说时代的罗马叙述至公元前9年,共744年,凡142卷,整部著作大气磅礴,是罗马历史编纂史上的通史巨著。
《建城以来史》(Ab Urbe Condita)
国内学界对古典史学和李维史学的研究相对薄弱,但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世纪,早年留学瑞士的阎宗临是国内最早从事李维研究的中国学者,其后,郭圣铭、王敦书、王乃新、张广智、郭小凌等学者也相继在西方史学史领域著书立说,对李维史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阎宗临先生撰写出有关李维史学的论文。郭圣铭先生编著的《西方史学史概要》廓清了西方史学发展的源流及规律,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价各个时代的历史学家。该书评价了李维史作的特点,同时也指出李维作为一位史家的严重不足。此外,在《外国史学名著选》之《李维〈罗马史〉》选中,王敦书先生对李维的历史观、道德标准、爱国思想及其文学造诣都作了简要介绍,该书最为可贵之处在于选译了《建城以来史》第五卷的部分章节,为读者近距离感受李维的治史特色提供便利。《外国史学名著评介》一书中,王乃新先生的论文评述了《建城以来史》的写作特点及李维作为史家的长处与不足。两部同名史学论著《西方史学史》囊括了对李维研究的重要成果。张广智先生在书中将李维与塔西佗并称为罗马史学双擘,从通史体例、垂训思想和文学修养三方面总结了李维的史学思想及其在史学史上的贡献。郭小凌先生指出,李维的著作不是政治家、军事家们的回忆录,而是以治史为己任的书斋学者的自觉之作,他试图探讨和说明罗马人曾经是怎样的民族,具有怎样值得尊敬也令人生畏的道德财富,落脚点是在解释现代,他书斋学者的特质决定了他著作的优缺点。同时,对李维史著的基础性翻译工作也在进行,日知古典丛书之李维《建城以来史》(前言·卷一)将李维的拉丁语译为中文,王焕生先生译有《建城以来史》前十卷拉汉对照选译本,为学者们的研究提供了可贵资料。
近些年来,国内学界对李维史学的专题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所博士刘君玲就李维《建城以来史》第2-4卷写成论文,研究了这三卷的史料价值、文学价值及从中反映出的李维的历史观。该论文还附有第2-4卷自拉丁文翻译的汉译文,体现出作者扎实的拉丁文功底。蔡丽娟老师以《李维史学探微》为题作成博士论文,并发表了有关李维史学的专题论文和专著,加深了史学界对李维史学方法、史学思想、李维史学与奥古斯都时代的认识,推动了李维史学研究走向深入。《建城以来史》第1-5卷叙述埃涅阿斯到达拉丁姆,罗马建城,至公元前390年高卢人入侵罗马;第6-10卷记述公元前293年之前的史事;第11-15卷记述罗马征服意大利至第一次布匿战争开始;第16-20卷记述第二次布匿战争前的史事;第21-30卷记述第二次布匿战争;第31-45卷记述马其顿和叙利亚战争,至公元前167年第二次马其顿战争结束;第46-90卷记述到公元前78年苏拉之死;第91-120卷记述至公元前43年,包括内战和恺撒之死;第121-142卷记述至公元前9年德鲁苏之死。李维也许原计划写成150卷,终于奥古斯都之死,因为这样的结构处理更为合理,但因李维亡故,该著作成为未竟之作,终于第142卷。
《建城以来史》问世后即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因该书卷帙浩繁,不便阅读,因此出现了多种概要本和缩写本。现今存世的卷数不到全书的四分之一,仅存35卷,第1-10卷和第21-45卷,其中41-45卷还有不少残缺之处,横跨公元前753年-前293年、公元前219年-前167年的史事。除至今存世的35卷外,其余诸卷在7-15世纪散佚,西方社会尚未发明印刷术是这部巨著难以传承的主要原因。仅现存一个重要的断片于1772年被发现,即在梵蒂冈发现的第91卷的残篇,由尼布尔(BartholdGeorgNiebuhr,1776-1831年)于1820年编辑。散佚各卷的内容梗概可从诸如普鲁塔克和狄奥·卡西乌斯等人的作品中,还有像弗罗鲁斯(Florus)和尤特罗比乌斯(Eutropius)所写《纲要》(Periochae)中得见。我们对其内容的了解主要来自《纲要》,这使我们可以略知全书的内容梗概,第136卷和第137卷不在此列。
李维虽在第四个十卷的开篇表明自己对这项宏大任务越来越不安,但我们从现存各卷中发现,他较为谨慎地考量史料,选择符合他写作意图的素材,对著作的组织结构也有统筹规划。这种总体上的考量可以推而广之,及至他对所处时代的历史记述。在行文组织上,他以五卷为一组谋篇布局。《建城以来史》后期各卷的结构安排较前面各卷稍显混乱,有学者认为在第109-116卷对共和国后期内战的描写中,李维已经放弃条理清晰的结构安排,不如早期各卷那样对重要战事的叙述井然有序、分划有致。实际上,他们忽视了李维所述历史的复杂性。编年史体例与浑然一体的通史建构既有相合之处,也有相左之处。早期各卷所述大多为连续的战争,因此做到整齐有序较为容易。随着罗马疆界的扩大,国内国外事件与日俱增,李维的史著不能单单以一个战场铺垫一个五卷。战争并非你方唱罢我登场,多是同时进行,国内政治事态的发展也如火如荼,统合纷繁的历史并非易事。即使这样,《建城以来史》各个五卷通常都具有相当程度的统一性。读者应把五卷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加以考察,不仅应关注该部分的第一卷,更应留意其中的最后一卷,李维往往将某一重要事件留到下个五卷,以一个引人注目的主题开启新的五卷。例如,迦太基的陷落和毁灭被安排在第51卷,俘虏朱古达在第66卷,刺杀尤利乌斯·恺撒在第116卷。李维五卷一组的布局是精心构思的结果。
以现存各卷分别查之,第一卷囊括整个王政时代(公元前753-前510年),可能单独出版,因为第二卷记有一段新序言。第2-5卷囊括下讫高卢攻陷罗马的史事(公元前509-前390年),也许一同出版。第6-10卷的主题是萨莫奈战争,不仅以萨莫奈人的失败,更以埃特鲁里亚人、高卢人和翁布里亚人的失败作为高潮部分。散佚的第11-20卷包含两个独立的部分,一是罗马与他林敦的战争,再是罗马与迦太基的第一次布匿战争。第二次布匿战争横跨整个21-30卷,这十卷又一分为二,前者是以汉尼拔的崛起为主线,后者则是以罗马的反攻为主线。第31-45卷由三个五卷组成,第31-35卷的主要内容为罗马与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的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以及与塞琉古国王安条克的叙利亚战争之前的希腊事件;第36-40卷是罗马在希腊和小亚细亚与安条克三世的战争;第41-45卷是第三次马其顿战争及罗马对马其顿国王珀尔修斯(Perseus)的胜利。《纲要》表明第45卷之后的各卷仍以五卷为一个单元谋篇布局。例如,第九个十卷主题有二,一是米特拉达梯战争,二是苏拉归途中的残酷之举。在第十二个十卷中,前五卷涵盖恺撒发动的第拉奇乌姆(Dyrrachium)战役到蒙达(Munda)战役,后五卷的时间跨度为从恺撒之死到建立“后三头同盟”的20个月。从这些实例中我们可知,后面各卷中五卷一体的结构往往不围绕某一战事,而是围绕某个重要人物展开。第51卷从记述罗马夺取迦太基开始,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ScipioAemilianus)是第六个十卷的核心人物。第66卷开始记述马略的生涯,后面三个五卷围绕他的个人成就展开,终于第80卷马略之死。苏拉在第81-90卷中的地位举足轻重,第90卷讲述苏拉之死。庞培的名字则第一次出现在下一卷,即第91卷。由于后面各卷的摘要过于简短,尤其是第136-137卷的摘要佚失,因此无法推断《建城以来史》后一部分的结构。
五卷、十卷的编排体现出李维别具匠心的构思,这一构思不仅是结构上的规划,更是内容上的荟萃,不仅以重要事件作为起篇与完章的标志,而且将历史进程与城市历史衔接起来,时常呼应《建城以来史》的著作书名。罗马城市的发展变迁,罗马疆域的不断扩大,随着各卷的推进顺次展开,罗马史的演进和城市史的发展协调一致。如在卷六卷首,即新的五卷的开篇,李维撰写一段新序言,写到罗马城经历高卢战火后开启崭新篇章,与此一致的,罗马史也摆脱史料缺乏的局限开启了新篇章,城市的发展与历史书写齐头并进。
较早的《建城以来史》各卷多以某场战争为主线,而较晚的各卷常以某个人物为主线。李维对全书的结构考虑周全,安排得当。撰述自罗马建城以来的通史是一项宏大工程,处理稍有不慎,整座大厦必然倾斜甚至倾覆,而李维将整个工程化整为零、又合零为整,远望巍然而立,近观井然有序。由于李维决定书写一部编年史,按年代顺序描述各自区别的历史活动场景,因此每一卷不可能总是自成一体,不可能如希腊史家狄奥多鲁斯所追求的那样,“从头至尾地完整叙述城邦和国王的行动”。
如果李维临终之前才辍笔,那么他在四十年的著史生涯中平均每年至少成书三卷,或许笔耕更勤,因为《建城以来史》的第121-142卷推迟到公元14年奥古斯都去世后才出版,所以李维在完成这22卷后也许将之尘封多年。《建城以来史》所包含的纷繁复杂的人物、事件和年代足以说明这位史家的非凡成就和坚定意志。每一卷至少参考三种史料,尽量协调内中关系,将其中的记载改写成优美的散文。李维在四十年里以每三年写成十卷的进度笔耕不辍,将毕生之力倾注在《建城以来史》的创作之中,我们不禁对他兢兢业业的治史精神仰慕备至。古罗马的百科全书式学者老普林尼,斥责侄儿步行是在浪费时间,不如乘坐交通工具节省时间用于学习,“不用来学习的每一分秒都是在浪费时间”,老普林尼的时间观念用来说明李维的敬业精神再恰当不过。
奥古斯都时代的主要评论家之一盖尤斯·阿西尼乌斯·波利奥,语含贬义地称李维著作带有“帕塔维乌姆风格”(Patavinitas)。为何语出贬义引起众多评说,我们试作如下解释:波利奥在任山南高卢总督期间,曾出台阻碍帕塔维乌姆发展的强硬政策,这也许出于他对帕塔维乌姆城的私愤。波利奥也像历史学家撒路斯特一样离开仕途后撰史,他和撒路斯特的文学咨询人费洛洛古斯(AteiusPhilologus)要好,续写了撒路斯特于公元前35年亡故时未及完成的历史著作。波利奥肯定撒路斯特作为史家的地位,赞成其古朴沉稳的写作风格,即使这种风格也许冷峻粗犷(durusetsiccus)。李维与撒路斯特的写作风格截然不同,李维不赞成运用古老粗陋的词汇,认为晦涩难懂并不会使演说词显得严肃庄重,批评撒路斯特翻译修昔底德的警句以及其译文有损警句的真正内涵。波利奥所谓的“帕塔维乌姆风格”暗藏贬义,这一方面可能源于他本人在山南高卢的政治经历,来自他对帕塔维乌姆城的不满;另一方面,他和李维两人的创作风格差别极大,两人风格偏好的不同影响到他对李维的评价;再者,波利奥的贬低之词可能也有几分根据,帕塔维乌姆人的个别拼写有特殊之处,“帕塔维乌姆风格”可能说的是当地口音或拼写,暗指李维的用词夹带地方方言。
李维的战争主题
希腊罗马历史学家往往都会在史书开篇开宗明义地说明本书主题的宏大卓然,这些人类历史上的丰功伟绩需要有人保存下来,这些伟大人物的事迹值得人们追念铭记,历史书写的必要性,历史学家的使命感,甚至读者阅读历史的必要性,这一切在对伟大主题的彰显中变得不言自明。
宏大主题是历史学家著史的重要动力。希罗多德留给后世历史学家的一笔重要遗产便在于凸显战争主题的宏大壮阔和举足轻重。他在提到特洛伊时,已经隐含着媲美诗人荷马的伟大抱负,期望自己的主题像荷马流传下来的作品一样享有同样的赞誉。在《历史》开篇有提:“哈利卡纳苏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所得发表于此,以便对往事的记忆不会因为时间而被人遗忘,以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丰功伟业,尤其是他们彼此为战的原因,不会失去光芒。”希腊人和异邦人的战争和事迹值得书写下来,永世留存。
修昔底德在对主题的阐述中与希罗多德和荷马一脉相承,他以最高级的表述形式突出伯罗奔尼撒战争在持续时间和惨烈程度上是前所未有的,称这场战争“延续时间极长,战争过程中希腊人经历的灾难是从前任何时候都不曾经历过的。许多城市沦陷或荒凉,有些是蛮族所为,有些则是希腊人兵戈相向所致。从没有如此多的人流亡异乡,从没有如此多的人生灵涂炭,不论在战争过程中,还是战争和内乱的结果中”。他在强调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战争的同时,仅用一句话便把希罗多德花费近五卷篇幅记述的希腊和波斯的战争一笔带过:“过去最伟大的成就是波斯战争,但很快由两场海战和两场陆战决定了战局”,以薄古厚今的方式凸显自己的主题意义不凡,也间接宣告了自己的历史著作出类拔萃。
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不仅强调战争的惨烈程度和惨痛结果,他最为关注的是战争带给希腊罗马世界的普遍联系,因为在他有生之年见证了整个希腊罗马世界的统一。波利比乌斯对主题的阐述既是历史性的,也是史学性的,既说明了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趋势,“人类居住的世界”尽在罗马的掌握是“一件从前绝无仅有的事”,又说明了当罗马超越从前所有的帝国,他书写的历史便超越了某一特定主题,而成为一部涵盖整个希腊罗马世界的世界史。这部世界史在对罗马帝国和从前各帝国的比较中,凸显出书写主题的恢宏壮阔,罗马帝国不论在地理范围还是在时间跨度上,都超越从前的所有帝国,他笔下的这部世界史具有了超越从前所有历史著作的隐含意思。他称:“我计划书写的这一时期所呈现的景观是多么让人叹为观止,如果我们将罗马的统治与过去最著名的那些帝国比较,这将更为明显。波斯人曾在一段时期拥有大帝国,但却明目张胆越过亚细亚边界,以至于不仅危及帝国的安全,而且危及自身的存亡。拉西第梦人多年里争夺希腊霸权,之后花很长时间获得独尊地位却仅保持了12年。马其顿对欧罗巴的统治从亚得里亚海拓展到多瑙河,那里似乎是陆地上无足轻重的部分。后来马其顿将波斯帝国取而代之,成为亚细亚霸主。尽管马其顿帝国现在被认为在范围和实力上是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但他们把人居世界的大部分置于帝国之外。他们从未试图占领西西里、撒丁岛或阿非利加。说实话,他们从未听闻欧罗巴西部最好战的民族。但罗马人不是把部分世界,而是把整个世界归于自己的统治,拥有一个不仅比从前任何一个帝国更广袤,而且不需要未来惧怕对手的帝国。”波利比乌斯的《历史》因为记载和探究成就这个无与伦比的罗马帝国的原因而具有了重要的历史价值。
古典作家通常把战争看作影响世界历史发展的积极因素,这些恢宏的战争叙事不仅永远载入人类的文明史册,而且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罗马的征服战争成就了一个空前强大的帝国,书写这样一个伟大帝国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对李维而言,其主题是广博一体的,一部从蕞尔小邦成长为辽阔帝国的历史,“我记录从城市建立以来罗马人的功业,我能否算是完成了一件值得做的事,我不太清楚……无论如何,我也尽我个人之能置身于世界上最优秀民族业绩的记述,那将是一种乐趣”。罗马建城以来的漫长历史是一个宏大的主题,涉及幅员辽阔的帝国的成长历程,涉及这个优秀民族的丰功伟业,对李维而言,选择这一主题本身便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就第三个十卷的主题汉尼拔战争而言,这场战争名垂青史,李维强调了两个强大对手之间分庭抗礼,决一雌雄,战局变化多端,危险重重,是世所罕见的,“在我著作的这一部分,请允许我像多数史家在其全部著述的开篇所声称的那样预言,我将记述的战争——迦太基人在汉尼拔率领下对罗马人民的战争——是所有发生过的战争中最令人难忘的。因为没有哪个势力如此强大的城邦和民族彼此交战,它们也从未如此骁勇善战,双方并非不谙战事,而是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积累了经验,战争的偶然性如此多变,结局如此不详,以至于那些获胜的人面临的危险更大”。罗马人和迦太基人都处在实力的巅峰,都具有精湛的作战技术,双方的战争规模前所未有,战争结局事出偶然,战事的过程跌宕起伏,李维以这段十卷卷首的序言吊足了读者的阅读胃口。马其顿国王腓力了解到迦太基在意大利势如破竹,决定与汉尼拔缔结友好条约,李维称“这是世界上两个最富有民族之间的战争,吸引了所有国王和所有国家的注意”,突出这场战争的规模级别和世界影响。
在完成第三个十卷的记述之后,李维在第四个十卷的开篇再次总结了汉尼拔战争的宏大规模和这段历史书写的重担:“我也为写到布匿战争结束而释然,仿佛我本人共担了劳作与危险。对于一个贸然立誓书写罗马全史的人来说,他根本不应该对从事如此巨大的任务的一部分而感到疲惫,然而,当我想起有多卷记述了这六十三年——从第一次布匿战争开始到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的时间段,从建城到开启与迦太基人的第一次战争的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Appius Claudius)任执政官的四百八十七年,我已经想象得到,像被近岸的浅滩吸引、涉水入海的人,无论我走了多远,我正被拉向更广的深渊,这项任务变得更大,而我之前完成的各部分似乎变得更小。”十卷里对汉尼拔战争的记述和这场举足轻重的战争一样,规模超乎想象,这可能是其他历史学家整部作品的主题,但在这里只是李维“巨大任务的一部分”。宏大的主题形成一种强大的召唤,召唤他去记录这场伟大的战争,哪怕这项任务如此艰巨,让他疲惫不堪,但他仍从撰史的辛劳中体会精神的安宁自在。
李维的撰史动力除了在于主题的宏大,还在于撰史本身为他带来愉悦,这种带来精神慰藉的说法在古典史家中独一无二。李维说历史主要是出于他个人的愉悦而从事的,与他的个人感受不同,读者大多不关心古代史,他们更喜欢阅读近代史,李维勇敢地宣称他所有努力换来的嘉奖将是对当下的弊端避而不见。他的写作动力在某种程度上是极为个人的,他享受置身于撰史之中的惬意。
李维撰写历史秉持着严肃的初衷,即通过罗马历史教化人心。经常被援引阐述李维治史目标的前言第10节有言:“在认识往事时,尤其有利而有益的在于:你可以注意到载于昭昭史册中各种例子的教训,从中为你和你的国家吸取你所应当仿效的东西,从中吸取你所应当避免的开端恶劣与结局不光彩的东西”。这句话提纲挈领,申明主旨,表达出作者想以罗马道德兴衰的事例启迪人心的情怀。“注意到……各种例子的教训”一句的意象内涵丰富,读者的观察对象在这里指李维的《建城以来史》,即他在前言第6节中所说的“纯粹的历史记录”(incorruptis rerumgestearum monumentis)。“纯粹的”(incorruptis)意味着历史记述既是不朽的,流传后世的,也是真实可信的。同时,“纯粹的”一词也具有医学的意象,意指医学意义上“未受污染的”,这里更多指的是李维在史学意义上的求真主张,不以虚构杜撰有损历史的真实。
“希腊罗马世界的历史写作仍是以修辞法则为根基的文学事业,是建筑、艺术、钱币、戏剧、词源研究、铭文、习惯、口头传说、地形研究所有这些事物的相互作用形成了罗马人的历史感。这些事物是‘monumenta’,也就是意在保存人们对伟大功业(resgestae)记忆的图像、文字。”李维的历史可以视作一座纪念性的丰碑(monumentum),其纪念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纪念过去列祖列宗的丰功伟业;二是对当代和后世罗马人提出警示告诫。前言第6和第10节中的“记录”(monumentum)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是指李维书写的罗马历史,他想要当代人从学习历史中接受历史中的道德教训,借此医治时代的痹症;另一方面是指李维写就的《建城以来史》一书,这部著作是“记述世界上最优秀民族业绩”b的结晶,是归类于“纯粹的历史记录”的典范,是李维“从事的工作”(negotiisuscepti)和“伟大工作”(tantumoperis)的丰硕成果。因此当我们回顾第三个十卷的序言,李维是这样评价第二次布匿战争的,“我将记述的战争是所有发生过的战争中最令人难忘的”。形容词“令人难忘”(memorabile)照应的是纪念性的丰碑(monumentum),第二次布匿战争史是罗马历史上值得后世纪念的崇高丰碑,对这场战争的历史书写是李维《建城以来史》这座文本纪念碑上的瑰丽明珠。李维撰写的罗马史是经久不衰、垂诸久远的纪念碑,其经久不变的旨归便是以这部作品帮助支撑起“大厦将倾的罗马国家”,这与医学意象上“不受污染”所传达的信息是一致的,期望罗马国家健康发展,永葆青春。
战争是古典史家极为钟爱的主题,前所未有的战争规模和意义影响成为古典史家书写序言时的老生常谈。从希罗多德开始,西方古代史学便延续了强调宏大主题的书写传统,值得铭记的历史人物的丰功伟绩构成了对历史编纂的强大召唤。历史学家追随这一召唤,历尽艰辛完成书写历史的宏大任务,他们怀着保存人类功业的崇高使命记录下那些值得记录的人物和事迹,李维以第二次布匿战争的主题向读者展现了自己作品的同一特征。罗马和迦太基两国的强强对决,战争场面的波澜壮阔表现出这部历史作品的可读性,这场战争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决定了这部历史作品的必读性。蕞尔小邦的罗马在与外族的激烈交锋中成长为大帝国,甚至发展到“苦于自身宏大的程度”,宏大主题背后的深切忧虑也在李维的作品中隐约显现出来。
(本文摘自王悦著《战争与史学家:李维历史书写中的汉尼拔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3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