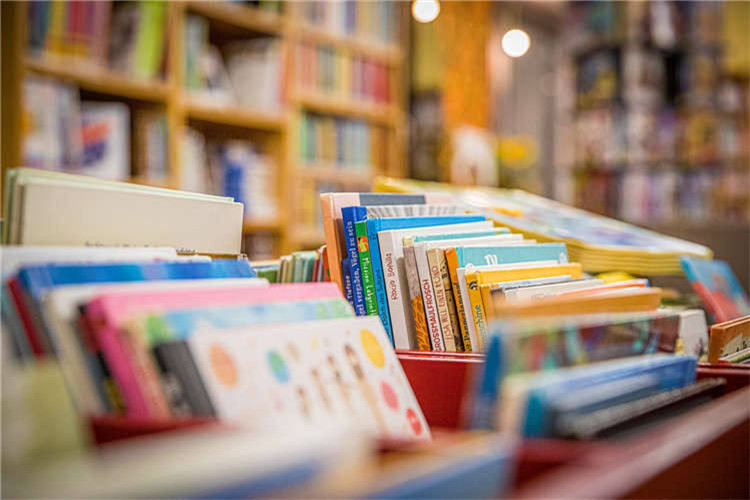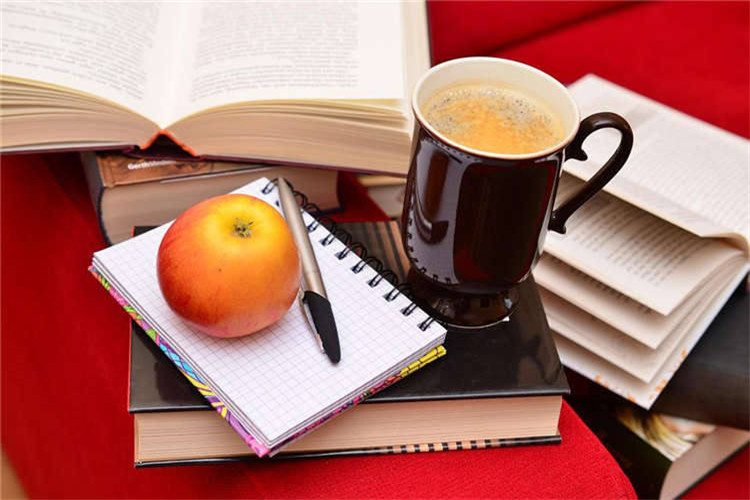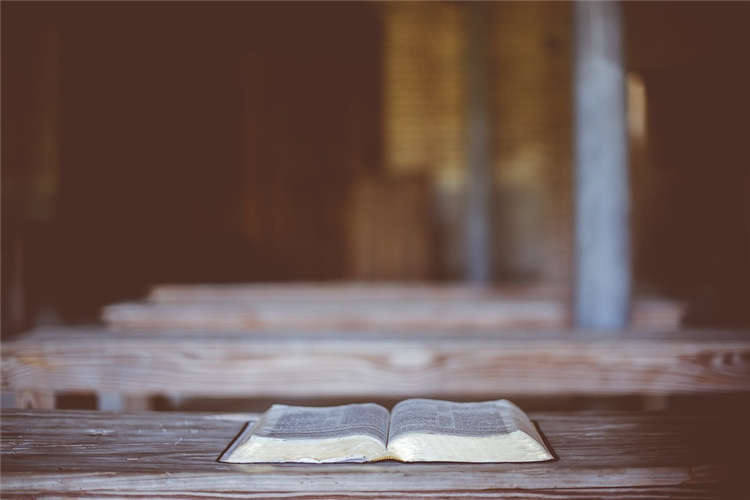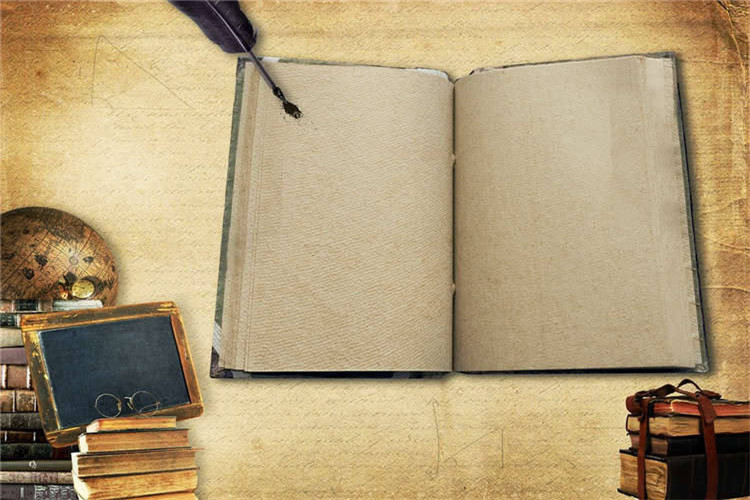《通勤梦魇:东京地铁与机器的人类学》,迈克尔·菲什著,孟超、桑元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384页,69.00
在东京各大铁路车站又或是地铁站,时常能看到这么一幕:几位外国人对着挂在墙上复杂如蛛网一般的电车运行图“吃手”,又或是不知所措地一会儿低头看着手机,一会儿抬头望向墙上的运行图。日本东京都市圈作为全球最大的都会区之一,其境内轨道交通网络的复杂程度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数一数二的。目前,东京都市圈内的轨道线路有近一百六十条、运营轨道的总里程超过四千七百公里,每天运送的乘客超过四千万人次(不同运营主体间换乘会被重新计算)。而在东京地区内,每平方公里就有零点二四座车站,可见其网络的密度之高。
各式各样穿梭在摩天大楼与低矮民房间的电车,穿着西装衬衫或制服等着上下车的乘客、拥挤但却有序的人群都己经成为东京这座巨大都市的日常景观。每天都有数百万人乘坐电车穿行于城市的大街小巷,密布各处的轨道交通线早已成为东京这座巨型都市的血管。电车网络的延伸发展与都市扩张相互促进,正如血管与肌体的关系一样。电车线沿线催生出新的社区和商业中心,城市规划也往往围绕车站展开,形成“站城一体”的独特布局,塑造了东京市民生活的基本样貌。
芝加哥大学人类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迈克尔·菲什通过细致的田野调查结合他个人在东京的生活经历,在《通勤梦魇:东京地铁与机器的人类学》(An Anthropology of the Machine:Tokyo’s Commuter Train Network)一书中对东京的电车通勤网络进了一番别开生面的人类学考察,探究了东京的轨道交通系统是如何与都市发展以及市民生活交织在一起的。他敏锐地指出尽管东京的电车系统经常超负荷运行,但却依旧能保持高效运作,而这得益于列车运营方和通勤者之间的“协作”。这种协作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更涉及到社会和文化层面的互动且重新形塑了都市人的生活状态,例如“时间感”。
众所周知,东京的电车班次极其紧密且以准点率高而全球闻名。这种高度制度化的电车时刻表塑造了东京市民的时间感。上班族们的生活作息被电车时刻所规范:清晨赶首班车,深夜的“终电”(末班车)则决定了人们归家的时间。这些均已成为都市人生物钟的一部分,甚至连加班与夜生活也都是围绕电车时刻表展开的。有趣的是,迈克尔·菲什还对东京市民的一项“特技”印象深刻。那就是在车厢座位上打盹的乘客似乎总能在自己该下车的时候及时醒来,在睡眼惺忪中拖着身子挤出车厢。在菲什看来,这几乎就是一种“现代人与机器关系的范例”,通勤的乘客在日常的出行中被“驯化”成服从机器操作指令的客体,甚至还将其内化成一种潜意识。
繁密的电车时刻表让人们对时间变得格外敏感——等车时屏幕上倒计时的几十秒,似乎都能将人们内心的时间体感放慢、拉长。东京的通勤族们往往能够精确记住自己的通勤时间,比如从家门口到公司“刚好55分钟”,又或是换乘衔接必须在“90秒内”完成等等。打开日本本地的交通导航软件,甚至可以告诉你从电车的第几节车厢下车,换乘时可以更快、更方便。又如菲什例举的那类通勤者,他们每日从池袋站或新桥站出发,在涩谷、新宿有或是大手町换乘,他们每日的步行路径、站点选择、靠门方向都精准一致,日复一日,从不出错。他们的身体已经“自动化”,与电车系统形成了默契的协同节奏。这类对时间的精确感知,源自长期规律的电车通勤体验,这都让东京的通勤族们仿佛生活在时钟齿轮般精准的节奏中。然而,当这种节奏因故被打乱(例如电车延误)时,人们多会产生强烈的不安乃至焦虑。由此,菲什在本书中引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间隔”(interval)。
所谓“间隔”, 菲什将之解释为电车时刻表与实际运营之间的差异。显而易见,这种差异是必然存在的,可以是意外事件导致的延误,也可以是系统本身超负荷的结果。面对这种无法避免的“间隔”,东京电车网络却总能通过一系列调整来保持运行。这种调整不仅是网络运营方(电车公司)单方面努力的结果,也仰赖于通勤者的配合,而这恰好体现着人与机器之间互相协作的关系。菲什在书中还借用了法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西蒙栋所提出的另一个概念,即所谓“不确定性边际”(margin of indeterminacy)。 在东京电车网络中,每天都在上演着这种“不确定性边际”的情景:司机根据乘客上下车速度略微调整发车时间、乘客根据实时信息更改换乘计划、工作人员处理突发事件等等。在这些细小的时空“间隙”中,人和机器共同作用,维系着这个东京电车网络——这个庞大系统的“暂时稳定”。在拥挤狭窄的车厢中,人与人之间却能维持某种微妙的平衡,既身处公共场合又维持着个人的空间。而这也是日本文艺作品特别喜欢借用的意象,例如《新世纪福音战士(EVA)》中多次借用电车车厢的场景来刻画男主角碇真嗣的心理状态。电车车厢作为一个公共但封闭的空间,亦如碇真嗣与他人同处一个城市却又难以互动的状态。
菲什在书中将东京的电车网络描述一个精密运行在“接近负荷极限状态”的机器系统,乘客需要将自己努力“嵌入”这个高速运转的系统并时刻提醒自己“不要给别人添麻烦”。随之孕育而生的便是一套有日本特色的“电车礼仪”。凡是在日本搭乘过电车的人,都应该会对车厢内的安静与沉默印象深刻。在车厢打电话或高声喧哗都被认为是一种严重失礼的行为,尤其是在上下班的高峰时间。用菲什的话来说,便是“沉默是日本电车礼仪的最高表现形式”。此外,为了迅速高效地上下车,如何在车门口排队自然也是这种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保障这个常年高负荷、乃至超负荷运行的交通网络能够持续运行下去。换言之,在巨型都市的“通勤梦魇”中,忙于通勤的乘客们“进化”出一种应对之道与群体默契,如此才能维持着日常生活的出行效率与秩序。这正是菲什在书中为我们提供的有趣观察角度。显而易见,任何生活在大都市的人对于《通勤梦魇》所描绘的情景都不会感到陌生。东京电车所构筑的都市通勤系统,只是大多数城市与人类生存状态的一种缩影,因此这也赋予了菲什的研究更多价值和意义。
在《通勤梦魇》描绘的图景里,电车网络是都市赖以存续的机器设施,其平稳运行离不开人的配合与适应,而人的生活方式也被这套机器系统所塑造和定义。于是乎,东京人的通勤之路本质上是一种“人机组合”的产物,人与电车网络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人们的生活节奏与机器同步,他们身体感官借助机器的技术而延伸。不过,菲什并不认为这仅仅是一种刻板印象中机器或技术对人的“异化”,更不是在提倡一种重归田园式的“反技术”论调。东京的通勤者并非只是被动接受技术系统的安排,反而是通过日常的行为和习惯,积极参与到系统的运作之中。这种关系是彼此互动、互为因果的。换言之,菲什希望强调的是当下人类的生活方式是人与技术系统共同构建的。那些奔波于池袋、新宿、涩谷、新桥各个车站之间的通勤者,绝非只是一个庞大系统的小齿轮,而是承载着主体性的鲜活生命。他们虽然被这个机器系统规训,但也反向定义了这个机器系统的运行法则。从哲学层面看,身处东京电车系统中的人在自觉间正扮演着某种“赛博格式”(Cyborg)的角色——即人与机器的混合体。就这点而言,当前社会似乎已经与《攻壳机动队》等赛博朋克风故事里所呈现的未来,在本质上别无二致,无非是程度上的区别而已。又如菲什所言“我们没有回头路可走”,但我们可能需要认识技术、机器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哲学家、人类学的视野,可以观察到技术系统与人类生活如何互相形塑,赛博格式的人机共生状态如何在日常通勤中化为日常。
繁忙的东京地铁
最后顺便一提,本作的中文译名为《通勤梦魇:东京地铁与机器的人类学》。副标题中“东京地铁”的翻译表述可能不太准确,极易让人误解或心生困惑。因为东京的轨道交通网络是由多个彼此独立的运营主体所组成的。中文语境中的“地铁”根本无法对应东京的轨道交通网络。
例如环绕东京市区的“山手线”就属于“东日本旅客铁道会社”(即“JR东日本”),而“JR东日本”又是东京都市圈内最重要的铁路公司,拥有众多重要的主干线路。至于“东京地铁”则是另一家公司:“东京地下铁株式会社”(即东京Metro),运营着东京市内九条地铁线路。实际上,除了“东京Metro”外,东京还另有一个“地铁系统”即由东京都交通局运营的“都市地下铁”,共有四条线路,与“东京Metro”是彼此独立的。除此之外,东京都市圈内还有众多其他铁路公司,如“西武铁道”“东武铁道”“京王电铁”等,有几十家之多。由这些不同企业运营的轨道交通线路,共同构筑起了东京都市圈巨大而复杂的电车通勤网络,而副标题中“东京地铁”的翻译很容易让中文读者产生似是而非的误解。其实,作者迈克尔·菲什对此有着充分的认知,所以本书英语原文的表述是“Commuter Train Network”,因此译为“通勤轨交”可能更精准且符合原义,或者干脆借用日语汉字的意涵译为“东京电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