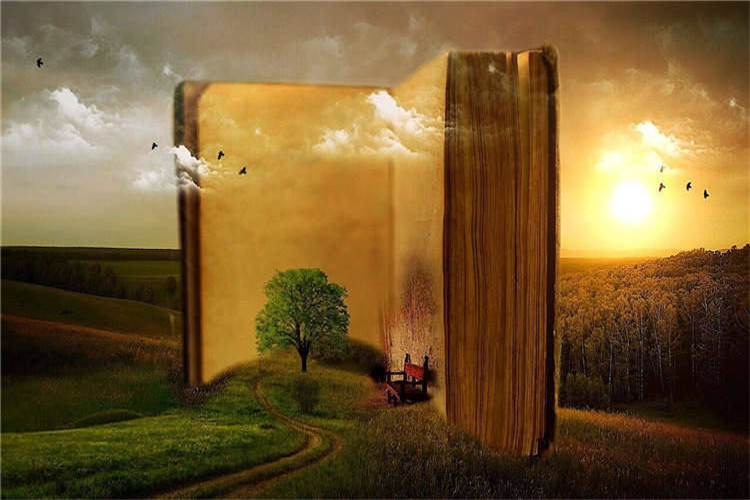作为一座国际大都市,上海不仅承载着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扬,更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万花筒。海纳百川,中外交融,在这里,古老与现代交织,东方与西方交融,共同塑造出这座城市独有的文化底蕴。
“建投读书会·澎湃北外滩”第十三季以“东西汇流”为主题,选题从“上海作为一座因河而生、连江入海的国际大都市,不仅承载着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扬,更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万花筒”出发,选取了音乐、电影、体育、建筑、戏剧、器物六大方面,与读者们共读上海城市基因中的生机勃勃与包容开阔。
本期为第六场,由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朝晖主讲。
前言
这场报告的题目叫做《全球物品》,我用“全球物品”来指代中国古代的瓷器,特别是明清时候的外销瓷。这个题目受到了耶鲁大学一位教授前两年出版的一本叫做Global Objects的书的启发,主要是通过物品讲全球的连接以及物品反映的全球艺术史。
中国瓷器很早就开始了外销的历程。有一艘非常有名的唐代沉船“黑石号”,它告诉我们,早在晚唐的9世纪,中国瓷器已经开始大量外销。在早期外销阶段,中国瓷器主要在亚洲和非洲流传。但到了16世纪,中国瓷器行销的地域更广,到达了欧洲、美洲,真正成为了全球性的商品。但比起简单地介绍明清外销瓷的历史,我更希望通过明清外销瓷,来看东西方文化在早期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展开互动。本次分享的内容主要针对中欧之间的交流。
我首先会讲中国瓷器在欧洲的传播,包括中国瓷器最早什么时候到达欧洲、如何传播到欧洲。
第二部分,通过讲解从西方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绘画作品中的东方瓷器,特别是青花瓷器,来看中国瓷器的对外传播和交流。中国瓷器到达欧洲后,引发了欧洲的中国热,促进了欧洲的陶瓷模仿,刺激欧洲生产出真正的瓷器。
第三部分会以代尔夫特陶瓷为例,谈谈欧洲瓷器对于中国明清外销瓷的模仿。中国瓷器到达欧洲以后,欧洲除了接受,还出现了一种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改装和重新装饰。我会以金属镶嵌为例,来讨论异文化物质到达了欧洲后是如何被接纳、改造的。
中国瓷器输入到国外,最初的情况是中国生产什么,当地就接受什么。但随后出现了另外一种现象——当地提出需求,要求中国按照一定样式来设计。所以最后我们会以普朗克“执伞妇人”瓷盘为例,来看明清外销瓷中的欧洲设计。
一、引言:中国瓷器在欧洲的早期传播
中国瓷器最早何时到达西方、到达欧洲?研究陶瓷史的,尤其是研究外销瓷的老师,都对左边这件青白瓷器不陌生。它的器身上装饰有璎珞纹的开光,内有花卉纹。右边这张水彩画,画的就是这件器物。这是一件景德镇生产的元代青白瓷。
这件青白瓷,是目前我们所知最早的有著录的输入到欧洲的中国瓷器。那么它的拥有者是谁?追溯历史,最早的拥有者是拿波里及耶路撒冷的国王查尔斯二世,他下令为这件器物加装了金属。这件器物后来被查尔斯二世传给了他的儿子,匈牙利国王路易一世。路易一世在金属上刻了家族的徽章和文字,然后把它送给了查尔斯三世,祝贺他1381年登基。这件器物后来还传到了法国宫廷,成为法国路易十四的王太子的个人财产。又再流传到法国贵族手中,金属镶嵌上又多了贵族的徽章。后来传到了英国,最后被拍卖,进入爱尔兰国家博物馆。在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V&A)工作的刘明倩老师写过一本书,叫做《从丝绸到瓷器:英国收藏家和博物馆的故事》,书里呈现了这件元代青白瓷器的流传经过。
元代青白瓷玉壶春瓶,爱尔兰国家博物馆藏,本篇相关图片素材由刘朝晖老师提供
纸本水彩画,1713年,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以往认为,中国瓷器最早在元代到达欧洲。但是新的研究发现,实际上中国瓷器进入到欧洲的时间要更早一些。前些年,中国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和英国杜伦大学考古系合作,对西班牙一批出土的瓷器进行了整理,认为最早在唐、宋时期,中国瓷器就进入了欧洲。在他们发表的文章所包含的材料里,我看到一件宋代耀州窑的青瓷,它的年代毫无问题。但我个人对文章里提到的唐代的中国瓷器有些疑惑。
从器物底部来看,这件白瓷的玉璧底确实是唐代中国瓷器的特征,但里面还刻有划花,这不是唐代白瓷的特征。所以我有一点怀疑这件器物会不会是伊斯兰陶瓷对中国瓷器的模仿,因为伊斯兰白陶有模仿中国的白瓷,而且会有划花。当然我也跟这篇论文的执笔者之一、杜伦大学的张然教授有过交流,他认为还有一种可能性——会不会是中国的白瓷到了伊斯兰地区或欧洲以后,新增了这些划花。因为没有亲自上手看过这些器物,所以我现在对这件器物只是有一个问号。报告中所谓的“唐代”,我觉得还需要有更多、更坚实的证据。
报告中提到的“唐代白瓷”残片图
宋代青瓷碎片图、复原图
讨论过中国瓷器最早传播到欧洲的年代后,再来看这些瓷器是怎么到达欧洲的。大航海时代之前,只有极少数的中国瓷器能够到达欧洲,而且不是通过直接的商业贸易,而是通过中东的转口贸易,或是通过外交馈赠的方式。据记载,1447年,埃及马穆鲁克王朝苏丹将三件瓷盘送给法王查理七世;1487年,埃及苏丹亦以瓷器馈赠意大利美第奇家族;1547年,弗朗索瓦·德·菲梅勒男爵受法国亨利二世的指派,作为外交使节前往君士坦丁堡觐见苏莱曼一世,返程时将这件永乐青花执壶携回法国。
青花缠枝牡丹纹执壶明永乐(1403-1424)法国吉美博物馆藏
二、写真:中国瓷器在西方绘画中的呈现
从西方绘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瓷器在西方社会里是如何被接纳或被反映的,还可以看到中国瓷器进入欧洲的阶段性。之前已经有学者研究了西方绘画中的宗教图像,我把这些材料整合起来,加上与中国瓷器的对比,结合起来进行展现。
我来展示一些绘画作品。第一幅是绘制于1460年左右的《圣母子像》。把画面中有关瓷器的局部拿出来,可以看到画中瓷器的器型,跟台北故宫馆藏的明永乐官窑的青花花卉莲子碗很接近。在永乐时期,这类瓷器会作为宫廷赏赐到达伊斯兰世界。图中画的这件瓷器有可能是这一类产品。因为在15世纪后半叶的陶瓷器上绘制有这种蓝、白花色的,要么是中国的瓷器,要么是伊斯兰地区的陶器。
《圣母子像》(约1460年)与青花花卉莲子碗对照
再过40年,《耶稣给门徒洗脚》这幅画里的瓷器,如果和中国瓷器进行对比,相似度比刚才那件还要高得多。基本上可以判断就是明代初年的官窑瓷器。东方瓷器在宗教题材的西方绘画中的出现,体现了这些器物当时的珍贵性。
《耶稣给门徒洗脚》(1500年)与瓷器对照
再看这幅《三王朝拜》。三个东方使者手里拿的器物都是宝物,其中居前的老者手里拿着青花小杯,里面放着金币。有学者认为这件器物跟明初的永乐压手杯有些形似,但从图像来看,还是有差别的。关于这件器物到底是中国的青花瓷器,还是伊斯兰的陶器,比较难确认。但画家画的肯定是一件东方器物。最近还有研究者讨论这幅画作,认为有可能是画家曼特尼亚看到过中国和伊斯兰的青花瓷器,然后经过想象画成此件器物。
15世纪中期开始,中国的青花瓷器,特别是民窑青花,大量通过走私贸易输出至各地,欧洲绘画中瓷器的身影也更多了。
《三王朝拜》Adoration of the Magi (1495-1505)安德烈亚·曼特尼亚(Andrea Mantegna,1431~1506)
《三王朝拜》中的瓷器及对照
比如《诸神之宴》所画的青花,我们完全可以用实物来对应,极其相似。
•《诸神之宴》(1514年,乔瓦尼·贝利尼)及瓷器对照
这幅葡萄牙的绘画作品《圣母领报》里绘有一件蓝白罐子,如果用中国的瓷器来对比,与嘉靖年间的青花鱼游荷池纹罐很接近。
《圣母领报》约1535-1540葡萄牙加西亚·费尔南德斯
青花鱼游荷池纹罐明嘉靖(1522-1566)江西省博物馆藏
到了明代晚期,地理大发现以及大航海时代来临后,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人先后来到亚洲,“加入到传统的亚洲贸易网络中,并通过长距离的跨洲洋贸易将其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中国瓷器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当中国瓷器成为东西方贸易的重要商品,开始大规模销往欧洲后,欧洲的王室、贵族纷纷建立瓷器厅或瓷器室,珍藏并展示中国瓷器,以彰显权势和财富。1670年,法王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内修建了著名的托里阿诺宫,专门陈列其珍藏的中国青花瓷。英国王后玛丽对中国瓷器相当喜爱,美国旅行家迪福在1724年出版的《回忆录》称:“玛丽王后的习惯是在宫殿里陈列许多中国瓷器,甚至达到惊人的程度。我们可以看到,在橱柜以及家具的最高顶上也放着架子,架子上陈列着珍贵的中国瓷器。”
德国的德累斯顿茨温格宫里摆放了波兰国王及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都二世的收藏,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热衷于收藏东方瓷器的奥古斯都二世以600名萨克森近卫骑兵与普鲁士交换的151件中国瓷器,被称为龙骑兵罐。葡萄牙里斯本的桑托斯宫也有非常有名的瓷器厅。桑托斯宫曾为葡萄牙国王的宫殿,现在是法国驻葡萄牙大使馆的官邸,瓷器就放在这个屋子的穹顶上。这类装饰在伊斯兰世界也能够看到,如伊朗的阿特比尔寺,在建筑穹顶和壁龛里摆放的全是中国的青花瓷器。不知伊比利亚半岛是否是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而把瓷器装饰在穹顶上。
德国德累斯顿茨温格宫
龙骑兵罐
葡萄牙桑托斯宫(Santos Palace)瓷器厅
在佛兰德斯地区,画家扬·勃鲁盖尔(Jan Brueghel the Elder)开创了一种欧洲“艺术收藏”类别的绘画,称为艺术馆(Kunstkammer),或珍宝馆(Wunderkammern),是佛兰德斯地区独有的艺术种类。在这些绘画中,可以见到当时最主流的中国外销瓷——克拉克瓷器。
南开大学的吴若明老师在2022年发表了论文《普拉多的柜子——17世纪克拉克瓷的异域传播与镜像呈现》,对鲁本斯与扬·勃鲁盖尔创作的绘画《视觉的寓意》(1617—1618)及其中的瓷器做了研究。这幅绘画作品是为了赠送给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家族大公夫妇阿尔伯特(Albert)和伊莎贝娜(Isabella)而创作。作品展现了艺术馆中丰富的艺术收藏,其中有不少来自东方的克拉克瓷器,包括盘、碗、军持、玉壶春瓶等器型,反映了17世纪早期作为奢侈品的中国瓷器在贵族府邸的收藏。
《视觉的寓言》及局部图
《视觉的寓言》瓷器对照图
之前我们讲到西方绘画里,中国瓷器最初都出现在宗教题材中,承担了类似圣物的功能,但到这一时期,我们看到它成为了一种收藏的写真。在17世纪,中国瓷器在欧洲除了用于陈设,还会作为存放食物等物品的器皿,无论是《静物:水果与青花盘》,还是大画家维米尔的名画《窗边读信的少女》,都可以看到这种展现。
《静物:水果与青花盘》与瓷器对照图
《窗边读信的少女》与瓷器对照图
我还想分享法国十七世纪静物画家雅克·林纳德(Jacques Linard,1597-1645)在1627年绘制的一幅题为《五感》的静物油画,这是已知最早的苏东坡《赤壁赋》图像在欧洲的记录。画家所描绘的中国瓷碗,很可能先由荷兰人进口,再通过法国商贩运到巴黎。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已大获成功,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大陆最大的中国产品销售地。由于法国没有直接参与中国瓷器的海上贸易,所以其宫廷和上层贵族多通过荷兰间接获得中国商品。巴黎的圣日耳曼和圣罗兰形成了中国商品的大型集散市集,而林纳德就居住在巴黎的圣日耳曼区。这只瓷碗很有可能被林纳德拥有,亦出现在画家另外的两幅静物画中。
《五感》与瓷器对照图
三、欧洲陶瓷对中国瓷器的模仿:以代尔夫特陶瓷为例
从欧洲绘画图像里,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中国瓷器的再现。欧洲人喜欢中国瓷器的同时,也非常想知道中国瓷器是怎么制作的,进而去模仿生产。我们先来看看欧洲的一些仿制。中国瓷器在文艺复兴时期已经流传至意大利,当地采用钴料仿制青花。因为中国唐代、元代的青花瓷器用的钴料都是从西亚进口的,所以跟伊斯兰世界有密切往来的欧洲能拿到同样的原料也不意外。意大利美第奇家族也仿造中国瓷器,但做出来的是软瓷,因为其火候温度还不够高。这件美第奇软瓷罐也模仿了中国的青花瓷器,可以看到,它装饰中缠枝花卉的画法具有东方味道。其底部画的是穹顶图案,应该是佛罗伦萨大教堂,另外还写有一个字母“F”,推测是弗朗西斯一世或佛罗伦萨的代称。
德鲁塔仿青花釉陶壶16世纪上半叶意大利佛罗伦萨巴杰罗国家博物馆藏
美第奇软瓷罐1575年
荷兰代尔夫特陶瓷是白地蓝彩的锡釉陶器,盛产于荷兰代尔夫特。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在欧洲掀起中国热的背景之下,荷兰代尔夫特的陶器厂用本地的锡釉陶工艺仿制中国、日本外销瓷。它将源自东方的装饰纹样与适应欧洲人生活习俗的器物造型结合起来,在欧洲市场获得极大成功,并引起欧洲各国的竞相模仿。荷兰代尔夫特与该国其他制陶中心生产的这种锡釉陶器,以及别国的仿制品都被称为“代尔夫特陶器”。
我挑选了一些代尔夫特陶器和中国瓷器的对比图供大家辨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件中国器物,它的花卉纹饰是郁金香图案,这其实是荷兰人特别要求定制的。现在郁金香是荷兰的国花,但它最早流行于伊斯兰世界,是后来传到荷兰的。而同样造型的代尔夫特陶器上,画的是欧洲人想象中的中国人形象,以及郁金香图案。
代尔夫特蓝陶执壶和景德镇青花执壶对照
还有这种用来装杜松子酒的瓶子,1件是代尔夫特生产,另1件是景德镇生产,光从照片来看很难辨认。
代尔夫特方瓶及与景德镇青花方瓶对照
还有代尔夫特仿制的清代康熙青花花觚。
代尔夫特蓝陶对康熙瓷器的仿制
欧洲不仅模仿中国瓷器,也在这一过程中进行自己的再创造,如根据中国的意象制作的这样的盘子。
模仿中的再创造
终于在18世纪初,德国麦森创烧出了真正的瓷器——欧洲最早的瓷器。
四、明清外销瓷在欧洲的改装和重饰:以金属镶嵌为中心
在欧洲,来自中国的外销瓷不仅会被使用,也会被改造。其实,中国瓷器在本土也会经历改装。如秘色瓷的金银平脱:五代北宋时期,一些瓷器的口沿会被镶嵌上金银。此举的目的多被解释为用金银提高器物身价,或解决覆烧所带来的“不堪用”的情况。对中国瓷器的再装饰,在中东和欧洲都有深远而广泛的传统,并衍生了丰富的类型和鲜明的特色。
“海上丝绸之路”,也被称为“陶瓷之路”,最早是由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在《陶瓷之路》中提出的。书中写到了位于旧开罗的首个伊斯兰首都福斯塔特出土了大量的中国瓷器,其中有一件瓷片上有黄褐色的彩绘。这不是在中国就制作完成的,而是宋代白瓷运到伊斯兰世界后经历了加彩(Over-decorating)的工序,这种彩色装饰叫做Luster彩。
中东的再加彩
欧洲也会对中国瓷器进行再加彩。以普莱勒斯为代表,其采取黑色锡绘工艺,沿用西方的用色与画法,在中国瓷器上进行再绘制,画面内容却充满东方风情。
欧洲的再加彩
这种画法与题材在玻璃器的加彩中也频繁出现,应该是有流行的绘画粉本。例如图中这件青花加彩堆塑龙纹人物图瓶,充满了欧洲人对中国的想象。这是根据1670年在伦敦出版的《日本国志》中的插画,绘制了一个男子的形象,还画了中国的宝塔。
荷兰加彩青花加彩堆塑龙纹人物图瓶康熙
中国的宝塔在欧洲作为代表东方的一类元素,经常会出现在加彩里。欧洲后加彩中,也画有纯粹的西方题材。例如这件白釉加彩圣经故事图杯,是在意大利加的彩,画的是圣经中“五饼二鱼”故事。
意大利加彩白釉加彩圣经故事图杯康熙
除了加彩,还有在中国瓷器上进行再刻花。如现藏于V&A的青花酱釉杯碟,这件器物的外壁上本没有纹饰,后在德国刻制出中国式的花鸟。
欧洲再刻花
对中国瓷器另一种非常重要的改装,就是金属镶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布卡比宫殿收藏了从元代到清代的大量中国瓷器,其中不少经过了中东的改装。比如用中国瓷器中的两件碗、一个盘子改成香薰,再镶上珠宝。还有一类青花笔盒,是中国专为伊斯兰世界所制,在当地又被重新装饰,将金片做成朵花,加以宝石镶嵌。
被改装的中国瓷器
被改装的中国瓷器
在波斯细密画里,我们看到阿赫麦德三世为儿子举行的割礼庆典上,黑太监总管呈上首相所赠的镶宝石的中国瓷碗。
细密画里被改装的中国瓷碗
“金属镶嵌”这一概念并不是仅针对东方瓷器的做法。实际上,在东方瓷器大量进入之前,对器物进行金属镶嵌这一做法,在欧洲已经有了相当深厚的历史基础。在拜占庭和中世纪时期的宗教艺术中,金属就被大量地运用。比如在木板宗教画的人物周边涂绘金漆,或是为圣物添加金属底座。这些有别于本体材质的金属不仅突出了画面中的人物和圣物,也以金属的稀缺性强化了被衬托者的高贵地位。
14世纪起,欧洲人就开始为进口的珍贵器物镶嵌上金属附件,镶嵌对象的范围拓展到包括陶瓷在内的各式奇珍异宝和工艺品。在荷兰静物画中大量出现的鹦鹉螺杯就是以金属镶嵌的方式完成的,以螺形为杯身,以金属附件固定并连上高足,水晶也被以同样的方式装饰成高足杯。
14世纪起,欧洲人就开始为进口的珍贵器物镶嵌上金属附件
荷兰静物画1638水晶杯
在欧洲,对东方瓷器进行金属镶嵌的做法至少可追溯到中世纪,现存最早的器件是从文艺复兴早期留存下来的。早期流入西方的中国瓷极其珍贵,被改装的中国瓷器往往在重要事件中扮演被交换的角色,有时是皇室贵族间相互馈赠的礼品,足显其地位尊贵。我们先前讲的元代青白瓷玉壶春瓶,即丰山瓶,就是一件经过金属镶嵌的礼物。
水彩画德国画家阿尔布雷希特·杜勒大英博物馆藏画中被托高的金属加饰中国瓷瓶所构成的梦幻高柱,给人“高不可攀”之感
十七世纪以来,中国、日本瓷器大量外销欧洲,为东方瓷器加装金属附件已然成为一种风尚。目前能看到的欧洲早期被镶嵌的中国瓷器,多集中于英国和德国。
依照现存记录来看,渥兰碗(Warham bowl)是第一件抵达英国的中国瓷器。这件明代龙泉青瓷在1532年即出现在英国牛津大学新学院(New College, Oxford)的收藏清单中。由于被认为是当时威廉·渥兰·坎特伯雷大主教(Archbishop William Warham,1450-1532)捐赠给新学院的,故以此得名。其所加的镀金银质底座和器壁及口沿上的镶嵌被认为是坎特伯雷大主教请人订制。从金银附件的特征判断,很可能是十六世纪早期英国的银匠工艺。早期镶嵌附件上往往都有印刻和标记,能够传达出诸多器物之外的信息。
渥兰碗(Warham bowl)
比如伦纳德杯的金属底座上有1569-70年代之间代表金属质量的伦敦戳记,标出了伦纳德杯进入英国的年代下限。根据伊丽莎白时期的工艺装饰风格,以及金属杯盖和底座上留有的花式字母组合“FR”判断,西方学者推测它出自银匠Roger Flynt之手(其活跃于1568-1588年间)。此外,金属上留有代表伦敦市的皇冠豹头戳印、纯银的标准印记,以及代表1569-70年代的带有字母“m”的盾形标记。
伦纳德杯(Lennard cup)
还有这件矾红彩描金花卉纹碗,它在1583年由艾伯哈特·冯·曼德沙伊德伯爵从土耳其带回。其镀鎏金的银底座可能是在慕尼黑加装的,还刻有纪念兄弟的铭文。这些早期流入西方的中国瓷极其珍贵,本身就被视若珍宝。以金属衬托主体的珍贵也是欧洲镶嵌行为一贯的模式。与此同时,针对具体器物进行金属镶嵌,再加上专属的铭文或者家族标示的行为,是器物私有化和其拥有者彰显地位的一种过程。
矾红彩描金花卉纹碗(金襕手)明嘉靖
“如果说金属装饰瓷在十八世纪达到了最为旺盛的历史顶点,那么,在任何实际的意义上,它都应该是在巴黎加装的历史。”
如Francis Waston所说,十八世纪是在瓷器上加装金属附件的黄金年代。与其他国家相比,法国尤其钟情于镶嵌金属附件的器物,而巴黎更是金属附件镶嵌的制造中心和集散地。
“镶嵌”是可以拆卸的,“镶嵌”用到的金属,后面可以拿下来重新组装。如保罗盖蒂博物馆藏的青瓷香薰,就是由两个青瓷碗扣合而成,是一种典型的改造范式。
保罗盖蒂博物馆藏的青瓷香薰
从改装材料的变化来看,装饰的材质也会随时代而有所不同。早期镀金银,后因路易十四后期财政短缺,对铺张行为的敕令使得金银制附件的使用降低,转而使用花费更少的青铜镀金。
改装材料的变化
“镶嵌”的功能多种多样,且也会发生变化。
第一种是保护和优化。作为一类珍贵器物,中国瓷器往往会被金属附件镶嵌在脆弱位置以做保护处理,这是镶嵌瓷长期一贯的做法。这种以保护为目的的装饰思路在十八世纪依然十分常见。除防止破损外,一些简单的附件镶嵌也被用来优化现有的瓷器样式。比如为瓶加金属盖、为杯加手柄、在盖与器身间加金属链条以防丢失等等。
保护优化
保护优化
第二种则是改变功能。初入异文化的中国外销瓷并不能完全满足欧洲人的使用需求,金属附件因此被用来改装现有的东方瓷器,使之改变器物功能,以符合当地的使用习惯。如这对德化大瓶,肩部以下位置各有一对狮形纽,后被截去颈部。18世纪20年代,这对花瓶被加装了银质的底和镂空盖,整个肩部被打孔,并在孔处镶嵌六瓣星形银扣。这对德化瓶被重新改装成承装香料的扩香器,香料的香气可以通过肩部的孔洞和镂空盖散发出来。最有意思的是这一件孔雀蓝釉“布袋和尚”,金属附件上加入麦森瓷厂制作的花朵和花苞,被改造成了烛台。
改变功能
改变功能
改变功能
第三种是华丽装饰。金属和瓷器间装饰材质的反差效果是设计者极为注意的,这也可以解释他们为什么后期多选择对单色釉瓷器进行镶嵌。
当然,这些金属附件自身价格不菲,也足以提高整个器物的价格。从18世纪40年代开始,镶嵌附件不只是用来保护和强调器皿的顶部和底部,还出现了手柄、底足之外加在瓷器部件上更加成熟的装饰元素,尤其追求成对的器物和对称性的装饰。这些逐渐华丽的金属附件诠释了那个时代流行的装饰语汇——洛可可及之后的新古典主义。这些装饰往往并不改变器物原来的用途,更为准确地说,这些装饰的意图已经和使用没有直接的关系了。
自十八世纪(尤其到了后半叶),改装最为重要的目的就是适应当地的室内装修风格。这使得洛可可风格的中心——巴黎同样成为了整个欧洲的改装中心。
华丽装饰
华丽装饰
华丽装饰
那么,这方面的经营是谁在做、如何做?巴黎的各类工艺制作和贸易都有极为严密的行会制度,不同分工的手工匠人和商人都被限定于不同的行会中。marchand-merciers自1613年开始确立自己的行会。在诸多行会中显得尤为特别的是,其成员可以售卖不由他们自己制作的商品。大部分的行会规定都限制手工匠人和商人只能制作某一种特定材料,然而奢侈品商人却被赋予超越材料,随意组合的权利。“不是任何东西的制造者,但是所有东西的承办人”,正是marchands-merciers工作的写照。奢侈品商人统领下的金属镶嵌工艺流程大致如此:获得瓷器、切割、设计附件、制作模型、制范浇铸、镂刻、镀金、售卖。
在具体的制作过程中,奢侈品商人并不需要出手完成具体的操作(虽然有时参与设计的部分),而是更多地担任起组织、协调各工种的工作。类似这样由奢侈品商人牵头,雇佣各类工匠合作完成商品的工作方式也同样发生在家具制作中。十七世纪的中央市场(Les Halles)是当时巴黎奢侈品交易的中心。很多奢侈品商人还会在巴黎两大年度集会展示他们的中国瓷器:圣罗兰市集(Saint-Laurent Fair)和圣日尔曼市集(Saint-Germain Fair)。
到十八世纪,圣日尔曼市集依然有着极高的参与度,而城镇里的中心则明确地集中在了圣奥诺雷街。从十八世纪开始,大部分重要的奢侈品商人都在这里设立店铺。
作为售卖者,同时相当于室内装潢的设计师,奢侈品商人擅长通过改造异域材料使之适应环境。他们对东方材料极为感兴趣(除瓷器外,还有漆器)。
这些奢侈品商人售卖的物品反映着巴黎贵族的选择,他们也利用自己的职能和偏好主动塑造着贵族的审美。有一位非常重要的奢侈品商人,叫做Lazare Duvaux(拉扎尔•杜福),路易十五和皇后曾资助了他的店铺Au Chafrin de Turquie。他记录了1748-1758年这一东方瓷器镶嵌最为风行的时期,其经手的数百件镶嵌瓷器的情况,包括金属镶嵌瓷器的类型和价格、未经镶嵌的瓷器及金属附件的单独价格、金属镶嵌瓷器的购买者及购买数量,还有金属附件制作者的姓名与工作内容。从记录中我们能看到,巴黎社会的重要人物,包括众多欧洲皇室和英国收藏者,都是杜福的客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蓬皮杜夫人,她是洛可可风尚的重要推动者。另外还能看到合作的工匠,如著名的工匠杜普莱西。
再来看当时的室内装饰场景。整个十八世纪,东方瓷器都被放置在各个房间的不同位置,在各类家具上摆放中国瓷器尤为常见。我们可以看到室内装饰环境中的瓷器镶嵌与洛可可风格的紧密结合。
室内装饰环境与洛可可风格的盛行
这一风尚从18世纪后就走下坡路了。但在20世纪上半叶奢侈品的设计中,仍然运用了这样的理念。如用乾隆粉彩镂空人物故事图香笼改装成的台式烟盒,就是卡地亚于1927年在巴黎设计并镶嵌完成的。
乾隆粉彩镂空人物故事图香笼改装台式烟盒卡地亚巴黎设计镶嵌1927
还有《姜瓶上的观音》这件当代艺术品,也延续了欧洲对中国瓷器进行改造的传统,这是对中国瓷器进行的艺术再创作。
《姜瓶上的观音》柏克·德弗里斯2018
五、欧洲设计:普朗克“执伞妇人”瓷盘
最后从普朗克“执伞妇人”瓷盘切入,谈谈明清外销瓷中的欧洲设计。之前已经提到过荷兰东印度公司(VOC)在亚洲的瓷器贸易,那么被荷兰东印度公司聘请的普朗克到底是谁?考奈利·普朗克(Cornelis Pronk,1691-1759),荷兰画家,以创作荷兰风景画而出名,现存有作品汇编Het verheerlykt Nederland("The glorified Netherlands")。瓷器图样设计是普朗克留存作品中比较特殊的一类。1734年8月31日,荷兰东印度公司(VOC)的十七人董事会委任普朗克作为设计师,专门设计瓷器图样,而后将图样发往亚洲,进行生产。
绘有VOC标志的帆船瓷砖
普朗克肖像1759
普朗克的设计《博士图》
普朗克的设计《执伞妇人》
普朗克设计灵感的来源之一是当年中国的外销瓷。普朗克的设计题材里,有水禽、有人物、有阳伞,中国外销瓷里面也有相似元素。所以对他的设计来说,中国瓷器应该是一个灵感来源。
他也受到了当时欧洲版画的影响。普朗克可能参考了大量的版画、游记插画以及与东方有关的绘画作品。Jörg最早提出,“执伞妇人”的形象与服饰很像范·林斯霍滕《东方旅行记》中的中国女性人物形象;Angela Ho认为,中国版画中的女子形象迎合了彼时欧洲贵族女性对于室内生活情趣的表现与经营,“执伞妇人”与水鸟的互动可能是对当时女性消费需求的回应。
在巴达维亚的VOC官员也留存下了一些撑伞的图像。他们在巴达维亚需要借助一些视觉表达,来体现自己的地位等级,伞就是其中一种。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用撑伞以表示身份等级的做法,在当时的荷兰本土并不存在,应当是一种文化融合的产物。实际上,这一时期欧洲生产的陶瓷器已出现大量有东方风情的撑伞人物图像,只是场景有所不同。
设计的图像来源-中国瓷器
设计的图像来源-欧洲陶瓷器
绘画、版画对普朗克设计的影响
VOC官员在巴达维亚
普朗克设计的图像流传到中国以后,有较为忠实原画样的青花、粉彩、中国伊万里等;也有中国的工匠根据经验对其做一定改编,如将芦苇改为牡丹、将水鸟改为雉鸡或仙鹤,将边纹改为花卉、石榴与佛手柑……这些元素的使用,都具有一定的吉祥象征。
也就是说,欧洲人设计的中国风图案,在中国又被中国人按照自己熟悉的方式进行了改编。更有趣的是,这一图案后来又被欧洲人再度模仿。
较忠实原样的中国生产
加以改编的中国生产
中国生产与欧洲模仿
总之,可以看到,东西方之间通过器物进行着不断的交流。
转载请注明来自研顺网,本文标题:《建投读书会·东西汇流|全球物品:跨文化交流视域下的明清外销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