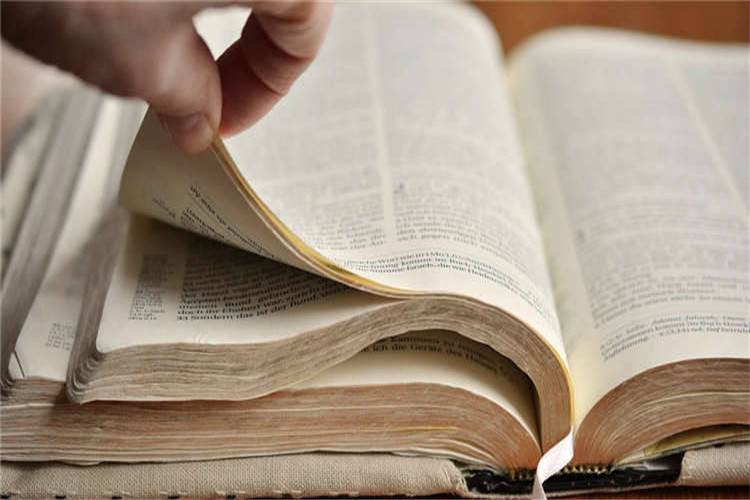在此刻,读者也许会问自己一个明显的问题:当历史学家发现一些原始资料,而这些资料告诉他们一些之前不知道的事情,这时历史是否发生了改变?对这个问题的简短回答就是:历史并没有发生改变。就像考古学不是印第安纳·琼斯一路披荆斩棘寻找失传的约柜,历史研究也不是偶然发现一份文献,而这份文献“可以解释一切”或者“改变所有认知”;发现惊人的文献往往是结果而不是创新研究的原因。如果有人找到一份关于希特勒下令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真实文件,这肯定会上头条新闻,但最终大屠杀研究领域并不会因此转型,因为几乎所有研究者都意见一致,认为大屠杀基于非常复杂的原因和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在研究过程中,历史学家有许多“我找到了!”的时刻(eureka moments),但唯有结合在这个领域的训练和对主题的潜心钻研,才能发现一份史料的潜在价值。其他人遇到一份曾让学者兴奋得大声欢呼的文献,可能会因为它晦涩难懂、乏味无趣或者两者兼有而转身离去。不寻常的史料的确存在,但只有在具有非凡创造力的历史学家想出如何处理这份史料时,它才能获得不寻常的地位。
在近年来的北美史研究中,最著名的史料之一就是玛莎·巴拉德(Martha Ballard)每天所记的日记。身为缅因州的产婆,她从 1785年即50岁起记日记,一直写到1812年过世。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这份史料并非鲜为人知,几十年来被地方学者和研究分娩的历史学者引用,但即便是这些人也倾向于轻视这份日记,视其为重复琐事的记录。实际上,如果你随意地翻阅这份日记(原始手稿和转录的印刷版都可以在网上看到),古雅而有趣的条目很快就变得枯燥乏味。1791年6月7日:“[今天]早晨微霜。我给玉米和豆子[除草松土]。我的[女儿们]和帕尔特娜(Parthena)去了哈姆林先生家(mr Hamlins)。怀特太太(mrs White)和苏姬·诺克罗斯(Suky Norcross)在我这里。我和她们一起去了利弗莫尔先生家(mr Livermores)。”6月8日:“天气晴朗,利弗莫尔太太在这里织了一张网。舒鲍尔·欣克利先生的千金(mr Shuball Hinklys Lady)在这里。我在家,所有孩子都和我一起吃了饭。乔纳(Jona)吃了早饭喝了茶,赛勒斯(Cyrus)出去了,带了一头猪回家。”诸如此类, 日复一日,有近万条简短的条目。扣人心弦的事也会发生:孩子和成年人死于疾病或分娩;巴拉德多次风雨无阻地渡过肯纳贝克河,这些折磨人的旅行是为了帮助分娩的女性。她在日记里描述了参加的一场尸检,记录了一位法官被控强奸了邻居的妻子之后又被宣判无罪,以及有人被谋杀。但是,这些戏剧性事件都被巴拉德用朴实无华而又精确简洁的风格记录了下来,只是偶尔会暗示这些事件所引发的少许情感:“萨维奇先生(Mr Savage)在这里,告诉我福斯特太太(Mrs Foster)宣誓称她被一群男人强奸了,其中就有法官诺思(Judge North)。真是让人震惊。”
《产婆的故事》( A Midwife’s Tale)
利用这种毫无用处的史料,历史学家劳雷尔·撒切尔·乌尔里克写就了一本女性史的经典作品——《产婆的故事》(A Midwife’s Tale)。乌尔里克完整地整理了27年的有用条目,并用纳税清册、土地契约、法庭档案、其他人的日记,甚至小说来补充所有环节,完成了一项非凡的重建壮举,拼凑了这位默默无闻却令人钦佩的女性的日常活动,以及她所在的社区在18世纪末的生活。从数千条条目信息中,乌尔里克梳理出一位杰出的产婆的故事,她为814个孩子接生,自己生了9个孩子,协助了一次尸检,但她的重要性却被当地的男医生们掩盖了。在那个世界里,丈夫和妻子在独立、平行的经济环境中工作,各自购买、销售物品或进行物物交换;婚前的性行为是普遍的,子女多半可以自己选择伴侣,婚礼较为随意;访客源源不绝,女性一起工作,但似乎缺乏亲密的友谊。感谢历史学家的决心和耐性,整个世界从这些日常条目中走出来,变得生机勃勃。“日记的价值和研究难处都在于其惊人的稳定性,” 乌尔里克写道,“日记极具感染力,部分是因为它很难被使用,也因为它总是呈现日常生活的平淡之处。”乌尔里克的书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例子—历史学家通过直觉发现文献的潜力,从而“创造”了史料。更普遍而言,当问题形成后,史料才会出现:没有社会史与女性史的兴起,就没有人会想到花费许多年去仔细研究一位不为人知的18世纪新英格兰妇女的日常记录。
强调历史学家在“创造”史料中发挥的作用,并不是说文献的具体存在和可获取性是不重要的:当政权更迭,严控或者放开档案获取规定;或者当时光流逝,档案宝库被打开;又或者相反,当人为或自然灾害导致档案损毁,整个研究领域都会受到决定性的影响。当然,历史学家提出某些问题,而对其他问题不予深究,以此“制造”他们的证据,这是的确存在的现象。同样,史料的存在也主导了历史术语的形成,近年来这个观点引发了一系列批判性思考。什么内容可以算作档案以及为什么?谁决定什么样的文献应当被保存下来?没有文献记载的过去,其历史又是什么样的?
标准的历史书写入门指南通常会包括一系列史料的类型:记述与回忆录,国家和地方政府档案,新闻报刊,宗教与司法档案,私人文件和日记,多种类型的图像,录像和录音,等等。通常紧接着的是一些告诫,要对上述史料批判性地评估,还有一些建议,指出如何纠正偏见或避免虚构。史料问题应该是历史研究中最无争议的技术层面问题,因为我们都同意,必须找到最佳且最多的资料,并且尽最大努力地、负责任地、批判性地、谨慎地使用它们。
就像这一领域的其他方面一样,事情在近几十年变得复杂而耐人寻味。对历史研究的普遍看法是一名学者在灰尘覆盖的档案中工作;在大多数时候,情况实际上仍然如此,尽管许多档案不再布满灰尘(特别是对那些近世的而言),而且“去档案馆”越来越有可能意味着在网络上研究数字化的文献。但究竟什么是档案?谁创造了它们并决定用它们来做什么?我们今天所认为的档案通常是由那些在当时社会中拥有权力的群体和个人所创造,这些人有机会习得读写能力以及获取其他资源,并坚信他们的历史记载必须保存于世。千百年来,统治者个体和家庭、执政主体、宗教和教育机构保存档案既出于实际的原因——建立所有权和获得权力,记录仲裁与惩罚——又出于一种信念,就是他们的行为和决定值得被人记住。与西方现代历史写作相关的其他事情一样,“革命的时代”(18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50年代)标志着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国家档案馆的建立确保新成立的国家可以储存它们的集体记忆。创办于 1790年的法国国家档案馆就是一例,与新的政府一道,作为“一个储藏室,保存那些确立本国宪法、本国公众权利以及本国法律的法案”。通过确立统一原则(一个单独的存放处)和民主透明原则(至少在理论上人们可以公开获取政府记录),这一国家机构的建立体现了新秩序的意识形态宗旨。其他欧洲国家不久后纷纷效仿法国。
档案馆定义了现代国家,通过控制档案获取权限,政府拥有极大的权力去塑造其国家的历史:基于各类广泛的理由,政府决定什么是机密信息,并决定在多长时间内保密,因此对国家历史的叙述产生重要影响。此外,正如海地裔学者米歇尔-罗尔夫·特鲁约(Michel-Rolph Trouillot)观察到的,档案通过创造书写历史的机会条件,划分了历史学者的现代派别。如此一来,他们便可鉴定历史作品:“获取档案的能力决定了历史学者之间的差异,是业余人士还是专业的历史学者,或者一个江湖骗子。”据安托瓦妮特·伯顿(Antoinette Burton)所言,档案馆并不只是被动的文献储藏室,“还是完全成熟的历史行动者”。殖民地档案馆的例子显然很符合后面这种情况,在这些档案馆中,记录的保存与推行和维持外国控制的计划难以分割。
于是,文献收集和保存的方式无疑决定了历史被书写的方式。在19世纪建立的西方国家档案,适合借以书写政治史和制度史。即便所研究的组织是反对派—比如一个劳工组织、参政权组织或民权组织—它们的档案也通常优先记录领导者的活动,以及人们生活中最慎重和公开的方面。为了重建寻常百姓的生活,历史学家必须诉诸一些策略,比如多管齐下,仔细重构,像乌尔里克的《产婆的故事》那样,或阅读那些不能佐证研究课题的文献。例如,传教士或探险家遇到“野蛮人”的记述只告诉我们故事的一个方面,但是通过阅读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我们可以尝试重建故事的另一面。
社会史学者往往从文献中获得与他们最初目标无关的信息。司法档案就是一个经典例子,事实证明,此类材料是一座金矿,提供了关于日常生活和不识字者的社会观念的信息。创造档案的法官或审判者试图确定被告有罪或是无辜,但社会史学者却寻找被告或证人证词边缘揭示的无关细节。比如在14世纪初,一位名叫雅克·富尼耶(Jacques Fournier)的主教设立了审判庭,借以交叉询问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小村庄——蒙塔尤(Montaillou)的村民。这个村庄有许多人信奉一种名为纯洁派(Catharism)的异端邪说。富尼耶的法庭留下了丰富的记录,这些文献为宗教史学者所熟知。但在20世纪70年代,一名法国社会史学者——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挖掘了这些档案,不仅是为了寻找宗教信仰的证据,更是为了以一种前所未见的方式重建中世纪村庄的社会生活。在透露他们自己和邻居们的宗教观点时,村民们打开了一扇借以观察消失了的社会的窗户。比如,一个女人讲述了两个邻居在闲聊的时候,说“他们的女儿帮他们在太阳底下除虱子……这四个人都在他们屋子的房顶上”。富尼耶主教毫无疑问对谈话中的某些部分很感兴趣,即这个女人提到人们如何忍受火刑的痛苦。(“无知的受造物!上帝当然会承担一切痛苦。”) 但是,这样的故事提供了卫生和社会关系的相关信息:为某人的头发除虱子是一个长时间的私密过程,发生在情侣、家庭成员和朋友之间亲近并交换信息的场合。这些和其他的小插曲形成了生动地重建一切的基础,从村民们对卫生、性和性别角色的态度,到牧羊少年的世界观。总而言之,社会史研究通常在官方档案的边缘内容和“弃用片段”中发现最丰富的证据。
《蒙塔尤 : 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法]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著,许明龙、马胜利译,商务印书馆2023年8月出版
尽管如此,历史仍建立在沉默之上,正如特鲁约提醒我们的,每个故事的展开都有其代价,有些人或者不会被提及,或者被掩埋在其他诸多叙述中。特鲁约的《沉默的过去》(Silencing the Past)专辟一章,讨论了一系列故事的相互嵌套,仿佛是俄罗斯套娃。故事的开端描述了一座18世纪典雅皇宫的废墟,这座叫“无忧”(Sans-Souci)的宫殿坐落在海地北部的山上,由亨利·克里斯托夫(Henry Christophe)所建。此人是海地革命的英雄,于1804年成为海地北部地区的国王,称亨利一世。鲜有海地之外的历史学家知道这座宫殿,因为加勒比地区的历史长期以来都被过去的其他故事掩盖,Sans-Souci(法语中的“无忧无虑”)这个名字让人想起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18世纪40年代末,他在柏林郊外修建了一座著名的洛可可式宫殿,也是用这个名字。在亨利在世和刚过世之后,岛屿的西方访客因这个名字,以为海地国王将腓特烈大帝的作为其宫殿的模型。虽然并无直接证据证明这种影响,但亨利的确精通欧洲史,并且与他王国中的一些德裔居民相识。但是正如特鲁约所示,宫殿名与普鲁士有关的预设隐藏了一个叫“桑-苏西”的人的存在,这个男人可能用海地某个乡村地区或街区的名字命名。让-巴蒂斯特·桑-苏西(Jean- Baptiste Sans-Souci)曾经是种植园的奴隶,后来成为奴隶起义军队的指挥官,在亨利手下与法国军队作战。到了1802年,在像亨利这样黑肤色的克里奥尔人(海地本土人)法军指挥官与桑- 苏西这样出生于非洲的领导者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中的战争”:亨利以协商为托词,召唤他的前部下来开会,随即杀害了桑- 苏西。国王的宫殿与他杀害的敌人同名是极其古怪的巧合吗?在注意到皇宫所在地与杀人场所在地理上有重叠之处后,特鲁约认为这种巧合是不大可能的:“更有可能的是,国王在进行一种转换仪式,以同化他的老对手。”
每一个桑-苏西的故事都掩盖了另一个版本:著名的德国宫殿掩盖了海地版本;亨利国王是亲欧派,掩盖了非洲人让-巴蒂斯特·桑-苏西之死。正如西方的历史学家记住了腓特烈而不是亨利,海地的历史学家也选择不去回忆那场嵌套在他们光荣的民族解放战争中的战争:海地本土克里奥尔人和非洲出生的“刚果人”之间的战争。特鲁约指出,在历史记载中,一些事实占据了中心舞台而另一些则被掩盖,“就像消音器让枪消音一样”。当代欧洲和美国访客的记述是显而易见的材料,这些材料自然而然地把历史学家引向故事的一个版本,即海地国王以其欣赏的欧洲宫殿命名自己的城堡。被掩藏的故事则需要更多的妙想和更深入的挖掘,才能揭示这位被谋杀的非洲对手的传奇。
从广为接受的叙述中提取隐藏的故事并非总是可行的。对我们找寻答案的许多问题(17世纪易洛魁部族女性如何看待她们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而言,史料极其稀少或者根本不存在。我们很容易假设,没有文字的社会以及缺乏权力的群体很少留下或者没有留下任何踪迹,尤其是这些社会和群体来自遥远的过去。然而,足智多谋且很有耐心的研究者常常证明这种怀疑是错误的。例如,研究中非的历史学家借助一种被称为历史语言学的方法,打破了一个神话——在赤道地区非洲雨林中或班图大湖区的社会已经几个世纪或上千年没有变化。这一方法在于从早至18世纪或19世纪的记录——比如语言学家的文献或需要使用当地语言进行沟通的传教士的文献—往回追溯。文献里记载的词汇详细描绘了被记载时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现实,但是还可以起到更多作用:如果两种或更多的不同语言包含类似的词语,它们可以追溯到同一种根源语言,让历史学家能够拼凑出当地生活的早期模式。比如,如果东库希特语(Eastern Cushitic language)的两个分支有相联系的词语指称驴子,且这两种语言只在原始语言的节点上产生联系,那么历史学家可以假设驴子存在于说原始东库希特语的社会中。早期语言和后世语言之间存在的意义类型的差异让历史学家,特别是研究非洲的历史学家打破一种神话——某些人生活在“时间停止之地”(lands out of time)。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是一项极其耗费心力的工作,其结果通常具备令人生畏的专业性,但这种方法突出地展现了想象的价值和历史重建中的执着。
只有研究非常晚近时期的历史学家才会采用一种直接解决文献缺乏问题的方式,用一种叫作口述史的方法创造他们自己的史料。这种方法包括通过系统地采访那些亲历者以捕捉过去,长期以来主流历史学家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声称,采访者很有可能带着某种目的或偏见,被采访者的记忆和动机也不可信,所说的话一般而言也不可靠而且是主观的,远不及文本档案。迟至2001年,一本历史研究指南提醒道:“只有在口述史料可以通过其他方式验证的情况下,历史学家才可以信任它们。”此外,采访“本身就是一种阐释,分析口述史料时必须极其小心”。
如今,许多历史学家反对一种观念—文字史料优于口述史料,认为这是对历史中未受教育群体暗含的偏见。所有类别的文字档案实际上都是对口头事件的文字转录,比如演讲、议会辩论记录和法庭证词。但是,口述史研究者也欣然接受这些方法,尽管访谈带有歪曲和主观性,与其说让历史学家接触到关于过去的难以捉摸的真相,不如说让他们了解过去对亲历者有何种意义。甚至证词中存在的错误和扭曲,以及被记录下来的话的独特之处—语速、停顿和犹豫,等等,都提供了有关情感和态度的线索。正如一位重要的口述史研究者指出的,“口述史料迫使历史学家接受的独特且珍贵的要素……就是说话者的主观性”。
口述史研究也从其他诸多方法中脱颖而出,唯有这种方法能让历史学家在进行研究的时候创造他们的史料。历史学家- 采访者通常很自觉地对待他们的角色,充分意识到他们的存在和提问的内容最有可能改变材料。
作为一种题材,历史在描述和阐释之间切换,而后者通常由争论所塑造。“仅仅是一个故事”,这种历史类型仍存在于某些形式的大众历史书写中,尽管即使是畅销的传记和军事史著作,也必然包含某种观点或价值判断,并且通常提出一个明确的观点。书籍、纪录片和博物馆展览不可避免地包含或多或少的可见选择。此外,最为“公共的”历史形式—博物馆、遗产景点——有时会发现自己卷入了更激烈的争论。专业史学坦然地接受争论,视其为推动研究和阐释的引擎:从本科生到荣休教授,每一位学人的抱负都是通过提出一些新观点来加入对话。一般而言,历史学者提出的问题推动了史料的搜寻(而不是史料创造了研究项目)。历史研究需要极大的毅力、耐心和创造性的才智,有的时候是碰巧走运,大多数时候需要经年累月的训练才能“无意中碰到”绝佳的史料,并且你的发现源自你所提出的问题。在口述史这种不寻常的例子中,研究者实际上通过创造他们需要的史料,将这种方法的逻辑发挥到极致。但是,对许多问题而言,史料从未存在过,那些被认为不值得记载的人的人生故事将永远不为人知。
(《思考历史》,[美] 萨拉·马萨著,曹鸿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11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