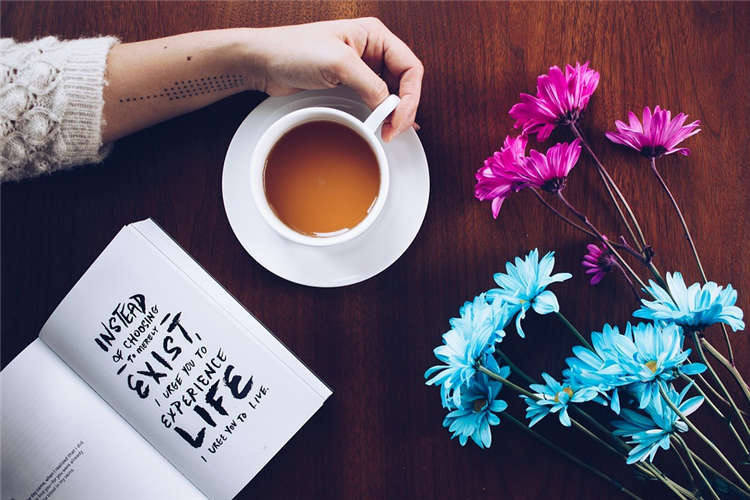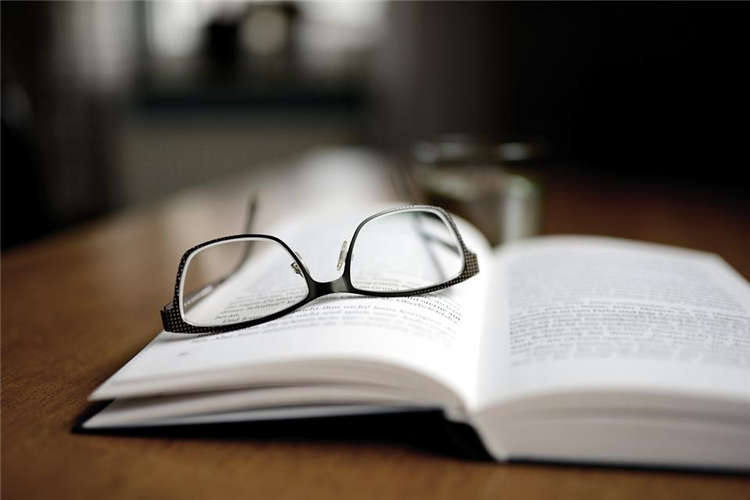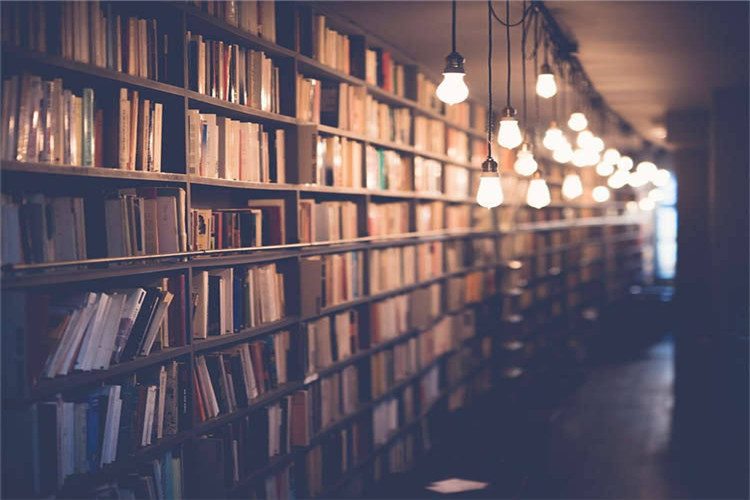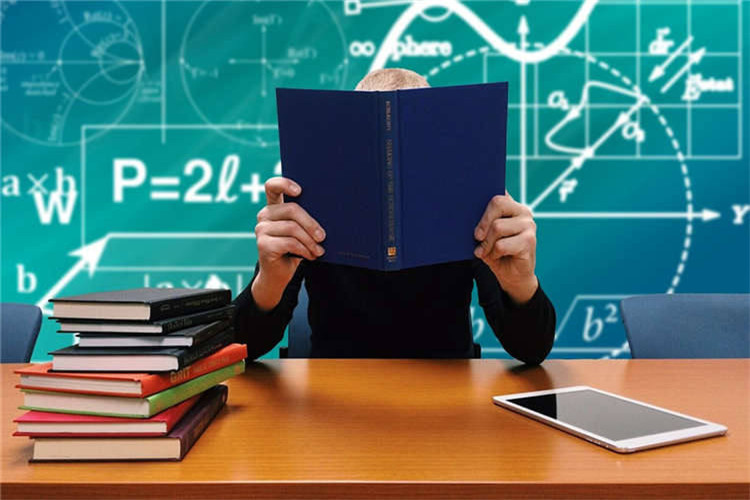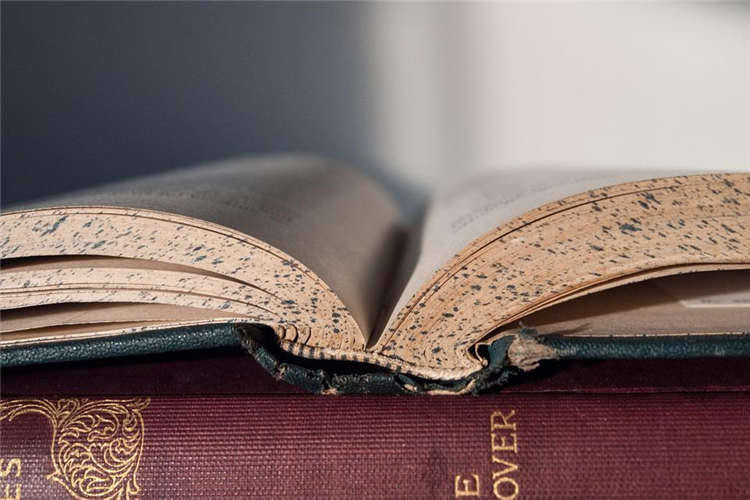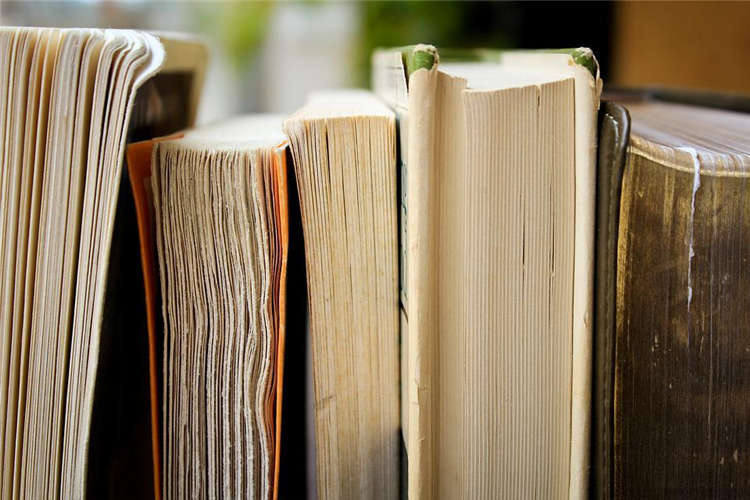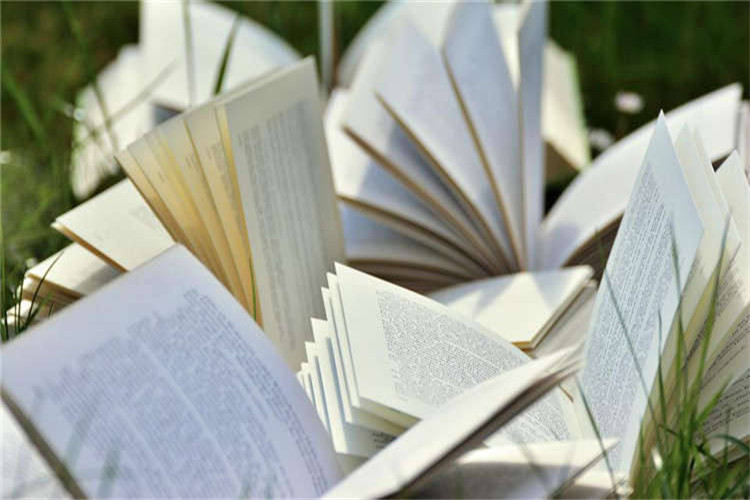2023年底工信部印发《人形机器人创新意见》,2024年被称为“人形机器人元年”,2025年“两会”热议融合大模型与机器人的具身智能。种种迹象表明,机器人将不再被局限于工厂的劳动场所中,很快将大规模出现于日常的家居环境中,人机情感互动将成为未来智能社会的常态。有论者甚至认为,随着实体机器人革命走向深入,AI正在成为新的“情感主体”“社交主体”。所谓机器情感、AI陪伴的实质是什么,对人机交互、人机关系产生何种影响?比如说,从文化视角和性别视角,应该如何看待人机情感关系呢?人与机器的情感交流,将会产生何种社会冲击,导致何种技术风险和技术伦理问题,又应该如何应对?类似问题,已经引发诸多热议。本次笔谈聚焦“机器情感与AI陪伴的人文审度”,从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文学和人工智能等进行跨学科研究,抛砖引玉,以期推动该领域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第一组6篇论文由本刊2025年第3期刊发,引起学界极大的兴趣和关注。本期刊发第二组共7篇论文。在《智能时代情感操控技术的三重特征解析》中,闫宏秀和罗菲围绕“谁在操控”“操控如何实现”“操控如何呈现”三大关键问题,指出AI情感操控技术中的动机代理化、系统性生成与结构性隐匿的特征,主张构建适应人机复合系统的新型伦理责任框架。在《情感计算的哲学缺陷及其技术克服进路》中,孙强梳理情感识别、情感生成和人智情感交互等情感计算领域关键技术的哲学缺陷,提出在以人为本核心价值指导下克服缺陷的潜在进路。在《情为何物?——机器情感的哲学分析》中,史晨和刘鹏从情感与理性的关系入手分析机器情感的实质,主张打破情感幻像,走向适度情感、适度理性的人机互动。在《谁决定我们的情感生活?》中,黄柏恒以Moxie社交机器人停运引发的儿童哀悼为主要案例,揭示商业逻辑主导下情感AI的结构性情感不公正,呼吁通过认知赋权重塑技术公司与用户的情感权力关系。在《“DeepSeek中文情感难题”与可能出路——一种“共在—预测AI”进路》中,吴雪梅指出“DeepSeek中文情感难题”表现为难以理解中文情感与难以识别语义两方面,并提出“共在—预测AI”的解决方案,主张发展以中文共在情感为启发的群体智能以提升DeepSeek的中文情感计算能力。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的人工亲密关系及其社会情感对齐》一文中,段伟文探讨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下人工情感和人工亲密关系带来的社会情感冲击,强调超越似真情感悖论和机器贬低等数字文化批判的视野,转而从基于“主体—他者—世界”参照三角的“社会—情感—认知”发生机制出发,寻求AI个人主义时代的社会情感对齐之道。在《风骨智能体与智能人文》中,杨庆峰提出构建风骨智能体来克服理性智能体过于强调目的和理性优先的局限,并为智能人文的研究提供一条可能的路径。(专题特邀主持:刘永谋)
本系列文章原刊《科学·经济·社会》2025年第5期,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本文摘要】如何应对“DeepSeek中文情感难题”是AI界面临的一大难点,这要求我们从哲学层面思考可能的解决方案。根据DeepSeek的预测特征,DeepSeek所应用的情绪理论倾向于“预测心智—情绪建构论”,应用这一理论预测中文情感面临两大难题:难以理解中文情感与难以识别语义,即“DeepSeek中文情感难题”。基于对中西方哲学传统中心物关系的研究,鉴于中文情感的本质是一种共在情感,尽管导致DeepSeek难以识别语义的根源在于预测方法,但目前AI的最优方法又只能限于预测方法。以中文情感的共在特征为启发,发展一种“共在—预测AI”进路,通过群体智能提升DeepSeek的中文情感预测能力,或许能够以此为突破口实现未来AI在情商、智商与审美能力的实质性增强。
DeepSeek这一国产大语言模型的出现,不仅引领国际知名大模型开源免费,极大地推进了国内各行各业的应用发展。值得重视的是,除了解决相关智力问题外,Deep-Seek所提供的情感咨询服务也备受关注,将其视为“赛博恋人”成为年轻人的潮流。基于此,国内多款情感陪伴类AI也接入Deep-
Seek,这证明DeepSeek目前在基于语言的情感模拟这一情感计算领域表现良好。但目前也有越来越多证据表明DeepSeek在预测中文对话中的情感上存在困难。最新有研究团队对大语言模型是否能够预测中文对话中的“大五人格特质”开展了实证分析,对现有的DeepSeek、GPT-4与Qwen1.5等22个大语言模型与该团队微调的Llama3-8B-BFI模型,在基于中文对话预测性格特质上的表现进行了研究①。该研究指出,包括DeepSeek在内的大模型在中文对话的情感理解方面表现较差,比如有时中文用户对挫折持积极态度,但大模型却会将其理解为沮丧等消极情绪,除此之外,还容易将中文对话中“我总是担心别人对我有负面评价”理解为字面意思,而事实上用户的真实动机并非如此,只是语言上强调感受的表达。
要解决这一困境,需应对三大问题:第一,DeepSeek预测中文对话中情感的理论与方法所导致的难题,本文称之为“Deep-Seek中文情感难题”是什么?第二,造成这一难题的原因是什么?第三,如何能够提升DeepSeek对中文对话中情感的预测能力?
一、DeepSeek中文情感难题
鉴于DeepSeek作为大语言模型处理情感的方式是以语言为基础进行的,要想深入研究“DeepSeek中文情感难题”,就需要首先从方法论层面剖析DeepSeek预测中文对话的基本原理究竟是什么。根据相关研究,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核心技术是贝叶斯方法论,原因在于其基本原理是“后继标识预测算法”(next token prediction)。考虑到尽管相比于ChatGPT,作为国产大模型的DeepSeek在中文表现上更为突出,但在实现智能的基本原理层面二者的底层逻辑都为贝叶斯方法论。具体而言,贝叶斯方法
的基本公式P(A|B)=[P(B|A)P(A)]/P(B),意味着人们对未来的概率判断,是在已知某些证据的情况下先对其给出一个预先估计的“预设概率”,再不断以新经验的“后验概率”去修正“预设概率”所做出的。DeepSeek与ChatGPT一样,在生成知识内容的基本原理上,所有语言内容都会转化为计算机能够识别的同质标识,通过不断以新经验标识修正旧知识标识以达到预测生成内容的目标。正因如此,在方法论层面,DeepSeek预测中文对话的基本原理为基于贝叶斯方法的“后继标识预测算法”。但若要分析DeepSeek在预测中文情感时所使用的理论,则还需要在已知其使用的方法论为贝叶斯概率的基础上,对相应的情绪理论进行分析。
当前在认知科学哲学界,影响力最大的情绪理论包括基本情绪论(basic emotion theory,BET)与情绪建构论(the theory of constructed emotion,TCE)。那么,DeepSeek在预测中文对话的情感内容时,实际所应用的情绪理论究竟是哪一种呢?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将DeepSeek预测中文情感内容的核心特征与两种情绪理论的核心主张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这是因为DeepSeek实际应用的情绪理论必然需要同时满足其预测的核心特征。经研究,DeepSeek作为大语言模型在预测中文情感方面具有以下两点核心特征:从目标来看,DeepSeek需要以实用为目标选择相应的情绪理论进行分析;从方法来看,DeepSeek实质上也像ChatGPT一样是以贝叶斯概率实现中文情感对话的预测与生成。接下来,我们需要分析究竟是基本情绪论还是情绪建构论满足以上两点特征。基本情绪论的核心主张包括两点:第一,根据进化心理学,人的情绪可以被划分为基本情绪与非基本情绪,基本情绪包括幸福、悲伤、恐惧、惊奇、愤怒与恶心等①,基本情绪是跨物种、跨文化共有的;第二,情绪有自然类,换言之,每种情绪有特定的生物学基础,可通过相应的生理信号得到识别。鉴于基本情绪论的核心主张包括以上两点,可见,DeepSeek在预测中文情感时基于实现特征的实用目的,在进行情感识别时往往会呈现出对情绪进行标签分类的情况。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尽管DeepSeek会基于相关生理信号的文本数据,根据基本情绪论对情感进行预测,但DeepSeek本身只能够处理语言,而无法直接像人类等生物一样处理生理信号。除此之外,基本情绪论预测情感的方法主要是与进化心理学相关的生物学方法,而并非DeepSeek所应用的贝叶斯方法。由此可见,基本情绪论并非DeepSeek所实际应用的情绪理论。
情绪建构论以丽莎·巴瑞特(Lisa Barrett)提出的版本最为典型,巴瑞特明确指出其情绪建构论对大脑的理解建立在预测编码(predictive coding)理论的基础之上,鉴于哲学上往往将预测编码称之为预测心智(predictive mind),因此,我们可以将巴瑞特的情绪建构论称之为“预测心智—情绪建构论”。该理论的核心主张包括两点:第一,根据预测心智理论,情绪是大脑自上而下的预测所主动构建的,这种构建是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对输入的当前情境的感觉实现预测误差最小化的结果;第二,情绪是大脑为了能量的动态平衡,基于贝叶斯定理,对当下情境构建相应的情绪类别(如幸福)概念的心理事件。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鉴于“预测心智—情绪建构论”主张情绪是由概念或者说语言所构建的,因此,这对于DeepSeek需要以实用目标选择具有可操作性的情绪理论而言,无疑是更加契合的。更重要的是,“预测心智—情绪建构论”中所借鉴的预测心智理论,其核心要素之一就在于贝叶斯方法,且巴瑞特在相关论述时也强调贝叶斯定理对于其情绪建构论的重要启发。由此可见,从方法论上而言,也能够支持DeepSeek在预测情感上以贝叶斯方法实现的方法特征。综上,DeepSeek目前所实际应用的情绪理论从哲学层面的内在逻辑而言,更倾向于巴瑞特的“预测心智—情绪建构论”。
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进一步对Deep-Seek目前在预测中文对话的情感方面所表现的强项与困境做出哲学层面的解释。正是由于“预测心智—情绪建构论”在核心主张上更适用于DeepSeek的特征,因此能够保证DeepSeek在简单的情绪理解与情绪模拟中表现良好。之所以包括DeepSeek在内的大模型会在中文对话的情感理解方面出现预测错位的情况,如将中文用户对挫折的积极态度误判为消极情绪,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事实上也源自“预测心智—情绪建构论”应用于中文情感计算的局限性。具体而言,“DeepSeek中文情感难题”的首要表现在于“预测心智—情绪建构论”是巴瑞特在西方认知科学哲学与情感哲学的传统下所提出的情绪理论,而中文情感在文化传统上与西方有显著区别。因此,DeepSeek以“预测心智—情绪建构论”难以处理中文情感的复杂性,特别是中文对话中的情感与价值观。第二个表现则涉及当前DeepSeek等大语言模型所面临的共同困境,正是由于“预测心智—情绪建构论”也基于贝叶斯概率或者说预测方法,因此,DeepSeek仍然只是在将自然语言转化为计算机能够理解的标识的基础上,基于贝叶斯定理生成内容,无法理解情感文本的语义。要想真正解决这两大难题,需要进一步从哲学层面上分别对导致“预测心智—情绪建构论”与预测方法之局限性的原因进行深入剖析。
二、中文情感相比英文情感的特征:一种共在情感
“DeepSeek中文情感难题”的首要表现在于,DeepSeek所应用的“预测心智—情绪建构论”难以处理中文情感的复杂性。这要求我们从哲学层面分别对英文情感与中文情感进行研究。
(一)英文情感:以“自我”为基础的个人情感
尽管“预测心智—情绪建构论”强调情感具有文化多样性,但该理论所理解的情感从哲学本质而言仍然是一种英文情感,这种情感是基于西方哲学传统中对心物关系的理解所得出的。因此,为了深入研究英文情感与中文情感的差异,有必要首先回溯至西方哲学传统与中国哲学传统基于心物关系对情感的理解。西方哲学传统对情感的现代理解可以追溯至笛卡尔,笛卡尔在《论灵魂的激情》中将激情定义为“相连于灵魂自身的知觉”,即“自我”的当下知觉。自此以来,以“自我”为基点理解情感就成为西方情感哲学的理论前提。巴瑞特的“预测心智—情绪建构论”也延续了这种“自我”情感的理解,巴瑞特与齐奥娜·琳达(Tsiona Lida)明确指出其对情绪的理解受到笛卡尔将激情理解为知觉的影响,进而将情绪实例定义为是“自我”在特定情境下的实时心理事件。
这种基于笛卡尔的心身关系对激情的理解能够在理论预设层面解释“预测心智—情绪建构论”的做法,但难以从方法论层面说明现代科学的形而上学为何支持科学方法研究“自我”情感这一关键问题,有证据表明只有深入心物关系才能回答这一问题。关于笛卡尔对心物关系的认识,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基于相关论证指出,尽管笛卡尔在第二沉思中明确指出“人的精神的本性以及精神比物体更容易认识”,但笛卡尔所使用的科学方法证明了这一主张是错误的,因为基于其机械论的有机体理论,笛卡尔实际上坚持包括身体在内的物体才是最少理智的,也是唯一可理解的。这意味着如果说笛卡尔的科学方法成立,那么在心物关系的主张上应该是物体的本质比心灵的本质更容易认识,而这一逻辑更加融贯的主张正是笛卡尔主义者尼古拉斯·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所持有的。马勒伯朗士反对笛卡尔对心物关系的论断,指出我们对灵魂的认识远不如我们对广延的认识那么完美。基于此,马勒伯朗士明确指出为了详细证明激情在身体与心灵中的变化,“首先有必要对物理学进行概述,接着对人体做出非常精确的描述。”由此可见,在马勒伯朗士那里,具体需要研究作为“心”的激情时,也需要首先基于物理学与生物学对作为一种特殊的“物”的身体进行研究。质言之,以马勒伯朗士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实质上是基于一种科学物论研究激情。而“预测心智—情绪建构论”尽管被称为是一种心理建构论,但巴瑞特明确表明该理论并非沿用源自哲学的民间心理学(folk psychology)研究情绪的大脑基础,而是基于贝叶斯方法与认知神经科学对大脑的结构与功能出发,对个体情绪的生物学基础进行研究。
综上可见,笛卡尔基于心身关系对激情的理解证明西方情绪哲学从理论前提而言是基于“自我”的,而马勒伯朗士对心物关系的主张,即物体的本质比心灵的本质更容易认识,证明西方情绪哲学传统支持以科学方法研究“自我”情感。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中文情感是基于中国哲学传统对心物关系的理解所发展出来的,而并非基于西方哲学传统。因此,要想研究中文情感的本质,需要回溯至中国哲学传统基于心物关系对情感的研究中去。
(二)中文情感:以“亲亲”为基础的共在情感
在中国哲学传统中,朱熹曾说道“理未知觉,气聚成形,理与气合,便能知觉”。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理本身没有知觉能力,但当气凝聚成具体形体或者说有了物质基础后,理与气相结合便能产生知觉。有研究表明,朱熹所说的知觉是“性命之理的知觉化的呈现”。质言之,朱熹所说的“物”并非西方哲学理解的那样一种科学层面上作为客观对象的物,而是指与周围人与物之间的互相联系中的性命体。由此可见,在中国哲学传统中,不仅如有研究指出的那样“心”的概念是偏心的,“物”的概念也是偏心的。也就是说,在中国哲学传统中,与物相比,心是更基础的,即便是研究物,也需要通过思考心的方式获取对物的理解,因而心物关系整体是偏心的。
基于在中国哲学传统下“心”“物”概念与心物关系都偏心,偏心意味着心物关系是以人的情感或精神为核心展开的,因而在思考中文对情感的理解时,需要以人为中心,同时贯通考虑到“心”与“物”,通过研究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由此可见,基于这样一种主客观融合且整体偏心的心物关系,中国哲学并非像西方哲学那样以“自我”为单位定义情感,而是在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中理解情感。有研究明确在存在论意义上将中国哲学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优先性称之为一种共在存在论,这种存在论主张“共在先于存在,并且,共在规定存在”,意在强调我们“每个人都存在于与他人的共在关系中,每个人都不可能先于共在而具有存在的意义”。据此,从重视共在关系的优先性上这一点而言,我们可以说中文情感在总体上是一种共在情感,而非西方哲学传统下的自我情感。而根据前文对中国哲学传统下心物关系的分析,我们已知,在讨论情感问题时,除了共在存在论强调的人与人的关系之外,也需要考虑到人与物的关系,因此在涉及具体是以什么为基础的共在情感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基于心物关系进行分析。
在人与人的共在关系中,首先需要面对的是“亲亲”问题,之所以说“亲亲”也属于心,主要因为第一个“亲”是在动词的意义上意为亲近,因而属于情感层面的“心”“。亲亲”也就是在性命或者说生命的意义上理解“我如何对待生我者、我生者、与我共生者”。以“亲亲”这一生命的共在关系为基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需要思考关于伦理关系的知识,即如何在伦理意义上推己及人以尊重他人,也就是“仁民”。换言之“,仁民”意为致力于建立自己的心与他心之间的良好关系,也就是心际关系。因而可以说,从“亲亲”到“仁民”的情感思考逻辑,是从生命层面对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思考,过渡到从伦理层面对建立良好心际关系的思考。在上述人与人的共在关系的基础上,对情感的思考还需要考虑人与物的共在关系。在人与物的关系中,儒家主张“爱物”,“爱”属于心物关系的“心”的层面,考虑到前文已经证明“物”在儒家那里具有主客观交融的特点,也就是说,我们是在物与自身的共在关系中理解物,本质上而言是将“物”理解为与人有关系的“事”。正因如此,国内有研究指出共在存在论研究的是“事”的世界,而非西方哲学中所定义的客观的“物”的世界。因此,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哲学所主张的“爱物”本质上是爱与人有关系的“事”。由此可见,中文情感是以“亲亲—仁民—爱物”的思考逻辑,将情感理解为一种共在情感。可以说,中文情感的本质是以“亲亲”为基础的共在情感。正因如此,DeepSeek以“预测心智—情绪建构论”这样一种英文情感的理解,处理中文情感时会面临识别与理解错位的困境。
三、理解语义中情感的困难:预测方法的局限性
前文已证明DeepSeek除了在理解中文情感方面存在困难之外,在理解中文情感文本的语义上也存在困难。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目前尚无法理解语义这一结论,已基本成为哲学界的共识。鉴于DeepSeek在实现智能的底层逻辑上仍然与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类似,要想回答DeepSeek究竟为什么难以理解中文情感文本的语义,需要对目前造成生成式AI难以理解语义的根源入手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研究DeepSeek无法理解中文情感文本语义的根源是什么。
首先,关于目前生成式AI为什么难以理解语义的问题。有研究指出目前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所使用的贝叶斯方法,从哲学层面上本质上基于经验论思维而非先验论思维。经验论与先验论是西方哲学史上两种对立的理解人类思维本质的理论方案,特别是休谟问题就因果关系提出挑战之后,进一步引发了包括康德与胡塞尔等先验论者对先验论的辩护。休谟在《人类理智研究》中提出:“我们关于因果关系的知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从先验的推理获得的,而是完全产生于经验,即产生于当我们看到一切特殊的对象恒常地彼此联结在一起的那种经验。”休谟进一步指出“根据经验作出的任何论证都不可能证明过去与未来相似……即使承认事物的过程从来都是这样有规律,但是如果只凭这一点而没有什么新的论证或推论,并不能证明将来会继续是这样。”由此可见,休谟对先验论的挑战在于因为经验无法解释因果概念,这意味着依据过去的经验无法预测未来,因此先验论所承诺的先验原理并非普遍必然。即便是康德与胡塞尔为解决休谟问题提出的先验论方案仍然没有解决休谟问题。但目前生成式AI仅使用属于经验论的贝叶斯方法就实现了对文本内容的预测,因而不可否认至少在人工智能领域,这种经验论的贝叶斯方法即便是基于概率对下一个标识进行预测,但也在预测文本内容上表现出了较高的智能水平。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有证据表明,也正是因为贝叶斯方法只是对未来进行概率预测,因而导致目前大语言模型仍然无法理解文本语义。关于这一点,有研究从科学研究方法的角度指出,推理方法与预测方法是科学研究中重要的两种方法。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得出的结论具有必然性,在科学研究中可用于构建理论模型;后者往往需要通过建立数学模型的方式进行预测,得到的结果并非必然的,而是依据后验概率不断修正先验概率的预估值。鉴于此,我们可以发现这里所说的预测方法也就是贝叶斯方法,而推理方法与预测方法也分别对应于前文从哲学层面上所说的先验论与经验论。该研究指出当前人工智能所运用的主要是预测方法,而预测方法的局限性则在于忽视了推理对认知的重要性,这一点的表现之一就在于现有模型依据预测方法难以理解语义,特别是情感语义。也就是说,从哲学层面上而言,预测方法只能帮助AI实现人的经验思维能力,但对于理解情感语义至关重要的先验理性能力,预测方法是难以达到的。更重要的是,鉴于目前应用预测方法的“Transformer等模型用整数标注词汇,忽略了词汇在语义空间中的真实含义是多重或模糊的”,因而如果在技术层面上解决不了语义问题,那么就难以完备地构建杨立昆(Yann Lecun)所主张的世界模型。由此可见,正是预测方法或者说贝叶斯方法的局限性是造成DeepSeek在内的大语言模型难以理解语义的根本原因。
具体至DeepSeek在理解中文情感语义面临困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一问题,则需要结合中文情感的本质特征进行研究。前文已经证明中文情感的本质不同于英文情感,其本质是以“亲亲”为基础的共在情感。但DeepSeek目前所应用的“预测心智—情绪建构论”所使用的预测方法是基于英文情感的理解做出的,以个体为单位通过预测方法实现对情感的量化研究,因而会导致在理解中文情感语义时出现误读现象。因此,我们可以说,DeepSeek在理解中文情感语义上存在困难的根源在于“预测心智—情绪建构论”所使用的预测方法难以适用于对中文情感的研究。
四、一种新方案:“共在—预测AI”进路
基于“DeepSeek中文情感难题”成因主要集中在中文情感的理解与预测方法两个方面,要想提升DeepSeek对中文情感的预测能力,就需要找到能够解决这两大难题的路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两大难题本身似乎陷入了一种循环。因为如果要使Deep-Seek认识到中文情感的本质在于以“亲亲”为基础的共在情感,这本身似乎对DeepSeek提出了能够理解语义的要求,然而预测方法本身的局限性决定了DeepSeek无法理解语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这一困境是无法解决的。之所以会陷入两个难题的循环,是因为这种传统思路本质上将DeepSeek理解中文情感语义的能力类比于人的先验理性能力,而将DeepSeek所使用的“预测心智—情绪建构论”的预测方法类比于人的经验预测能力,以此类比,那么要想解决这一难题就只能通过研究如何协作先验论能力与经验论能力找到突破口。这种研究思路或许适用于英语的大语言模型场景,因为先验论与经验论是西方哲学传统下对人类思维能力的理解,但忽视了DeepSeek预测中文情感需要针对性地考虑中国哲学传统下对情感的认识。因此,我们需要从中文情感的共在特征入手思考解决这一难题的新进路。
关于中文情感的共在特征,首先需要回到中国哲学共在存在论的相关主张,以探寻DeepSeek如何能够以此为突破口同时化解在理解中文情感与预测方法上的困境。共在存在论的基本问题是“共在”(coexistence)而非“存在”(existence),也就是说,鉴于情感的这种共在特征,每个人所产生的情感都处在与他人情感的共在关系之中。换言之,这种与他人情感的共在关系是比个人情感更基础的存在,共在关系是确定个人情感的前提。从中国哲学对心物关系的思考,也能够看出,中文情感并非像英文情感那样以科学物论为基础理解情感,因此像“预测心智—情绪建构论”那样仅仅以科学的预测方法研究情感是不适宜研究中文情感的。当然这并非否定基于经验论的预测方法在实现语言预测上发挥重要作用,而是强调在“DeepSeek中文情感预测难题”方面,首先需要解决如何让AI理解中文情感的共在特征这一难题。具体而言,考虑到中国哲学对心物关系的理解,中文情感是以“心”为基点在人与人、人与物的共在关系中以“亲亲—仁民—爱物”的思考逻辑展开的。因此,从理论上而言,要想让AI理解中文情感的共在特征,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基于共在存在论,我们需要以“亲亲—仁民—爱物”中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去确定个体对他人与物的情感。
那么,要想让DeepSeek认识中文情感的共在关系,是否需要以不同于预测方法的推理方法实现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尽管DeepSeek应用的“预测心智—情绪建构论”的预测方法的局限性决定了语义识别的困难。但鉴于目前AI还属于图灵机的概念,因此尚且无法使其突破预测方法掌握推理方法才能够获取的通用数学、逻辑的先验理性能力,因此目前AI处理大数据的最优方法还是只能限于经验论的预测方法。况且,我们不能否认,目前DeepSeek应用的“预测心智—情绪建构论”用预测方法的确能够帮助AI基于过去的经验,以较高准确率实现对当前情境情感实例的预测。由此可见,真正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在预测方法的基础上,通过对中文情感共在特征的认识,帮助DeepSeek提升预测中文情感的能力,我们将这种研究思路称之为一种“共在—预测AI”进路。具体而言,鉴于DeepSeek基于预测方法无法从语义上直接理解中文情感的共在特征,因此,要想使得AI理解“共在”这一点具有技术可行性,我们需要放弃让AI理解语义这一思路,转换成借助中文情感具有共在特征这一洞见,使得AI利用预测方法实现对中文情感共在特征的理解。具体而言,鉴于中文情感的共在特征本身强调的人与人、人与物的共在关系,以此为启发,DeepSeek对这种共在情感的理解或许可以通过群体智能(swarm intelligence)的方式间接实现。有研究已经证明通过GPT-4o驱动的多智能体系统(multi-agent systems)以蚁群觅食与鸟群飞行为例,证实了大语言模型在驱动群体智能方面具有较大潜力。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研究表明,多个大语言模型智能体(multiple LLM agents),比单个智能体更智能。甚至有学者经由实证研究指出在涉及需要密集逻辑推理的任务时,与单个智能体相比,多智能体系统能够提高集体的推理能力。有证据表明,群体智能除了能够提升AI的推理能力,也能够显著提升基于脑电图的情绪识别的准确率。当然,群体智能并非简单的多模型集成或投票,而是需要将其内部机制的设计与“亲亲—仁民—爱物”的共在关系结构进行深度耦合,从而将哲学理念操作化。系统的目标函数需要从“个体最优”转向“关系最优”,即单个智能体的成功不仅在于其自身预测的准确性,更在于它对提升整个集体理解能力的贡献度,这模拟了“仁民”中个体价值在促进集体福祉中实现的思想。引入“亲疏”权重以模拟“亲亲”关系,系统根据对话内容动态识别核心关系人物,并临时性地增强代表这些角色的智能体之间的互动权重,从而更好地捕捉由亲密关系主导的情感。建立“协商—反思”机制模拟“爱物”思想以取代简单投票,不同智能体提出见解并交叉辩论,在多轮修正与反思后形成更具层次感的最终判断。通过这种方式,群体智能不再是单纯的技术路径,而是“共在”理念的具体机制化呈现。由此可见,通过以DeepSeek驱动多智能体系统或许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预测方法在推理能力上的局限性,还能够提升情绪识别的准确率。因此,如果我们尝试“共在—预测AI”进路,以群体智能的方式在多个AI智能体之间实现共在思维,在此基础上,DeepSeek或许能够以共在特征为基础理解中文情感,以此显著提升其对中文对话中情感的预测能力。
综上可见,“共在—预测AI”进路对解决“DeepSeek中文情感难题”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新方向,这一方案不再困在基于西方哲学传统的情感概念与研究思路之中,而是更有针对性地从中国哲学传统下的心物关系出发认识到中文情感的共在特征。在批判性分析预测方法的优势与局限性的基础上,看到了以共在情感为启发,依靠群体智能提升中文情感预测能力的可能性。这意味着未来以DeepSeek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在提升中文情感计算能力方面,会产生真正突破的方向或许不再是以西方哲学传统下的个人情感为启发的单个智能体研究思路,而是以中国哲学传统下的共在情感为启发的群体智能研究进路。如果“共在—预测AI”进路能够显著提升DeepSeek在中文对话中情感的能力,那么或许也能够为AI在预测英文对话中情感上所面临的瓶颈提供启发,进而提升AI的情商、智商,甚至审美能力。